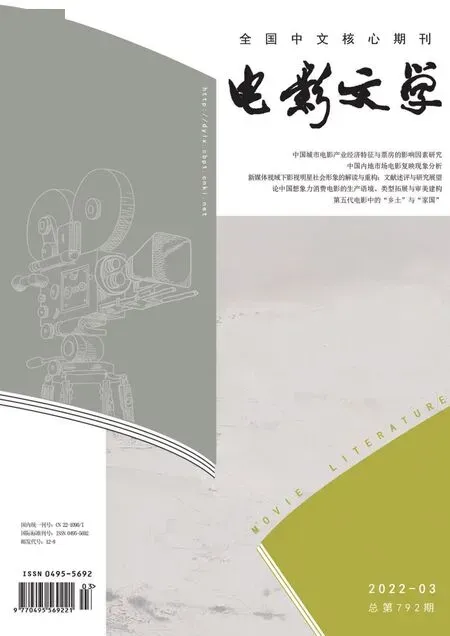時代使命與共和國情結:李前寬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的史詩性內涵研究
吳楊爽 張 梅
(重慶移通學院藝術傳媒學院,重慶 401520)
20世紀80年代,李前寬與肖桂云開啟了重大歷史題材電影的新時代創作之路,其創作風格一改過往保守的文獻記錄化的歷史再現創作模式,以獨特的風姿和飽滿的激情,大刀闊斧地進行了從理念到手法上的創新,與上一輩主旋律電影創作的集大成者湯曉丹、成蔭、謝鐵驪等老一代藝術家形成了繼承與革新之勢。
一、莊嚴的創作使命:歷史紀實與浪漫寫意的精妙遇合
李前寬秉承著“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創作原則,在呈現歷史真實的同時,輔之以浪漫主義的細節虛構,揭示歷史事件的本質與內涵,著重呈現歷史語境中那些撥弄風云、揮斥方遒的人之真實,尤其是重大歷史事件中革命領導人的風姿。導演用富有浪漫色彩的春秋筆法,賦予了歷史事件以獨特的詩性特征,將史實提升到了史詩的高度,并形成一種歷史的穿透力。
(一)敘事情節上的藝術性虛構
創作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影片首先要確保歷史事件的真實,因此在李前寬創作的《開國大典》(1989)之前,同類型影片在表現革命歷史事件時多傾向于使用更安全的文獻記錄式的敘事手法,如由湯曉丹導演的《南昌起義》(1981),便是在查證了海量歷史資料后,以文獻記錄和編年史的手法進行的影像敘事。這種模式在確保歷史真實的同時,可以有效地進行意識形態的宣導。但在藝術手法的使用和與觀眾的貼近性上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南昌起義》開創性地使用了特型演員飾演周恩來,打破了國家領導人不得由演員扮演的禁忌,但圍繞周恩來的具體敘事,則最大限度地參照了有證可循的歷史資料,少有虛構。雖然影片也虛構出了以兩組小人物為代表的階級矛盾,以凸顯情感訴求,但總有隔靴搔癢之意。同時期成蔭執導的《西安事變》(1981)也無法規避此問題,影片對于重大歷史事件的講述更接近于歷史事件的羅列和普及,創作主體的精神思考未有更豐富的傳達,這當然是時局所限,正如成蔭所說:“創作這么重大政治性的反映歷史事件的影片,創作者的神經是很脆弱的。”電影是虛構的藝術,由虛構而產生的特定時空中的戲劇沖突和意義傳達是電影藝術的魅力所在。法國著名電影理論家讓·米特里曾言:“藝術沒有‘真正’的現實,電影和其他藝術一樣也是如此。”因此,如何在遵循歷史真實的同時,進行大膽的藝術虛構,所體現的既是導演的藝術修養,更是導演的創作魄力,“銀幕將軍”的名號正是在此創作情境下對李前寬的高度褒揚。
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電影界迎來了一陣春風,“藝術創新”的口號成為時代最強音。李前寬作為被時代精神所激勵的第四代導演,文化和思想的雙重革新,令他的創作充滿了思想者的風骨。《開國大典》(1989)便是一部虛實結合氣吞山河的史詩性作品,影片高屋建瓴,大刀闊斧地對冗長的歷史事件進行篩選與藝術加工,將敘事重點集中在解放戰爭最后一年間的風云變幻,將敘事矛盾落幅于毛澤東、蔣介石這兩個歷史角色身上。羅伯特·麥基在其著作《故事:材質、結構、風格和銀幕劇作的原理》一書中對電影結構的論述是:“結構是對人物生活故事中一系列事件的選擇,這種選擇將事件組合成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序列,以激發特定而具體的情感,并表達一種特定而具體的人生觀。”李前寬在敘事結構上的定調和對具體歷史事件的排列選擇正顯現出了其對歷史精神的宏觀把控,創作主體的歷史觀與價值觀隨之悄然附著。
在最終的大決戰中,毛澤東和蔣介石實際并無正面交鋒,如何使不同時空中的兩位歷史人物發生戲劇性的交集,需要藝術層面的虛構與創造。例如,在開國大典前夜,導演虛構出了兩組隔空相呼應的“訓子”故事,用平行蒙太奇的剪輯手法呈現出了一幕別開生面的歷史碰撞。在北京,毛澤東告誡兒子毛岸英:“千古興亡只有一條規律,得民心、順民意者得天下;失民心、逆民意者失天下。”要毛岸英永遠銘記這一歷史鐵律。同一時間,在臺北的陽明山莊,蔣介石也在與兒子蔣經國深夜對話,蔣介石告誡兒子:“要知恥而后勇,毛澤東有時比我高明。國父說過,天下大事,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蔣介石敗北退居后,導演沒有刻板功利地表現蔣介石的失敗者形象,而是借以父子對話,跨越山河與毛澤東訓子形成觀點上的統一。這當然是影像敘事對歷史的虛構,卻在精神價值上毫不違和,毛澤東與蔣介石,作為時代風云的撥弄者,雖在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下,成為分隔在海峽兩岸的勝利者和失敗者,但對國家興亡的思考與認知卻是一致的。影片通過極具藝術性的情節虛構,將二人的思考復沓呈現于銀幕之上,形成了一種極具張力的藝術概括力。
同樣,在《重慶談判》(1993)中,導演沒有固守成規地采用政治功利主義的手法一味偏頗或純粹歌頌,再一次將視角聚焦于重要歷史轉折時刻具有決定導向力的毛、蔣二人身上,二人從思想到行動上的對決與交鋒成為影片最為華彩之處。如何在正面交鋒的重慶談判中,體現出歷史必然與歷史機遇之間的因緣際會,需要創作主體賦予作品統領全局的謀篇智慧。影片在遵照歷史既定現實,把握歷史精神內涵的同時,大膽創新,重構歷史,將史實性的政治交鋒賦予了史詩性的藝術美感。例如,影片展現毛澤東一行從延安到重慶機場的這場戲中,虛構了一場接受記者采訪的情節,毛澤東被女記者童欣犀利提問:“毛先生來重慶,不怕是鴻門宴嗎?”面對刁難,毛澤東反應迅速,談笑間不僅化解了尷尬,還將皮球踢向了蔣介石:“你年紀輕輕很厲害呀,你這樣發問是貶低了蔣先生一番美意,面對四萬萬民眾,他會擺鴻門宴嗎?我第一個不信。”這種暗藏珠璣的臺詞風格,在影片中比比皆是,不僅渲染出了重慶談判期間緊張敏感的政治氛圍,同時也賦予了歷史人物鮮活的精神氣質。
(二)形于勢,表于情:影像呈現中的革新之舉
1989年,長春電影制片廠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周年,決定開拍《開國大典》,該片從創作題材、歷史事件到所表現的138位歷史人物,其規模和勇氣都是空前的。如何在影片中復現開國大典的宏大歷史場面,再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天安門盛況,這是一項巨大的創作挑戰。但導演氣勢恢宏,破舊立新,開創了在影片中加入歷史資料片的革新之舉。歷史資料片非常真實地保存了歷史景象,但囿于當時的技術設施和年代久遠,許多資料片的畫質都無法滿足20世紀80年代的影像表達。李前寬沒有固守影像表現上的機械式藝術追求,而是嘗試將歷史紀實畫面與影像虛構的詩情畫面進行融合銜接,使影片的鏡頭語言形于勢又含于情,生成了具有開創與革新之勢的新鏡頭語言。在具體引用歷史資料片時,導演是謹慎的,因為正如巴贊所言:“所有的藝術都必須解決現實與藝術的關系,刻板地再現真實,不是藝術。”如何在真實記錄與藝術表達間彰顯出均衡之美,需要導演李前寬始終立于時代高度,通盤把握全局,正如他總結所言:“在浩瀚的資料片中篩選出所需畫面,從整體結構和節奏上有章法地進行布局和銜接,通盤考慮鏡頭的景別、機位和長度,通過影片色彩的漸變,將每個鏡頭連接得嚴絲合縫,有節奏地凸顯出情節的震撼性、真實性和文獻性。”
《開國大典》全片共1082 個鏡頭,其來源有三類,分別是歷史資料片;新拍攝后做舊的特效鏡頭;實拍彩色畫面。全片涉及的歷史紀實與實拍虛構的融合畫面有40多處,為了使兩種截然不同風格的畫面和諧地融為一體,導演刻意將新拍攝的彩色畫面用特效做成懷舊的黑白,并以假亂真地與歷史資料片剪輯在一起,形成了真中有假,假里混真,虛實相結合的全新影像表達,由此也生成出一種真實性與假定性、紀實性與表現性相結合的紀實美學風格,賦予了影片獨特的歷史厚重感與真實質感。
這種虛實相生的創作手法一直延續到了之后的《決戰之后》《重慶談判》等影片中,例如《重慶談判》中表現美國投放原子彈,日本無條件簽訂投降條約以及抗日戰爭勝利的宏大歷史場面時都采用了歷史影像資料予以輔助。這種手法繼李前寬的開創性使用后,逐漸成為此類題材創作的常用手法之一,并沿用至今。
二、春秋筆法:歷史語境下立體化呈現人物風姿
(一)微言大義:歷史人物的細節描摹
李前寬在創作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時,除善于在恢宏的歷史大場面中再現時代大氣象外,亦非常注重對歷史人物的塑造與建構,常在細微處輔之以細膩的春秋筆法,挖掘歷史人物的多個棱角,塑造出既叱咤風云又鮮活真實的歷史人物形象,這充分體現出了導演的勇氣與智慧。例如,在氣勢恢宏的《開國大典》中,導演在表現毛澤東、周恩來這些革命領袖人物時,并未如十七年電影那般一味高大全,神化領袖人物和英雄人物,而是在尊重歷史精神的同時,充分發揮藝術構造力,細膩呈現出領袖人物走下神壇后的煙火之氣。片中曾引發審查矛盾的警衛員給毛澤東梳頭的戲,實際是導演在充分考證后的藝術創作,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的時代氛圍下,這份艱難與擔當卻并非如此簡單。面對審查的不同聲音,李前寬據理力爭,這種超脫功利主義私欲,超脫時代局限,為作品的藝術性價值,像文化斗士一般去創作的勇氣,最終賦予了作品以革新的時代精神,擁有了持久的藝術生命力。
類似的戲劇性塑造在影片中均以一種輕松自然的方式娓娓呈現,不虛張、不奪目,卻意味雋永。例如,毛澤東看材料看得入神,抓起茶葉放在嘴里咀嚼的畫面;毛澤東新得一包好煙,還未焐熱便被周恩來從背后拿走,二人一路玩笑走著去開中央會議的戲劇性設計。領袖人物不再是居于廟堂之高的神話人物,而是擁有煙火之氣的真實的人。導演大膽構思,敢于表達,一字含褒貶,閑筆之間便呈現出了歷史人物的鮮活氣息,春秋筆法,意味雋永,充溢著罕見的戲劇張力。
(二)身正膽直:歷史人物的多面開掘
李前寬在塑造蔣介石時,也沒有一味貶損,而是注重歷史真實與人物個性的“形神畢肖”,在遵照歷史精神的同時,將創作主體的歷史認知融匯于影片的藝術表達之中,給予了蔣介石以公正而不失本色的真實刻畫。例如在影片《開國大典》中,對蔣介石的刻畫并未停留在失敗者的形象上,而是將筆觸放置在歷史機遇、人物性格命運,以及與毛澤東的對比表達上凸顯蔣介石的歷史形象。臺灣著名導演李行在看過《開國大典》后,評價稱:“沒想到大陸電影這么表現蔣介石;沒想到在這部片子里知道這么多的歷史知識;沒想到大陸導演水平這么高,氣魄這么大!”
值得一提的是,在影片《重慶談判》中,導演對蔣介石的藝術性虛構與描摹更是深入精髓。史料記載,重慶談判一共持續了43天,在這次談判中,毛與蔣除正式會晤之余也有多次非正式交流,但私下交談的內容并無秘錄記載,這便為李前寬的藝術虛構留下了豐富的資源與廣闊的空間。例如,影片中毛、蔣二人在林圓的偶遇,關于這次偶遇史料記錄確有其事,但因是偶遇,二人具體的交談內容便無所依憑,導演充分發揮藝術想象力,在歷史的縫隙中馳騁想象,精雕細琢。薄霧籠罩,竹林深處,毛澤東散步偶遇在挖筍的蔣介石,二人像多年老友般從桑麻之樂、世外桃源、青梅煮酒一路談天說地,談笑間,二人翻開各自手上的書,竟是同一卷《資治通鑒》,不禁莞爾。毛、蔣二人雖政見不同,但從共同北伐到五次反“圍剿”,再到聯合抗日,二人雖交鋒多年卻并無私怨,相反,在歷史的因緣際會下,林園偶遇的片刻閑聊,二人亦可暢聊天地,講史論經,雖你來我往,各不相讓,卻也別有一番歷史諧趣。春秋筆法,不可謂不精妙,閑筆之間盡是雋永意味。
除對蔣介石的細致描摹與公正表現外,在影片《決戰之后》中,李前寬以群像描摹的藝術手法,聚焦“功德林”中以杜聿明為首的一群國民黨戰犯。深度開掘人性的多元復雜,立于時代高度,在封閉的戰犯改造空間中,以充滿史詩性的藝術虛構手法生動呈現了“沙盤對決”“圍堵屠豬”等戲劇性情節,刻畫出了一代抗日名將杜聿明面對無法規避的政治對抗,最終淪為階下囚的命運悲劇,為觀眾呈現出了一場細致且客觀的國民黨軍官的群像故事,而群像中每一位具體歷史人物又各不相同,尤其是杜聿明在經過改造后,感慨而出的那句:“敗在敵人手里可以挽回,敗在人民手里就不能挽回了。”影片的主題借此君之口甚為分明。觀眾通過影像對國民黨軍官的抗日事跡深感可敬,同時又對其命運感到可悲可嘆。正如英國作家萊辛所言:“悲劇的目的遠比歷史的目的更具有哲理性。”
三、堅守與展望:歷史更迭中的創作初心
主旋律電影作為中國電影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意義承載上從來都不囿于單純的藝術表達或商業訴求,自20世紀中期的十七年電影創作伊始便涌現出大量在風格、題材、主題表達上各不相同的時代性創作。作為意識形態表達至關重要的傳播媒介,每個時代在具體創作內容、表現手法甚至表述權限上都各有側重。在既定的政治體制內,如何使主旋律影片在意識形態宣導、藝術創作、觀眾訴求上最大限度地實現融合與促進,應是每一時期的電影藝術家們孜孜以求,努力實踐,勇于探索的前行之所在,只有當藝術家們放下小我之功利主義,以歷史為坐標,尊重藝術規律,始終將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作為首要創作綱領,才能有效規避時代短視與政治功利主義造成的公式化、臉譜化的創作僵局。正如李前寬所言:“政治性愈強的影片愈要講究藝術性。”
作為被時代精神所激勵的電影創作者,李前寬在文化與思想的雙重革新下創作了許多精彩又影響深遠的優秀作品,與前人創作的經典主旋律作品,諸如《南征北戰》《南昌起義》《西安事變》《今夜星光燦爛》等形成了革新之勢,同時又伴隨著時代更迭,順應時代所趨,開創了新格局。然而,所謂大氣魄,歸根結底也不過是導演始終站在時代的高度,規避狹隘的功利主義,用獨到的自我認知,對龐雜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予以深度思考,致力于挖掘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表象背后的精神內核之創作初衷。
如今,伴隨著時代精神的再次呼喚,主旋律電影創作規格全面升級,新主流大片數以群計地涌入大眾視野,明星、類型、技術、市場等多重元素的全面融合,匯成一股強悍的商業沖擊力,暴擊觀眾的視覺神經。2021年國慶檔熱映的講述抗美援朝戰爭歷史的《長津湖》,集齊了陳凱歌、林超賢、徐克三位業界知名導演,以185分鐘的超常規時長創下國產電影單片時長新紀錄,為觀眾呈現了一部愛國戰爭歷史大片的基本演繹,完成了一次主旋律電影的票房破圈之旅。但細究影片的精神內核,似乎在一股咆哮的愛國吶喊之后并未留下太多回味,戰爭場面的花樣視覺表現力吸引了觀眾,卻也許未能準確擊中觀眾內心,尚未達到史詩性的表述厚度。在此語境下,重讀李前寬導演對宏大歷史題材的史詩性創作內核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