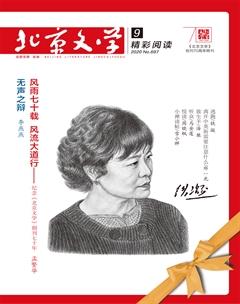遇見北海
楊鷗
銀杏樹金燦燦的樹葉綴滿枝頭,枝葉披掛下來像皇帝的龍袍,北海公園的銀杏樹也有皇家氣派。
這座皇家園林,留著皇家的印記,皇家的人已經煙消云散,來來往往的游人神情悠然,舉著手機四處拍照。
那座白塔,塔身潔白,聳立在綠樹叢之上,塔身輪廓呈優美的弧線,漸次向上收束,像天籟向天空裊裊上升。在綠樹的烘托下,白塔是捧向上天的一份圣潔的祝福。
北海公園是個色彩豐富的地方,白塔、綠樹、紅墻、金黃的琉璃瓦,公園東南角有幾棵金黃的銀杏樹。快雪堂平時不太被游人注意,里面有乾隆皇帝收藏的48方書法石刻。快雪堂的建筑是棕褐色木質的,有一種返璞歸真的味道。院中通靈剔透的太湖石是青灰色的,堆砌成曲徑通幽的夾道。
有一天,我注意到白塔并不是通體白色,白塔的正面有紅黃相間的盾形圖案,中間還有字。后來查了一下,方知那盾形門叫眼光門,紅底黃字是藏文圖案,是“吉祥如意”的意思。
每次去北海公園,總會有新的發現。北海公園是個常去常新的地方。比如北海北岸的闡福寺,也是我新發現的。紅墻碧瓦的建筑,寺內有大佛殿的遺址,殿內原來有千手千眼佛,佛身用整株金絲楠木雕刻,鑲嵌無數珍寶,手持幾十米長的大白傘蓋。1900年大佛殿被八國聯軍焚毀。八國聯軍專揀最貴重的東西焚毀。金絲楠木的千手千眼佛像上的珠寶全部被他們挖走,佛像他們帶不走,就給焚毀了。可以見出這些侵略者的貪婪和險惡。
乾隆皇帝每年來闡福寺拈香拜佛,舉行“書福”盛典,為圣母祈壽,為百姓祈福。
祈福是北海公園的主題,順治帝建北海白塔和康熙帝重建白塔,均有為民祈福之意。白塔敦厚的塔身就有福相。乾隆皇帝建闡福寺,“上為慈圣祝釐,下為海宇蒼生祈佑”。帝王心中的福是什么呢?在濠濮間,我看到水榭上的對聯:“山參常靜云參動,躍有潛魚飛有鳶。”濠濮間山石參差重疊,環繞著水面,沉靜古雅。“濠濮”出自《莊子·秋水》的兩個故事:莊子與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爭辯魚樂與否的典故;還有莊子在濮水邊釣魚,拒絕楚王來請他做官的典故。“濠濮間”出自《世說新語》:“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帝王政務纏身,也會有對大自然的向往,對出世的羨慕。
極樂世界是人們想象中的西天,眾仙人有的彈琴吹簫,有的站在蓮花座上,手做佛教手印,這些仙人臉部豐腴潤澤,慈眉善目。玉皇大帝端坐在仙山的最高處。這是人們向往的仙境,是沒有煩惱的極樂世界,這是帝王向往的“福”嗎?
西天梵境殿里供奉著三世佛和十八羅漢塑像,也是皇帝拜佛的地方。
北海公園不僅包含了皇家人對物質的寄托,也包含了對精神的寄托。在這個小空間里,可以飽覽人間美景,也可以上天入地,求仙問道。
皇家的園林萃取了園林的精華,小空間包容了大千世界,包含了人間和自然美的精華。從精神到物質的精華都在園林里具備了。皇家人的活動范圍其實小得可憐,在這個范圍內盡可能地做到盡善盡美。他們不像現代人可以到處行走。他們的向往、他們的追求都寄托在這園林里了。北海公園濃縮著皇家的背影。
對北海公園既熟悉又陌生。多年來,北海公園在我心目中是個清雅美麗的所在。它的標志性的白塔是那么潔白脫俗,白塔四周是茂密的綠樹簇擁著它,如眾星捧月,塔身的倒影在湖水中蕩漾。在京城那么多富麗堂皇的皇家園林中,白塔使北海顯出獨特。
從北門進入北海公園,沿著湖的北邊走,靜心齋、九龍壁、極樂世界、五龍亭……北海的景點密度很大。80多歲的爸爸一時興起,帶我們去靜心齋照相。靜心齋里九曲回廊、亭臺軒榭、綠水清波、亭亭修竹和太湖石堆成的假山,排列得錯落有致,空間不大但步步有景,設計者想把所有的園林美景都安放在這小小的空間里。爸爸取景很用心別致,給我們照了很多照片,我們好像又回到了小時候在父母身邊的快樂時光。小時候父母帶我們去得最多的公園,除了家附近的紫竹院公園,就是北海公園了。那時說起北京,首先會想到北海公園。還有那首《讓我們蕩起雙槳》的歌:“水面輝映著美麗的白塔,四周環繞著綠樹紅墻。”北海和它的白塔在我心目中幾乎就代表了北京。有一次爸爸帶我們在北海公園劃船,遇上了刮風,船逆著風,怎么也劃不回岸邊了。后來等風小了一些才劃回去。北海公園的山里有一個仙人承露盤的銅像,那時覺得很神秘。
工作后不久有一次和朋友在北海公園看花燈展,夜晚的人流熙熙攘攘,有“東風夜放花千樹”的感覺。有兩個年輕人邀請我們去舞會跳舞,我們對這樣一個奇遇感到很興奮,年輕的心總是向往奇遇。
過去每逢家里有客人來,我們一家人就陪客人去北海公園游覽。一個表舅從國外回來,帶了一個相機,給我們在北海公園照了很多相。那時照相是件稀罕事,因為買不起相機。如今拿著手機可以隨處照相。
與白塔的合影從少年時代一直到今天,照片上白塔依舊,人在一年一年地變化著。我們走在北海公園的瓊島上,一路向前,發現又回到了原地,原來是走了一個圈。人的一生是一條不歸路。“出走半生,歸來仍是少年”,有人在朋友圈里發了這樣的一句話。歸來仍是少年,有這樣豪情的人經得起時間的打磨。
北海承載著少年的快樂記憶、青春的浪漫記憶。如今來到北海,公園的亭子里有人在唱戲,有人在空地上跳舞,多是老年人,現在的大部分公園成為老年人的娛樂場所。北海公園是親民的皇家園林。什么是福?一家人在一起其樂融融也是一種福,青春的浪漫也是一種福。老百姓有他們的理解,帝王有帝王的理解。
曾有記者舉著話筒問路人:“你幸福嗎?”你幸福嗎?這個問題既簡單又復雜。《詩經·樛木》說:“樂只君子,福履成之。”對他人善良友好,心懷美好,內心便是快樂的。曹操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養好自己的身體便是一種福氣,便可以延年益壽,這是帝王眼中的福。范成大詩:“男解牽牛女能織,不須徼福渡河星。”指男人能夠牽牛女人能夠紡織,不需要像牛郎織女渡過星河來迎接生活的福氣,這是老百姓眼中的福。憂國憂民的杜甫,也有“漫卷詩書喜欲狂”的幸福時刻。文人談到幸福,念天地之悠悠,想到天地人生更宏大的命題,他們對幸福也許有更深刻的理解。今天我們不愁吃穿,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很豐富,可是我們比過去物質匱乏的時代幸福嗎?幸福有時其實很簡單,一點小小的成就感,和親人的一次團聚,和朋友的一次會面,品嘗美食,欣賞美景,都會給我們帶來幸福感。幸福其實就在我們身邊,看我們能不能發現和體會,幸福在于我們的心境。幸福也需要創造。
多年前的一個中秋夜,我們在北海公園的一座樓閣上賞月,皎皎的月輪懸在空中,像一張慈和的臉龐,月光純凈如洗,照耀著湖光塔影,照耀著人間眾生。天地一片蒼茫。
責任編輯 侯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