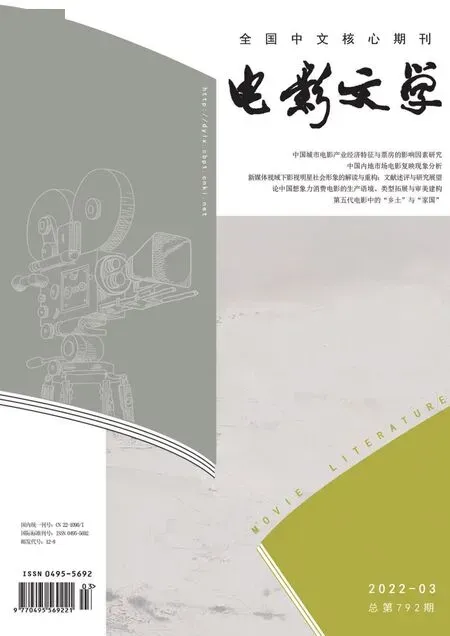《矮婆》:鄉愁美學與社會議題的紀實表達
崔福凱
(山東藝術學院傳媒學院,山東 濟南 250300)
紀錄電影《矮婆》是“網盤導演”蔣能杰執導的第一部劇情長片,也是他的首部院線電影,更是一部鮮有的關注留守兒童與空巢老人的社會公益題材電影,主要講述了留守兒童蔣云杰(外號矮婆)與奶奶以及妹妹在鄉下相依為命的故事。該片改編自導演蔣能杰的童年往事以及他過去紀錄片中的真人真事,以紀實化的美學風格還原了真實的、“去李子柒式”的鄉村圖景,喚醒了當下處在城鎮化進程中的人們的鄉土記憶。在此之前,蔣能杰已經執導了抗戰老兵、留守兒童、塵肺病等多部社會公益題材紀錄片,這次他依舊將鏡頭聚焦當下鄉村在城鎮化進程中所面臨的種種困境,其中夾雜了留守兒童、空巢老人、隔代教育、鄉村教育等諸多社會議題,引發了觀眾的熱議與思考。
電影在上映之前,就因入圍上海國際電影節與華沙國際電影節兩大國際A類電影節而聲名鵲起,上映后更是好評不斷,豆瓣評分高達7.7分,然而奈何排片量太低(<0.1%),甚至很多城市零排片,上映20天總票房勉強突破20萬元。面對這種“高口碑低票房”的落敗,蔣能杰導演也只得無奈地表示:“我也知道文藝片、紀錄片排片不會多理想,我們也只能盡人事,聽天命。”而這也不僅是電影《矮婆》的悲哀與無奈,更是映射出了當下文藝片普遍面臨的困境與尷尬。
一、鄉愁美學:喚醒城市寄居者的鄉土記憶
“當下,隨著國家城鎮化加快推進,傳統村落及浸潤于其中的傳統文化正在迅速消失,人們不由感嘆‘鄉愁’何以安放。”盡管大城市給人們帶來了優渥的物質生活,但是城市生活的緊張感、社交的互利性以及“被動生活”的疼痛使人們又墜入了“無夢、無痛、無趣”的空虛感,于是“鄉村就有可能成為一個寄托人們審美理想的烏托邦”。而電影《矮婆》之所以成功,正是因為抓住了城市寄居者普遍存在的“鄉愁”心理,喚醒了他們內心最美好、最真實的鄉土記憶,以及濃濃的對故鄉家園的思念之情,這種情感共鳴最終驅使他們產生了強烈的文化與身份認同。
電影《矮婆》很好地打破了以往通過濾鏡、美顏、搭景、擺拍等人為手段拍攝的鄉村短視頻里的那種“李子柒式”“桃花源般”的田園夢境,將觀眾的視線再次拉回到了真實的鄉村圖景,并試圖消弭都市的喧囂、工作的壓力以及人情的淡漠給人帶來的痛苦。狹小封閉的小山村、漏雨的屋頂、顛簸崎嶇的泥濘小路,以及為了生活操勞的年邁奶奶與年幼孩子,這些都描摹出了一幅真實的甚至略顯乏味的鄉村圖景。觀眾在驚醒之余,除了感受生活的殘酷之外,更能夠體會導演在影片中所極力展現出的鄉村內在之美。在這其中,最為凸顯的自然是獨屬于鄉村的那份淳樸真摯的情感以及堅韌頑強的生命力。
鄉村雖然凋敝,但卻比城市更有人情味。堂哥一家對矮婆父親臨走前托付的欣然應允、年邁的舅爺爺幫助矮婆家修補屋頂、農忙時族人幫助矮婆家收稻谷,以及矮婆的奶奶病倒后族人的噓寒問暖,導演通過這些平凡的小事書寫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鄰里溫情。然而,這種鄰里溫情顯然是不屬于城市的,當下城市正日漸成為陌生化的社會。影片中當全家人為了矮婆和妹妹能在城里上學,準備求助當教導主任的同鄉時,好友國華說道:“你得先準備個紅包,現在這社會沒有紅包行不通。”這句話恰恰體現出了大城市里以人情換利益的畸形人情關系。這種畸形的人情與農村那種鄰里相望、互幫互助的人情關系不同,前者是淡漠的,而后者則是愉悅的。影片正是通過鄉村里的那些濃濃的人情味來溫暖著人心,在一定程度上縫合了城市寄居者空虛寂寞的內心世界,喚醒了早已封存于內心的那些以誠待人的人間真情。
此外,導演通過春夏秋冬的輪回交替,暗喻了主人公矮婆的心路成長歷程,借此贊美了那些在困境中堅韌而又不屈的鄉村生命力。夏天,父母的遠去,迫使矮婆不得不從“襁褓”中走出來獨當一面,既要面對繁重的功課,又要面對瑣碎的家務,日子雖然很苦,但是卻構成了她少有笑容的日常;秋天,身邊的小伙伴都紛紛輟學,前往大城市打工,為此矮婆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同時朋友們的離去又使她不免有些失落;冬天,奶奶的猝然離世,使矮婆臉上少有的笑容也不復存在,悲痛的她只能帶著妹妹來到異鄉尋找父親和繼母;又一年春天,繼母帶著三個孩子再次回到小山村,矮婆也在一陣睡夢的呢喃聲“奶奶,奶奶”中“長大成人”,并在驚喜地發現原本凍僵的花兒又冒出新芽后,重新露出了燦爛笑容。生活的陣陣刺痛與看似平淡卻歡樂無比的生活相互交織,矮婆也在此間成長蛻變。這無不令觀眾在贊嘆那些困境中頑強的生命力的同時,也自然而然地聯想到他們的童年生活以及喚醒他們的鄉土記憶,或許此刻的他們也正如同影片最后那盆原本死去的花兒,在春日暖陽的照耀下重新煥發生機與活力,給人無限的暖意。
二、社會議題:聚焦城鎮化進程中的鄉村現狀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城鎮化的加快推進,大批的農村青壯年走向外出務工的道路,農村出現了大量的留守兒童與空巢老人,他們的生活現狀和內心世界急需社會關注。而電影《矮婆》正是一部關注留守兒童與空巢老人的社會公益電影。在此之前,導演蔣能杰拍攝留守兒童題材的紀錄片已有十年時間,從2010年的紀錄片《路》,到2014年的紀錄片《村小的孩子》,再到2016年的紀錄片《加一》,他一次次將鏡頭聚焦留守兒童的生活和學習狀況,試圖喚醒人們對留守兒童、鄉村教育的關注。當然,這次的劇情片《矮婆》自然也不例外。
周星老師認為,當下電影創作“相較于以往階級立場或政治角度反映現實的傳統現實主義,更為偏向對生命本體價值的探索和對人生意義的褒揚”。作為“留守兒童三部曲”的延續,電影《矮婆》這部“半自傳”性質的劇情長片,在通過影像來真實記錄留守兒童生活現狀的同時,也贊美了他們的某種精神特質。與城市的孩子不同,鏡頭里留守兒童的日常歡樂并不是各式各樣的玩具,也不是豐富多彩的特長班,而是像玻璃球、跳皮筋、捉迷藏等并不時興的娛樂活動,而這些卻構成了他們整個童年的快樂時光。除此之外,在更多的時間里,他們還要面臨緊張的學習壓力,以及承擔起繁重的家務活動。影片中矮婆作為家里最為年長的孩子,自然要承擔起家庭勞作的重擔,邊看書邊燒火做飯、在大雨瓢潑的夜里到處找盆子接漏下的雨水、去山里拾完柴火后還要獨自扛回家……可見矮婆小小年紀就已經過早地進入“當家人”的角色。盡管繁重的家務使得矮婆的成績有所下滑,但是乖巧懂事的她,卻在奶奶訓斥她時,并沒有向奶奶吐露“因勞作而影響考試”的實情。這種性格上的剛毅、隱忍,不禁讓我們為她所折服。而在影片中像矮婆這樣心思細膩、性格堅忍的留守兒童并不在少數。蔣云霞為了一百元的跳舞費而憂愁萬分,當奶奶告訴她家里沒有錢時,她并沒有選擇哭鬧,而是拎著書包走回房間;當矮婆和蔣恒被小伙伴們嘲諷為夫妻時,矮婆陷入了深深的苦惱中,善良的蔣恒為了證明矮婆的“清白”,只得悄悄躲開;矮婆、佳依、蔣恒三人因貪玩而把牛弄丟,或許是怕受到大人的責罵,躲在山里而不敢回家。從他們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留守兒童或多或少都帶著堅忍與敏感的精神特質:一方面,他們乖巧懂事、善解人意,不辭辛勞地操持著家務;另一方面,他們內向敏感,生怕自己做錯事給家庭帶來深重的災難。
同臺灣鄉土電影大師侯孝賢一樣,蔣能杰也“并不回避鄉土文化自身的缺陷,并不一味美化鄉土文化,而是冷靜地解釋鄉土文化愚昧、落后的一面”。電影《矮婆》除了真實地記錄留守兒童生活、展現他們內在精神特質之外,還夾雜著導演對隔代教育、鄉村教育等社會議題的關注與思考,傳遞著充滿力量的人文關懷。正如蔣能杰所描述的那樣,“在改善現狀之前,很關鍵的一步是拋開標簽,透過鏡頭重新認識他們是誰。我們與他們同時共代,理解他們,也有助于我們理解社會的撕裂程度與背后的結構問題”。
在留守兒童萬耀伍的溺水死亡事件中,盡管導演采用遠景、虛化的方式進行處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死亡的殘酷性,但我們還是會不禁發問:“僅僅依靠祖輩對孫輩的‘隔代教育’,真的能夠保障留守兒童的安全嗎?”就在萬耀伍溺死不久后,蔣恒和蔣鑫依舊在河里嬉鬧,他們的爺爺在得知后也只是對他們棍棒相向,嘴里抱怨著“你不知道這里淹死過小孩嗎”“我帶你有好大的責任”,卻從未想過要進行必要的安全教育。村中留守兒童聰聰沒能考上高中,在通過手機接觸到外面各種時髦文化后,一心渴望大城市的“自由生活”。當矮婆向他請教功課時,他冷嘲熱諷道:“你讀什么鬼書,以后又是個打工的相。”而他的爺爺則訓斥道:“沒力氣、沒本事、沒技術,打工,打你個頭。”然而最終,聰聰還是帶著年紀比他還要小的蔣鑫也踏上了他們父輩的“打工之路”。對于這些“三無”(沒力氣、沒本事、沒技術)的“留守一代”來說,他們也許會陷入同父輩一樣艱難謀生的困境。而究其根源,正是由于父母情感教育的缺失、祖輩對孫輩的疏于監督,導致許多留守兒童性格變得孤僻自卑,安全事故、打架滋事、輟學打工頻頻發生,而這些也許是難以規避的社會隱痛。此外,我們也透過影片看到了鄉村教育資源相對匱乏的現實。村里學校的老師多為代課老師,新舊代課老師的不斷更迭似乎也已是常態,蔣云霞在更換老師后的哭鬧、矮婆奶奶的牢騷話“村里留不住老師”、矮婆那滿臉習以為常的木訥傾聽,導演在以這種管中窺豹的方式記錄著鄉村教育現狀的同時,也傳遞著村里孩子們的心聲,寄予著他對留守兒童、鄉村教育的現狀得以改善的殷切期望。
三、意蘊涌現:紀實與詩意的融合
從首部紀錄片《路》到如今的紀錄電影《矮婆》,蔣能杰始終扎根于鄉土文化,以冷峻的眼光來關注真實的鄉村風貌,拍出了很多高品質的鄉土電影。但是這類影片也由于缺少升騰跌宕的情節、炫人眼球的特效等而缺乏社會的關注,可以說在商業化泛濫的當下,他的電影仍屬邊緣化、小眾化。然而,即便是在自己電影鮮有人問津、財務狀況負債累累的艱難處境之下,蔣能杰也從未想過要在電影中加入過多的商業元素,而是堅持以極致的紀實美學來還原真實的鄉村圖景,記錄社會的真實存在以及邊緣小人物生活的諸多困境,給予著他們飽含善意的溫暖關懷。而這種極致的紀實美學主要體現在實景拍攝、非職業演員的即興表演以及固定長鏡頭和空鏡頭的運用三個方面。
其一,電影《矮婆》完全采用實景拍攝,原汁原味地還原了真實的鄉村圖景,以情感來驅動觀影者對于遠方故鄉的牽掛之情。正如電影《矮婆》所體現的核心主題“對于故鄉家園的懷念”那樣,蔣能杰同樣也極具故鄉情結。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以他的家鄉湖南邵陽新寧渡水鎮光安村為取景地,而這其中的原因莫過于這是他最為熟悉,也是他長大成人的地方。縱觀蔣能杰的成長經歷,我們不難發現他從小家境貧寒,父母都是農民,然而與村里其他家長“散養”的教育方式不同,父親對他的學習格外嚴厲,這才使得蔣能杰沒有像村里其他的孩子一樣過早地走上輟學打工的道路。正是這段貧苦的成長經歷,大學畢業后本該留在大城市發展的蔣能杰毫不猶豫地回到了生養他的小山村,來拍攝家鄉的人和事,這既是借助影像來保留住時代浪潮中的家鄉記憶,也是希望家鄉的現狀能夠得到社會的普遍關注。因此從情感機制上來看,導演蔣能杰對于自己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的實景化的書寫,也使得觀眾與自己家鄉展開了一次心靈對話。
其二,電影《矮婆》還將演員還于原型,絕大部分扮演者都是蔣能杰的族人,這些人的本色出演顯現出了一種逼真呈現生活的紀實性。影片除改編自導演的童年往事之外,還改編自他以往紀錄片中的真人真事。例如影片中女主角蔣云潔的扮演者,現實生活中也叫蔣云潔,此前她就已經以蔣云潔的身份出演了《村小的孩子》。而《矮婆》里蔣云潔的故事,其實就是她現實生活中的翻版和再現。與現實稍有不同的兩點是,現實中她的媽媽是親生母親,而在電影中為了更好地凸顯蔣云潔性格的堅忍,故將其親生母親改編成了繼母;現實生活中云潔的奶奶是不鼓勵她讀書的,而在電影中她的奶奶面對成績不佳的云潔則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奶奶形象的細微改變其實也是導演心存善意的體現。除此之外,影片中外出打工的代課老師在現實中也是代課老師,蔣云潔的同學也是現實中她的同學,像蔣鑫、蔣恒等也曾在《村小的孩子》中出現。而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后來的結局也與電影《矮婆》出奇地相似,代課老師真的外出打工去了,那些向往“自由”的學生也真的走上了輟學打工之路。可以說,正是影片中人物的這種原生態的即興表演,才會讓觀眾有種看紀錄片似的感覺,這種情感狀態的到位無疑使得觀眾與劇中角色之間實現了最有力量的共情。
其三,電影《矮婆》在鏡頭運用上大量采用固定長鏡頭和空鏡頭,同時在剪輯與音樂上又分別由侯孝賢御用剪輯師廖慶松、賈樟柯御用音樂師林強操刀,使得影片呈現出了極強的散文化詩意風格。同所有的紀錄電影導演一樣,蔣能杰對于固定長鏡頭也是極為偏愛的。對于這種故事性較弱、節奏緩慢的影片來說,固定長鏡頭無疑也是最佳的選擇。與那些流于形式的運動鏡頭相比,它更為出色地發揮電影最本質的功能——記錄功能,真實再現了鄉村的日常生活。例如影片中三位老奶奶圍繞蔣云霞的成績討論的固定畫面就長達1分多鐘,兩位不識字的老奶奶想要知道成績的急切、大奶奶對蔣云霞的夸贊“考得好,考了第一名”,以及進門后一臉落寞的蔣云霞全都呈現在了觀眾面前,再加上一口難以聽清的方言,顯得極為生活化。當然,影片除了專注寫實之外,也充分發揮了空鏡頭的寫意功能,使畫面具有了意蘊悠長的詩意美感。電影開篇,導演就通過三組空鏡頭來展現村落的地理風貌。前兩組空鏡頭呈現的是一個坐落于大山深處、云霧繚繞、山清水秀、灰磚白墻的典型的江南村落,配上清脆的鐘聲,猶如李白詩中的桃花源,令人心曠神怡;最后一組空鏡頭則是對村頭大樹的凝視,原本清脆的鐘聲此刻變得些許低沉,營造出了“空樹臨風襟袖寒”的蒼涼意境,而這背后是對人生的哲思、對人性的追問。
從藝術性與思想性來看,電影《矮婆》無疑是極為成功的。一方面,電影很好地抓住了當下那些漂泊于城市卻又無力扎根于城市的人們的鄉愁心理,在呈現“去李子柒式”的鄉村圖景,還原樸實動人的生活場面的同時,也喚醒了城市寄居者最真實、最深沉的鄉土記憶;另一方面,電影以點帶面,探討了留守兒童、空巢老人、隔代教育、鄉村教育等城鎮化進程中的社會議題,使其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為社會公益做出了突出貢獻。而從商業價值的角度來看,電影《矮婆》又無疑是慘敗的。由于缺乏足夠的資金來支持宣發,再加上題材的小眾化,導致影片的排片量、上座率低得可憐,上映20天才靠口碑力量艱難突破20萬票房大關。然而無論如何,作為一名頗有經驗的紀錄片導演,蔣能杰導演的作品能夠從網盤放映轉為院線放映,這已是極為難得的突破。想必他的成功經驗也必定能給其他在艱難中奮力拼搏的藝術片工作者們帶來一定的啟發,中國藝術電影市場也終會迎來“井噴式”的蓬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