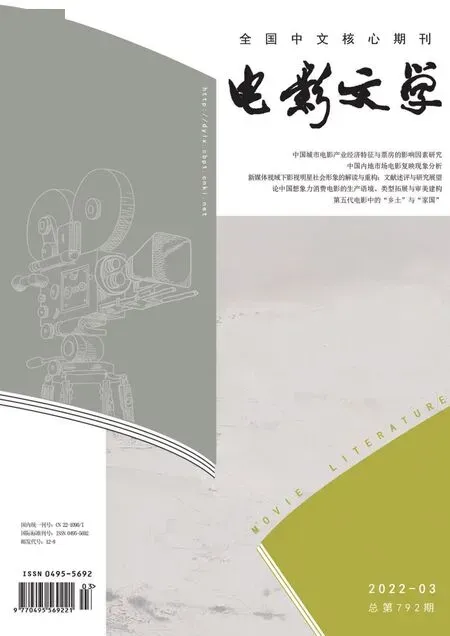《與我跳舞》的文學化表達
郝慧敏
(山西大同大學,山西 大同 037009)
矢口史靖作為目前日本最炙手可熱的導演之一,他的電影向來節奏舒緩卻不失幽默,其每一次創作的作品都會在觀眾心里刮起一股和煦的春風。憑著《與我跳舞》這部電影,矢口史靖再次獲得了特別導演獎,而電影本身則獲得了觀眾獎。觀眾獎可以說是對作品本身最高的評價了。導演本人并不擅長歌舞,對音樂也不感興趣,但正是這一點反而幫助他成就了《與我跳舞》,讓他能脫離傳統歌舞電影的思路,以獨特的手法把歌舞變成電影的劇情內聲音,同時在延續個人喜劇風格的道路上,延展了音樂這一元素對角色的明暗雙層意義,最終在電影的整體效果上達到了對主題的極度呈現。
一、延續:導演濃郁的個人風格
與其說《與我跳舞》是矢口史靖對歌舞電影的新探索,不如說是他個人風格一以貫之的再度展現。法國著名畫家保羅·高更在25歲時方才開始學習繪畫,他有流傳于世的名言稱:“我身上有兩樣東西不容嘲諷:野性和童真。”本部電影的導演矢口史靖可以說是同樣具有以上兩種高貴品行的人,這一點在他歷來的電影作品中都可窺見一斑。
矢口史靖作為一位20世紀60年代出生的鬼才導演,他所拍攝的影片卻都顯得如此青春而富有活力,這青春中又蘊含了導演樂觀看待人生的豁達和平和。他的野性在于他天馬行空的想象,導演總是能給電影人物和觀眾一個荒謬卻有效的契機,讓他們能換個環境生活,克服重重困難達到目標,最終發現、順從、釋放出內心的熱情,平和地生活著。他的童真則在于他對生活的態度,他雖然有自己的觀點,但從不冒進,而是以一種平和的創作手法引導觀眾去感受他理想中的生活本真的模樣,給觀眾一個平和地切入新世界、新視角、新體驗的機會。因此可以說,導演本身擅長的就是一種生活化文學的表達和引導,他以電影為筆,另辟空間,為觀眾書寫一個能認知自我、認識生活的新世界。
比如2001年的《五個撲水的少年》,導演讓五個高中少年玩起了花樣游泳。花樣游泳似乎一直都是被女性占據的世界,導演卻讓五個少年因老師的原因踏入這個“女性世界”,這種反差喜劇充斥著著青春期孩子們一往無前的勇氣和童真。在2018年上映的喜劇電影《生存家族》中,矢口史靖以一個荒誕但無人在意的理由引發了東京大停電,這場貌似會曠日持久的大停電讓所有人放下手機、放慢節奏,回歸到鄉野去生活。導演以此契機讓人們接受停電這一現實,突破都市桎梏、回歸生活本真的樣子。與此手法相同的,《與我跳舞》也是用后催眠暗示的手法給了鈴木靜香認識內心渴望的機會,讓她在這場催眠與追尋催眠解除的路途中,重新發現自己內心生活的熱情在何處。
矢口史靖的喜劇式表達是他獨有的風格,《與我跳舞》整部電影就有如電影名一樣——與我一起放松、歡快地跳舞。《與我跳舞》這一電影名的意義與風格貫穿全片,其喜劇效果也圍繞著“與我跳舞”這一故事元素得以實現。鈴木靜香被鼻毛吸引注意力而被催眠,這一催眠道具令人捧腹大笑;自我沉浸于音樂中而一次次在公共場合獨舞的瀟灑與后知后覺的尷尬形成喜劇反差;在公路上開車時與滿身文身的硬漢吵架,被對方綁架后卻發現硬漢也跳舞,甚至在地下停車場群體斗舞……種種荒誕不經的設定,是導演矢口史靖童真又野性的喜劇風格的再現。這條公路之旅讓鈴木靜香有機會去面對最真實的自己,也讓觀眾跟鈴木靜香一起體味這豐富多彩的日子。
矢口史靖就像本電影中的催眠師一般,他用自己獨有的文學化喜劇風格,以《與我跳舞》為治療工具,給觀眾來了一場積極心理學層面的認知療法,讓大眾可以用積極的心態來重新解讀自己,激發出自己被壓制的、內在的潛能。他永遠是平和的生活智者,用這種智慧的方式去引導大眾回歸本心、快樂生活。
二、創新:讓歌舞變為“劇情內聲音”
劇情內聲音,顧名思義就是發生在整個劇情世界之內的聲音,如人物的對話、場景物體碰撞發出的聲音等,與背景音樂、內心獨白、旁白解說等相對而言。除了導演一以貫之的文學性喜劇風格外,《與我跳舞》與眾多的歌舞類電影的不同之處正在于此,導演在如何將音樂劇的形式融入電影的問題中另辟蹊徑,借文學性的創作手法設計“劇情內聲音”,加上場景調度和音量控制,讓歌舞情節自然流暢地嵌入電影世界里,避免了觀眾產生觀影中斷之感。
在此電影的表現形式上,矢口史靖作為怪才導演并沒有因循守舊,他不是單純地延續音樂劇的舞臺形式,簡單地將音樂劇和電影情節并列、堆疊在一起,而是用文學的方式,即通過劇情設定——女主角產生了深度的后催眠暗示,一聽到音樂就會像音樂劇明星一樣情不自禁地唱跳,從而將音樂劇以必要情節的形式完美地銜接到電影世界里,使之成為劇情內聲音。誠如《冰雪奇緣》這樣的歌舞動畫電影,其主題曲Let
It
Go
雖不是劇情內聲音,但其貼合劇情與角色情緒的歌唱也讓這部電影大放異彩,主題曲能如此朗朗上口并讓觀眾沉浸其中的電影很少。從這一點來說,《與我跳舞》最大限度地規避了這一風險,用劇情內聲音的設定保證了觀眾的觀影效果,是歌舞電影的一種文學化表達。這一特殊的表現形式也影響了歌舞電影的通俗化、電影化。與絕大多數電影的通俗化、娛樂化不同,音樂劇并不如電影一樣有廣泛的大眾審美基礎,歌舞電影也鮮少成為受大眾喜愛的電影類型。《與我跳舞》突破了這一難題,它是以故事為主、音樂劇輔之的形式,在文學性基礎上讓整體更電影化、通俗化,并反其道而行,從通俗的視角重新切入音樂劇的世界。
關于這一點,導演借助劇情設計,從女主角鈴木靜香之口說出了大眾的心聲,讓觀眾在共鳴中跟隨鈴木靜香逐步改變觀點。音樂劇最為大眾詬病的,就是演員忽然在那么多人跟前又唱又跳,太不正常了,平時大家都包裹著自我,循規蹈矩地正裝上班,因此很難接受音樂劇那種截然相反的釋放狀態。導演處理之妙正在于此,鈴木靜香因兒時表演出糗的事,一直很抵觸音樂劇,她跟大眾一樣吐槽音樂劇,但她卻陰差陽錯被催眠,重新釋放出壓抑于內心深處的對音樂劇的熱愛,而這一點觀眾跟鈴木靜香一樣,在催眠效果出現前并不知曉。次日清晨鈴木靜香戴上耳機開始起床后的準備工作,這一點很日常化,很多人都是在音樂聲中洗漱,出門上班路上也戴著耳機聽歌。此時觀眾還未意識到什么不同,直到導演進行音量控制,從女主角的視聽視角切換出去。
在晨起的這首舞蹈表演中,導演的跟隨式鏡頭調度和靜音控制,顯示出女主角的自我沉浸,直到在鈴木靜香和物業保潔兩方都被靜音的視聽空間里,觀眾才意識到鈴木靜香這不尋常的一聽音樂就跳舞的現象。相同的靜音控制技巧在電影上半場快結束時再一次使用了,即從餐廳外的視角看鈴木靜香攀上吊燈在空中飛舞的樣子,從場外空間看室內運動,塑造出環境情節的現實感,用鈴木靜香自我沉浸的歌舞世界和餐廳被弄得狼狽不堪和用餐人員被驚嚇到的現實世界形成夸張的喜劇反差,以這種形式讓歌舞完美地以故事必要情節的形式融入電影中成為劇情內聲音,毫無突兀之感。
三、破與立:用聲音引導情緒
要實現電影主題的表達,除了以獨特的文學化喜劇風格和劇情內聲音的設定讓觀眾沉浸其中外,還需要導演對觀眾認知的改變。喬治·盧卡斯說過:“聲音和音樂占據電影娛樂的一半。”在此電影中,導演并沒有因新嘗試而完全地“避音樂性、就故事性”,他依然發揮了歌舞電影的天然優勢,用聲音來引導情緒的釋放,對觀眾和角色的人生觀念進行破與立。當然,如矢口史靖所言,他對音樂并不太感興趣,所以在本部電影中音樂的表現力也只能說達到了及格線,無功無過。因此導演在對聲音的表現上,尋找了文學性表達的助力。這就表現在:在本電影中,聲音的破與立,有明暗兩個層面的展現,其文學性表達則主要體現在其暗面上。
就明面上來說,聲音的電影一開場就以魔術電視節目歌曲的錄制開始,自然地接入《催眠之夜》這一串聯起整個故事的元素,并以歡快的歌曲奠定了整部電影的情緒氛圍。如絕大多數電影一樣,聲音同時引導了電影人物和觀眾的情緒體驗。女主角的情緒變化在整個故事中的脈絡是很清晰的,聲音在鈴木靜香心理改變的每個階段,都恰到好處地做了點綴。歌詞也從“踏入夢中的世界,難道你不想去嗎”,變成電影片尾曲中“去拜托時光機吧,跟隨哆啦A夢看恐龍散步”,這些歌詞里的童真、平和、美好,喚醒了鈴木靜香內心深處對做熱愛之事的生活的渴望。此外,導演選用了更直白的方式去展現聲音對情緒的引導作用,即鈴木靜香用歡快的調子引導改變了樂隊女吉他手哀怨的調子。同一首歌,歌唱者的情緒不同,最終呈現出的效果就截然相反。這一設置可以說是對音樂更通俗化、更直白的理解。音樂無國界,即使是日語電影,各國觀眾也能被歡快的氛圍所感染。
聲音的破與立在象征意義上即暗面的展現,也借助于女吉他手的出現。這點是導演對聲音意義的二次開發,頗有些哲思的意味。女吉他手的出現和遭遇正暗合著鈴木靜香的工作、生活遭遇。女吉他手稱,和男朋友在一起很久,彼此都很累,現在分開一段時間反而輕松,不再需要隱藏真實的自己,只需要做好自己就足夠了。聽完這些話,鈴木靜香低頭看了看自己的工作牌,若有所思。對鈴木靜香來說,她離家在大公司工作,租住在大城市里的房子,衣著光鮮,時常被調侃是人生贏家,家人會問一句:“你這么拼,辛不辛苦?”鈴木靜香表面很不在意地回答,她很努力也很習慣。這種生活就像是她的“男朋友”,彼此在一起太久,她其實是在戴著面具,辛苦地生活。女吉他手就是音樂的象征,分手的男友就是都市面具生活的象征。因此,鈴木靜香在身無分文時看到女吉他手,并與她一起在街邊賣唱賺錢,是她對音樂熱愛的覺醒和坦然接受,與女吉他手大鬧男友與他人的新婚現場,是對都市禁錮的一次突破。這種象征意義上的“聲音”設置,不可謂不高明。
總的來說,《與我跳舞》依舊發揮了歌舞電影中音樂影響情緒的天然優勢,但它卻能借助矢口史靖的文學化喜劇風格,讓聲音對情緒的引導更加潤物細無聲,不刻意地凸顯主題,避免了說教之嫌,從聲音的明暗兩面加強對主題的呈現,讓觀眾在影片中自然流淌的平和氛圍中看到角色和自己的內心所愿,實現了對觀者心境的破與立。
在矢口史靖獨特喜劇風格的延續中,借助文學創作方式,以劇情內聲音的設定讓音樂劇完美地融入電影中,使故事主題的表達與音樂氛圍的渲染得到最大限度的結合與發揮,讓《與我跳舞》這一整體實現了歌舞與電影文學的完美融合。嚴格來說,這部電影并不是嚴肅意義上的歌舞劇,它反其道而行,以通俗化、電影化為切入口進入觀眾的心靈,使其在一定層面上達到了如音樂作品般余音繞梁的效果,引發觀眾的心靈震蕩,最終實現了歌舞電影的文學性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