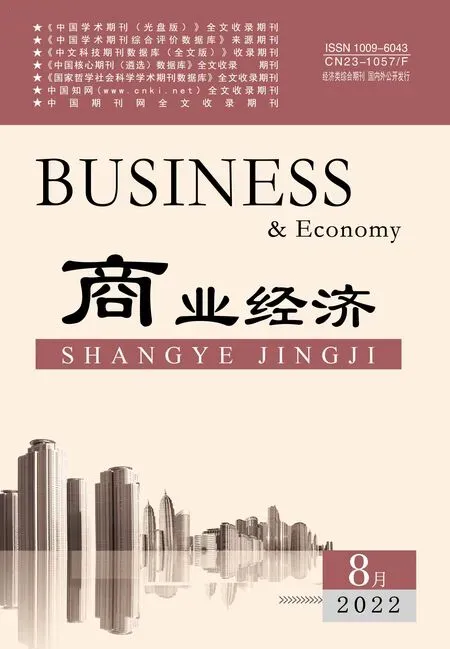基于《巴塞爾協議Ⅲ》框架下我國金融業宏觀審慎監管制度研究
許夢凡
(倫敦國王學院, 英國 倫敦 WC2R2LS)
一、宏觀審慎監管的理論內涵
(一)概念
“宏觀審慎監管”這一理念在20 世紀被國際清算銀行所提出。國際清算銀行在金融危機過后,意識到全球金融體系缺乏宏觀層面的監管,而這一缺失意味著監管者僅著重單個金融主體的監督檢查,而忽略金融機構系統整體的監管職責。宏觀審慎的概念首次被界定是在2000年,國際清算銀行的行長指出,宏觀審慎監管是指監管者在宏觀層面監督金融系統,以便降低金融市場不穩定所帶來的金融成本。此外,銀行業學者在探索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時,也察覺到隱藏在微觀審慎監管模式下的系統風險,而該風險恰好可以被宏觀審慎監管模式所緩解。由此,宏觀審慎監管被全球銀行業監管者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微觀審慎以及宏觀審慎相結合的監管模式在G20 峰會報告中被明確提出。除此之外,我國在2010 年召開的十七屆五中全會中再次強調在監管體系中加強應用宏觀審慎監管模式,預防金融市場的周期性波動。
(二)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監管的區別
第一,監管客體不同。宏觀審慎監管著重關注宏觀層面所有金融機構的穩定,而微觀審慎監管注重微觀層面單個金融機構的穩定。簡言之,宏觀審慎監管關注整片森林,微觀審慎監管關注森林中的一棵樹。第二,監管目的不同。宏觀審慎監管關注金融系統整體,金融系統的整體穩健是其目標。而微觀審慎監管關注單個金融機構的平穩運行,保證微觀層面的監管。第三,風險來源不同。宏觀審慎監管主要防范的是來自內部的風險,防止各個金融機構風險聚集,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微觀審慎監管的風險來源于外部,主要防范外部因素給單個金融機構帶來的不穩定。
二、巴塞爾協議Ⅲ框架下宏觀審慎監管維度
(一)橫向維度
在橫向維度上,宏觀審慎監管側重于關注在同一時段內分布在不同金融機構風險的相互作用導致的風險傳染問題。各個金融機構相互之間通常有著類似的金融風險敞口,在特定時間段內面對風險的來臨,所有機構采取相同的措施來降低風險,往往會導致市場流動性下降進而引發金融市場的崩潰。所以從橫向維度上看,金融監管者應充分解決相似的風險敞口給各金融機構帶來的波動問題,在經濟快速發展階段,監管者可以相應地提高銀行所需的資本門檻,防止在經濟增長期,整個金融市場陷入過度風險的困境。此外,監管者應加緊對系統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金融機構的監管,預防機構連鎖反應導致的系統風險傳播。根據巴塞爾監管委員會的規定,要從銀行規模、關聯度以及可替代性來區分系統重要性銀行。
(二)縱向維度
在縱向維度上,宏觀審慎監管側重于關注風險在不同時間段內發生的變化所導致的順周期問題。金融機構的內在風險是動態變化的,隨著時間累積而不同。在經濟上行期,經濟市場參與者對市場持樂觀心態,監管者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放松,由此帶來資產價格以及杠桿率的不斷上漲,整個金融體系處于過度風險狀態。在這種情形下,只要受到外部沖擊,那么金融市場都將面臨“順周期性”危機。因此監管者規定在經濟繁榮發展階段提高銀行所需資本的門檻,儲備充足的逆周期資本來緩解市場周期性波動,提高金融市場的風險承受力。
三、巴塞爾協議I I I 的主要內容
巴塞爾協議III 相對于巴塞爾協議II 來說,其主要特征為資本要求、流動性監管、宏觀審慎監管等方面的加強。根據宏觀審慎監管的橫向與縱向維度來看,巴塞爾協議主要體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橫向監管
橫向監管是為了防止不同金融機構之間在相同的時間段內發生風險傳染的行為。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監管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因為其與其他金融機構的關聯性極強,在面臨相似的風險缺口時,十分容易出現擴散傳播的現象。而關于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的定義,巴塞爾委員會也給出了評判標準,銀行規模大、關聯性強且具有不可替代性的金融機構就屬于在金融領域占據核心地位的系統重要性機構。由于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重要與否關乎實體經濟的發展,巴塞爾委員會增加了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資本限制,預防“大到不能倒”的道德風險。
(二)縱向監管
縱向監管是為了預防實體經濟受到金融機構周期性波動。巴塞爾協議提出建立資本緩沖制度,在經濟上行時期留存資金,為了穩定周期帶來的經濟損失。資本緩沖制度包括兩種方式,一是資本留存,二是逆周期資本。除此之外,提高資本充足率、增加杠桿率以及流動性指標也是縱向監管的工具。資本充足率的提高意味著金融機構能夠承擔違約風險的能力越強,資本風險越低。而增加杠桿率作為監管的另一個工具,對于金融機構最低資本充足的維持有利,并且可以保證金融機構擁有高質量的資本。另外,流動性監管有利于金融機構完成支付,盡管資本充足率和杠桿率符合監管要求,金融機構缺乏流動性,也會加劇風險的暴露。在金融危機發生以后,監管者意識到金融市場流動的脆弱性,因此巴塞爾委員會規定了流動性覆蓋率等流動性監管要求。
四、巴塞爾協議Ⅲ下宏觀審慎監管在我國的應用
(一)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相結合
微觀審慎以及宏觀審慎相結合的監管模式在巴塞爾協議Ⅲ的框架下被提出,結合這兩種監管模式,可以在市場出現波動時,保障資本充足率,不至于對經濟社會造成嚴重影響,保障金融機構的平穩運營。我國在微觀審慎監管方面已經較為成熟,但對于宏觀審慎監管的理念貫徹不到位。我國銀行業要更關注整體金融機構的監督檢查,但也不能忽略單個主體的監管。監管機構要明確分工,建立具體部門分別進行宏觀以及微觀監管。
(二)加強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
系統重要性機構是指在金融系統中占有核心地位的機構,其從事的業務交易廣泛滲透在金融市場的各個機構之間,因此該重要性機構的穩定運營,決定著金融市場不受經濟動蕩的影響。建立關于系統重要機構的特別處置機制,以便在重大風險來臨時,可以及時作出應對,確保平穩有效地度過風險,保障金融機構的平穩運營,同時也要防范“大到不能倒”的道德風險。對于我國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征收“金融穩定貢獻”稅或者提高資本要求,以便在危機來臨時,有足夠的資金來擺脫困境。
(三)宏觀審慎監管與貨幣政策相協調
雙支柱調控框架在十九大中被提出,報告中明確說明宏觀審慎監管應與微觀審慎監管相互促進、相互協調,著重強調健全宏觀與微觀審慎監管模式的重要性,這不僅僅符合目前金融趨勢也符合我國基本金融國情。我國實行的是有多重目標的貨幣政策,其不僅要維護價格穩定、維持收支平衡,也要穩定經濟增長和促進就業,這無疑給貨幣政策的執行者帶來巨大壓力,各個目標也存在平衡問題而宏觀審慎監管減輕了貨幣政策的多目標壓力,使貨幣政策工具定位更加準確。此外,健全的宏觀審慎監管制度有利于防范金融市場“順周期性”現象的發生,也有利于防止各機構間風險傳染現象。貨幣政策著重關注于幣值穩定,而要想在穩定幣值的基礎上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是不現實的。近些年來我國金融機構越發多元化,金融創新蓬勃發展,互聯網技術廣泛應用,這些因素進一步加劇了金融市場風險傳播擴散的程度。因此我們除了利用貨幣政策來穩定市場物價以外,還需要從宏觀層面對整體金融機構的運行態勢進行監管。貨幣政策通過總量調控可以穩定貨幣金融市場,而宏觀審慎政策利用定向控制來降低系統性風險,兩者相輔相成,穩定宏觀環境,降低市場的波動。除此之外,不同且難以替換的政策目標以及政策工具,都使宏觀審慎監管與貨幣政策相結合成為必然。
(四)加強對影子銀行的監管
影子銀行是指在傳統商業銀行的體系之外,從事著“類銀行”業務的非銀行金融機構。自從美國次貸危機發生之后,監管者對影子銀行越發關注,影子銀行從事著與商業銀行類似的業務交易,但不受到銀行監管者的監管,這一度成為金融風險的嚴重隱患。影子銀行有三個基本特點:批發型交易、不公開交易、高杠桿率。這三點也是與商業銀行的不同之處,商業銀行的交易是零售型且公開的。由于影子銀行業務交易的復雜性以及信息披露的不完整性導致影子銀行造成的潛在風險十分隱蔽,往往在監管者發現問題時,已經難以彌補。除此之外,影子銀行由于缺乏監管,其資本要求沒有限制,這就導致影子銀行可以在資產規模不大的情況下進行大規模信貸交易。影子銀行在我國2016 年底達到最大規模,違法違規行為暴露,加劇了金融風險的潛在隱患,危及社會穩定。因此,監管部門應該根據影子銀行的業務特點實施監管要求,規定資本充足率以及杠桿率標準。另外,監管部門應該明確要求影子銀行公開業務交易內容、披露業務完整信息,提高透明度。最后,加強國際之間的監管合作,影子銀行同樣具有全球性,相似的風險敞口會傳導至各國影子銀行,因此要加強建設國際影子銀行監管制度。
五、結語
宏觀審慎監管模式作為銀行業監管者所支持的監管模式,順理成章地在巴塞爾協議中占據重要地位。具體來說,宏觀審慎監管著重要求監管者在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以及貨幣政策等方面進行關注。金融市場的穩定也正是宏觀審慎監管通過這幾方面實現的,一方面宏觀審慎監管要求銀行業準備充足的資金來緩解周期性波動,另一方面通過監管金融市場中具有極強關聯性的金融機構來防御金融系統內部風險傳播。我國應該在結合自身銀行業監管現狀的情況下,借鑒巴塞爾協議III 中符合我國金融監管體系的先進經驗,并針對我國客觀現狀進行適當調整。巴塞爾協議給全球金融業帶來了更嚴格的監管體制,是金融監管方法的不斷改革與創新,提高了各國金融監管的效率,使全球金融體系處于平穩狀態。我國應積極主動融入金融全球化進程,充分利用巴塞爾協議III 的精華部分,提高我國銀行業監管水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且符合金融監管客觀現狀的監管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