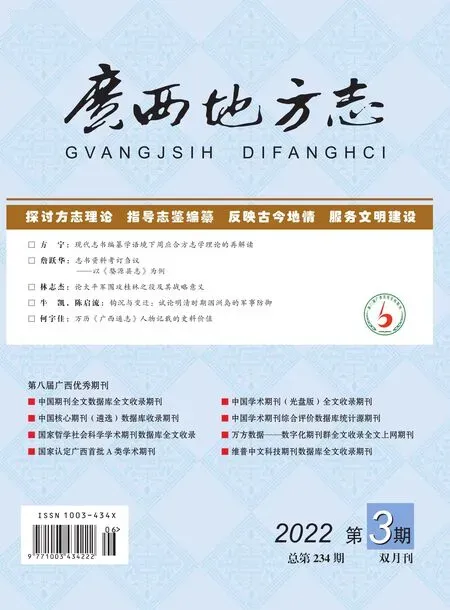一部優秀的不可移動文物志
——《石峁遺址志》
王 暉
(安徽省地方志辦公室,安徽 合肥 230001)
2018年5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會宣布,石峁與良渚、陶寺、二里頭文化遺址一起成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重要成果,相關內容編入中學教材。2021年12月,由陜西省地方志辦公室與陜西省文物局聯合編纂、方志出版社出版的《石峁遺址志》全面系統記錄了石峁遺址的考古成果,它的出版發行實現了方志文化和考古文化的協同傳播,讓歷史復活起來,為古老的石峁遺址插上騰飛的翅膀,走向世界;也為方志園地增添了一部獨特優秀的文物志。這部文物志是由石峁自然實體與人工建筑石城遺址合成的一部大型不可移動文物志。所謂不可移動文物,是指“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畫、近代現代重要史跡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動文物”①2013年6月29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第三條。。編纂不可移動文物志的體例不同于一般的館藏文物志,它具有自然環境與人工建筑雙重屬性。《石峁遺址志》采用綱目體,首設“概述”“大事記”,卷末有“附錄”,正文從自然環境到考古發掘、石砌城址、文物收藏、學術研究、保護管理、宣傳展示、藝文、雜記、人物,大類為綱,類為一志,“志”分十類,特色鮮明。
一、突出自然實體特色——設置“遺址環境”志
不可移動文物是坐落在一定的自然實體之上的。編修《石峁遺址志》,首先要考慮到不可移動文物的自然實體,以確定志書的區域性和記述空間范圍。《石峁遺址志》第一大類即設置“遺址環境”志,下設兩個分目“自然環境”“人工環境”。“自然環境”記述的是這一自然實體狀況,故設置“區位交通、地形地貌、河流水文、氣候植物、礦產資源”等目。“人工環境”無疑記述的是自然實體之上的社會環境,設置“政區建置、名鎮榮譽、村莊人口、經濟業態、文化教育、名勝古城、風土民情”等目,人工環境的內容是從石峁遺址向外放射狀擴散,將石峁村和高家堡鎮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環境囊括其中。“遺址環境”志這樣的設置,使志書的首要特征地方性和大型不可移動文物志的自然屬性得到很好的體現,萬事萬物都賦存在一定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之中,因此,“遺址環境”志的設置是非常必要的,科學的。
二、突出文物考古特色——設置“考古發掘”志
文物是靜態的物體,而對其發掘是動態的活動。《石峁遺址志》第二大類設置“考古發掘”志,成為《石峁遺址志》中最吸引眼球的鮮活內容。該類首列“考古調查”分目,將歷次調查分別設置條目;然后依次設置“發掘項目”分目,記述歷次發掘地點;“重要榮譽”分目,設置“中國考古新發現、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世界重大田野考古發現、田野考古獎、世界十大考古發現”條目,一個個令世人震驚的考古發現,讀之滿目驚喜和驕傲;最后一個分目“考古工作隊”,記述人員結構、考古工作平臺、石峁文物醫院以及考古實習生、雇工等條目,這個分目是專門記述考古隊伍的,突出了人在考古工作中的作用。人是社會活動的主體,每次參與調查的人,即便屢次參加學術研討會的人,都有單位和人員姓名記載,見事見人,既突出文物考古特色,又彰顯志書人文精神,此志堪稱是以事系人的典范。
三、突出建筑物體特色——設置“石砌城址”志
不可移動文物基本特征是屬于人工建筑的遺址。《石峁遺址志》的主體內容是石峁城遺址,志書第三大類設置“石砌城址”志,分別記述石峁城核心區“皇城臺、內城、外城、城外地點”。皇城臺位于石峁內城中部偏西的高阜臺地,為四圍包砌護坡石墻的建筑,面積達24萬平方米,頂部面積達8萬平方米,最大垂直高度超過70米,9至11層級護墻逐漸內收,階階相疊,呈底大頂小覆斗狀“金字塔”結構。皇城臺為大型宮殿及高級建筑基址,構建年代在公元前2300—前1800年之間,人們想象當初宮殿錯落有致、堅固巍峨、雄偉壯麗,凸顯威儀感和震懾力。“內城”面積210多萬平方米,已發現城門4座、馬面6個、角臺3個、殘存城墻60余段;“外城”面積約190萬平方米,已發現城門4座、馬面9個、角臺3個,殘存城墻20余段。“外城地點”兩處。每個城址記述有經緯度、城墻、門址和出土文物介紹,配有精美圖片,圖文并茂,敘述簡明。“石城”是石峁遺址的核心,“石砌城址”志也是《石峁遺址志》的核心,為全志之魂所在,十分珍貴。
四、突出石峁文化特色——設置“出土器物”志
石峁文化不見諸多少文獻,其標志完全在于出土文物。《石峁遺址志》第四類即設置“出土器物”志。自2012年石峁遺址系統考古發掘以來,石峁遺址出土了玉器、石器、陶器、骨器、銅器、壁畫、紡織物、水晶、松綠石等各類器物。志書分5個小類記述,用文物說話,這些實物證實了石峁璀璨的歷史。皇城臺遺址出土的玉鉞、玉環、玉琮,標志著龍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石峁是繼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之后,與齊家文化、后石家河文化鼎足而立的一座史前玉器寶庫。陶器是新石器時代先民日常使用的生活器皿,又是判斷考古學年代和考古學文化的標準器物。石峁出土的“雙鋬鬲”為代表的陶制穩定器物成為“石峁文化”命名的最重要依據。石峁城是石頭的王國,石雕品種多樣,有直立一米多高的雙神面大石雕令人震撼,橫置神面石雕長達2.67米,雙虎面石雕長達1.79米,還有人面石雕、牛馬石雕、人射馬石雕、眼形石雕、對獸石雕、蛇紋石雕、石鏃等,其形狀自身是時代的產物,有待人們與石對話,進一步發現其中的奧秘。其次還有骨器,卜骨、針具、口簧、管哨、箭鏃等。至于其他類的銅刀、銅鏃、壁畫殘片、麻布殘片、海貝等,這些文物在志中沒有記載考古認定的年代,但它能告訴人們,石峁的遺物并非某一時期某一地的產物,而是多個歷史時期多個地方的器物隨著人類文明往來活動而遺存下來,因此,考察發掘無窮期。
五、突出人文科研特色——設置“學術研究、人物、藝文”志
《石峁遺址志》記述的實體是石峁城址,對于石峁城址本體的考古發掘離不開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志書為突出人文科研特色,設置了“學術研究、藝文和人物”等類志。“學術研究”設“學術會議”“研究成果”兩個分目。文物考古界召開多次學術會議,通過對石峁遺址考古新發現進行深入交流和研討,石峁文化的概念屬性及年代特征也逐漸明晰,取得豐碩成果。“藝文”類設置“文獻書目、詩文選萃、書法題詞、石雕拓片”4個分目,內容十分豐富,是全志分量最重的一類,56個頁碼,其中“詩文選萃”41個頁碼,詩只有2首,文的篇幅就顯得收錄過多,有些考古紀事、工作匯報內容可記入考古發掘類目,用不著不加提煉地收入“藝文”中。“人物”志設置6個目,全是參與考古的專家學者,收錄面不夠廣,還應該收錄歷史上在石峁留下足跡的有影響的人物。
人文活動方面還設置了“保護管理、宣傳展示、雜記”三類。這些類目設置有必要,但微觀上出現交叉現象,例如“宣傳展示”中的文物,比前面“出土器物”類中記述的品種還要多,“出土器物”中的“玉器”只有2頁7個目的介紹,而在“宣傳展示”類中的“玉器”就有8頁33個目的文字介紹,明顯歸屬不當,可以合并到前者,“宣傳展示”綜合簡記展示概況,不必具體到每個器物。再如“雜記”類沒有分目,下設5個條目,14個頁碼,篇幅單薄,難以支撐一個大類,其中“學術爭鳴”文章完全可以移入“學術研究”類目中,“周邊同期遺址”可以移入“石砌城址”類“城外地點”分目中,其他條目可以移入“附錄”下“資料文獻”中去。
形式為內容服務。體例設置微觀上出現小交叉不影響資料的記述。瑕不掩瑜,《石峁遺址志》是一部總體結構合理、文字敘述精準、圖片設置精美、出土文物輝煌、歷史厚重深邃、以人為本鮮明、學術性與通俗性并舉的好志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