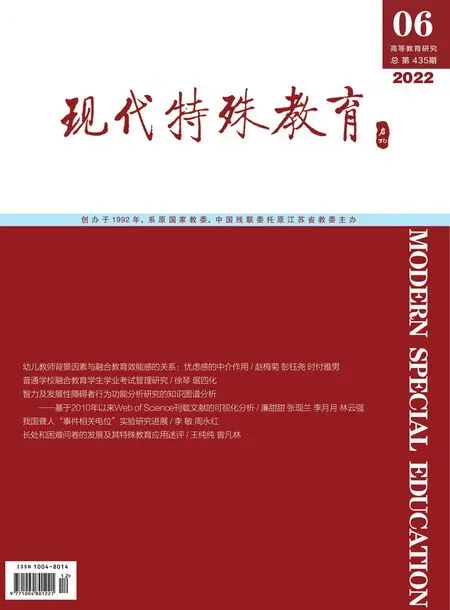特教史史料收集整理的問題意識與檔案策略
季 瑾 梁思綺
(1.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院副研究員,教育學博士;2.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院特殊教育學院2019級卓越班學生,中國特殊教育博物館優秀學生志愿者)
翔實的史料是呈現歷史圖景、分析歷史問題并得出研究結論的基本依據。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先生概括總結過史學撰寫的基本功為“文史哲”,這其中的“史”,即是如此。史料作為史學研究的基礎性支撐,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兩年來,中國特殊教育博物館先后承擔了《中國特殊教育史資料選新編》《中國特殊教育通史》的撰寫工作。為了充實以此為支柱的中國特殊教育通史研究的內涵,熟悉、收集、整理、呈現、研究中國特殊教育史史料便是重中之重。而在搜集和整理特殊教育史史料的過程中,適時地總結和反思更是當務之急。
一、特教史史料收集與整理工作的新進展
中國特殊教育博物館自建館伊始,就以“融合致和,存古開新”為館訓,致力于中國特殊教育史各門各類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依托現有館藏資源和區位優勢,中國特殊教育博物館廣泛收集中國特殊教育史史料,前往全國各地特殊教育學校,走訪老一輩特殊教育工作者,于2020年出版了《共和國教育學七十年:特殊教育學卷》,2021年完成了《中國特殊教育活動史》的初稿撰寫。
2021年中國特殊教育博物館受北京師范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委托,開始了《中國特殊教育史資料選新編》的編纂工作,于同年1月4日舉行了《中國特殊教育史資料選新編》的開題會,會議期間多次與北京師范大學顧定倩教授交換意見,赴國家圖書館、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南京市圖書館、南京市聾校等地收集史料,并及時進行整理匯編工作。
現階段,基于長期的、有規劃的、可持續性的歷史研究指向,中國特殊教育博物館不斷豐富史料類型,拓寬史料收集范圍。實物史料方面,我館不斷走訪特教名校,收集如教具、學具等類型的特教實物;圖文史料方面,著名檔案館所存檔案是最好的一手史料,同時特教名家、一線特教工作者、有突出貢獻殘疾人的文字材料與圖片材料也收集頗多,且在不斷增加;口傳史料方面,中國特殊教育博物館極為重視特教名家口述史的記錄與研究工作,不斷走訪特殊教育名家,進行搶救式的采訪、收集與整理。基于已經開展的史料積累工作,中國特殊教育博物館現承擔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和數個省級、廳級研究課題;同時整理形成了近百篇有效的完整史料匯編冊,約六十萬字,并存有近千張史料檔案圖片。
二、特教史史料收集工作中的問題
作為歷史學研究對象的“歷史”,是人類在文明進程中所形成的客觀實際,不以時間的更迭和人類的意志為轉移。因此,有效挖掘史料,進行多方驗證,盡可能地接近歷史真相,應成為基本的史學研究態度。我館在為《中國特殊教育史資料選新編》進行特教史史料的收集和整理過程中,堅持尊重歷史、還原歷史的價值取向,同時以發現問題為導向,探索發現特教史史料的收集和整理過程中的問題,深入思考,改進特教史史料收集和整理的方式方法,以實現材料與方法的平衡呼應。
(一)“特教史史料”的概念界定模糊
現階段的“特教史史料”定義暫為本研究所作的定義,是在特殊教育和史料雙重疊加下的單一語境下的定義;而“特教史史料”科學、準確的定義一定不是二者的簡單疊加,而是有其內在邏輯聯系的。依據現有的特教史史料來看,多數特教史史料所屬的研究范圍很大,與“預防殘疾”“殘疾”“障礙”“殘疾人”“社會救助”“慈善”“慈幼教育”等概念本身的歷史發展密切相關。如果單純從教育史的角度出發,部分有價值、可以佐證特殊教育發展歷史的史料便無法被收錄。因此,“特教史史料”的定義需要適當外延。
(二)特教史史料收集效率有待提高
受到特殊教育本身發展時段的歷史限制,特教史史料鮮見單獨成冊,邏輯很清晰、內容很完整的特教史史料難以獲得。有的在官方檔案中,有的在地方志中,有的在書籍報刊中,還有的在私人信件中,很少單獨出現。史料來源的多樣性使得特教史史料的收集猶如大海撈針,效率有待提高。無論是前往檔案館查檔,還是網絡資源檢索,都面臨篩選、辨識和解讀的困難。同時,大多數特教史史料分布在各省、市的檔案館、圖書館、高校檔案室、特校校史館等地,均屬于內部資料,借閱手續繁瑣,機構之間交流不暢,資料查找、獲取困難。并且,盡管有時收集到了相關史料,也只是某個篇章中的一小部分,史料殘缺,難以將其放置于完整的歷史語境中呈現。
(三)特教史史料類型有待豐富
如果將視角進一步投射到檔案這一重要的一手史料中,我們會發現此問題較為明顯。比如,檔案除了官方檔案,還有社會組織檔案和民間私人檔案。作為特教史史料收集的重要來源,依據現有情況,仍是官方檔案的查閱相對便捷。那么,如何收集另外兩類檔案?誰或者哪里會有檔案?諸如一些特教名家或政治社團、學術團體、慈善機構等,都有相應的歷史檔案,且都是接近原生態的,如何尋找與說服對方同意分享利用是一個難題。當我們得以知曉,或已經獲取信息,就會思考怎樣獲取收集這一問題。事實上,很多社會檔案或者民間檔案,往往對還原歷史原貌有著較高的價值,可能會將特教史研究引向深入甚至取得突破性成果,關鍵就在于如何聯系、交流、獲取收集。
(四)特殊教育史古代部分史料收集困難
古代的特殊教育與現代對特殊教育概念的理解并不一樣,理念、定義、目標、對象都不是完全相同的,古代的特殊教育不完全是今天的特殊教育,今天的特殊教育也不完全是古代的特殊教育。如果用現代特殊教育的視角去看古代的史料,史料收集的范圍和類型都并不完全符合現代的標準,但是古代的很多史料對于研究我國特殊教育的歷史發展卻有著重要的前推意義與價值。
三、特教史史料整理中的問題
特教史史料整理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主要源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缺失史料分類標準
現有的特教史史料匯編主體以時間序列進行整理,子目錄按類別分類。但特教史史料內部結構復雜,整理可選用的方式多樣,在子目錄分類時出現了如下問題。
1.圖片畫冊難以歸類
有些特教史料是圖片畫冊,還有些特教史料的原稿是書畫、圖紙。對于以上的史料,一般的分類方式是依據時間,找到下屬的子目錄,考慮到史料整理的寫實性,其實是可以考慮單獨成冊進行整理的。
2.史料的類別分類與史料的相關性分類的矛盾
舉例來說,按照史料的類別分類,《北平市立聾啞學校為在特別科內添設復式班致北平社會局呈文》將被分類到“各地特殊教育”下的“北京特殊教育”子目錄下,《北平市政府社會局指令》將被分類到“法律文件”下。但是,如果細細研究內容,能發現《北平市政府社會局指令》是對《北平市立聾啞學校為在特別科內添設復式班致北平社會局呈文》的回復,從專家學者研究的角度講,這樣更利于專家學者進行歷史研究。
(二)書籍拆分與完整呈現的矛盾
以《中國殘疾人史》為例,現有的整理是將《中國殘疾人史》拆分到了“古代部分”“近代部分”和“現代部分”下,但由于《中國殘疾人史》本身具有一定的內在編寫邏輯,貿然粗略以時間拆分的做法有失妥當。
(三)近代部分的史料繁簡混雜
現在的史料錄入遵循“盡可能保留歷史全貌”的錄入原則,對于所有繁體資料都盡可能依照原件整理,但是不利于后期的校對和出版后的使用。如果把繁體字資料轉化成簡體字,也會出現新的問題,如,由于文字繁簡體的更迭,繁體字與簡化字內容用法不完全對應,轉化內容與原文的一致性不一定相匹配。
(四)史料整理呈現方式較為單一
目前所收集到的特教史史料主要分為書報、公文、實物和口述史訪談資料,主體集中于書報和公文,整理方式主要為錄入成冊,編成書籍。考慮到拓展史料多樣性的現實需要及后續史料整理工作的展開,可能還需要以圖冊、展覽等方式呈現史料。與此相關,每種呈現方式的改變,如何進行調配、整合并建立邏輯關聯就顯得很重要。
四、特教史史料收集與整理的問題解決策略
(一)建立特教史史料收集與整理的標準
特教史史料的收集與整理工作應建立一套完整、細致、科學、符合史學研究要求的標準體系,為特教史史料收集與整理提供科學的學科指引和學術指導。標準體系的內容大致涵蓋特教史史料的界定、收集、整理、呈現、學術研究、社會服務等各個方面。
(二)完善特教史史料收集與整理的合作機制
1.成立并不斷充實特教史史料收集與整理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負責具體的特教史史料收集整理工作,以專業人員為主體,成員相對固定,關鍵人員長期固定,人員責任明晰,以確保特教史史料收集整理、校對審稿、學術研究、成果轉化的持續推進,形成高效、系統的閉環工作體系。
2.拓展特教史史料收集與整理的合作機構
將現有的合作單位繼續向更深領域、更廣地域拓展,可與具有較長辦學歷史的特教學校、省市博物館、檔案館、專題性博物館、高校研究所、私人收藏家等機構與個人進行學術合作,使特教史史料收集整理更加便利,拓寬特教史史料收集的渠道,提高特教史史料收集與整理的效率。
3.定期舉行特教史史料收集、整理、研究方面的學術會議
舉行學術會議需要有特殊教育、教育史、歷史學、醫學、博物館學、檔案學等多學科背景的專家學者、組織管理者、分管領導等人員參加,多方共同參與,商討特教史史料收集整理的疑難問題,制訂解決執行方案,推進工作執行。會議既能為特教史史料收集整理提供指導,也是特教史史料收集整理的交流平臺,還是特教史史料收集整理的監督和檢查機制。
(三)健全特教史料收集整理的支持保障體系
1.組織和專業團隊保障
中國殘疾人史研究中心依托成立中國特殊教育博物館研究中心建立特教史史料收集整理的組織團隊,依托南京豐富的學術資源優勢尋求各專業機構或專家學者的支持,相互交流、協作、配合。
2.財政支持保障
特教史史料收集整理前期投入大,短期內直接的經濟效益少,需要來自政府、高校研究機構持續的資金支持。有充足的資金支持還可以設立獎勵機制,激發團隊工作的自覺性和主動性,更好地服務于特教史研究和殘疾人史研究。
3.課題支持保障
特教史史料收集整理僅靠一家機構或一群人的力量難以長久,以課題為引領,組織整合各學科背景的專家、學者、老師,能夠更好、更全面地開展特教史史料收集與整理工作,并保障其有效性。
4.技術支持保障
現代史料資源庫十分豐富多元,可充分利用信息技術為特教史史料收集與整理解決基礎性的技術難題,提升特教史史料收集整理和校對審稿的效率;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工具建立數字化特教史料資源庫,方便查找利用,促進學術研究,推進史料的成果轉化。與此同時,數字化的特教史史料擬面向大眾,這樣具有開放性的史料資源庫將幫助“特教圈外”的人認識和了解特殊教育,吸引其參與到特教史史料收集、整理、研究的過程中來,也更利于向社會大眾宣傳殘健融合的理念,促進和諧社會的殘健共融,充分發揮史學研究的社會服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