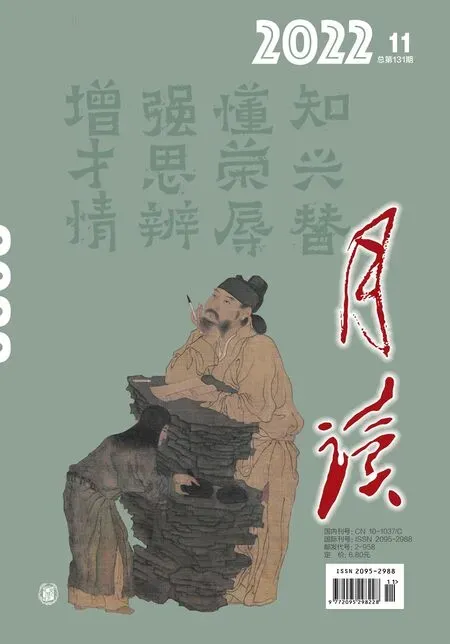中國流芳千古的石刻碑碣
◎ 黃劍華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頒布了一系列規章制度,以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完成四海歸一的大業。其中最重要的一項,便是采用小篆,統一文字。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東巡泰山,命丞相李斯刻石于泰山絕頂,以炫耀其文治武功。其后,秦始皇又數次前往東方和南方地區巡游,每到一個地方,便祭祀名山,刻石豎碑,為其歌功頌德。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先后在泰山、瑯邪臺、芝罘、碣石、會稽、嶧山六處七次刻石。秦二世時,又補刻了詔書和從臣之名。后人將這些刻石統稱為秦刻石。這些刻石均由丞相李斯采用小篆書寫,字體瀟灑優雅,備受贊賞。秦朝的這些刻石群,雖然今天大都已被毀壞湮沒,難窺全貌,卻是書法與石刻藝術上的一件輝煌壯舉,對開啟和推動石刻碑碣風雅文化的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陜西臨潼兵馬俑博物館中的秦始皇浮雕像

秦《嶧山刻石》拓本
漢朝建立統治后,廢除了秦的苛政,經濟文化繁榮發展。特別是西漢前期的文景之治和中期漢武帝的蓬勃開拓,物產豐富,國力鼎盛,有力地促進了西漢書法藝術的發展。秦篆這時已被漢隸所取代,成為流行全國的書法字體。漢隸靈氣飛動,形態優美,風格多樣,情趣盎然。比起古樸的先秦篆書,漢隸貫注了人們更多的主觀情感,顯示了書法藝術的跳躍式發展。西漢留下的石刻不多,目前所知,主要有《魯孝王泮池刻石》《群臣上壽刻石》《麃孝禹刻石》等。
到了東漢時期,終于迎來了石刻藝術發展的高峰,出現了數量眾多的碑刻,遍布于全國各地,據今人統計,傳世的漢碑約有170余種,真可謂琳瑯滿目,蔚然大觀。
東漢碑刻,種類繁多。根據形制和用途的不同,可以分為碑、碣、墓志、摩崖石刻、石經等數種。其中數量最多的是碑刻,形制大都為長方形石刻,由趺座、碑身、碑額組成。碑刻內容,大體可分為頌功、記事、契約、墓志、經典等幾類。著名的頌功碑刻,主要有《裴岑紀功碑》《楊君石門頌》《劉平國碑》《西狹頌》《曹全碑》《張遷碑》等;著名的記事碑,有《乙瑛碑》《禮器碑》《張景碑》《史晨碑》等;著名的墓志有《鮮于璜碑》《孔宙碑》《袁安碑》等。上述這些漢代名碑,其石刻文字,不僅是研究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珍貴材料,也是流芳千古的書法藝術珍品,為歷代文人雅士所珍愛。在豐富多彩的東漢碑石中,《史晨碑》《乙瑛碑》《禮器碑》《西狹頌》《曹全碑》《張遷碑》等,都是值得介紹的名碑。它們的書法風格多樣,各具特色,或方整,或散逸,或雄厚,或秀勁,或高古,表現了漢代石刻藝術的百花齊放,各臻其妙。
漢代碑刻風格多樣,絢麗多姿,洋溢著一種宏大雄健的磅礴氣勢。當我們站在那些巍然巨制的摩崖石刻前,面對那些渾厚古拙的碑刻文字,仿佛感受到了漢王朝在歷史風雨中蓬勃前進的雄壯腳步聲。漢代碑刻書法豪放熱烈壯觀的風格,帶給我們的不僅是古趣盎然的藝術享受,更使我們體會到了漢文化的壯麗和大氣。
由先秦發展到漢代的石刻書法藝術,已由稚拙走向成熟。許慎編撰的《說文解字》這時也問世了。篆書得到了全面的總結,隸書獲得進一步的規范和完善,草書已成熟,楷書和行書的雛形也在東漢末年出現。這一切奠定了一個雄厚的基礎,預示和孕育了魏晉風雅文化的燦爛來臨。
值得一提的是,東漢還出現了刻在石頭上的教科書《熹平石經》,刻于熹平四年(175),相傳為當時的著名書法家蔡邕用隸體書寫,將《詩》《書》《禮》《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等儒學經典,鐫刻在46塊石碑上,豎立在洛陽的太學之中。《熹平石經》的問世,不僅是漢朝教育事業上的一件盛舉,也是書法史上流芳千古的美談。由于《熹平石經》是我國第一部石經,開啟了將石刻與教育事業相結合的傳統,也為后世所繼承,譬如曹魏《正始石經》、唐朝《開成石經》、五代《孟蜀石經》、北宋《嘉祐石經》、南宋《國子監石經》、清朝《乾隆石經》等,都傳為美談,可謂影響深遠。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朝的碑刻不多,最著名的有《瘞鶴銘》《爨寶子碑》和《爨龍顏碑》。《瘞鶴銘》為摩崖刻石,刻在丹徒(今江蘇鎮江)焦山西麓的巖壁上,有人認為《瘞鶴銘》是梁天監十三年(514)陶弘景所書。這一考證,得到了后世文人學者的普遍認同。《爨寶子碑》,刻立于東晉義熙元年(405),是東晉爨寶子的墓碑。《爨龍顏碑》刻立于南朝宋大明二年(458),敘述了爨氏的家世淵源和爨龍顏祖孫三代在本州做官的政績,是了解當時邊疆地區政治、軍事機構組織的重要文物資料。書法史上將《爨寶子碑》稱為“小爨”,《爨龍顏碑》稱為“大爨”,二者并稱為“二爨”。此碑書體仍在隸楷之間,顯示了書法由隸體向楷體的演變,如果說“小爨”是隸多楷少的化合體,那么“大爨”已經是楷多隸少的典范了。“大爨”書法古拙敦厚,強健茂美,氣魄雄渾,神韻高曠,備受文人雅士的珍愛,被推許為“六朝碑版之冠”。1961年,“二爨”同時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兩座石碑,不僅是書法發展演變進程中的奇珍異寶,也是漢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藝術水乳交融的燦爛結晶。
這個時期,北朝的書法石刻藝術在沒有禁令與干涉的情形下,獲得了興盛發展。南朝屬地因為采石不易,又因東晉時禁止隨意刻碑,故南朝碑刻稀少。北朝碑刻數量眾多,著名的碑刻大都出于北魏,所以習慣稱之為魏碑。在清代以前,研究北史的學者不多,北朝碑刻一直沒有得到重視。漢隸唐楷,占據著清代書壇的主流。乾隆、嘉慶年間,學者兼書法家包世臣(1775—1855)開始竭力推許北魏書法,認為魏碑所具有的河朔清剛之氣,可以挽救書壇當時流行的晉草唐楷柔弱之弊。他撰寫了一本名為《藝舟雙楫》的書,宣傳他的書法觀點。近代康有為繼承了包世臣的理論觀點,并作了進一步的宣揚,寫了一本《廣藝舟雙楫》,為北魏書法大聲疾呼,提出了“尊魏卑唐”的口號。由于包、康兩位人物的大力號召,掀起了一股臨摹魏碑之風,各種魏碑拓本成了書法家們爭相求購和學習的范本。
魏碑的種類較多,有造像題記、墓志、碑碣、摩崖石刻等。最著名的有:《龍門二十品》、《鄭文公碑》、云峰山(今山東萊州境內)諸石刻、《石門銘》、《華岳廟碑》、《嵩高靈廟碑》、《暉福寺碑》、《皇帝吊比干文》、《賈思伯碑》、《馬鳴寺根法師碑》、《張猛龍碑》、《崔敬邕墓志》、《張黑女墓志》、《刁遵墓志》等,以及近世出土的《元澄》《李氏》諸墓志。康有為研究總結了魏碑的造型風格特點,將魏碑分為“龍門造像”“云峰石刻”“四山(岡山、尖山、鐵山、葛山)摩崖”三大類型。當代書家翁闿運根據魏碑的筆法結構和風姿神采的不同,在《談北魏書法》中更細分為“方勁古秀”“亂頭粗服”“沖和靈秀”“貌拙實巧”四類。在眾多的魏碑中,最值得推許和介紹的應數《鄭文公碑》了。鄭文公即鄭羲,所以此碑又稱為《鄭羲碑》。碑文內容是鄭羲小兒子鄭道昭撰寫的稱頌父德之文,其書法相傳由鄭道昭書丹上石。其書法寬博凝重,渾厚雄健,既有篆書的氣勢、分隸的韻味,又有草書的情致。學者與書家們常將《鄭文公碑》與《瘞鶴銘》相提并論,稱贊它們是兩朵開放在長江兩岸的石刻書法藝術奇葩,一南一北,雙峰對峙,雄視千古。
隋朝結束了南北朝對峙的局面,經濟與文化在南北融合的情形下獲得了新的發展。這個時期的石刻碑碣也開始興盛起來。宋代趙明誠《金石錄》記錄的隋代石刻達76種之多。清代嘉慶年間王昶編撰的《金石萃編》,記錄了隋代石刻30種。同治年間陸增祥校訂的《金石續編》,也記錄了7種隋代石刻。從上述記載可以知道,隋代石刻的數量是相當豐富的。遺憾的是,保存完好流傳至今的已不多,大都已毀壞散失。至今猶存的著名隋碑有《龍藏寺碑》《陳茂碑》《修孔子廟碑》《曹子建碑》等,約10余種。其中開皇六年(586)刻立于河北真定(今正定縣)的《龍藏寺碑》,書法遒麗寬博,無六朝儉陋習氣,開初唐楷書之先河,被認為是最有影響的隋碑,為后世書家研習楷書者所珍愛。
唐朝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光輝燦爛的階段,政治清平,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涌現了眾多的大詩人和大書法家。碑碣石刻藝術也百花齊放,出現了興旺昌盛的發展高潮。唐碑數量眾多,風格多樣,大都為名家手跡,洋溢著不同的個性特色,如群星閃爍,絢麗多彩。上至帝王,下至普通文人,都雅愛書法。

唐太宗像(宋人畫)

《溫泉銘》傳世摹刻拓本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文韜武略,一世之雄,而且酷愛書法,唐碑中的《晉祠銘》《溫泉銘》便是李世民手書。碑文為行書,筆力遒勁,神氣雄厚,雍容和雅,圓潤流麗。后人評價說,以行書入碑刻,就是從李世民開始的。李世民在書法上學習二王,已登堂入奧,達到了縱橫自如的境界。唐太宗開啟了帝王撰書碑銘的風氣,之后唐高宗李治(628—683)也是一位嗜好書法的皇帝,唐代張彥遠《法書要錄》曾生動地記述了李治的書法造詣,說他“兼絕二王”。北宋朱長文《墨池編》稱其雅善真草隸飛白,擅長各種書體。李治于顯慶四年(659)親自撰文書寫了《大唐紀功頌》,刻碑于河南汜水(今滎陽縣)等慈寺。其后做了女皇帝的武則天也擅長書法,《升仙太子碑》便是武則天的手筆,碑文中的“飛白”靈逸飛揚,華艷飄蕩,堪與唐太宗、唐高宗的飛白筆法媲美,令后代書家大開眼界。唐玄宗李隆基(685—762)也是一位書法家,雅善各種書體,尤其擅長隸書。
唐代的書風極盛,書法家們燦若群星。數量眾多的唐代碑碣石刻,絕大多數都是這些書法家們的杰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顏真卿。顏真卿(709—785),因其官職和封號,又稱“顏平原”“顏太師”“顏魯公”。他擅長多種書體,參用篆書筆意寫楷書,筆力彌滿,端莊雄偉,氣勢森嚴,其行書遒勁郁勃,闊達自在,被譽為唐代書家中的集大成者,世稱“顏體”,對我國的書法藝術發展具有重大影響。《新唐書》本傳說他“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唐人稱贊他的書法:“如荊卿按劍,樊噲擁盾,金剛瞋目,力士揮拳。”顏真卿的傳世書跡甚多,流傳后世的碑刻、拓本、真跡作品大約有70多種。其碑刻如《大唐中興頌》《多寶塔感應碑》《麻姑山仙壇記》《李玄靖碑》《顏家廟碑》《顏勤禮碑》《離堆記》等,皆為歷代文人雅士所推崇和珍愛。顏真卿留下的這些碑帖書法真跡,表現了他在書法藝術上高超完美的境界,至今仍洋溢著強大的藝術生命力。
宋朝的碑碣石刻藝術,繼承了晉唐的遺風,文人墨客留下的碑帖甚多。著名文人和書法家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稱為宋四家,至今許多名勝古跡處,都留有他們的碑刻書跡。他們的書法各具風格,代表著北宋書壇的時尚,順應了書法藝術由楷體向行書演變的潮流。觀賞他們的碑刻書跡,能感悟到他們強烈的個性特色,領略到他們橫溢的才情,體會到他們的豪放與瀟灑,不由自主地發出贊嘆。宋人留在名勝處的刻石,有的是幾句詩文,有的只有只言片語,已不再像唐人那么莊重,摻入了更多的灑脫和隨意。習帖之風,日漸興盛,相比之下,碑刻某種意義上反而成了一種點綴和裝飾。這種風氣一直沿襲到元、明兩代。數百年間雖然書家輩出,如元朝的趙孟頫,明朝的吳中三家(祝枝山、文徵明、王寵)、徐渭、董其昌等人,皆負盛名,但他們流傳后世的大都是帖而不是碑。到了清代,這種風氣才有所改變,出現了碑帖結合、大放異彩的情形。清初的“揚州八怪”中,鄭燮、金農等人,以及后來的何紹基、趙之謙等人,走的都是碑帖結合的道路。

顏真卿像
中國的碑碣石刻藝術,遍布于山川名勝、宮苑寺廟、園林建筑之內,是刻在石頭上的漢文化,將歷史事跡、人文景觀、書法篆刻藝術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絢麗多彩,堪稱華夏文明中的一朵奇葩,不僅內容豐富,而且數量繁多。從內容上來說,有古人刻在石上的歷史文化的記載,有文人歌頌大好河山的詩文之作,有墨客的書法遺跡,有記述廟宇寺觀園林建筑的石刻碑文,更有古代帝王將相和官僚們用以歌功頌德炫耀政績的勒石樹碑;從形式上看,更是千姿百態,豐富多彩,有鐫刻在懸崖絕壁上的華章佳句,有名勝古跡處的牌坊石刻妙語楹聯,有雄峙在殿堂上的巨碑,有寺觀園林游廊間靈巧多姿的碣文,更有名聞遐邇的碑林,可謂蔚然大觀。它們不僅是傳播歷史文化的重要手段,更是珍貴的文物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