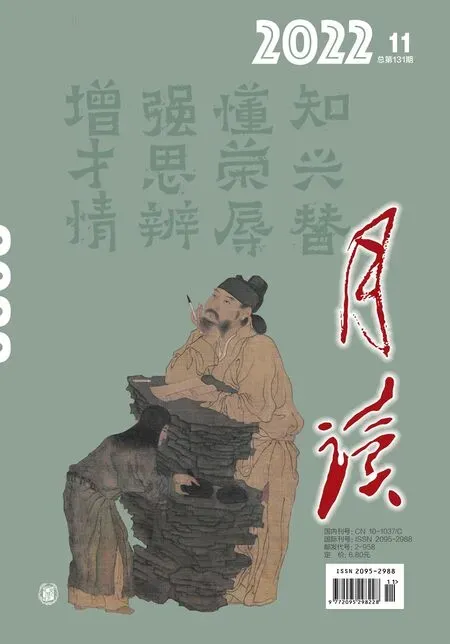讀《詩經》:做人的規矩
◎ 李 永

俗話說:“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這句出自《孟子·離婁》:“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意思是即使有離婁那樣明敏的視力,有公輸般那樣精巧的手藝,如果不使用圓規和曲尺,就不能準確地畫出方形和圓形。同樣,作為人特別是普通人,更需要做人的“規”和“矩”。《詩經》無疑為我們展示了做人的“規”和“矩”。
孔子可為證。他讓他的兒子伯魚學詩。他告訴伯魚:“不學詩,無以言。”過了一段時間,他又問:“你讀過《周南》《召南》嗎?”如果不讀,那就好像正對著墻壁站立,不能再向前行走了。不學詩,不會說話;不學詩,不能行走。而他讓弟子們學《詩》的解釋則更為詳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孔子所說絕非虛談,他積極推行詩教,源于他對《詩經》的整理,源于他對《詩經》的感悟。
但,詩經不是好讀的。一是生僻字較多,二是義項較為復雜,這就為理解《詩經》帶來了困難,難免讀著讀著就放棄。有的即使讀過,也是一帶而過,并沒有發現句子有什么特別的深意。等發現別人在引用《詩經》里的句子,并解釋得津津有味時,不免又對《詩經》充滿向往。“詩無達詁”,有的詩意不顯露,需要從幽隱中加以探索。這沒有一點閱歷和功力是很難做到的。正應了這句話:經典很難讀,一旦讀懂了,卻很難忘。“詩旨之部,從《左傳》所記當時士大夫之‘賦詩斷章’起,次《論語》《孟子》《禮記》及周秦諸子引《詩》所取義,下至《韓詩外傳》《新序》《說苑》及《兩漢書》各傳中之引《詩》語止,博采其說分系本詩之下,以考見古人‘以意逆志’‘告往知來’之法,俾詩學可以適用于人生。”(梁啟超《讀〈詩〉法》)《詩經》在“適用人生”之修身、齊家等方面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謹言慎行,辨識真偽
人總要說話,總要聽人說話。“人之為言,茍亦無信。”(《采苓》)“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巧言》)。不管說者是信口開河還是別有用心,都要用自己的頭腦思考辨別,“往來行言,心焉數之”(《巧言》),謠言止于智者,“豈弟君子,無信讒言”(《青蠅》)。而《賓之初筵》描寫的是酒席宴前人們“溫溫其恭”,還未喝醉時態度慎重又恭謙。一旦喝醉,就一反常態,亂我籩豆、大呼小叫、手舞足蹈、行為不檢,揭示的是“不醉反恥”的心態,提出“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另外還特別提醒不要做勸酒者,醉酒者之所以醉,勸酒者難逃其責。因勸酒致使醉酒者出現事故,勸酒者要承擔民事責任。這樣的案例時有耳聞。想想《詩經》時代酒席宴上的規矩,就是在今天依然有其現實意義。“人之齊圣,飲酒溫克”(《小宛》),“匪言勿言,匪由勿語”(《巧言》),很接地氣。“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可玷,不可為也。”(《抑》)意思是白玉上的污點還可以把它磨掉,但說話不謹慎而出錯,卻無可挽回。《論語》記載,孔子的弟子南容多次朗誦此句以告誡自己要謹言慎行,孔子就把侄女嫁給他做妻子。起碼,在孔子看來,一個謹言慎行的人是個可以托付的人,值得終身依靠。
二、友愛兄弟,宜爾室家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斯干》)家中兄弟,要相愛相親,不要虛情假意。“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癒。”(《角弓》)好兄弟即使有摩擦糾紛也不要相互怨恨,而應相互寬容多多包涵。“兄弟鬩于墻,外御其務。”(《常棣》)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常棣》)夫妻父子各相親就像琴瑟相協調。當然,最重要的不要忘了感恩。“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父母“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蓼莪》),恩德無極。懂得感恩,孝敬父母,學會包容是家庭和睦的不二法門。“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常棣》)也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家庭夢想。
三、職思其居,求福不回
《蟋蟀》描寫了時光飛逝但又提醒人們:要“職思其居”“職思其外”“職思其憂”,行樂不能放縱,要像“良士”那樣,時刻記著自己的職責,干好本職工作,同時也不能忘記自己的其他責任。要居安思危,時刻保持清醒,警惕安樂思想的侵蝕;要勤奮敏捷,積極進取。在人生追求的道路上,要分清追求的目標,什么是該追求的,什么是不值得追求的。“不忮不求,何用不藏”(《雄雉》),不嫉妒,不貪求。孔子當年曾用這兩句贊揚子路,說穿著破舊的棉袍與穿著狐裘皮袍的人站在一起,卻不感到羞恥的,大概只有子路。子路聽了,很高興,就終身誦之。“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旱麓》)君子求福,不違正道,該止則止。“綿蠻黃鳥,止于丘隅”(《綿蠻》),孔子讀之則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身后有余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就是該止不止的注腳。
四、有物有則,不失其馳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烝民》)萬事萬物,一定有它的法則。《烝民》這首詩就描寫了仲山甫明理識體、遵守法則、深得民心的輔佐者的典范。他儀表端莊,溫和善良;他日夜辛勞,從不懈怠;他不侮矜寡,不畏強暴;他修身其德,德高望重。結果一呼百應,“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及甫作誦,穆如清風”。孔子說:“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孟子·告子上》)在那個時代,即使駕車,也有其規則:“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車攻》)。《孟子·滕文公下》記載,從前趙簡子派王良為他寵幸的小臣奚駕車,一整天捕不到一只鳥。奚就跟趙簡子匯報說:“王良是天下最拙劣的車手。”王良知道后,說:“請讓我們再去一次。”經過強求之后才獲準予,結果一個早上就捕到了十只。奚很高興,就跟趙簡子匯報說:“王良是天下最優秀的車手。”趙簡子準備讓王良專門給奚駕車。王良不同意,說:“我替他按規范駕車,一整天捕不到一只;不按照規范駕車,一個早上就捕到了十只。《詩經》里說‘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習慣替小人駕車,請不要任命。”車手尚且懂得規范,羞于與不懂規則、破壞規則的人合作,即使合作得到的鳥獸多得像山丘一樣,“如枉道而從彼,何也?”(《孟子·滕文公下》)
“敬慎威儀”是規則,“彼交匪敖”是規則,“終溫且惠,淑慎其身”是規則,“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是規則,“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也是規則。知難行亦難。只要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執著和堅守,只要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耐心和精進,定能展示人格的魅力、人性的光輝。
近讀樂黛云先生的文章《我的公公湯用彤》,湯老先生寬容溫厚學貫中西,對兒媳關懷備至。當他得知,兒媳上大學時連《詩經》也沒讀過一遍時,表現少有的驚訝,連說:“你,《詩經》都沒讀過一遍嗎?連《詩經》中常被引用的話都不知道,還算是中文系畢業生嗎?”這讓樂先生慚愧萬分,從此開始發奮背誦《詩經》。多年后,樂先生認識到:“作為一個中國學者,做什么學問都要有中國文化的根基就是從湯老的教訓開始的。”湯老的良苦用心可見一斑。其實,做人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