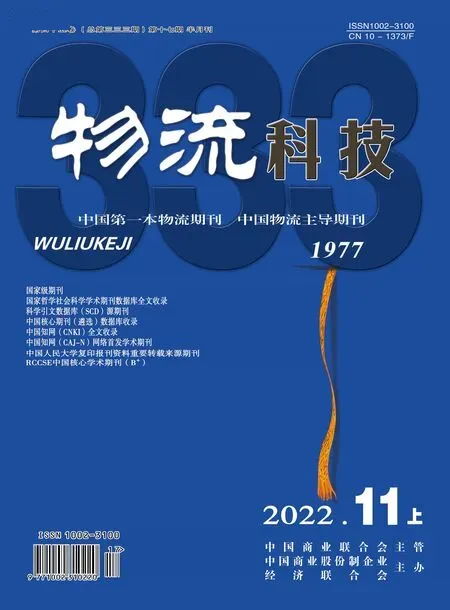中國旅游城市航線網絡特征分析
李國棟,吳凱偉 (中國民航大學,天津 300300)
近年來,我國旅游業快速發展,旅游消費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的占比超過12%,對民航和鐵路客運業的貢獻率超過80%。旅游業已成為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強勁推動力。隨著交通設施的不斷改善,以機場為節點構建的立體、高速交通網絡,改變了游客的出行方式、旅游行為以及時空關系,從而使航空成為現代旅游的基本交通方式。在旅游市場規模急速擴張、旅游方式多樣化的趨勢下,旅游空間網絡與航空網絡的合理銜接,已經成為實現旅游業與航空運輸業共同發展的重要基礎。
國內外學者對于旅游與航空運輸的研究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為入境旅游與航空運輸的關系,如吳晉峰等[1]發現中國航空國際網絡對入境旅游具有決定性影響;王兆峰[2]對我國西南地區的入境旅游流與航空運輸網絡協同發展的規律進行了研究,發現入境旅游流與航空客流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航空客流對入境旅游具有促進作用;Khan S R[3]研究發現航空運輸對于國際出入境旅游相較于其他運輸方式具有顯著影響。另一方面為區域旅游景點的航空可達性研究,如Hao J[4]通過對中國云南地區的旅游城市與航線網絡研究,發現為了旅游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旅游城市應重視航線網絡的建設,將航空網絡與陸運網絡協調發展;楊春華[5]從航空和鐵路兩個角度對比分析城市交通通達水平,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類型的旅游城市提出了相應的發展對策。綜上所述,現有的研究大多都在研究入境旅游或區域旅游的航線網絡結構變化,沒有相關論文對國內旅游城市的整體航線網絡構建分析,本文以社會網絡分析法對國內旅游城市的航線網絡進行整體分析,以期為國內旅游業與航空運輸協同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1 數據來源及研究對象
本文采用的各項基礎數據,如城市劃分級別及數量、城市旅游收入、城市旅游人數、民航航段航班數據、A 級景區數量等,來源于2015—2018 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6]、《中國民航統計年鑒》、《中國旅游統計年鑒》,各省、市統計局網站和旅游局網站上公布的相關數據,以及各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告》內容;結合中國旅游局公布的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名錄,總計選出186 個地級市作為本文的航線網絡構建分析,本文將186 個旅游城市按照中國空管局劃分的七大區域進行劃分。

表1 旅游城市地區分布
2 研究方法
2.1 構建網絡
首先,構建旅游城市航線網絡,航線網絡是由點集V (G )和邊集E (G )組成,V (G )= {0,i=1,2,3,…,n },E (G )= {eij,ij=1,2,3,…,n },點集V(G )是由所選擇的旅游城市組成,邊集E(G )是由通航城市間的直飛航線組成。此時形成了以186 個城市為節點,以有無直達航班為有向邊的中國旅游流網絡,然后用Ucinet 軟件基于復雜網絡分析法[7]對其網絡結構進行測算。
2.2 網絡評價指標
(1) 網絡密度
網絡密度是指網絡實際擁有的關系數目與理論上可能擁有的最大關系數目之比,計算公式為:

其中:m 表示航線網絡中實際有的邊數,n 表示此網絡中存在的總節點數。網絡密度的取值范圍是0~1,網絡密度越大,表明機場城市之間的聯系越密切,航空網絡功能越完善。
(2) 程度中心度與中心勢[6]
程度中心度是通過機場城市i 與之相連的城市數進行測量的,如果某機場城市具有最高的度數,則該機場城市居于網絡重要的中心地位。機場城市的旅游流量越大,程度中心性指數越高,表明其在航空網絡中有最多關聯,最具核心競爭力。
相應的程度中心勢則通過各城市中心度的差值與同等規模網絡最大差值的比較反映網絡整體的中心趨勢,如果網絡的中心勢越大,則說明航空網絡越趨向于樞紐機場城市為中心集中。但是程度中心勢越大,表明中心地位集中在少數城市,整體的均衡性和穩定性就越差。
(3) 聚類指數
聚類系數是描述網絡集團化程度的指標,是描述網絡性質的一個重要指標,它是指網絡中一個點的鄰接點之間相互連接的程度。網絡中每個節點的聚類指數計算公式為:

整個網絡的聚類系數C 就是所有節點i 的聚類系數Ci的平均值,C 值越大整個網絡的局部連接就越明顯。
3 旅游城市航線網絡結構
3.1 旅游城市在地理和航線網絡上均呈現出東密西疏的特征
從旅游城市空間布局的角度看,其中中南地區擁有56 個,華東地區擁有54 個,華北地區19 個,熱門的旅游城市多位于東部地區,如京津冀地區、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而擁有廣泛土地資源的西部地區旅游城市分布較少。
在航線網絡分布方面,由圖1 可以看出,2015—2018 年中國旅游城市的航線數量快速增長,由2015 年的1 154 條增長到2018 年的1 646 條。整體航線網絡密度也隨著航線數量增長而快速增長,但是因為有86 個旅游城市正在建設或沒有機場,并且大部分偏遠地區機場的航線數量較少,導致旅游城市航線網絡密度雖然快速增長,但整體仍然密度偏低,航空網絡結構較為簡單。

圖1 2015-2018 年旅游城市航線網絡
由圖2 可以看出,旅游城市的航線網絡主要集中在華北、華東、中南和西南地區,四個區域擁有的航線占到了2018 年旅游城市航線網絡的82.6%,而西北和新疆所在的西部地區的航線占比僅為7.6%。擁有廣泛旅游資源的新疆和西北地區,航線網絡卻極為稀疏,航空連通性有待進一步提高。

圖2 2018 年各大區之間航線統計

表2 2018 年各區域間連接的航線條數
3.2 航線網絡呈現出區外大循環,區內小循環的格局
從大區之間的通航情況看,東北地區的航線網絡主要連接華北和華東,而西部地區的連接較少,對于東北地區前往西部地區旅游的旅客來說,出行更加不便利。而華北地區的航線網絡主要集中在華北和華東兩個地區,網絡集團化效應明顯,形成了區內小循環的網絡布局。華東地區的航線網絡較為均衡,和其他6 個區域的連接較為緊密,并且區內航線網絡相當緊密,得益于長江三角洲優秀的航線網絡布局。中南地區的航線網絡具有明顯的區內循環特征,航線網絡集中于廣州、深圳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并且和其他大區直接連接緊密。西南地區的航線網絡于華東和中南地區連接較緊密,雖然華東到西南地區的直達航線較少,但西南地區到華東地區的直達航線在各區之間最多,并且西南地區區內循環特性也很明顯,西南地區直達新疆地區的航線數量在各區之間也最多。新疆地區通往其他各大區之間的直達航線都較少,而且新疆的大部分地區都通過烏魯木齊進行中轉,再飛往其他城市,形成了區內的小循環格局。旅游城市中心性特征如表3 所示。

表3 旅游城市中心性特征
從聚類系數的角度看,2015—2018 年全國旅游城市的聚集系數不斷提升,說明旅游城市網絡之間的連接偏向于大量節點內部之間的連接,并且多區域樞紐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另外,華北、華東、西南、中南四個區域因為京津冀機場群、長三角機場群、粵港澳機場群和成渝機場群的存在,聚類系數處于相對較高的水平(如表4 所示),并且在各自的地區內部航線網絡連接緊密,通過樞紐機場與區域外部其他機場相連接,不同區域相對落后的城市之間直接相連的機會較小。如圖3 和圖4 所示,華北地區的旅游城市網絡形成以北京、天津為樞紐城市向國內其他機場城市輻射的軸-輻式航線網絡結構,華東地區的旅游城市則以上海、杭州和南京為樞紐城市向國內其他機場城市輻射。

圖3 華北地區區內航線網絡

圖4 華東地區區內航線網絡

表4 2018 年7 大區聚類系數
3.3 旅游城市航線網絡穩定性增強,以成都、西安等為代表的旅游城市的集散能力增強
從表5 可看出,2015—2018 年旅游城市連通的節點不斷增多,不斷有新機場投入運營,其中2016 年營口機場、三明機場和日照機場通航,2017 年承德機場和上饒機場通航,新航點的投入增加了網絡的覆蓋度,并且可以提高連通性。
從程度中心勢來看,2015—2018 年網絡的總體中心勢都在85%以上,表明中國旅游城市的航線網絡表現為中樞式航線網絡。從表5 可以看出,2015—2018 年程度中心度排名前十的城市中,北京市得分一直在90 分左右,以絕對的優勢成為全國旅游城市的樞紐,上海、廣州、深圳分別作為華東和中南地區的樞紐也有很高的得分,并且程度中心度也在逐年升高,而熱門旅游城市如成都、西安、重慶的程度中心度得分也在不斷提高,與其他旅游城市直接的聯系也更加緊密,在旅游城市網絡中也有了更重要的地位,而一些省會城市如杭州、南京、鄭州也在區域網絡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表5 2015—2018 年程度中心度排名前十的城市
旅游城市的程度中心度得分總體在增加,減輕了大型旅游樞紐城市如北京等的負擔,同時也增加了航線網絡的密集程度。此外,旅游城市的程度中心勢也逐年降低,表現為從2015 年的89.9%降低到了2018 年的85.6%,大型旅游樞紐城市的中心地位得以降低,整體的均衡性和穩定性變高。
4 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對中國186 個旅游城市的地理位置和航線網絡進行分析,得到以下結論:中國的旅游城市航線網絡整體密度偏低,旅游城市與航線網絡大部分聚集在東部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而西部地區航線網絡密度偏低。在各大區內部,旅游城市通過與樞紐旅游城市連接形成區內小循環,在各大區之間,通過樞紐與次樞紐旅游城市連接實現整個旅游城市航線網絡連接。另外,旅游城市的航線網絡穩定性正在不斷增強,新型旅游城市如西安、重慶等在航線網絡中的地位不斷提升,與其他非樞紐城市的連接更加緊密,減少了大型樞紐如北京、上海的負擔。
基于以上結論,中國旅游城市的航線網絡建設應更加注重西部地區的發展,挖掘西部地區優秀的旅游城市并完善航線網絡。同時,加強各大區內次樞紐旅游城市的航線網絡建設,以緩解樞紐城市的航線網絡壓力,增強航線網絡的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