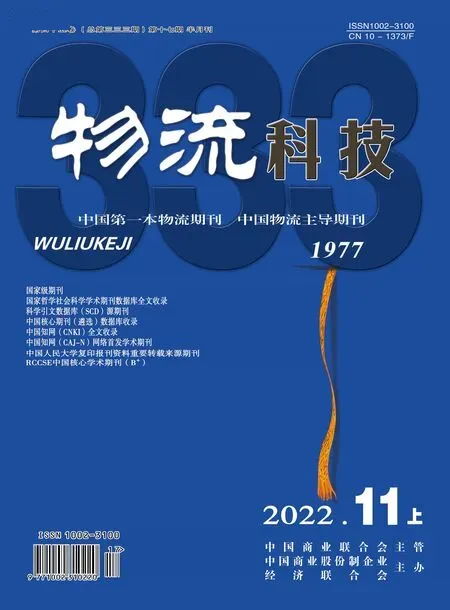數字普惠金融縮小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實證研究
——基于農民就業中介效應的分析
錢柳燁,石淑華 (江蘇師范大學 商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質量的健康發展,城鎮居民的生活質量與收入水平顯著提升。但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城鄉二元經濟體制特點越來越明顯。雖然發達地區的蓬勃發展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資源配置失衡、城鄉收入差距較大的問題也隨之凸顯,長此以往必然會影響經濟發展甚至社會安定。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較大的原因之一是我國農村金融資源相比于城市來說較為匱乏,金融服務普及程度較低,農民的理財、融資等業務需求很難被滿足。而城鎮居民金融服務水平和可獲得性明顯高于農村居民,城鎮居民有更多機會獲取金融服務和得到更多資本投資并從中獲利,這從一定程度上導致城鄉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數字普惠金融在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涌現和應用的背景下,在降低金融服務成本的同時也提升了農民獲得金融服務的效率,并更好地為欠發達地區貧困弱勢群體提供更為有效與便捷的金融支持與幫助,有利于農民更好地利用金融資源來增收,從而減少城鄉收入差距。
1 文獻綜述
目前,學者們從多個角度分析了數字普惠金融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有學者從門檻效應這一角度分析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Ouma, et al[1]提出智能手機的便利性和廣泛性擴大了數字普惠金融的服務范圍,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獲得家庭儲蓄的可能性和額度。Gabor and Brooks[2]指出在當今金融科技時代,數字普惠金融極大降低了低收入人群獲得金融服務的難度。周利[3]主要通過分解城鄉收入并進行實證研究,得出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降低門檻效應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結論。
金融包容性增長效應視角上,Ozili[4]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在保障用戶的支付安全的同時,有助于用戶精準快速決策,體現了數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和穩定性。張勛[5]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顯著地促進中國經濟的包容性增長,特別是通過促進農民的創業行為進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減貧效應理論方面,劉金全和畢振豫[6]通過實證分析指出數字普惠金融會促進經濟水平的提高減緩貧困,從而實現城鄉收入差距的減小。馬彧菲和杜朝運[7]、黃倩[8]通過實證分析得出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有利于貧困群體,改善了居民收入不均的情況。朱一鳴和王偉[9]通過實證研究分層比較了數字普惠金融對不同收入群體的減貧效應,研究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的減貧增收存在顯著的異質性。
涓滴效應方面,劉自強、張天[10]指出數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對中小企業的服務,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并促進中心城市對周邊農民增收的涓滴效應。陳嘯、陳鑫[11]通過空間計量模型探討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涓滴效應。易揚和王磊[12]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不僅有利于縮小本地收入差距,也對臨近地區收入差距也有抑制效應,具有空間溢出效應。
綜上所述,學術界對數字普惠金融和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進行較為充分的研究。然而,大部分文獻集中在兩者之間的直接關系,缺乏對間接關系的研究分析,而從就業這一視角探討兩者的影響研究就更少。因此,本文在已有文獻的基礎上分析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并基于就業這一中介變量進一步分析兩者的關系。
2 傳導機制
為實現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縮小城鄉差距是不可回避的問題。而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夠通過技術進步來增加農民的就業崗位、優化農民的就業結構以及提升農民的就業質量這三方面促進農民就業實現增收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首先,依托數字技術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能創造新的就業崗位,使農民能夠在當地或轉向城市就業,提升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黃海清和魏航[13]指出數字經濟產生的廣化效應可以增加創業活躍度刺激創業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以及高額報酬,這使農民提升就業動力與工資薪金。我國第三方線上支付與交易平臺的出現以及電子商務的興起,從多維度上改變了我國的商業模式,尤其是農民也可以利用移動支付完成線上各項交易。這為貧困地區的弱勢群體提供了新的商業機會,增加了農村群體參與新的商業模式的可能性。新的商業模式創造了大量新的用工需求,使農民也能進入這種就業面廣、機制靈活的就業市場。因此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增加就業總體規模來提升農民就業率,從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其次,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有利于優化農民就業結構,提高農民的勞動報酬,從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數字技術的發展提高了對中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而降低勞動密集型企業普通崗位的需求,這會對農民這些低技能勞動力帶來就業轉型壓力,讓原處于第二產業的農民工轉向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等低技能的新型服務業,加速第三產業就業服務化趨勢。另外,一般認為農業部門的邊際收益低于非農部門,且農民因為知識技能偏低、就業信息匱乏等原因較難向非農部門轉移。Acemoglu and Restrepo[14]指出在技術背景下,長期內技能偏低者可以通過自主學習提高個人的技能水平,從而提升就業率與工資薪金。數字普惠金融有效緩解了農民在時空上的限制,互聯網技術使得大量信息可以流通,有助于緩解農村地區信息不對稱問題。那些新型服務業又具有靈活就業的特點,衍生出了許多非農崗位,拓寬了農民在第三產業上的職業選擇,整體勞動報酬有所提高。
再次,數字普惠金融能夠提升農民的就業質量,從而提升農民的收入。郭晴和孟世超[15]構建了就業質量衡量機制,并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相較于其他群體數字普惠金融更能顯著提升農民的小時工資率以及工作自主性,促進了農民增收。數字普惠金融的開展降低了資本流通的成本,使得金融服務的效率與針對性都有所提高,實現了經濟增長,有助于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和就業質量,優化整體就業環境。經濟增長可以帶動當地特色的鄉村產業的發展,促進不發達地區實體經濟的增長,提高農村地區的整體經濟水平,衍生出更多的非農就業崗位,解決不發達地區貧困人群的就業問題。因此,數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農民個人就業質量,從而實現農民增收,減小城鄉收入差距。
根據上述有關數字普惠金融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機制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1: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夠通過增加農村居民的收入從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假設2:農民就業機會在數字普惠金融抑制城鄉收入差距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中介作用。
3 模型設定與變量說明
3.1 模型設定
首先,本文綜合眾多學者們關于數字普惠金融和城鄉收入差距文獻的參考,以及結合對相關理論的思考和本文的研究思路,構建如下基本回歸計量模型:

公式(1) 中的i 和t 分別表示第i 個省份(直轄市) 和第t 年。被解釋變量theilit代表城鄉收入差距,解釋變量indexit是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而Ζjt是第j 個控制變量,共有4 個控制變量,β0是截距項,β1是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的系數,λj是第j 個控制變量的系數,εit則是隨機擾動項。
其次,根據前文的機制分析,本文選取農民就業機會作為中介變量進一步考察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本文借鑒Boron 和Kenny[16]、溫忠麟等[17]學者的研究,構建如下以農民就業為中介變量的中介效應模型:

3.2 變量說明
(1) 被解釋變量。城鄉收入差距。參考以往學者的研究,本文采用納入人口加權因素的泰爾指數,泰爾指數越小代表城鄉收入差距越小,相關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泰爾指數的計算公式如下:

(2) 解釋變量。數字普惠金融。本文選擇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郭峰、王靖一等[18]發布的2011~2019 年省級層面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作為核心解釋變量。本文在原始數據的基礎縮小100 倍,使其符合其他數據的大小便于計量。
(3) 控制變量。城鎮化率(urban )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來表示。田麗[19]研究發現,城鎮化有利于農村人均收入的提高。該數值越大,表示一省有越多的人口生活在城市。產業結構水平(str u )由第二產業以及第三產業增加值之和占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表示。財政支出占比(go v )控制政府干預的影響,是通過政府一般預算支出比上地區生產總值來衡量。教育發展水平(ed u ),用各省教育支出與財政支出之比來表示所在地區教育水平。
(4) 中介變量。農民就業機會(job )。本文用農村私營企業和個體就業人員人數之和作為衡量農民就業的指標,為了使指標更符合其他數據的計量大小,本文采用對原數值取對數的方式對該指標進行縮放。
3.3 描述統計
本文選取的是2011~2019 年我國31 個省(直轄市) 的面板數據,除前面列舉的變量外,加入表示城鄉居民收入比ga( )p 用于回歸之后的穩健性分析,先對涉及到的變量進行描述統計分析,相關結果匯總如表1 所示。

表1 全國樣本的描述性統計
4 實證檢驗與分析
4.1 基準回歸分析
本文首先進行Hausman 檢驗,結果表明應選擇固定效應模型而非隨機效應模型。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并通過逐步添加控制變量的方法對全樣本數據進行回歸。
從主要核心解釋變量看,表2 中第一列數字普惠金融的系數是-0.1230,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這表示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會抑制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同時,第1 列到第5 列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系數一直為負。基準回歸的結果驗證了本文的研究假設1,即數字普惠金融對減小城鄉收入差距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表2 固定效應模型下的全國層面回歸結果
從其他控制變量看,城鎮化率、財政支出占比、教育發展水平的系數都為負,這表明三者在一定程度上都能顯著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在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夠向城市轉移,并在城鎮尋找工作崗位,從而減小城鄉收入差距;近年來政府通過大量財政支持來緩解城鄉差距,這說明財政支持的增加會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教育發展水平的提高,使城鄉居民能夠提升文化素養和專業技能,使其也能參與工作要求較高的崗位,從而提高收入水平,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而產業結構的系數為正,這說明二、三產業結構比重的提高加大了城鄉收入差距,可能的原因是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仍然依托于第一產業,而城鎮居民主要從事的非農部門工作的勞動報酬高于農民從事的農業部門的工資。
4.2 中介效應分析
本文選取農民就業機會作為中介變量,借助Stata 軟件采用中介效應模型驗證農民就業機會在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中所起的作用,然后采用Sobel 法和Bootstrap 法進行檢驗。
由表3 回歸結果可知,中介效應模型中總效應估計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且其值為-0.00810,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總效應為負。同時,表3 也顯示,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直接效應為負向關系,其估計系數為-0.0060。另外,通過計算可知農民就業率在抑制城鄉收入差距過大過程中的中介效應為-0.0016,表示數字普惠金融每提高1 個單位,將通過農民就業率的增加間接讓城鄉收入差距下降0.0016 個單位。這說明數字普惠金融在發展過程會促進農民就業,從而達到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效果。進一步考察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重,由表3 可知其估計占比為21.04%,也就是說,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效應有21.04%的比例是通過增加農民就業機會這一中介機制實現的。

表3 農民就業機會對于數字普惠金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中介效應檢驗
為了使中介效應更精準,本文通過Sobel 檢驗發現農民就業率的中介效應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再運用Bootstrap 檢驗結果顯示其間接效應系數為-0.0016,這與前文Sobel 檢驗的結果一致,因此通過了中介效應顯著的穩健性檢驗。中介效應的回歸結果驗證了本文的研究假設2,即農民就業機會在數字普惠金融抑制城鄉收入差距中起著中介作用。
4.3 穩健性分析
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采用城鎮居民可分配收入與農民可分配收入的比值ga( )p 代替前文的泰爾指數這一指標進行回歸,再次論證數字普惠金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作用(如表4 所示)。從核心變量來看,第1 列到第5 列的系數估計值均為負,這說明數字普惠金融可以較顯著地促進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減小。回歸結果顯示,在改變了被解釋變量的衡量指標之后,主要解釋變量的系數值和符號相較于基準回歸都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說明模型通過了穩健性檢驗。

表4 更換被解釋變量指標為城鄉收入比的回歸結果
在改變了被解釋變量的計算指標后,再次進行中介效應檢驗(如表5 所示)。中介效應模型中總效應估計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且其值為-0.1110,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總效應為負。另外表5 顯示,兩者的直接效應也呈負向關系,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直接效應可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農民就業率在數字普惠金融抑制城鄉收入差距過大過程中的中介效應為-0.0181。進一步考察可知,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效應有16.22%的比例是通過增加農民就業機會這一中介機制實現的,這說明數字普惠金融在發展過程中具有促進農民就業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效果。

表5 更換被解釋變量中介效應檢驗
5 結束語
5.1 研究結論
首先,從總體的基準固定效應回歸結果可知,數字普惠金融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有顯著作用。數字普惠金融憑借其數字技術優勢有助于緩解城鄉收入差距。其次,從中介效應的分析結果可知,數字普惠金融可通過提升農民就業這一中介變量間接改善城鄉收入差距。數字普惠金融能通過各種作用機制促進農民就業,有助于提高農民收入,從而減少城鄉收入差距。
5.2 啟 示
首先,完善數字普惠金融系統,充分利用數字普惠減少城鄉收入差距。由于農村地區缺少完備的征信系統,弱勢群體缺少有效的信用信息與記錄。因此,需要利用數字技術來建立覆蓋面更廣泛以及更規范完備的征信系統。另外,由于數字普惠金融能夠更好地服務于弱勢群體,但在此過程中,要重視風險控制的強化,避免用戶的信息泄露,完善相關的法律。
其次,重視數字普惠金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中就業的中介作用。抓住數字技術所帶來的機遇,持續推動農民就業結構的改善,進一步完善落實農民就業政策,切實擴大農民在二、三產業的就業吸納能力。另外,完善農民就業的保障體系以提升農民就業質量。在推進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過程中,要重視各個業務維度的相互配合,推動農村居民非農就業以及就業結構的改善與就業質量的提高,從而達到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