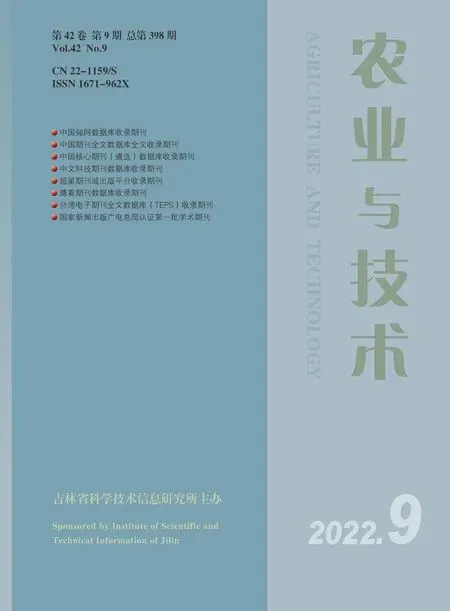土壤中鉛污染來源及其危害綜述
王思遠 楊樹俊 張賀 孫東年 劉耕苑
(江蘇省地質工程勘察院,江蘇 南京 210012)
近年來,人口的飛速增長、工業的迅速發展、農藥與化肥的大量使用、采礦行業對礦產資源的開采致使降塵、大氣降水及污水中大量的重金屬污染物進入農田土壤生態環境,土壤的重金屬污染與日俱增。據不完全統計,在過去的50a中,由于工業生產的大量開展,全球由人類排放到環境中的重金屬污染物數量巨大,其中,鎘為2.2萬t、銅為93.9萬t、鉛為78.3萬t、鋅為13.5萬t,這些重金屬大多隨著灌溉、粉塵、降水等進入土壤中[1]。進入土壤中的重金屬大部分不會被土壤微生物分解,而是長期積累,達到一定量后,最終通過生物濃縮作用,通過食物鏈積累在食物中,威脅人類健康。因此,土壤重金屬污染領域的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和其他污染物一樣,已成為全球面臨的重大環境問題,并成為環境和土壤科學家研究的熱點方向。
1 土壤中鉛污染的現狀
現在,全世界平均每年有大約500萬t的鉛蓄電池被報廢。而這造成了在過去的50a里,進入環境的鉛量大約有7.83×105t,其中大部分進入了土壤,從而對土壤造成了重金屬鉛污染[2]。全國24個省(市)郊外320的重點地區、污染地區灌溉、工業污染礦區等經濟快速發展領域,重金屬超過允許標準值農產品的產量和種植面積超過總量和總面積的80%以上,其中鉛污染所占比例相對較高[3]。根據統計數據,蔬菜、谷物、水果、肉類、畜產品等的含鉛超標率分別為蔬菜38.6%、谷物28.8%、水果27.6%、肉類41.9%、畜產品71.1%。根據前期研究,沈陽市環境中鉛暴露非常普遍,城市土壤中總鉛含量為26~2910mg·kg-1,說明污染程度較高。
鉛不僅污染城市環境,隨著工業的發展和農藥化肥的大量使用,農業生產中鉛污染的風險也在加大。根據前人的研究,對廣州市郊某蔬菜生產基地生產的部分蔬菜樣品進行檢測,評估蔬菜的污染程度及其食用健康風險。通過對大量蔬菜樣本的檢測結果進行分析,得出平均含量鉛為0.08mg·kg-1。超過《農產品安全質量 無公害蔬菜安全要求》中鉛含量限定值0.2mg·kg-1的比例約占總量的12.9%。這證明農地的土壤有相當大的比例被鉛污染。
2 重金屬鉛污染的來源
2.1 鉛的開采、冶煉和精煉
金屬鉛的物理、化學性質,如延展性、耐腐蝕性等,在古代就被人們所熟知。鉛礦產的開采、冶煉、精煉過程對周圍的大氣和土壤有很大的影響。在此過程中排出的重金屬粒子尺寸為0.001~100μm,煙氣粒子尺寸為0.01~2.00μm,在冶煉廠周圍的表土中,鉛含量可達1000mg·kg-1。這些鉛經過風吹雨淋,流入周邊環境和地下水,使污染面積進一步擴大。鉛礦主要是伴生礦,在開采和冶煉過程中,不僅會造成鉛元素的污染,由于其伴生其他元素的存在,還會造成重金屬和鉛元素的復合污染,造成農業的進一步減產。
2.2 工業“三廢”
生產、使用鉛和鉛化合物的工廠排出的廢氣、廢水、廢渣污染環境,進而污染食物,對人類造成危害。特殊的微生物,可將環境中的無機鉛轉化為有機鉛,從而增加了鉛在環境中的毒性。世界上很多地方,特別是工業發達的地區,大氣中的鉛含量極高。其中,歐洲的大氣鉛為0.055×10-6~0.34×10-6g·m-3,日本的平均值為0.2×10-6g·m-3,1980年中國北京的平均值為0.56×10-6g·m-3。我國部分地區土壤鉛含量調查結果顯示,北京為18.78mg·kg-1、重慶為22.2mg·kg-1、南京為24.8mg·kg-1、上海為23.0mg·kg-1、華南為26.47mg·kg-1、長江三峽庫區為20.51mg·kg-1。
2.3 蓄電池
18世紀50年代末,法國物理學家加斯頓·普蘭特(Gaston Plante)發現,將氧化鉛和鉛金屬電極浸泡在硫酸電解液中會產生電能,之后可以反復充電。從那時起,技術逐漸成熟,鉛酸電池于1889年實現商用化。電池市場隨著汽車的發展在20世紀迅速發展,最終消耗了世界約75%的鉛產量。鉛酸蓄電池用于汽車的啟動、照明、點火。如果沒有安全有效的回收鉛酸電池的措施,就會浪費資源,污染環境。同時,鉛酸蓄電池的隨意丟棄,不僅造成土壤污染,同時也造成周圍水體的污染。
2.4 汽油添加劑
四乙基鉛作為高壓引擎高溫運轉時的爆震聲問題的汽油添加劑被使用,因此廢氣中含有大量的鉛,成為公路干線附近鉛污染的主要原因。四乙基鉛隨著汽車工業的發展,產量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達到頂峰。其對環境的毒性是無機鉛的100倍。目前,隨著經濟的發展,汽車成為了重要的交通工具,私人汽車的數量增加,進一步增大了汽油使用量,周邊環境污染嚴重,另外,隨著汽車的普及,汽油的燃燒,使鉛污染的范圍也擴展到了城市郊區和農村地區。
2.5 含鉛肥料
隨著礦產冶煉的發展,將礦產廢料應用于肥料生產中具有重要的意義,且符合綠色發展的要求。然而,以礦物為基礎輔料的磷肥中含有多種有害重金屬元素,其中以鉻、鉛、砷的含量最高。如果磷肥在農業生產中過量施用,土壤中就會積累重金屬,達到一定量就會危害農作物,并通過食物鏈威脅人類健康。從磷肥帶入土壤中的鉛污染物具有多種形態,都會不同程度地危害農業生產。除了磷肥,其他含鉛礦物肥料的施用均會引起重金屬在土壤中積累。
2.6 污泥、城市垃圾的農業利用
工業污泥或城市道路污泥中會含有大量的鉛,當這些污泥被用于農業肥料施入土壤中時,就會引起土壤中鉛含量超標,從而產生污染。城市垃圾中也會有鉛污染物,當大量城市垃圾經過處理以后,雖然其中鉛含量會顯著降低,但長期施用后也會造成土壤重金屬鉛超標,進而隨著植物吸收和土壤流失造成周邊環境污染及加大對人體健康危害的風險。
3 土壤中鉛的存在形態及植物對其吸收作用
土壤中的鉛主要以Pb(OH)2、PbCO3和PbSO4等固體形式存在,絕大多數的鉛鹽均是難溶或不溶于水的,在土壤溶液中的水溶性鉛含量很低。比較華北石灰性土壤對幾種元素的吸附強弱順序為Pb>Hg>Cd>As>Cr[4]。并且土壤有機質對鉛具有絡合作用。土壤有機質的-SH、-NH2基團能與鉛離子可形成穩定的絡合物;另外,土壤粘土礦物對鉛也具有吸附作用,粘土礦物的陽離子交換官能團可對鉛離子進行交換性吸附。鉛離子進入土壤中,可進一步進入水合氧化物的配位殼,直接通過共價鍵或配位鍵結合于固體表面。因此,鉛元素進入土壤中大部分被吸附固持,以固定態形式存在。但在特定的酸堿及生物的作用下,又可被植物吸收,從而進入植物體,不同作物對鉛的積累不同,研究表明,作物對鉛的耐性依次為小麥>水稻>大豆[5]。不同種類或不同基因型的植物吸收鉛的能力也不同。不同種類的作物,生長期長的作物含鉛量高于生長期短的作物含鉛量,研究表明,雜交晚稻籽粒對鉛的富集能力比早稻強,在同一生長期,作物不同部位對鉛的吸收表現不同的效果,一般情況下,植物地下部分對鉛的積累大于地上部分[6]。
4 土壤中鉛的生物可給性及其對人體的健康風險
近年來,國內外大量研究證明,風險評估為環境管理的重要決策提供了支持。生物有效性是評估土壤污染物是否直接進入人體的重要參數。Ruby等在1992年就已經關注并報道了鉛的生物有效性[7]。研究鉛的生物利用率已經成為世界各地環境科學家關注的焦點[8]。研究土壤中鉛的生物有效性的常用測試方法主要包括生物體內和體外[9,10]。近年來,根據模擬試驗,隨著生物體外試驗方法的成熟,科學家們確立了基于體外試驗的研究方法,如簡單生物利用度提取法(SBET)、生理學原理提取法(PBET)、質量平衡及再生土壤法(MB&SR)、羅德里格斯體外腸胃法(IVG)、荷蘭國立公共衛生環境研究所法(RIVM)等。
生理學原理提取法(PBET,Physiologically Based Extraction Test)最早由Ruby等提出,通過添加胃蛋白酶和各種有機酸來模擬動物的胃,通過添加膽汁和胰腺酶來模擬小腸。與化學提取相比,更接近人體實際腸胃的生理條件[9]。用這種方法測定的土壤中鉛的生物有效性與室內測試結果顯示出良好的相關性。中國研究人員利用這種方法研究了土壤中鉛對人體的生物有效性[7,11,12]。
簡化的生物有效性提取試驗(SBET,Simplified Bioavailability Extraction Test),Medlin等為了研究土壤中鉛的生物有效性,開發了SBET(Simplified Bioavailability Extraction Test)方法[13]。Wang等利用該方法研究了12個土壤樣本中多種重金屬的生物有效性,發現鉛的生物有效性最高,達711%[14]。崔巖山教授等利用PBET、SBET、IVG3體外法,對浙江省上虞市4種受污染土壤中鉛的生物有效性進行了比較研究。這3種方法是模擬腸胃液中鉛的生物利用度差異性的方法。在胃液階段,SBET法和IVG法分別測得了鉛利用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在小腸階段,不添加食物后,IVG方法獲得最大值,而添加食物后的IVG方法獲得最小值[8]。
鉛元素在環境中不僅會降低農作物的產量和質量,還可通過食物鏈,在生態鏈上積累,影響動物和人類的健康[15]。研究發現,在德國鉛鋅冶煉廠周邊5km范圍內放牧的馬和牛都會產生鉛中毒。這些動物在中毒后,身體變得消瘦、關節腫痛,部分還出現喉返神經麻痹、呼吸急促等癥狀。中國學者研究發現,中國鱟的卵徑發育的大小,隨著水中鉛離子濃度的增加而變小,而在成胎后,胚胎的孵化率降低。當鉛離子濃度增加到1.6mg·L-1時,致畸性達到50%。
在日常生活中,人體通過呼吸道、消化道、皮膚吸收鉛,但進入呼吸道的鉛約有20%~40%留在體內。空氣的厚度為1μg·m-3血管中的鉛濃度為1~2μg·dL-1。無論攝入途徑如何,兒童對鉛化合物的敏感性都高于成人。有數據顯示,兒童攝入鉛化合物的比例高達50%,是成人的5倍。鉛嚴重影響幼兒的智力發展,由Peter Baghurst領導的澳大利亞研究人員發現,初期血鉛在10~30μg·dL-1的7歲兒童,智力比血鉛含量低的同齡兒童低5%。另外,長期接觸鉛的大齡兒童,智力會受到影響,連中學畢業都很困難。
鉛對人體的主要影響表現:造血系統,引起血紅蛋白合成改變、紅血球改變、易產生貧血;中樞神經系統,鉛對中樞神經系統有重要影響,會引起一般性的抑郁性腦障礙,并伴有微妙的生理和行為變化。鉛污染源從無機鉛轉變為有機鉛可能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外部神經系統,麻痹導致抑郁癥,甚至癱瘓,其主要外部表現為雙手無力。此外,人體受土壤及周邊環境中鉛的影響,泌尿系統、生殖系統、胃腸系統、內分泌系統、心血管系統、關節等生理系統也會受到破壞。
5 研究展望
近年來,隨著人們對土壤重金屬污染的進一步認識,國內外學者總結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對土壤中重金屬的含量和時空分布方面。重金屬進入土壤的途徑有多種,因此,導致土壤重金屬污染的因素較為復雜,現階段對土壤重金屬的來源分析,主要基于定性的描述及土壤中重金屬含量與污染源的相關性分析,而今后土壤重金屬污染源的分析及其定量工作重點將會逐漸轉向定量分析結合微觀來源鑒定分析,這對于控制日益嚴重的土壤重金屬污染具有重要的意義。對土壤中鉛污染源的分析起步于20世紀90年代,應用的各種分析方法均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在今后土壤鉛污染研究過程中應加強對鉛污染源分析方法的研究,同時結合相關分析的方法對鉛污染源分析進行論證。
雖然前人研究已經逐漸認識到,在工業發展過程中人為因素所導致的土壤鉛污染已大于自然本身(如火山噴發等),但貢獻率尚不明確,且人類的不同活動之間的貢獻率也無法具體獲得。人類在采礦、冶煉、工業生產、農業生產等各個領域都會形成污染源,從而造成土壤的鉛污染,但對各行業的貢獻率現階段沒有準確的分析方法。因此,在后期研究中應將分析土壤鉛污染來源的貢獻率作為研究重點,從而確定土壤中鉛污染物的來源和比例,為決策部門準確調控污染提供技術支撐。
隨著時代的發展,目前土壤鉛污染的總體發展趨勢逐漸由原來只關心土壤本身的污染狀況轉向準確尋找污染源,通過數理統計,獲得其貢獻率,同時結合土壤污染的時空變化,給決策者提供動態的可監測性的數據。在這個過程中,再利用形態分析、有效態分析等手段,綜合考察土壤受鉛元素污染的實際狀況,進而利用生物有效性分析鉛對人體的健康風險,目前這些方法在歐美一些國家已開始進行系統的研究并應用于實際決策指導中。美國學者利用體外模擬鉛污染,從而獲得鉛對人體的健康風險值;歐洲一些國家通過生物利用土壤中鉛元素的試驗,獲得通過計算生物利用率來評價土壤中鉛對人體健康所存在的風險性;英國等國家將土壤鉛體外模擬的生物利用率應用于評估土地對人類潛在風險的評估,結果顯示,體外模擬法在土壤鉛對人類健康的潛在危險評估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研究重金屬鉛的生物有效性,進而研究鉛對人類健康的風險已成為鉛污染土壤研究的一種趨勢,但我國在這方面還缺乏系統的研究。體外模擬方法將作為研究鉛污染土壤的重要手段,在國內外鉛污染健康風險評估中得到廣泛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