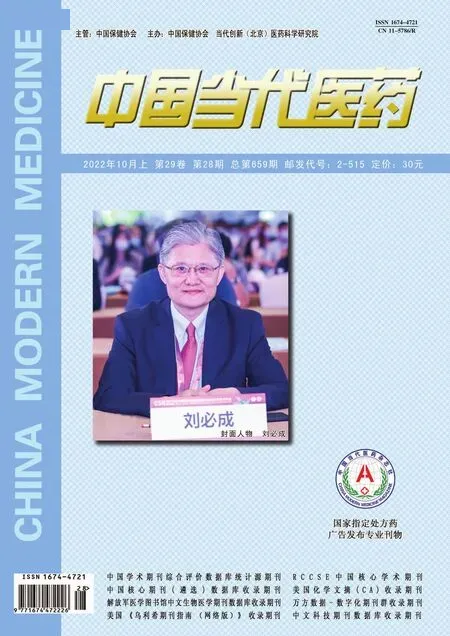3.0T磁共振多參數成像在乳腺癌新輔助化療中的應用價值
熊淑紅 阮玖根 肖 瓊 丁 瑤
江西省新余市人民醫院影像中心,江西新余 338025
乳腺癌是女性常見惡性腫瘤之一,有資料顯示,中國女性乳腺癌患病率以全球乳腺癌患病率2 倍的速度增長[1]。新輔助化療(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可減小腫瘤體積,為乳腺癌常用治療方式之一[2]。正確判斷NAC 對乳腺癌的療效,腫瘤殘余大小等對后續選擇何種手術方式、判斷疾病預后等具有重要意義。有研究指出,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可通過腫瘤體積變化對腫瘤NAC 療效進行預測[3],但NAC 早期療效通過腫瘤體積變化識別較為困難,故需尋找更為有效的預測指標。擴散加權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能對癌細胞水分子彌散進行定量測量[4],而動態增強磁共振(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RI,DCE-MRI)參數已證實和腫瘤組織學分級等密切相關[5],二者聯合應用于腫瘤診斷及NAC 療效中優勢顯著[6]。為此,本研究探究MRI 多參數成像在乳腺癌NAC 療效中的應用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選取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新余市人民醫院收治的60 例乳腺癌患者作為研究對象,按照NAC 治療后療效將患者分為顯效組(23 例)與非顯效組 (37 例)。顯效組中,年齡25~63 歲,平均(44.81±5.26)歲;其中浸潤性導管癌22 例,浸潤性小葉癌1 例。非顯效組中,年齡25~65 歲,平均(45.37±5.31)歲;其中浸潤性導管癌31 例,浸潤性小葉癌3例,浸潤性微乳頭狀癌3 例。兩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同意(YAWZ-00-Y)。納入標準:①經手術病理證實為乳腺癌;②均為女性,年齡18~65 歲;③單側病灶,影像學顯示未存在遠處轉移;④均接受NAC 治療,且治療前、治療6 周期后均行MRI 檢查。排除標準:①存在NAC 禁忌證者;②合并其他嚴重臟器疾病;③有乳腺癌遠處轉移;④存在MRI檢查禁忌證者;⑤處于妊娠、哺乳階段;⑥資料不全。
1.2 方法
以患者病理分類為依據,按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絡(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乳腺癌臨床實踐指南[6]推薦的NAC 標準,對患者進行各化療方案,化療期間嚴密監測患者,若發現化療毒副反應等異常及時上報醫生并給予相應處理。
MRI 檢查方法: 采用3.0T MRI 及專用乳腺線圈進行MRI 檢查,掃描序列包括T1WI、T2WI 等常規序列及DWI 與DCE-MRI。DWI 采用自旋回波I 平面成像序列,DCE-MRI 采用軸位三維液體衰減反轉恢復序列。將掃描圖像上傳至Mean Curve 工作站,并由2名乳腺診斷工作超過5年的醫師進行分析。腫瘤最大徑線(largest diameter,LD):在DCE-MRI 第2 個時相圖像上連測3 次LD,并取其平均值為最終結果,并計算NAC 前、后測量的LD 變化率(ΔLD)。表觀擴散系數(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 在DWI 圖像取病灶最大層面且信號均勻處作為感興趣區,連測3次ADC,并取其平均值作為最終結果,并計算NAC 前、后測量的ADC 變化率(ΔADC)。早期強化率(enhancement,E)、最大強化率(peak enhancement,PE):選取DCE-MRI 圖像上病灶感興趣區,并繪制時間信號強度曲線,計算E 為增強后1 min 信號強度增加的百分比,PE 為增強后最大信號強度增加的百分比,并計算NAC 前、后測量的E、PE 的變化率(ΔE、ΔPE)。
參照Miller&Payne 標準[7],將病理1~3 級定義為非顯效組,將病理4~5 級定義為顯效組。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 檢驗;采用ROC 曲線分析MRI 多參數變化率對NAC 療效的應用價值,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MRI 多參數的比較
顯效組患者NAC 后的ΔLD、ΔADC、ΔE、ΔPE 均高于非顯效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1)。
表1 兩組患者MRI 多參數的比較(%,±s)

表1 兩組患者MRI 多參數的比較(%,±s)
注 ΔLD:腫瘤最大徑線變化率;ΔADC:表觀擴散系數變化率;ΔE:早期強化率變化率;ΔPE:最大強化率變化率
組別 例數 ΔLD ΔADC ΔE ΔPE顯效組非顯效組t 值P 值23 37-61.38±17.15-48.85±11.28 3.419 0.001 69.12±19.01 35.86±10.53 8.729<0.001-77.59±20.92-65.13±16.25 2.584 0.012-56.57±15.28-28.15±8.31 9.336<0.001
2.2 MRI 多參數變化率對NAC 治療后療效的ROC曲線分析
經ROC 曲線分析顯示,MRI 多參數變化率聯合預測的AUC 最高,為0.871,聯合預測的靈敏度最高,為91.30%;ΔADC 預測的特異度最高,為91.89%(表2,圖1)。

表2 MRI 多參數變化率對NAC 治療后療效的ROC 曲線分析

圖1 MRI 多參數變化率對NAC 治療后療效的ROC 曲線圖
3 討論
乳腺癌多發于女性群體,其發病率高居首位[8]。NAC 為乳腺癌常用輔助治療手段,而MRI 多參數成像在其早期評估療效中意義重大[9-11]。
當前公認的NAC 療效評估的最直觀指標為腫瘤大小[12]。本研究中,顯效組NAC 后ΔLD 高于非顯效組,差異有統計學有意義(P<0.05);ROC 曲線分析指出,ΔLD 曲線下面積、靈敏度、特異度分別為0.716、60.87%、78.38%,表明ΔLD 可反映乳腺癌NAC 后療效,與以往報道類似[13]。DWI 作為一種以水分子微觀運動為基礎的MRI 序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量化指標是ADC 值,測量ADC 值可敏感反映腫瘤細胞微觀情況,在腫瘤預后預測中價值較高。王偉等[14]指出,DWI 中ADC 值變化可明顯反映乳腺癌化療療效。本研究中,顯效組NAC 后ΔADC 高于非顯效組,差異有統計學有意義 (P<0.05);ROC 曲線分析顯示,ΔADC評估NAC 療效的曲線下面積、靈敏度、特異度分別為0.854、65.22%、91.89%,和張彥收等[15-16]報道類似,提示ΔADC 可較好預測乳腺癌NAC 后療效。究其原因可能是腫瘤形態學改變不能對腫瘤細胞活動進行反映,而ADC 值可間接反映腫瘤細胞變化。DCE-MRI在乳腺癌疾病良惡性診斷及腫瘤分期中已廣泛應用,并可通過腫瘤形態學改變及血流動力學改變評估其NAC 療效[17]。本研究中,顯效組NAC 后ΔE、ΔPE 均高于非顯效組,差異有統計學有意義(P<0.05);ROC 曲線分析顯示,ΔE、ΔPE 評估NAC 療效的曲線下面積、靈敏度、特異度分別為0.816 與0.835、82.61%與82.61%、78.38%與78.38%,表明ΔE、ΔPE 對乳腺癌NAC 后療效具有一定預測價值,與王巍巍等[18]報道一致。此外,本研究發現,ΔLD、ΔADC、ΔE、ΔPE 聯合預測的曲線下面積及靈敏度最高,表明MRI 多參數變化率聯合預測對乳腺癌NAC 療效評估的臨床價值較高。
綜上所述,對乳腺癌新輔助化療患者采用3.0T磁共振多參數成像評估療效的臨床價值較高,是臨床重要的預測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