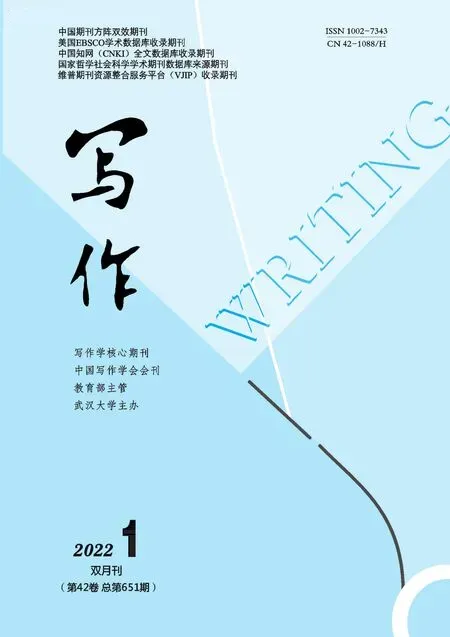“無形”與“有格”:沈從文寫作教學活動的當代啟示
金 鑫
作家、編輯、大學教員是1949年以前沈從文最重要的三個社會身份。豐產(chǎn)作家是其成為大學教員的基礎,從中國公學到青島大學、武漢大學、西南聯(lián)大,他都開設新文學相關課程,引發(fā)學生們的新文學創(chuàng)作熱情。擔任文藝副刊編輯便于他推薦學生作品發(fā)表,展示其教學成果,同時為新文學創(chuàng)作隊伍輸送新鮮血液。所以沈從文的三個身份是彼此關聯(lián),互相成就的。講授新文學,開設習作課,以作家的方式進行教學活動,是沈從文這位作家教員最主要的特征。
沈從文凡大學任教皆開設寫作課,頗受學生喜愛,也常被學生回憶。但寫作課并沒有像他開設的其他課程那樣留下系統(tǒng)、完整的講義,一定程度上說,他的寫作教學是“無形”的。但“無形”并不意味著沒有明確的目標和章法,沈從文重視將自己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通過賞析作品、評點試作、創(chuàng)作示范等方式傳遞給學生,更是將寫作與新文學課程統(tǒng)籌起來,在一個小的課程體系中進行“有格”的寫作教學。“無形”而“有格”的寫作課,體現(xiàn)了沈從文作為作家教員對寫作教育的獨到見解,不僅在當時具有典范性,對今天的大學寫作教學同樣有著諸多啟示。
一、沈從文大學寫作教學的典范性
沈從文進入大學任教的原因與多數(shù)作家一樣,都是為稻粱謀。民國時期多數(shù)作家無法只靠稿費維持生活,報館、學校因文化氛圍好、時間自由而成為作家們非常理想的去處,他們可以在這些單位一邊工作一邊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但與多數(shù)進入大學任教的作家不同,沈從文既沒有當時頗被看重的海外留學經(jīng)歷,也沒有國內大學的學歷,所以他進入大學謀職頗費周折,而且入職后也僅能講授與新文學創(chuàng)作關系較為密切的課程。
1929年沈從文向好友徐志摩表達了想到大學教書的想法,徐志摩便把他推薦給胡適,希望他能夠到吳淞的中國公學任教。沈從文深知自己的情況與大學選聘要求不符,主動致信向胡適表示:“在功課方面恐將來或只能給學生以趣味,不能給學生以多少知識,故范圍較窄,錢也不妨少點,且任何時學校方面感到從文無用時,不要從文也不甚要緊。可教的大致為改卷子與新興文學各方面之考察,及個人對各作家之感想,關于各教學方法,若能得先生為示一二,實為幸事。”①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頁。在胡適的推動下,1929年8月沈從文正式受聘為中國公學國文系講師,開啟了大學教員生涯。需要指出的是,胡適推動聘用沈從文,并非僅出于私人友誼以及對沈從文創(chuàng)作才華的欣賞,也與他的辦學思路有關。1934年2月14日,胡適回想中國公學聘用沈從文等作家任教,引領新文藝創(chuàng)作之風時談到:“大學之中國文學系當兼顧到三方面:歷史的;欣賞與批評的;創(chuàng)作的。”②胡適:《胡適全集》第3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頁。
沈從文任大學教員的起點,已基本決定了他教學活動的主要內容和基本特征。因為是作家,講授內容主要偏于新文學的欣賞批評和創(chuàng)作,而教學經(jīng)驗和方法的欠缺,促使他產(chǎn)生了“給學生以興趣”“改卷子”等想法。這些教學內容和方法雖然影響了沈從文在大學中的地位和處境,也在課堂上鬧出過笑話,但客觀上逐步催生出他寫作教學的優(yōu)長與特質。
1929年9月至1930年6月,沈從文在中國公學國文系任教,開設新文學研究和小說習作兩門課程,同時在上海暨南大學兼授中國小說史。1930年9月,經(jīng)胡適、徐志摩推薦,陳西瀅協(xié)調,沈從文到武漢大學國文系任助教,開設的課程還是新文學研究和習作,12月底學期結束即離開了武漢大學。1931年8月,沈從文受聘青島大學國文系任講師,開設中國小說史和高級作文兩門課,任教兩年后于1933年8月離開青島,回到北平。1933年9月,北平師范大學國文系主任錢玄同有意邀請沈從文到校任職,講授西洋文學或新文學,雖經(jīng)黎錦熙、鄭振鐸、周作人、楊振聲等人幾番邀請,沈從文仍堅持不再進入大學任職授課。
沈從文再次任教已是30年代末,從武昌幾經(jīng)輾轉到達昆明,在西南聯(lián)合大學附屬師范學院國文系任副教授,開設各體文習作、創(chuàng)作實習、中國小說史三門課程,直至1946年5月西南聯(lián)合大學正式結束。因為西南聯(lián)大在昆明時有個規(guī)定,因教學需要聘用新人,頒以西南聯(lián)大聘書即可,如果三校之中有一校認為此人很好,準備聯(lián)大結束后繼續(xù)聘用則可以給他另加一份聘書,表示將來聯(lián)大結束三校分家時此人的歸屬。所以沈從文1946年8月回到北平后受聘于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授,繼續(xù)開設現(xiàn)代文學選讀和習作兩門課③賀玉慶:《沈從文的寫作教學思想與現(xiàn)代寫作教學》,《寫作》2016年第8期。,直至1949年初因精神疾病住院。1949年4月沈從文出院,北京大學國文系已沒有他的課程。從1929年到1949年,沈從文近20年的國文系任教經(jīng)歷,始終沒有脫離新文學和寫作。其寫作教學活動的典范性主要表現(xiàn)為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時空影響的廣泛性。沈從文從1929年起開設寫作課,雖然在時間上錯過了現(xiàn)代大學教育萌生和快速發(fā)展的十幾年,但就寫作課而言,到1922年11月《大總統(tǒng)頒布實施之學校系統(tǒng)改革案》在大學推行選科制,才作為選修課逐步出現(xiàn)在大學國文系的課程體系中,直到1939年《大學及獨立學院各學系名稱》頒布,才被列為國文系必修課。所以沈從文的寫作教學幾乎貫穿了大學寫作課的初創(chuàng)期、發(fā)展期和定型期,全程參與了大學寫作課的發(fā)展建設。而空間上,沈從文先后在上海中國公學、武漢大學、青島大學、西南聯(lián)合大學、北京大學等多所大學授寫作,幾乎涵蓋了民國時期大學教育的所有重要城市,在學術交流尚不便利的時代,教員的流動是教育教學、學術研究交流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沈從文用個人的流動推動著大學寫作教學的交流和建設。
其次是教學內容和方式的代表性。民國大學寫作課從教學內容和方式上可分為兩支,一支以陳望道等學者為代表,他們授寫作主要講作文法,知識點明確,更具系統(tǒng)性,旨在通過知識的增加、認識的提升來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另一支就是作家任教,他們因新文學創(chuàng)作取得成績而開設寫作課,授課多偏重文學,從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出發(fā),通過鑒賞作品、修改作業(yè)等方式指導學生。周作人、俞平伯、沈從文、楊振聲、楊晦、張資平、孫席珍、許杰等作家都屬于這支寫作教員隊伍,他們在大學寫作教學方面的影響要超過前面的學者授課,而沈從文無論從授課時間還是影響力都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第三是教學效果的明確性。教育研究中教學效果是最難把握的,我們很難使教學內容、方法與學生的學習成績形成明確對應,民國大學寫作教育更是如此。一方面多數(shù)作家教寫作較為隨意,未留下系統(tǒng)完整的教學講義,很難掌握其教學內容;另一方面學生的習作成果保存不善,難以統(tǒng)計并獲得。但沈從文在開設寫作課的作家中是比較特殊的一位,其講義《從徐志摩作品學習抒情》《從周作人、魯迅作品學習抒情》《由冰心到廢名》等因在《國文月刊》發(fā)表得以示人,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其寫作教學內容和方式。更重要的是以汪曾祺為代表的一批學生撰寫了很多回憶文章,不僅利于鉤沉當年的授課情況,還融入頗多學習感受和收獲,這都使沈從文的寫作教學效果更為明晰。此外,因為沈從文擔任編輯,有推薦學生發(fā)表習作的便利,發(fā)表的學生習作一定程度上也能體現(xiàn)其寫作教學效果。
沈從文的寫作課在民國大學寫作教育中具有典范性,同時與當下的大學寫作教育也有一定對應性,可以為當今的教學提供一定的借鑒。首先,自教育部高等學校中文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建議將“大學寫作”列為漢語言文學專業(yè)必修課后,越來越多的中文系開設寫作課,大學寫作課的主體也逐步由校級通識選修課轉變?yōu)橹形南祵I(yè)課。而沈從文的寫作課一直都是在國文系開設的,與當下大學寫作課主流在學科歸屬、教學目標、授課對象等方面有頗多相近之處,這為今天的大學寫作教學提供借鑒是可能的。其次,今天從事大學寫作教學的教師全部是中文系畢業(yè)的研究生,有較為系統(tǒng)的中文學科知識儲備,在學術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積累,但絕大多數(shù)都缺乏寫作尤其是文學創(chuàng)作經(jīng)驗,課堂教學中這部分內容也往往缺失。而沈從文寫作教學正是以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為出發(fā)點和指向的,可以對今天的寫作教學形成一定補充,為豐富寫作課內涵、提升寫作教學質量提供幫助。
二、以經(jīng)驗轉化為目標的“無形”教學
作家在大學教寫作,多以賞析作品和點評作業(yè)為途徑,因此缺乏系統(tǒng)性,看起來也比較隨意。比如朱自清在清華大學授寫作,常用的方法是大聲朗誦優(yōu)秀的學生習作;胡山源在福建高師授寫作,主要通過面批習作一對一指導學生;孫席珍在中國大學授寫作,要求學生按時提交習作,自己隨堂點評提出修改意見;白薇在國立武昌中山大學授寫作,要求學生多讀作品,讀后寫讀書筆記積累寫作經(jīng)驗;冰心在燕京大學授寫作,看過習作后要和每個學生進行半小時以內的談話,還要求學生自辦刊物,自行組稿;路翎在中央大學授寫作,常把學生帶到戶外,邊觀察邊討論……
靈活自由的上課方式自然受到學生的喜愛和歡迎,但這樣授課也存在明顯的問題,即教學內容知識性不足,缺乏系統(tǒng)性,最直觀的表現(xiàn)就是在上課多編講義的大學國文系,作家的寫作課幾乎沒留下較為完整的講義。有跡可循的只有兩部,一部是孫席珍文藝習作課講義《詩歌論》,該講義1935年曾在中國大學校內印發(fā),但未正式出版。另一部是沈從文在西南聯(lián)大授各體文習作時結集的《習作舉例》,未正式出版,其中3篇刊于1940年《國文月刊》的前3期。講義的稀少,有一定客觀原因,作家入大學任教往往首先開的就是寫作課,教學經(jīng)驗不足,積累有限,編講義不免遇到困難。但更重要的是主觀原因,多數(shù)作家認為寫作主要依賴靈感的爆發(fā)和經(jīng)驗的積累,既然靈感無從把握,那就盡可能地傳遞經(jīng)驗。沈從文身為作家,很自然地也以經(jīng)驗傳遞為中心授寫作課,他的寫作教學是“無形”的。所謂“無形”就是放棄了對系統(tǒng)的寫作知識的梳理和建構,教學方式方法也沒有一定之規(guī)。
作家進入大學國文系任教,專任新文學和寫作課的并不多,多數(shù)都要想方設法開設文學史、文學概論等骨干課程,以保住自己的教職。同時開設包括新文學和寫作課在內的多門課程,為我們考察作家教寫作的態(tài)度提供了便利條件。以沈從文為例,他在上海中國公學開設新文學研究、中國小說史和小說習作三門課,到武漢大學后繼續(xù)開設新文學研究和小說習作。三門課程中,新文學研究編有講義,到1930年9月,講義《新文學研究》已相當完備,并在武漢大學校內印行。小說史課也有與孫俍工合作編寫的講義《中國小說史》,雖然沈從文只參編了緒論和第一講神話傳說,但講義他一直使用,到武漢大學任教后也曾校內印行過。與新文學研究和中國小說史不同,沈從文開設的寫作課一直沒有較為系統(tǒng)的講義,直到在西南聯(lián)大開設各體文習作,才有了《習作舉例》作為授課講義。不僅出現(xiàn)的時間晚,寫作課講義在形態(tài)上也與前兩部有很大不同。《新文學研究》分上下兩編,分別對應上下兩個學期的新文學教學,上編有總括,有按照時序、特點對新詩發(fā)展分階段的引例,下編則是六篇關于代表作家的詩論。對這部講義,沈從文的評價是“那個講義若是你用他教書倒很好,因為關于論中國新詩的,我做得比他們公平一點”①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頁。,可見在追求授課內容的系統(tǒng)性的同時,他也重視課堂講授的客觀性。《中國小說史》僅第一講為沈從文編寫,但講下設章,章下分專題,專題間邏輯清晰,章之間彼此呼應,體現(xiàn)出明顯的學理性、研究性和文學史意識。而各體文習作的講義《習作舉例》從可見的三篇《從徐志摩作品學習抒情》《從周作人、魯迅作品學習抒情》《由冰心到廢名》來看,都是各自獨立的專題,結構上較為松散,沒有時間、流派等方面的邏輯關系。
三門開設過的課程,兩門早早就編撰了比較完備的講義,一門很晚才有松散的講稿,這種差異說明作為教員的沈從文是了解課堂教學的要求的,也具備將新文學知識化,建構成系統(tǒng)文學知識的能力。所以寫作課缺乏完備講義是他主動放棄了對寫作知識的梳理和系統(tǒng)建構,是作為作家的沈從文的主動選擇。在《給一個作家》中可以看出沈從文對寫作教學的想法:“關于寫作事,我知道的極有限,近來看到許多并非是作家寫的‘創(chuàng)作指南’一類文章,尤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若按照那個方法試驗,我想若派我完成任何作品都是不可能的。”②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44頁。
沒有系統(tǒng)的講義也就意味著沈從文的寫作課在教學內容和教學形式上都與其他講授文學知識的課有所不同,修過沈從文“各體文習作(二)”課程的諸有瓊就回憶說,“他講課從來不成本大套地講什么定義,什么寫作方法等等”③諸有瓊:《憶沈從文先生教寫作課》,《新聞與寫作》1988年第7期。。
沒有成本大套的定義和寫作方法,沈從文的寫作課主要依靠文本賞析和習作評點。他在西南聯(lián)大教育學院國文系授“各體文習作”的三篇講義因發(fā)表在《國文月刊》得以保存,通過這三篇講義可以窺探他用文本賞析授寫作的方法。三篇講義都講抒情,這是寫作中主體性很強的一個方面,從講義內容看,有三方面特征值得注意:一是比較多地引用原文,比如《從徐志摩作品學習抒情》就引用了《巴黎的麟爪》(包括引言)、《龍虎胡同七號》《云游》《我所知道的康橋》等四篇作品,占到講義篇幅的七層以上;二是關注寫作中的微觀、細節(jié)問題,比較多地分析作品的語言細節(jié),遣詞造句;三是運用文本對照的方式更直觀地呈現(xiàn)作家的創(chuàng)作個性。
習作點評也是沈從文一直運用的寫作教學方法,他因重視習作將自己開設的所有寫作課都稱為“習作”或“實習”。通過學生回憶,我們可以大體把握沈從文習作課的幾個突出特點。一是拒絕宏觀、抽象的命題,讓學生練習細微表現(xiàn),進而培養(yǎng)寫作基本功。例如他曾在黑板上寫下“寒”“冷”“凍”“冰”四個字,讓學生用文字形象描繪這四種不同氣溫狀態(tài)。他還布置過“我們的小庭院有什么”“記一間屋子里的空氣”“燈下”等習作題目,都是需要學生細致觀察、刻畫才能完成的。二是堅持認真細致地點評學生習作。據(jù)樂黛云回憶,沈從文的寫作課“要求我們每兩周就要交一篇作文,長短不拘,題目則有時是一朵小花,有時是一陣微雨,有時是一片浮云。我們這個班大約二十七人,沈先生從來都是親自一字一句地改我們的文章,從來沒有聽說他有什么代筆的助教、秘書之類。……先生總是拈出來幾段他認為寫得不錯的文章,念給我們聽,并給我們分析為什么說這幾段文章寫得好。”①樂黛云:《1948年,我在北大中文系》,北京大學校友會編:《北大歲月:1946—1949的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5-46頁。除了寫評語、分析佳作,沈從文有時還會將習作與同題材名篇進行對比,沒有合適的同題材作品就自己“下水”示范,以此幫助學生查找寫作方面的差距,指明未來提高的方向。
沈從文寫作教育研究在學界已產(chǎn)生了比較多的成果,這里選擇性地鉤沉,旨在將其看似“無形”的寫作教學與當下中文系普遍開設的大學寫作進行對話,從中尋求可借鑒的東西。無論是鑒賞佳作,還是點評習作,沈從文的寫作教學都顯露出重視細節(jié)、盡量直觀的特點。這體現(xiàn)了他對經(jīng)驗的看重以及在傳遞寫作經(jīng)驗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如何在講授知識的課堂傳遞寫作經(jīng)驗一直是困擾寫作課的一個難題,甚至因此產(chǎn)生了寫作究竟能不能教的疑問。今天承擔大學寫作教學的老師絕大多數(shù)都是中文系畢業(yè)的研究生,已經(jīng)習慣了概念、理論和系統(tǒng)的文學、語言學知識,而且在文學創(chuàng)作、應用文寫作方面的經(jīng)驗也相對不足,寫作經(jīng)驗的傳遞成了無法完成的任務。這時再看沈從文“無形”的寫作教學,有一些方法是頗值得借鑒的。比如鑒賞佳作時,不做宏觀的、整體性的評價,將視野盡量下沉到具體的字句表達,在字里行間汲取小的寫作技巧;再比如教師也親自“下水”和學生一起寫,體會寫作中的難點,與學生在“共情”的前提下實現(xiàn)經(jīng)驗分享;還可以嘗試將整篇文章的寫作拆解為零散的小練習,與學生在很具體的寫作問題上進行交流;點評習作不做簡單的定性評價,由細節(jié)著眼為學生找出寫作中存在的優(yōu)長與不足。概言之,讓寫作經(jīng)驗在化整為零的過程中浮現(xiàn),在“共情”的交流中傳遞,不斷地在習作中轉化,是沈從文“無形”的寫作教學對今天大學寫作課的啟示。
三、與文學教育融為一體的“有格”寫作課
在大學教育已經(jīng)高度學科化、專業(yè)化的今天,大學寫作課往往會在學科歸屬、融入課程體系等方面遇到困難。以普遍開設大學寫作的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為例,寫作課雖然由中文系教師開設,但是從教學內容看,它無法歸入文學或語言學的任何一個二級學科,與專業(yè)課相比寫作更像通識課,而與通識課相比寫作又更像實踐課。這樣的后果就是,寫作課被孤立在漢語言文學的課程體系之外,難以與其他課程構成聯(lián)系,無法融入學生不斷系統(tǒng)化的專業(yè)知識,教師上課也顯得底氣不足。這個長期困擾大學寫作課的難題,可以從沈從文“有格”的寫作教育活動中找到一些辦法,獲得一些啟示。
稱沈從文的寫作課“有格”,大體有兩層含義,一是有格局,他在國文系開設的寫作課都有明顯的文學傾向,能很好地融入課程體系;二是有堅守,在授課中堅持以文學創(chuàng)作規(guī)律為重點,不為追求課程本身的知識性、系統(tǒng)性改變寫作教育初衷。
民國大學開設最多的寫作課是“各體文習作”,這門課最終也成為國文系的必修課,但從課名就能看出,習作的范圍是很廣的,決不限于文學,更不限于新文學。但多數(shù)開此課程的作家都將寫作重點放在文學,尤其是新文學方面。這自然與他們的作家身份有密切關系,但應該看到,多數(shù)作家在開寫作課同時還開設其他課程,他們具備不依靠創(chuàng)作成績和經(jīng)驗獨立開課的能力,所以作家寫作課側重文學創(chuàng)作不是簡單的身份局限,其中也包含他們的自主選擇。
以沈從文為例,他能夠以新詩創(chuàng)作為中心開出頗為嚴整的新文學研究課,能與孫俍工合作講中國小說史,而且在中國公學圖書館借閱大量的雜書,在武漢大學任助教期間,對金石學也有所研究,到了青島大學更是對先秦的巫文化產(chǎn)生了研究興趣,這都體現(xiàn)了沈從文極強的學習能力,其教員、學者身份隨著其任教經(jīng)歷的增加日益凸顯。到西南聯(lián)大時期,沈從文在行文上已開始引經(jīng)據(jù)典、旁征博引,像《見微齋筆談——小說上吃人肉記載》《宋人演劇的諷刺性》等收在《沈從文全集》第14卷《見微齋雜文》集中的文章,都明顯區(qū)別于一般的作家創(chuàng)作。所以沈從文有能力將各體文習作開成輻射更廣泛的文體類型,以知識、文獻填充的純講寫作理論、寫作發(fā)展史的課程。但他并沒有那樣做,而是始終堅持將寫作課作為文學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也基于此,沈從文的寫作課無論開到哪里都得到眾多學生的喜愛,這其中自然有新文學的擁躉,但也有相當多的學生是基于對國文專業(yè)的認同而接受進而喜愛寫作課的。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沈從文新文學研究主講新詩,中國小說史主講小說,寫作課無論是賞析名家作品還是布置習作題目都偏向于散文,在因人設課、教員自主性很強的時代,這種安排本身也可體現(xiàn)出沈從文的一種格局,他有意無意地從文體角度將寫作融入了正在逐步建立的新文學課程體系。
在寫作課就是文學創(chuàng)作課的大前提下,沈從文憑個人文學創(chuàng)作成績成為寫作課堂的權威,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課程因知識性不足帶來的權威感的缺乏。
比如鑒賞佳作的寫作課上,沈從文選擇的文章多出自自己好友或熟悉的作家之手,這樣他能更準確把握作品的特質,捕捉作品中作家的身影和精神,加上一些學生們完全無法知曉的作家間的交游往來故事,不僅成就了專深、充盈的寫作課堂,也奠定了自己的權威性。再比如沈從文利用自己在報刊界的影響力,積極推薦學生的優(yōu)秀習作發(fā)表,而他本人與各個報刊的熟絡關系以及他擔任主編多年所養(yǎng)成的敏銳的選稿眼光,也匯入寫作課,拓展了寫作課內容和學生的習作空間。汪曾祺曾說過:“我一九四六年前寫的作品,幾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①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3卷,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66頁。學生的作品在報刊發(fā)表,一方面會提升學生寫作的興趣與信心,另一方面也提升了沈從文在寫作教學中的權威性。
以創(chuàng)作成績和報刊資源成為課堂上的權威,獲得學生的認可和信服,沈從文便可以擺脫寫作經(jīng)驗必須知識化才能在課堂講授的束縛,將那些抽象的、甚至有些難以言說的創(chuàng)作體會都帶入課堂,這既是他身為作家所獨有的,更是符合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從他《習作舉例》中的三篇講義看,沈從文非常重視抒情這一帶有很強作家主觀性的寫作方式。但他并不單純分析寫法和技術,他講徐志摩的抒情,美質在于青年的“動”,他講周氏兄弟的抒情,立足于中年人對世事冷熱疏分的感慨與觀照。徐志摩也好,周氏兄弟也好,他們的抒情,都離不開作家本人的精神氣質。沈從文在傳遞一種寫作教育觀念,單純的寫作知識、修辭技術是無法成就佳作的,創(chuàng)作者自身的精神氣質、主觀條件才是作品優(yōu)劣的決定性因素。這是符合實際的,同時也是符合文學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但如果不是立足文學教育的寫作課,沒有讓學生信服的權威性,這些非常抽象、主觀的東西是無法進入寫作課堂的。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沈從文“有格”的寫作課,它以明確的文學傾向融入國文系課程體系,以教員的創(chuàng)作成就和報刊影響力在學生中樹立權威,以學科歸屬和權威性為基礎,將作家精神氣質、主體性等影響寫作的主觀因素引入課堂,克服了寫作規(guī)律抽象、模糊、難以令人信服等弊端,進而實現(xiàn)了對寫作教學的真正堅守。
陳平原曾總結沈從文的教員生涯:“不是大學教育啟發(fā)了他的文學才華,而是他改變了學院里的教學方式。”①陳平原:《大學校園里的“文學”》,《渤海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這充分肯定了沈從文寫作課對國文系教學的影響,而“無形”“有格”正是產(chǎn)生影響的兩個重要推動力。在眾多高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恢復開設寫作課的今天,回看沈從文“無形”與“有格”的寫作教學,仍有頗多值得借鑒的地方。微觀的教學方法上,正視寫作經(jīng)驗的重要性,教學重心下沉,從細節(jié)著眼,在師生不斷對話中傳遞寫作經(jīng)驗,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宏觀的教育觀念上,要認識到學科歸屬的重要性,將寫作課置于一定的課程體系中建構,以此獲得更廣泛學生的認可,再通過提升教員的課堂權威,彌補課程知識性、客觀性的不足,最后將抽象、主觀的寫作規(guī)律搬上以傳遞知識為主的大學課堂,實現(xiàn)真正的寫作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