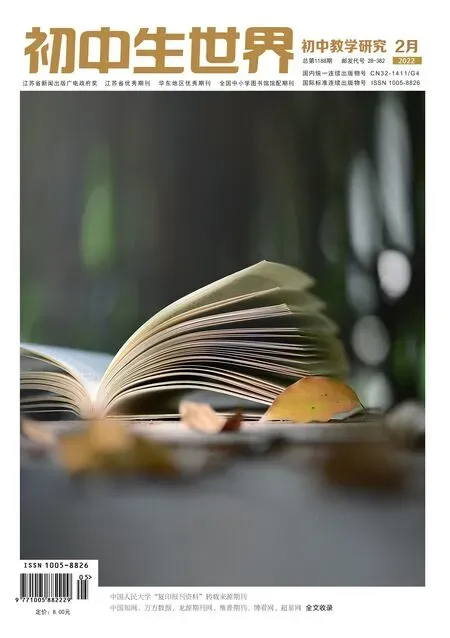有趣·有法·有得
——評李力老師的作文指導課
■司馬麗莉
閱讀者與文本對話的途徑很多。孫紹振教授認為,如果拘于讀者身份,只能順著文本的程序馴服地追隨,閱讀必然陷于被動。習作者與文本對話的方式更多,轉換視角,走進文本,與人物平等對話,是一種不拘泥于傳統解讀敘述性文本的新路徑。
李力老師的這節作文指導課從教材中來,從生活中來,從體驗中來,真正做到了有趣、有法、有得。
這是一節有趣的課,課堂上歡聲笑語不斷。教者導入巧妙,起點不高,每個學生都能有話說,也愿意表達。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比教授多少專業卻難以操作的知識點都有用。李老師設身處地地幾次轉換體驗的視角,讓學生從生活中找到了表達的樂趣,真正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這是一節有法的課。靜水流深,“法”在無形之中。李老師的這節寫作指導課由《散步》的閱讀教學聯想生發而來,轉換視角,通過內心獨白、行動暗示、環境襯托三種方法,引導學生走進人物內心,在閱讀文本的基礎上遷移到寫作實踐。在一次次交流中,李老師指導學生運用多種方法展現人物的內心世界。
這又是一節有得的課。閱讀和寫作本就不是割裂的,從閱讀到寫作,在讀寫結合與轉化之間,學生對《散步》的理解更趨深刻,也從文本中習得了寫作的技巧和方法。與其到處搜羅材料作為作文指導的范本,還不如以教材為抓手,切入口巧妙,且易操作。課堂上,學生真正理解了從內心獨白到行動暗示,再到環境襯托,都是有力展現人物內心、塑造人物形象的好方法。
當然,這節課也有可以繼續改進的地方。比如:雖然視角的多次轉換有利于對文本的解讀,但是在真正寫作的時候,還是要堅持一定的視角,避免敘述的混亂雜糅。這就是解讀和創作的區別,選擇恰當的視角去敘述故事對反映文章主題非常重要。《散步》一文選擇“我”作為敘述故事的角度是非常講究的。“我”是“母親”的兒子,是“妻子”的丈夫,是“兒子”的父親,每一個人都與“我”密切相關,并且“我”又是承前啟后的中年人的代表,是肩負過去和未來責任的人,因此選擇“我”作為敘述角度比選擇其他人都更合適。還有展示學生作品的時候,除了佳作之外,還可以展示一些有改進空間的作品,讓更多的學生參與到課堂中來,體驗“升格”的魅力,在今后的寫作中養成自改、互改的習慣。
人物描寫方法很多,心理描寫為一難。但是,我們如能像李老師這樣,緊緊抓住文本資源,合理安排訓練節奏,長期訓練,一定能讓學生的寫作水平不斷進步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