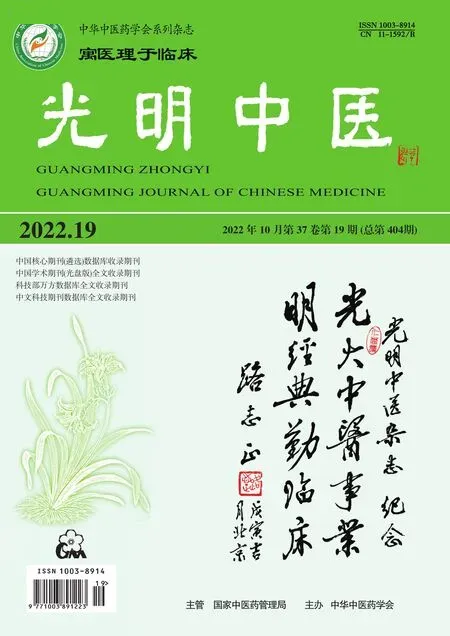基于水化于氣 氣生于水理論探討益氣養陰法治療膜性腎病*
柯嘉兒 李 季 蒙向欣
膜性腎病(Membranous nephropathy,MN)是原發性腎病綜合征常見的病理分型之一,以腎小球基底膜(GBM)上皮細胞下免疫復合物沉積伴基底膜彌漫增厚為特征[1],其發生血栓事件風險高于其他病理分型。近年來,膜性腎病發病率有逐年增高趨勢,其發病率占中國成人腎病綜合征的20%~30%[2],占原發性腎小球疾病(Primary glomerular disease,PGD)的23.4%[3]。部分患者對激素、免疫抑制劑等多種藥物不敏感,或因隨意停藥、飲食勞倦等因素,致使病情反復、遷延難愈。在臨床中發現,中醫藥對治療膜性腎病有著獨特的優勢,在癥狀改善及改善激素、免疫抑制劑的不良作用方面均有不錯的療效。然而中醫無“膜性腎病”的對應病名,其辨證分型尚未統一。筆者擬從“水化于氣,氣生于水”理論對益氣養陰法治療膜性腎病作一探討。
1 水化于氣 氣生于水理論
“水化于氣,氣生于水”出自清代唐容川的《血證論》[4],“然氣生于水,即能化水。水化于氣,亦能病氣。氣之所至,水亦無不至焉”。氣屬陽,為無形之物;水指津液,屬陰,為有形之物。津能生氣,氣能生津,氣與津在體內相互轉化,相互依存。氣的生成有賴于陰津的化生、滋潤,氣的運行依賴于陰津的運載。正如《素問·經脈別論》所言:“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飲食水谷化生陰津,通過臟腑的蒸騰溫化,生成為氣。因此陰津的耗損,可引起氣的虛衰,所謂“吐下之余,定無完氣”。而津液的生成、輸布及排泄,有賴于氣的升降出入及推動、固攝作用。正如《血證論》提到“膀胱腎中之水陰,即隨氣升騰,而為津液,是氣載水陰而行于上者也。氣化于下,則水道通而為溺”。氣是津液輸布運行的動力,氣所到達之處,陰津亦隨之而至。若氣虛,則無以化生、調控陰津,導致津液不足。氣與津液相互化生,互為影響,其中一方的病變可影響另一方,氣的運行障礙可引起水液的代謝失常,水液的代謝失常亦可影響氣的運行,所謂“病水亦即病氣, 病氣亦即病水”。
2 膜性腎病的病因病機
膜性腎病以中老年男性多發,以水腫、蛋白尿、鏡下血尿等為此病的臨床表現,常表現為腎病綜合征,部分患者可出現腎功能不全,甚至5~10年發展為終末期腎病[2,]。中醫無“膜性腎病”的病名,根據其臨床表現可歸屬于中醫“水腫”“尿濁”“虛勞”等范疇。其病因多為稟賦不足、外邪侵襲飲食不節、勞倦過度,致使肺之通調水道失司,脾失轉運,腎之開闔不利,水液代謝失常,發為水腫;脾虛中氣下陷,腎虛固攝無權,則膏濁下泄而致尿濁;久病脾腎之先后天之本虧虛,使諸臟虛衰、氣血津液陰陽虧損,機體失于振奮、濡養終致虛勞。
多數醫家認為,此病病機以本虛標實為主,本虛責之于脾腎,兼以風、濕、熱、瘀等標實。洪欽國教授認為,脾腎虧虛為膜性腎病發病之本,血瘀可貫穿疾病始終,而風邪、水濕、濕熱等常出現在不同階段[5]。黃文政教授認為,膜性腎病存在稟賦不足、脾腎虧虛、外邪侵襲和瘀血內阻的致病因素,影響三焦氣化功能致使此病的發生[6]。劉玉寧教授認為,此病治療應突出脾腎氣虛為本,腎絡瘀滯、毒邪傷腎為標,肝郁氣滯亦不可忽略[7]。戴恩來教授認為,此病病機為本虛標實,脾腎虧虛為本虛,濕熱、水濕、瘀血等病理產物為標實[8]。
3 從水化于氣 氣生于水理論分析膜性腎病
膜性腎病以脾腎虧虛為發病之本。《景岳全書》中言:“夫人之虛,不屬于氣,即屬于血,五臟六腑,莫能外焉。而獨舉脾腎者,水為萬物之源,土為萬物之母,二臟安和,一身皆治,百疾不生”。脾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氣與陰津皆化生于水谷。脾氣主升,脾主運化水濕。腎為先天之本,腎氣為臟腑之氣之根本,“腎者水臟,主津液”。脾腎二臟與“氣”“水”均密切相關。
脾氣虛則升降輸布水液之樞紐功能障礙,腎氣虛則蒸騰氣化功能失調,水液代謝失常,水濕停聚而為水腫。正如《諸病源候論·水腫病諸候》所言:“腎虛不能宣通水氣,脾虛又不能制水,故水氣盈溢,滲液皮膚,流遍四肢,所以通身腫也”。而“中氣不足,溲便為之變”,脾氣虛而無以升清,濁氣無以下降,水谷精微輸布失常,血失統攝而外溢,加之腎氣虛而封藏、固攝失司,則精微、血液下泄,而見蛋白尿、血尿。由此可見,膜性腎病以“病氣”為先,以氣的運行失常為發病的始動因素。
氣虛無以行水,水濕內停化為濕濁,濕邪內停阻滯氣血運行,加之“氣為血之帥”,氣虛則行血無力,故瘀血內生,瘀血阻滯則水停,瘀水互結則病勢纏綿,正如《血證論》所言: “又有瘀血流注,亦發水腫者,乃血變成水之證……”,現代醫學亦指出,膜性腎病患者體內呈高凝狀態,且膜性腎病在成人腎病綜合征中血栓和栓塞的并發癥發生幾率較高[2]。血液凝滯,濕濁黏膩,二者合而為病,久則郁而化熱,濕熱蒸騰耗傷陰液;氣虛日久,化生津液動力不足,無以化生陰津。陰津不足,則氣無以化,如此惡性循環,終致氣陰虧虛。而蛋白、血液等有形精微之物從下泄出,加重氣陰的耗傷,故病久者見氣陰兩虛之征。有研究指出,膜性腎病患者氣陰兩虛證者病程較長,尿白量較多,腎小球濾過率較低,病情較重[9]。所謂“氣根于津, 津根于氣”,膜性腎病“病氣”而及“病水”,終致氣陰兩傷。
另外,《素問·至真要大論》言:“調氣之方,必別陰陽……寒熱溫涼,衰之以屬”,藥物的性味歸經不同對機體的影響不同。膜性腎病患者常需使用激素治療,而激素從藥性來講屬于陽藥,為大辛大熱之品。長時間使用,可助熱耗氣傷陰,致使氣陰虧虛,并可見陰虛火旺之象。另外,此病常水腫為患,治療難免使用利水逐水藥物,久則耗傷陰津。因此,膜性腎病的治療,應注意顧護氣陰。
4 氣陰兩虛證與病理分型關系
基于“水化于氣,氣生于水”理論,膜性腎病早期以氣虛為主,隨著疾病的發展,氣水相生相化相互影響,逐漸出現氣陰兩虛證候。在臨床及相關報道中亦可發現,氣陰兩虛是膜性腎病常見的辨證分型,病理表現較重。膜性腎病根據病理表現可分為Ⅰ、Ⅱ、Ⅲ、Ⅳ期。宋李桃等[9]對150例膜性腎病的中醫辨證分型與病理進行分析,發現氣陰兩虛型以Ⅱ期以上多見,且腎小球硬化、腎小管間質損傷情況更加明顯。俞欣等[10]通過對117例膜性腎病患者的臨床表現、病理特點與中醫證型分布的相關性研究發現,氣陰兩虛型患者年齡較大,以Ⅲ期多見,腎臟病理中慢性化及小管間質積分較高,預后較差。黎民安等[11]將113 例膜性腎病患者進行辨證分型、腎臟病理分期、臨床生化指標進行檢測分析,發現氣陰兩虛證的病理類型較重,有比較明顯的系膜病變,24 h尿蛋白定量、血肌酐較高,白蛋白較低。由此可見,氣陰兩虛證的膜性腎病患者病情較重,預后較差。
5 益氣養陰法治療膜性腎病
益氣養陰法為治療膜性腎病氣陰兩虛證的治療大法,根據患者兼證情況酌加活血、化濕、清熱等藥物。多數醫家運用益氣養陰法治療膜性腎病亦得到良好療效。陳新政[12]自擬益氣養陰方治療膜性腎病,對比對照組,其對改善腎功能及凝血指標效果更佳。宋丹丹等[13]擬用益氣養陰活血方聯合激素、環磷酰胺治療成人原發性膜性腎病,發現對血白蛋白、膽固醇、24 h尿蛋白定量有改善作用,且能減輕西藥的不良作用。
參芪地黃湯是治療膜性腎病氣陰兩虛證的常用方劑,出自《沈氏尊生書》,本方為六味地黃湯化裁而來,去澤瀉而加用人參、黃芪,增強了健脾益氣之功。脾氣得實,氣之升降樞紐得運,則水濕可化,陰津可生,如《血證論》所言:“是以人參補氣,以其生于北方,水中之陽,甘寒滋潤,大生津液,津液充足”。而熟地黃、山茱萸可滋腎水,寓真陰,滋水以補氣,以先天生后天;山萸肉收斂固精,與參芪同用,增強益氣固腎之功;山藥可補脾氣滋腎陰,具氣陰雙補之效;茯苓利水,水去而氣行;陰虛則陽失所制,丹皮味苦微寒可清泄相火,所謂“血不利則為水”,可起到活血以利水之功。《血證論》所言:“此治水之邪,即以治氣。與滋水之陰,即以補氣者。固并行而不悖也。且水邪不去,則水陰亦不能生”。本方著眼于脾腎二臟,著手于氣陰,補中有泄,泄中寓補,起到滋腎陰而補脾氣功效,與膜性腎病的病機相契合。本方在膜性腎病的臨床治療中亦取得良好效果。趙凱等[14]使用加減參芪地黃湯配合西醫基礎支持治療,發現在血白蛋白、24 h尿蛋白定量及中醫證候積分方面均優于單純西醫治療組。蔡朕等[15]研究指出抗PLA2R抗體滴度越高,其病理越嚴重,治療難度越難。通過臨床觀察發現,參芪地黃湯對不同的抗PLA2R抗體滴度的患者的尿蛋白定量及血清白蛋白的改善均優于對照組,對抗PLA2R抗體滴度≤300 RU/ml效果更優。李偉等[16]使用參芪地黃湯加味配合小劑量激素聯合他克莫司治療特發性膜性腎病(Ⅰ~Ⅱ期),發現其能提高療效,且能減輕激素及他克莫司不良反應的作用。由此可見,運用益氣養陰法可改善膜性腎病患者的臨床癥狀、實驗室指標,且能減輕激素、免疫抑制劑的不良作用。
5 小結
基于“水化于氣,氣生于水”理論,氣水相生相化,二者相互影響。膜性腎病以脾腎之先后天之本虧虛為基礎,病氣則水停不化,津液不生,久則造成氣陰虧虛的病理狀態。氣陰兩虛型的膜性腎病病程較久、病理分型較重,通過益氣養陰法,可起到益氣而行水生津,育陰而滋水補氣之功。在臨床上,運用益氣養陰法治療膜性腎病,可改善患者實驗室指標及臨床癥狀,并能減輕激素等藥物的不良反應,值得臨床醫家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