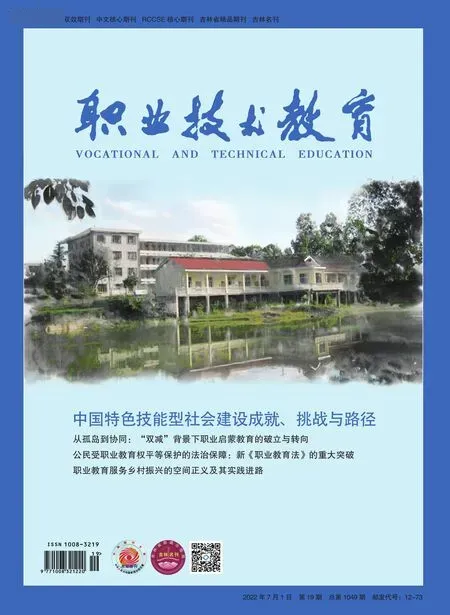凱興斯泰納與德國(guó)雙元職業(yè)教育制度的創(chuàng)建
傅修遠(yuǎn) 榮艷紅
建設(shè)高質(zhì)量的職業(yè)教育體系離不開(kāi)產(chǎn)教融合、校企合作。黨的十九大報(bào)告明確提出,要完善職業(yè)教育和培訓(xùn)體系,深化產(chǎn)教融合、校企合作[1]。這是黨和國(guó)家在新時(shí)代對(duì)職業(yè)教育體系建設(shè)所做的一個(gè)綜合性、整體性布局。從世界范圍看,推動(dòng)產(chǎn)教融合、校企合作最為成功的一個(gè)典范就是德國(guó)的雙元職業(yè)教育制度。
德國(guó)雙元職業(yè)教育制度的典型特征是將企業(yè)的學(xué)徒培訓(xùn)與學(xué)校職業(yè)教育緊密聯(lián)結(jié)在一起,且針對(duì)18周歲之前的青少年具有強(qiáng)迫教育的性質(zhì)。1969年德國(guó)《職業(yè)培訓(xùn)法案》(the Vocational Training Act)的頒布,標(biāo)志著雙元職業(yè)教育制度的確立。自該制度確立以來(lái),由于其對(duì)于德國(guó)高質(zhì)量技能人才培養(yǎng)的效果,很快就在世界范圍內(nèi)形成了良好聲譽(yù),進(jìn)而被許多國(guó)家所效仿。雙元職業(yè)教育制度的出現(xiàn)與德國(guó)教育家凱興斯泰納(Georg Kerschensteiner,1854~1932)的教育理論和實(shí)踐有著密切關(guān)系。作為國(guó)民教育、勞作教育與繼續(xù)教育的倡導(dǎo)者,凱興斯泰納積極回應(yīng)德國(guó)工業(yè)化、城市化對(duì)于青少年國(guó)民教育的新需求,他的國(guó)民教育理論不僅將學(xué)徒教育與繼續(xù)教育(即后來(lái)的學(xué)校職業(yè)教育)緊密連接在一起,而且他還強(qiáng)力推動(dòng)了兩種教育在現(xiàn)實(shí)中的聯(lián)姻,慕尼黑體系(Munich system)的出現(xiàn)就是兩種教育聯(lián)姻的結(jié)果。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凱興斯泰納的影響依然長(zhǎng)盛不衰,慕尼黑體系決定了這一時(shí)期德國(guó)職業(yè)教育的基本形態(tài),雙元職業(yè)教育制度正是在改造慕尼黑體系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分析凱興斯泰納對(duì)于雙元職業(yè)教育制度創(chuàng)建所起到的歷史性奠基作用,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更為清晰地認(rèn)識(shí)雙元職業(yè)教育制度的內(nèi)在本質(zhì)與精髓、準(zhǔn)確把握個(gè)人在教育制度形成過(guò)程中的巨大作用,而且對(duì)于推進(jìn)我國(guó)產(chǎn)教融合、校企合作,進(jìn)而創(chuàng)建具有中國(guó)特色的現(xiàn)代職業(yè)教育制度和理論體系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一、凱興斯泰納為雙元職業(yè)教育制度奠基的原因
(一)德國(guó)社會(huì)對(duì)于青少年國(guó)民教育的迫切需求
德國(guó)統(tǒng)一之前,其國(guó)內(nèi)邦國(guó)林立,邦國(guó)之間的關(guān)稅制度以及其他限制性制度的存在,導(dǎo)致機(jī)器大工業(yè)的發(fā)展舉步維艱,德國(guó)工業(yè)革命晚于英、法半個(gè)至一個(gè)世紀(jì)才發(fā)生。但是,統(tǒng)一后的德國(guó)卻在短短30年的時(shí)間內(nèi)完成了英國(guó)用100多年才完成的工業(yè)化,從而創(chuàng)造了世界近現(xiàn)代史上最令人驚異的篇章。與德國(guó)工業(yè)化并行的城市化速度也非常迅猛[2],其中青少年尤其成為流入城市人口中的重要組成部分[3]。對(duì)于這些生活在城市的青少年來(lái)說(shuō),其14歲之前的國(guó)民學(xué)校教育大多屬于強(qiáng)迫性的書(shū)本知識(shí)教育。大多數(shù)青少年14歲從學(xué)校畢業(yè)后,20歲才能服兵役,在14~20歲這幾年的時(shí)間,他們或者做學(xué)徒或者混跡社會(huì),由于此時(shí)期來(lái)自農(nóng)業(yè)社區(qū)傳統(tǒng)的約束早已經(jīng)自覺(jué)或非自覺(jué)地解除了,但城市生活的秩序、倫理規(guī)范又尚未完全建立,加上德國(guó)統(tǒng)一后主要效仿法國(guó)自由貿(mào)易的做法,允許所有人自由從事貿(mào)易活動(dòng),行會(huì)也勿需再承擔(dān)監(jiān)管學(xué)徒培訓(xùn)的責(zé)任[4],在學(xué)徒培訓(xùn)成為純粹私人事務(wù),而師傅的資質(zhì)又缺乏有效監(jiān)管,學(xué)徒培訓(xùn)的任意性、隨意性增強(qiáng)的背景下,許多師傅或雇主將指導(dǎo)青少年社會(huì)行為的重大責(zé)任拋之腦后,由此導(dǎo)致這些整日被關(guān)在工場(chǎng)、車間或者游蕩在街頭的青少年,或者沉迷于不良的娛樂(lè)活動(dòng),或者由于普遍的營(yíng)養(yǎng)不良加上缺乏適當(dāng)?shù)膽敉忮憻挘粌H身體難以符合未來(lái)兵役的要求,精神上也缺乏對(duì)于各類社會(huì)規(guī)范、權(quán)威、美德等應(yīng)有的尊重。使以上情形更加惡化的是:此時(shí)期倡導(dǎo)階級(jí)斗爭(zhēng)哲學(xué)的社會(huì)民主青年運(yùn)動(dòng)出現(xiàn),吸引了中下階層青少年的關(guān)注,這一情況遂引起了社會(huì)精英階層極大的不安。
為了青少年的文明教化,同時(shí)也為了已有社會(huì)秩序的正常運(yùn)轉(zhuǎn),當(dāng)時(shí)德國(guó)的一些管理部門曾多次召開(kāi)青年問(wèn)題會(huì)議,同期,一些州也出臺(tái)了多種促進(jìn)青年教化的舉措。如1911年普魯士文化部長(zhǎng)特推出“青年教化”(youth cultivation,Jugendpflege)政策[5]。此外,德國(guó)一些城市的宗教或非宗教團(tuán)體、體育運(yùn)動(dòng)團(tuán)體、科學(xué)或工藝協(xié)會(huì)等也紛紛通過(guò)舉辦各種演講、體育賽事、劇院演出、博物館參觀等活動(dòng)來(lái)教育或教化青年。當(dāng)然,在這一潮流中,德國(guó)原有的繼續(xù)教育機(jī)構(gòu)重新被發(fā)現(xiàn),人們希望該類機(jī)構(gòu)也能有更大的作為。
(二)德國(guó)繼續(xù)教育機(jī)構(gòu)無(wú)力承擔(dān)青少年國(guó)民教育的重任
德國(guó)最早的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是由符騰堡州的宗教人士創(chuàng)辦的主日學(xué)校,1559年的文獻(xiàn)曾首次提及此類學(xué)校。最初創(chuàng)建主日學(xué)校的目的是為了對(duì)離開(kāi)初等國(guó)民學(xué)校的青少年實(shí)施宗教和道德教育。在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1712-1786)時(shí)期,一些主日學(xué)校開(kāi)始教授世俗性的讀、寫(xiě)、算知識(shí)。由于主日學(xué)校填補(bǔ)了青少年教育的某些空白,至18世紀(jì)末,該類學(xué)校不僅遍及德國(guó)廣大地區(qū),且一些州還頒布了強(qiáng)迫所有未婚青年參加主日學(xué)校學(xué)習(xí)的法令。當(dāng)然,除了主日學(xué)校,面對(duì)貿(mào)易和商業(yè)的不斷增長(zhǎng),德國(guó)一些州還出現(xiàn)了專門招收青少年入學(xué)的采礦、建筑、商業(yè)、造船、紡織等貿(mào)易和技術(shù)類學(xué)校,這些學(xué)校大多是在周日開(kāi)辦。1870年的普法戰(zhàn)爭(zhēng)為主日學(xué)校、周日貿(mào)易技術(shù)類學(xué)校轉(zhuǎn)變?yōu)槔^續(xù)教育學(xué)校提供了契機(jī)。“如果德國(guó)不想被鄰國(guó)超過(guò),就不僅僅要讓國(guó)內(nèi)最優(yōu)秀的那一批人不斷進(jìn)步,還要確保民眾作為一個(gè)整體不斷進(jìn)步。”[6]由于以上兩類學(xué)校與絕大多數(shù)青少年有著天然的聯(lián)系,被普遍認(rèn)為是開(kāi)展廣大青少年繼續(xù)教育的理想機(jī)構(gòu),于是,一些學(xué)校被更名為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
受原來(lái)主日學(xué)校的影響,宗教和道德教育依然是大部分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的主要內(nèi)容,除此之外,由于19世紀(jì)中期以來(lái)德國(guó)新人文主義思想的廣泛影響,它們推崇完整的、全人的教育,認(rèn)為普通教育要在普通學(xué)校,而不是為了某些特殊目的設(shè)立的學(xué)校中開(kāi)展[7],于是,一些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簡(jiǎn)單地變成了普通初等義務(wù)教育的延續(xù)。除了以上問(wèn)題,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還存在數(shù)量不足的問(wèn)題,如普魯士曾是德國(guó)繼續(xù)教育類學(xué)校發(fā)展較好的州,即便已經(jīng)大力發(fā)展了10多年,1910年普魯士各類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的招生數(shù)還不及該州14~18歲青少年的一半[8],其他州此類學(xué)校的短缺問(wèn)題更加嚴(yán)重;此外,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平均每周僅有6~8個(gè)小時(shí)的教學(xué)時(shí)間,且大多數(shù)安排在晚上,這對(duì)于勞動(dòng)了一天的學(xué)徒來(lái)說(shuō),效果很難保障。加上這些學(xué)校的課程內(nèi)容與學(xué)生的日常工作和理想追求聯(lián)系不緊密,大部分學(xué)徒并不感興趣,雇主和師傅對(duì)這類教育也不甚支持;另外,當(dāng)時(shí)德國(guó)只有薩克森、巴登、黑森等少數(shù)幾個(gè)州頒布了繼續(xù)教育類學(xué)校強(qiáng)迫入學(xué)的法令[9],致使該類學(xué)校入學(xué)人數(shù)很難保障。而同期的大多數(shù)貿(mào)易技術(shù)類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又因?qū)W⒂谛袠I(yè)技能和實(shí)用知識(shí)的傳授而忽視了自己所應(yīng)承擔(dān)的青少年教化和國(guó)民教育的責(zé)任。盡管從爭(zhēng)奪青少年的角度來(lái)看,當(dāng)時(shí)的許多政治家和社會(huì)保守人士積極呼吁開(kāi)辦更多的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以便為更多的青少年提供更為健康、全面的國(guó)民教育,但在現(xiàn)實(shí)困境面前,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究竟該如何辦學(xué)、如何發(fā)展,卻鮮少有人能夠給出理想的答案。
(三)凱興斯泰納在解決青少年國(guó)民教育問(wèn)題的同時(shí)為雙元制奠基
凱興斯泰納生于巴伐利亞州慕尼黑市。他曾擔(dān)任過(guò)小學(xué)、文科中學(xué)教師、大學(xué)教授和慕尼黑市學(xué)監(jiān)等職務(wù)。作為一個(gè)非常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的人,德國(guó)社會(huì)的巨變很早就讓他意識(shí)到青少年國(guó)民教育這一重大的時(shí)代課題。長(zhǎng)期以來(lái),他廣泛汲取各種思想的營(yíng)養(yǎng),早已經(jīng)為解決該問(wèn)題進(jìn)行了廣博的知識(shí)儲(chǔ)備。比如,他從盧梭、洛克、裴斯泰洛齊等思想家那里學(xué)到教育教學(xué)應(yīng)遵循青少年身心發(fā)展規(guī)律和認(rèn)識(shí)特點(diǎn),讓青少年更多地借助對(duì)于生活實(shí)踐的切身體驗(yàn)來(lái)獲得知識(shí)和經(jīng)驗(yàn)[10];德國(guó)心理學(xué)家愛(ài)德華德·斯普林格(Eduard Spranger)所提出的應(yīng)該從整體的以及從個(gè)人和其所處的歷史文化環(huán)境交互關(guān)系的角度思考性格形成,也曾深深地啟發(fā)了他[11];由于自17世紀(jì)中葉起,民族國(guó)家作為獨(dú)立單元屹立于世,盧梭提出了國(guó)家是社會(huì)契約,也即公意的產(chǎn)物,國(guó)家代表著全體人結(jié)合而成的公共人格和道德,因此是最高道德價(jià)值的體現(xiàn)。只有國(guó)家辦學(xué)才能培養(yǎng)良好的國(guó)民,之后理想的社會(huì)和國(guó)家才能實(shí)現(xiàn)。盧梭的觀點(diǎn)為凱興斯泰納奠定了思想的底色[12];除此之外,社會(huì)學(xué)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喬治·塞謬爾(Georg Simmel)等人也從多方面對(duì)凱興斯泰納思想的形成有所啟發(fā)[13]。1895年,一個(gè)偶然的機(jī)會(huì),他被提升為慕尼黑市學(xué)監(jiān)(school inspector)和皇家學(xué)校委員會(huì)委員(royal school commissioner),該職位不僅激發(fā)了他進(jìn)一步改革初中等教育的愿望,也為他從更廣闊的視角思考并解決青少年的國(guó)民教育、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和學(xué)徒制等問(wèn)題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提供了絕佳時(shí)機(jī)。此外,凱興斯泰納在理論和實(shí)踐方面的努力也為雙元制的出現(xiàn)營(yíng)造了有利的氛圍,1969年的《職業(yè)培訓(xùn)法案》就是在此基礎(chǔ)上出臺(tái)的。
二、凱興斯泰納的理論為雙元職業(yè)教育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
(一)國(guó)民教育的本質(zhì)與實(shí)現(xiàn)的可能性
與赫爾巴特提出的“德行是整個(gè)教育目的的代名詞”[14]類似,采擷盧梭國(guó)民教育思想精髓的凱興斯泰納,也將倫理道德作為教育的最高目標(biāo),只是與赫爾巴特更為偏重抽象的人類道德品質(zhì)的養(yǎng)成不同,凱興斯泰納更多地將倫理道德國(guó)家以及如何創(chuàng)建該類國(guó)家作為整個(gè)教育學(xué)的基礎(chǔ)。凱興斯泰納認(rèn)為,文明法制國(guó)家是人類的最高理想或是人類至高無(wú)上的外在倫理財(cái)富,它是一種基于人類心理本能而產(chǎn)生的科學(xué)的、理想的組織,只是由于人類的某些缺陷,這樣的國(guó)家是不可能輕易實(shí)現(xiàn)的。他與約翰·杜威一樣非常看重審慎與系統(tǒng)的教育對(duì)于實(shí)現(xiàn)以上目標(biāo)的重要價(jià)值,“只要人類能夠建立一種以克服這些缺陷為目的的國(guó)民教育,這一理想國(guó)家組織的實(shí)現(xiàn)就是可望而又可及的”[15]。但究竟什么才是凱興斯泰納心目中理想的國(guó)民教育呢?由于凱興斯泰納將真正的“國(guó)民”看作是忘我地、忠心耿耿地為達(dá)到和實(shí)現(xiàn)倫理國(guó)家目標(biāo)而獻(xiàn)身的人,因此他提出國(guó)民教育就是國(guó)家信念教育,“其實(shí)質(zhì)就是培養(yǎng)人們將個(gè)人利益置于集體利益之中的教育”[16]。盡管他認(rèn)識(shí)到國(guó)民教育是一切教育問(wèn)題中最最艱巨的任務(wù),但是凱興斯泰納同時(shí)也指出該教育并非如想象中的那么困難。因?yàn)閺娜祟惖钠毡樘煨猿霭l(fā),滿足單個(gè)人物質(zhì)和精神本能的所有活動(dòng)都具有普遍性,而在這之上的個(gè)人道德目標(biāo)與國(guó)家倫理目標(biāo)也具有相互依存性,即在個(gè)人道德目標(biāo)得到實(shí)現(xiàn)的同時(shí),也必然在為實(shí)現(xiàn)普遍目標(biāo)貢獻(xiàn)力量。換句話說(shuō),所有教育機(jī)構(gòu)在推動(dòng)個(gè)人道德目標(biāo)實(shí)現(xiàn)的過(guò)程中,也在同時(shí)推動(dòng)國(guó)家道德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
(二)國(guó)民教育的實(shí)現(xiàn)路徑
基于長(zhǎng)期的生活經(jīng)驗(yàn)和對(duì)于人性的觀察,凱興斯泰納提出利己主義是人類行為的主要?jiǎng)訖C(jī),人總是對(duì)與自己利益密切相關(guān)的事務(wù)更感興趣。考慮到有能力且有意愿承擔(dān)國(guó)家的各種職務(wù)是國(guó)民立足的根本,凱興斯泰納提出為培養(yǎng)理想國(guó)民而開(kāi)辦的學(xué)校應(yīng)該圍繞著受教育者未來(lái)可能從事或目前正在從事的職業(yè)活動(dòng)來(lái)設(shè)計(jì),因?yàn)檫@樣才更容易引起學(xué)生的興趣和參與的積極性。凱興斯泰納之所以如此設(shè)計(jì)國(guó)民學(xué)校的課程,其意在于讓青少年在職業(yè)勞動(dòng)中,通過(guò)勞動(dòng),獲得勞動(dòng)技能,為其將來(lái)從事某一職業(yè)打下良好基礎(chǔ),此外,通過(guò)這樣的勞動(dòng),喚起青少年真正的勞動(dòng)熱情,使他們收獲細(xì)心、徹底和嚴(yán)謹(jǐn)?shù)膭趧?dòng)習(xí)慣,并在個(gè)人品德方面有所提高[17],這也正是凱興斯泰納借助職業(yè)勞動(dòng)塑造青少年性格,將該類學(xué)校命名為“勞作學(xué)校”的由來(lái)。
當(dāng)然,凱興斯泰納認(rèn)為完成以上任務(wù)的勞作學(xué)校僅僅是在實(shí)施低層次的國(guó)民教育,因?yàn)檫€有兩個(gè)更為重要的任務(wù)需要?jiǎng)谧鲗W(xué)校去完成,而只有同時(shí)完成彼此依賴、相互促進(jìn)的三重任務(wù),國(guó)民學(xué)校才可能真正推動(dòng)國(guó)家倫理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凱興斯泰納所謂的第二重任務(wù)就是要求勞作學(xué)校在學(xué)生共同的勞動(dòng)中,借助勞動(dòng)集體的組建和集體原則的實(shí)施,培養(yǎng)學(xué)生關(guān)心他人、自愿為他人服務(wù)的意識(shí),讓學(xué)生學(xué)會(huì)按照正義與公理的準(zhǔn)則,去解決哪怕是最小的利益爭(zhēng)端,同時(shí)喚起學(xué)生對(duì)一切行為負(fù)責(zé)的責(zé)任感,讓學(xué)生明白自己所從事的勞動(dòng)與集體利益緊密相連并自覺(jué)養(yǎng)成為集體利益服務(wù)的習(xí)慣。而他所謂的第三重任務(wù),就是要求勞作學(xué)校借助以上活動(dòng),讓學(xué)生體會(huì)個(gè)人與其所從事的工作之間,以及個(gè)人與更廣大的社會(huì)之間的關(guān)系,在完善自身人格的同時(shí),推動(dòng)更大范圍內(nèi)倫理國(guó)家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18]。
凱興斯泰納指出,由于性格最終是通過(guò)各種行為塑造的,人們對(duì)待勞動(dòng)的每一種態(tài)度和行為都會(huì)在意志中留下印記,因此勞作學(xué)校應(yīng)該力求使學(xué)生的所有行為都立足于周密的思考、極為認(rèn)真和誠(chéng)實(shí)態(tài)度的基礎(chǔ),這樣才可能為學(xué)生良好性格的形成以及性格的倫理化營(yíng)造有利的環(huán)境[19]。凱興斯泰納的以上設(shè)計(jì),與約翰·杜威所提到的讓學(xué)生在雛形的學(xué)校社會(huì)中掌握民主主義社會(huì)最基本的原則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他們幾乎是借助同樣的機(jī)構(gòu)、采取同樣的手段,來(lái)追求不一樣的理想社會(huì)的目標(biāo)。
(三)學(xué)徒教育與繼續(xù)教育的聯(lián)合是實(shí)現(xiàn)國(guó)民教育目標(biāo)的最重要路徑
凱興斯泰納將初等教育、學(xué)徒教育和繼續(xù)教育看作是連續(xù)的教育過(guò)程中的不同階段。針對(duì)當(dāng)時(shí)德國(guó)初等教育階段絕大多數(shù)國(guó)民學(xué)校都是典型的書(shū)本學(xué)校,國(guó)民教育的三重任務(wù)難以完成,他提出,應(yīng)該將此階段的書(shū)本學(xué)校轉(zhuǎn)變?yōu)閯谧鲗W(xué)校,專業(yè)的、系統(tǒng)的勞動(dòng)課應(yīng)該進(jìn)入這些學(xué)校的課表,不拘形式的各類實(shí)習(xí)場(chǎng)所,如工廠、苗圃、廚房、縫紉間、實(shí)驗(yàn)室等應(yīng)該成為學(xué)校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培養(yǎng)心智技能的語(yǔ)言、算術(shù)、歷史、地理、自然、繪畫(huà)等課程也是必須開(kāi)設(shè)的。心智教學(xué)與勞動(dòng)教學(xué)結(jié)合得越緊密,越有利于學(xué)生、學(xué)校的發(fā)展以及國(guó)民教育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
德國(guó)的工場(chǎng)、企業(yè)以及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是國(guó)民教育的主陣地。凱興斯泰納認(rèn)為,從財(cái)政、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發(fā)展的角度來(lái)看,讓所有學(xué)徒離開(kāi)工場(chǎng)、車間進(jìn)入國(guó)家專門開(kāi)辦的“勞作學(xué)校”是不現(xiàn)實(shí)的。最理想的辦法是:一方面,讓青年人仍然在師傅或雇主的管轄之下接受學(xué)徒教育,因?yàn)樵趧趧?dòng)實(shí)踐中進(jìn)行技能培訓(xùn)本身有著得天獨(dú)厚的優(yōu)勢(shì);另一方面,將現(xiàn)有的繼續(xù)教育機(jī)構(gòu)改造成勞作學(xué)校,讓它成為初等國(guó)民學(xué)校的繼續(xù)教育機(jī)構(gòu),且兼具強(qiáng)迫性質(zhì),讓所有不滿18歲的學(xué)徒每周抽出一定時(shí)間在此接受教育,此舉無(wú)疑將會(huì)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凱興斯泰納進(jìn)一步指出,為了激發(fā)青少年的興趣,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的課程務(wù)必圍繞學(xué)徒正在從事的活動(dòng)開(kāi)設(shè),且其理論課程的開(kāi)設(shè)務(wù)必與學(xué)徒期的工作同步,而其他的商業(yè)、科學(xué)、藝術(shù)和道德等的教學(xué)務(wù)必與學(xué)徒的職業(yè)活動(dòng)密切相關(guān)。這樣做的目的絕不僅是為了提升青少年的技能,而是旨在讓其成為學(xué)徒更為寬泛的國(guó)民教育的基礎(chǔ)或始點(diǎn)[20]。為了保證良好的教學(xué)效果,凱興斯泰納要求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要為學(xué)生的各類職業(yè)活動(dòng)準(zhǔn)備必要且良好的工具和設(shè)備,聘請(qǐng)經(jīng)驗(yàn)豐富的“師傅”和熟練工人,他們要能夠擔(dān)當(dāng)起實(shí)踐與理論教學(xué)的重?fù)?dān)。
凱興斯泰納以職業(yè)活動(dòng)為核心的國(guó)民教育設(shè)計(jì),將初等學(xué)校的普通與職業(yè)教育、學(xué)徒的實(shí)踐培訓(xùn)與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的理論學(xué)習(xí)連接起來(lái),此舉不僅改變了德國(guó)初等教育、繼續(xù)教育和學(xué)徒教育的舊面貌,也在理論上使雙元職業(yè)教育制度有了出現(xiàn)的可能。
三、凱興斯泰納的實(shí)踐為雙元職業(yè)教育制度奠定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
(一)力促慕尼黑學(xué)徒培訓(xùn)與繼續(xù)教育的聯(lián)姻
當(dāng)凱興斯泰納提出國(guó)民教育思想的時(shí)候,他的想法很快引起了許多知識(shí)分子的不滿。首先,人們對(duì)于他所提出的“國(guó)民教育”概念產(chǎn)生了誤解,他們攻擊他試圖培養(yǎng)盲目順從的國(guó)民。其次,由于普通教育與職業(yè)教育之間的鴻溝,占據(jù)當(dāng)時(shí)德國(guó)教育界主流的是席勒、洪堡等新人文主義思想家的思想,而凱興斯泰納以職業(yè)勞動(dòng)為核心的教育設(shè)計(jì),不僅表面上與以上理想相悖,還有將普通學(xué)校轉(zhuǎn)變?yōu)槁殬I(yè)學(xué)校之嫌,其改革遭遇巨大阻力在所難免。
除了以上阻礙之外,從工場(chǎng)企業(yè)和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的角度來(lái)看,盡管1897年德意志《手工業(yè)法》(the Handicraft Act)重新恢復(fù)了行會(huì)傳統(tǒng),但是由于手工業(yè)師傅或雇主的經(jīng)濟(jì)邏輯并沒(méi)有改變,他們對(duì)學(xué)徒的理論知識(shí)、道德、國(guó)民精神等的培養(yǎng)漠不關(guān)心,更不愿意讓學(xué)徒脫離工作崗位參加繼續(xù)教育;此外,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的數(shù)量、教學(xué)設(shè)施、機(jī)器設(shè)備、師資嚴(yán)重不足等問(wèn)題也一時(shí)難以解決。
為克服上述阻礙,凱興斯泰納意識(shí)到積極爭(zhēng)取地方政府和行會(huì)支持的重要性。他主動(dòng)游說(shuō)慕尼黑的市鎮(zhèn)官員,他從個(gè)人、企業(yè)、工業(yè)界、社區(qū)和國(guó)家利益的息息相關(guān)性談起,談到個(gè)人不僅是學(xué)徒,更是國(guó)民,個(gè)人與他人以及國(guó)家利益息息相關(guān)。此外,為了獲得更為關(guān)鍵的各行業(yè)行會(huì)的理解和實(shí)際支持,他又從一個(gè)行會(huì)游說(shuō)到另一個(gè)行會(huì)。他從行會(huì)師傅與雇主自身利益入手,提出僅讓學(xué)徒掌握靈巧的技術(shù)是絕對(duì)不夠的,因?yàn)殪`巧的技術(shù)只有在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尚品德的基礎(chǔ)上才更有利于學(xué)徒自身和行業(yè)的發(fā)展,如果師傅或雇主忽略學(xué)徒的洞察力和品德教育,或許短期內(nèi)可以盈利,但是長(zhǎng)期是難以為繼的。此外,一個(gè)完全由利欲、金錢和機(jī)器統(tǒng)治的國(guó)家,一旦土地財(cái)富耗盡,人口過(guò)于稠密,就注定不可避免地走向毀滅,而道德的國(guó)家才是行業(yè)繁榮發(fā)展的最終保障。除了力勸行會(huì)師傅們積極送自己的學(xué)徒參加學(xué)習(xí)之外,為了更好地調(diào)動(dòng)他們的積極性,凱興斯泰納還努力在繼續(xù)學(xué)校的辦學(xué)模式上有所創(chuàng)新。比如在當(dāng)時(shí)的巴登州和較大的城鎮(zhèn)萊比錫等地,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根據(jù)當(dāng)?shù)氐穆殬I(yè)群組開(kāi)展教學(xué)的情況,借鑒它們的做法,凱興斯泰納提出慕尼黑的每一個(gè)專業(yè)行會(huì)都應(yīng)有自己行業(yè)的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允許每一個(gè)專業(yè)行會(huì)參與行業(yè)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的課程設(shè)計(jì)與管理工作。
(二)慕尼黑體系形成且被國(guó)內(nèi)外同行效仿
1900年是凱興斯泰納思想開(kāi)始結(jié)出碩果的一年。這一年,慕尼黑屠夫、烘培師、鞋匠、煙囪師、理發(fā)師5大行會(huì)率先采納了凱興斯泰納的建議,創(chuàng)建了各自的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之后,木工、玻璃工、花園工、糖果商、馬車制造商、鐵匠等行業(yè)也及時(shí)跟進(jìn),擁有了自己的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行會(huì)師傅們的主動(dòng)參與,不僅較好地解決了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數(shù)量不足的問(wèn)題,且由于行會(huì)愿意主動(dòng)為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派遣高手師傅或技術(shù)工人作為帶薪教師,為學(xué)校的實(shí)踐教學(xué)提供免費(fèi)的材料等,與此同時(shí),慕尼黑市政當(dāng)局也逐步認(rèn)識(shí)到繼續(xù)教育的重要性,愿意承擔(dān)學(xué)校的建筑、教師工資、教具、機(jī)器和工具等的費(fèi)用……困擾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辦學(xué)的諸多問(wèn)題迎刃而解,加快了慕尼黑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的出現(xiàn)。1902年,慕尼黑已有22所這類學(xué)校,1906年有40所,1907年達(dá)到46所。到1912年,這類學(xué)校已達(dá)到54所,共有534名教師和9284名學(xué)徒[21]。慕尼黑新創(chuàng)設(shè)的或改造原有機(jī)構(gòu)建立的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致力于將先前割裂的理論、實(shí)踐知識(shí)與切實(shí)可行的國(guó)民教育結(jié)合起來(lái),其教育教學(xué)取得了較好效果;此外,1897年,在多方努力下,慕尼黑還率先規(guī)定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強(qiáng)制入學(xué),要求所有雇主必須同意學(xué)徒在周末離開(kāi)工作崗位一整天,或兩個(gè)半天去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接受教育[22]。慕尼黑的繼續(xù)教育系統(tǒng)因之成為滿足學(xué)徒公共教育、工業(yè)需求和社會(huì)需求的典范,被稱為慕尼黑體系。慕尼黑體系的形成以及同期凱興斯泰納論文的獲獎(jiǎng)進(jìn)一步提高了他的聲譽(yù),不僅國(guó)內(nèi)同行,來(lái)自匈牙利、瑞典、荷蘭、俄羅斯、丹麥、奧地利、美國(guó)等國(guó)外同行演講的邀請(qǐng)不斷,凱興斯泰納在收獲巨大國(guó)際聲望的同時(shí),他主導(dǎo)的慕尼黑體系也逐步在德國(guó)以及其他國(guó)家和地區(qū)出現(xiàn)。
四、德國(guó)雙元職業(yè)教育制度的形成
在慕尼黑體系的影響下,德國(guó)形成了學(xué)徒制與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密切合作的職業(yè)教育系統(tǒng),且它還是強(qiáng)迫性質(zhì)的。盡管1969年雙元職業(yè)教育制度在國(guó)會(huì)創(chuàng)建的過(guò)程具有極大的偶然性,但不可否認(rèn)的是:正是立足于凱興斯泰納所奠定的基礎(chǔ),德國(guó)出現(xiàn)的是雙元職業(yè)教育制度,而不是其他[23]。
(一)慕尼黑體系決定了戰(zhàn)后德國(guó)職業(yè)教育的基本形態(tài)
首先,從20世紀(jì)初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為了推動(dòng)各地的學(xué)徒更好地參加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的學(xué)習(xí),德國(guó)各州均做出了許多努力,如慕尼黑所在的巴伐利亞州最早頒布專門法律,要求還沒(méi)有變?yōu)槔^續(xù)教育學(xué)校的主日學(xué)校轉(zhuǎn)變?yōu)槊恐転閷W(xué)徒至少進(jìn)行6小時(shí)授課的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同期,其他州或者效仿巴伐利亞州的做法,或者提供更多補(bǔ)貼鼓勵(lì)創(chuàng)建新的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如普魯士大力提升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的補(bǔ)貼,1908年普魯士為各類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提供的補(bǔ)貼為300萬(wàn)馬克,該補(bǔ)貼是1885年補(bǔ)貼的6倍,同期普魯士此類學(xué)校數(shù)量從664所猛增到2100所,其接納的學(xué)徒也從5.8萬(wàn)名提高到36萬(wàn)名;1906年,維騰堡州通過(guò)了一項(xiàng)法律,要求每個(gè)人口超過(guò)5000人的城鎮(zhèn)為所有學(xué)徒組建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德國(guó)各地推動(dòng)學(xué)徒接受繼續(xù)教育的做法還進(jìn)一步影響到了德語(yǔ)區(qū)的其他國(guó)家和地區(qū),如瑞士的蘇黎世、奧地利的維也納等[24]。
其次,此時(shí)期的地方強(qiáng)迫立法還帶動(dòng)了國(guó)家層面的強(qiáng)迫立法,確保了不足18歲的所有青少年都能接受繼續(xù)教育。如1919年的《德意志帝國(guó)憲法》,即“魏瑪憲法”,其中第145條以國(guó)家立法的形式規(guī)定:從初等學(xué)校完成8年義務(wù)教育的學(xué)生必須參加強(qiáng)迫的、普遍的繼續(xù)學(xué)校學(xué)習(xí),直至其18歲[25]。“魏瑪憲法”是第一次將強(qiáng)迫性的繼續(xù)教育推廣到全德的有益嘗試,標(biāo)志著該類學(xué)校已經(jīng)成為與學(xué)徒教育密切合作的教育機(jī)構(gòu)。納粹時(shí)期繼續(xù)延續(xù)以上做法,只是在該時(shí)期,“職業(yè)學(xué)校”(Berufsschule)或“強(qiáng)迫的職業(yè)學(xué)校”(Berufsschulpflicht)取代繼續(xù)教育類學(xué)校成為廣泛使用的新稱呼。除了以上稱呼上的變化,20世紀(jì)初成立的德國(guó)技術(shù)教育委員會(huì)(The German Committee for Technical Education,DATSCH)對(duì)繼續(xù)教育學(xué)校的專業(yè)設(shè)置、課程開(kāi)設(shè)、教材編寫(xiě)、教學(xué)方法等也進(jìn)行了不斷的統(tǒng)一規(guī)范……經(jīng)過(guò)幾十年的發(fā)展,德國(guó)企業(yè)學(xué)徒參加規(guī)范的職業(yè)學(xué)校學(xué)習(xí)早已經(jīng)成為一種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如1953年,西德境內(nèi)共有6000余所職業(yè)學(xué)校,170余萬(wàn)名15~18歲的青少年在此學(xué)習(xí)。在這些學(xué)生當(dāng)中,有相當(dāng)高的比例同時(shí)參加了學(xué)徒培訓(xùn)[26]。
(二)雙元職業(yè)教育制度是在改造慕尼黑體系基礎(chǔ)上形成的
受慕尼黑體系的影響,德國(guó)職業(yè)培訓(xùn)主要是以行業(yè)為基礎(chǔ)實(shí)施。進(jìn)入1960年代,西德在歷經(jīng)10多年經(jīng)濟(jì)高速增長(zhǎng)后進(jìn)入衰退期,加之蘇聯(lián)衛(wèi)星上天事件強(qiáng)化了人們對(duì)于國(guó)家安全和教育質(zhì)量的持續(xù)擔(dān)憂,以及民主化浪潮使得教育機(jī)會(huì)均等的呼聲不斷高漲……在新的形勢(shì)下,由行業(yè)或企業(yè)負(fù)責(zé)招收、培訓(xùn)學(xué)徒和組織考試的方式如何顧及社會(huì)的總體需要?國(guó)家應(yīng)不應(yīng)該參與職業(yè)教育與培訓(xùn)的管理?如何保障不同地區(qū)青年人的平等教育和培訓(xùn)需求?如何規(guī)范不法行業(yè)或企業(yè)的培訓(xùn)行為?如何確保行業(yè)或企業(yè)培訓(xùn)的質(zhì)量標(biāo)準(zhǔn)?各州職業(yè)學(xué)校如何配合行業(yè)的培訓(xùn)?作為具有悠久契約傳統(tǒng)和法律精神的國(guó)度,從二戰(zhàn)結(jié)束至1969年的20余年間,各利益集團(tuán)圍繞以上問(wèn)題,已經(jīng)開(kāi)展了無(wú)數(shù)討論[27],且還向國(guó)會(huì)遞交了三份職業(yè)教育立法提案。
但是,受制于德國(guó)《基本法》對(duì)于聯(lián)邦政府插手各類教育的限制,加上其他復(fù)雜的原因,前兩份提案在聯(lián)邦政府插手行業(yè)企業(yè)職業(yè)培訓(xùn)方面都敗下陣來(lái),而如何大膽地將行業(yè)企業(yè)學(xué)徒培訓(xùn)和州管理的職業(yè)學(xué)校的教育聯(lián)結(jié)成完整的系統(tǒng),至少在第一份提案遞交時(shí),還沒(méi)有人能夠提出。事情的轉(zhuǎn)機(jī)發(fā)生在1964年7月10日,基于職業(yè)教育的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shí),德國(guó)教育委員會(huì)在一份評(píng)估報(bào)告中首次提到了“雙元”的概念,報(bào)告認(rèn)為行業(yè)企業(yè)和職業(yè)學(xué)校肩負(fù)著共同的責(zé)任,它們之間應(yīng)該是平等的伙伴關(guān)系,兩類機(jī)構(gòu)應(yīng)共同舉行期末考試,同時(shí)結(jié)束教學(xué)和培訓(xùn)[28]。第二份提案采納了教育委員會(huì)的該項(xiàng)建議,但是該提案隨即也在國(guó)會(huì)引發(fā)了激烈的論爭(zhēng),人們就聯(lián)邦政府是否有資格插手州政府傳統(tǒng)管理的領(lǐng)域?如何在聯(lián)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間劃分管理權(quán)限?聯(lián)邦法律究竟應(yīng)該規(guī)范職業(yè)教育和培訓(xùn)的哪些領(lǐng)域等論爭(zhēng)激烈,最后依然是沒(méi)有結(jié)果。直至1969年,此時(shí)期的聯(lián)邦立法者抓住《基本法》對(duì)聯(lián)邦政府資助、管理企業(yè)培訓(xùn)的法律障礙最終消除、黨派格局有利于職業(yè)教育法案通過(guò)的絕佳時(shí)機(jī),在繼續(xù)保留行業(yè)主導(dǎo)主要特征的基礎(chǔ)上,在第三份提案中直接增加了國(guó)家對(duì)于行業(yè)培訓(xùn)實(shí)施宏觀規(guī)范和引導(dǎo)的規(guī)定,并及時(shí)將雙元概念引入法案,且最終推動(dòng)了該法案的出臺(tái),雙元職業(yè)教育制度得以正式出現(xiàn)。
作為蜚聲世界的一種教育制度,德國(guó)雙元職業(yè)教育制度不僅較為完美地架起了企業(yè)培訓(xùn)和學(xué)校職業(yè)教育之間溝通的橋梁,且由于它的強(qiáng)迫教育特征,保證了絕大多數(shù)青年在18歲時(shí)都具備了一定的職業(yè)技能,從而推動(dòng)了德國(guó)技能型社會(huì)的創(chuàng)建。可以說(shuō),作為高質(zhì)量職業(yè)教育的制度保障,單從產(chǎn)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角度來(lái)看,德國(guó)雙元職業(yè)教育制度也是包括我國(guó)在內(nèi)的世界許多國(guó)家政府和民眾非常認(rèn)可的一種制度形式。追蹤雙元職業(yè)教育制度產(chǎn)生的理論與實(shí)踐淵源可以發(fā)現(xiàn):
首先,該制度的出現(xiàn)離不開(kāi)凱興斯泰納所做出的歷史性貢獻(xiàn)。作為一個(gè)終身致力于推動(dòng)德國(guó)實(shí)現(xiàn)文明富強(qiáng)這一最高倫理目標(biāo)的教育家,凱興斯泰納自覺(jué)地將自己的教育理論、教育實(shí)踐與國(guó)家的前途命運(yùn)緊密相連,他的國(guó)民教育理論,不僅使雙元職業(yè)教育制度有了創(chuàng)建的可能,且他還以自己的教育實(shí)踐,強(qiáng)力推動(dòng)了雙元制所立足的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慕尼黑體系的產(chǎn)生。可以說(shuō),沒(méi)有凱興斯泰納的奠基,德國(guó)在很大可能性上是不可能出現(xiàn)雙元職業(yè)教育制度的。
其次,德國(guó)雙元職業(yè)教育制度的出現(xiàn)除了得到德國(guó)州和聯(lián)邦政府的支持之外,行會(huì)(后演變?yōu)樯虝?huì))的作用自始至終都是不可低估的。與英法等國(guó)不同,德國(guó)職業(yè)教育領(lǐng)域最為獨(dú)特的地方是行會(huì)力量在近代被保留了下來(lái),在凱興斯泰納時(shí)期,正是行會(huì)的果斷插手才使得學(xué)徒培訓(xùn)和繼續(xù)學(xué)校教育出現(xiàn)了真正的融合,而雙元制也是在保留行業(yè)主導(dǎo)(occupation-led)特征的基礎(chǔ)上完善而成的[29]。目前,行業(yè)主導(dǎo)依然是雙元職業(yè)教育最重要的特征,是德國(guó)高質(zhì)量職業(yè)教育的堅(jiān)強(qiáng)保障。
推動(dòng)產(chǎn)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深入發(fā)展,進(jìn)而構(gòu)建具有中國(guó)特色的現(xiàn)代職業(yè)教育制度與理論體系,不僅需要像凱興斯泰納一樣卓越的教育理論家的高屋建瓴和傾情奉獻(xiàn),更需要有德國(guó)行會(huì)一樣的社會(huì)機(jī)構(gòu)的積極支持、奮力推動(dòng),此外,政府的正確引導(dǎo)和規(guī)范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只有多種因素的完美結(jié)合,以上目標(biāo)才能更快更好的出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