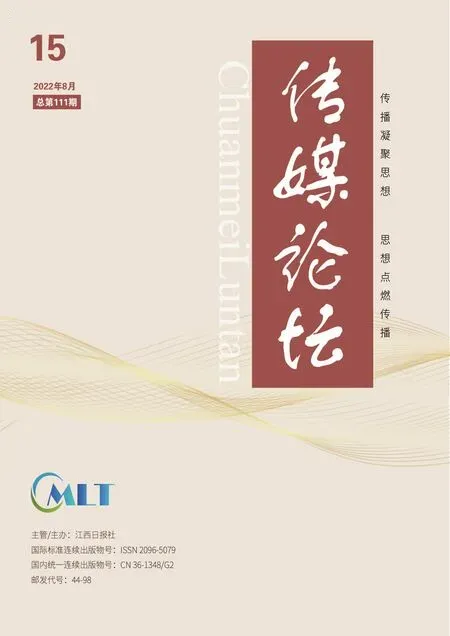新媒介環境對兒童社會化的消極影響研究
趙佳璐
一、研究背景與意義
從個體出生起,我們就開始了與社會的互動,開啟了社會化進程。兒童時期作為個人成長的一個初始化時期,為人類成長與發展起到一個鋪墊的基礎作用。大眾媒介飛速發展,波茲曼曾提出童年正在消逝,現代技術尤其是新媒體技術成為主要原因。與我們及我們的父輩不同,現如今成長起來的兒童是生長在新媒體環境中的原始居民,從出生起便受到媒介的熏陶,大眾傳媒成為影響兒童社會化的重要因素。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兒童,都不由自主地將媒介情景帶入到生活情景中,他們對于日常生活、社會認知、行為規范等都有著異于父輩的認識。以兒童在社會交往的媒介使用情況為例,不少兒童注冊了自己的社交賬號,可以學會搶紅包、刷視頻等簡單媒介行為。但與成人相比,他們并不具備對所點擊與滑動的內容的認知,缺乏對虛擬世界的正確認知。
隨著互聯網的飛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到了這一問題,對兒童社會化問題展開了討論,進一步豐富了相關理論研究。基于此指導,本文將視角轉向現實問題的研究,關注新媒介對于兒童社會化的影響。兒童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處于形成價值觀的關鍵階段,但卻缺乏自主選擇的能力,易于被外界影響與塑造。因而分析電子媒介在兒童成長過程中的消極影響,并對如何避免新媒介過度侵蝕兒童提出針對性對策具有重要意義。
二、兒童在新媒介環境中的社會化
處于不同社會化階段的個體所受到的客觀影響因素不同,與成人相比,兒童的社會化主要發生于家庭和學校,但電子技術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用于家庭和學校的場景,無形之中影響著兒童社會化的過程。
(一)新媒介消融了兒童與成人的界限
與印刷媒介相比,電視因視覺符號的直觀性而將場景信息輕松傳給兒童,降低了兒童編碼解碼的難度,以影像符號打開了新的視覺世界,直接作用于感官,帶來直觀的感受,且電視作為一種全家都可觀看的媒介,初步將兒童與成人拉入一個共同的情景中。兒童可以學習電視中的社會場景,跟隨父母窺探大人世界的秘密。
而到了科技飛速發展的新媒介時期,各種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移動終端逐漸普及,簡單觸碰便可進入到一個近距離接觸的互動世界,其豐富性與多樣性讓兒童以一種互動的方式快速融入公共場景與私人場景之中,兒童仿佛無師自通地進入了成人的世界,暴露于成人話題之中。與此同時,卻加劇了兒童隱私暴露于公眾視野的風險。由于兒童缺乏對虛擬世界的正確認知,原本隱秘的后臺行為通過手指的簡單觸碰便招致圍觀,泄露私人信息于無形之中。與傳統電視不同的是,這樣一個智能設備因其屏幕大小等原因而更具私人因素,當兒童接觸到這樣一種私人網絡世界時,他們更容易被暴露于惡意傳播環境中。
(二)新媒介成為兒童學習娛樂的主要方式
現代快節奏的生活導致成年人工作壓力增大,鮮少有時間精力陪伴孩子,親子相處時間不斷壓縮,而手機、平板等智能設備成為替代父母照看孩子的幫手,讓孩子玩一會兒手機、看一會兒平板便可完成照看孩子的復雜任務。而現代智能手機等終端由之前的按鍵發展到現如今的觸摸,更符合孩子好奇探索的天性,因而智能設備成了兒童的精神保姆,陪伴孩子成長。
在兒童認知世界方面,新媒介提供了視覺與聽覺上的感受,其信息呈現方式符合兒童認知水平,不需要深刻理解便能輕松掌握,較傳統的講授、閱讀等方式有著先天的優勢。因而,新媒介成為家庭與學校傳播知識的重要方式。此外,一些搜索引擎的使用為兒童提供了一切問題的答案。兒童不需要過度思考,通過網絡便可以輕松獲得答案。新媒介的誕生符合兒童的認知水平,但卻使他們進一步喪失了學習的自主性。
三、新媒介對兒童成長的消極影響
現如今,技術的廣泛應用已讓兒童不可避免的成長在媒介環境之下,不管有意或是無意,現代兒童早早便開始了觸網。盡管家庭學校教育對兒童的成長起著基礎和引導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電子媒介對兒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危害。
(一)使用不當危害兒童身心健康
兒童處于身體發展的重要時期,本應戶外活動加強身體素質,但媒介技術的廣泛應用,已將孩子們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室內的電子設備上,局限于屏幕空間和久坐觀看電子設備造成不少兒童視力下降、身體素質低等問題。據調查顯示,我國的近視眼發病率呈上漲趨勢,而電子媒介已成為主要致病因素。
此外,兒童過度使用媒介會造成不同程度的媒介依存癥,嚴重影響兒童的心理健康。電子媒介的界面、視頻、游戲等都對兒童有種極強的吸引力,再加上兒童難以對自我行為進行約束,所以很容易沉迷游戲世界帶來的刺激,長此以往,會增加兒童的焦慮感,制約兒童養成健全人格。并且,兒童難以區分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習慣于網絡世界的繁榮從而對現實生活產生不適感,降低對現實生活的期待,減弱現實行為的責任感。
(二)刻板成見導致兒童認知偏差
刻板成見指的是人們對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簡單化的觀念和印象,為人們認識現實世界提供簡單的標準。對于兒童來說,處于認知初步形成的萌芽時期,媒介中的角色觀念會進一步加深兒童對于現實生活中的理解,但也會進一步阻礙兒童對于新事物的認知。媒介中的刻板成見內容會影響兒童對于社會的期望值。比如媒體片面報道老人倒地路人冷漠不扶的新聞,兒童長期接觸此類內容降低內心的善良值,他會認為不應該去扶老人,社會對于不尊重老人、見死不救是認可的,那么當日常生活中遇到相似場景時,兒童出現角色認知的模糊,對現實理解便會偏離正確的軌道。
兒童對于現實的理解很大一部分來自網絡,而媒介中的人物形象容易使兒童產生先入為主的觀念,對于兒童來說容易形成社會角色的刻板成見,用在媒介接觸到的觀念與他人交往,難以找到身份認同感,并面對現實社會的規范時難以調節自己的行為。
(三)暴力內容增加兒童模仿風險
電視節目大多是迎合成年人的喜好制作,其中難免會涉及暴力因素與鏡頭。當兒童與家長共同觀看時,涉及血腥暴力鏡頭時家長可以阻止兒童接觸相關場景,但當兒童獨自接觸媒介時,不可避免地會目睹暴力場景。國外業界對電視內容實行分級制度,根據節目內容和不同年齡段確立劃分標準。我國尚未實行分級制度,部分移動端青少年模式的施行還不完善。網絡媒介將兒童與成人暴露于相似場景之中,兒童無法生活在真空之中,對外部世界消極現象的承受力與認知度有限。
觀看暴力場景的危害主要有兩點:一是引發兒童內心的精神恐懼,降低心理成熟度,對精神造成傷害;二是兒童在無法分辨鏡頭中暴力鏡頭的傷害性時,容易模仿鏡頭中的行為。兒童混淆虛擬與網絡世界,無法轉換角色,在從眾心理和不成熟的心智影響下進行不良模仿,對自我、家庭與社會造成危害。
四、智媒時代兒童如何應時而變
智媒時代下,兒童作為網絡媒介的原住民其行為和認知已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影響,但從現如今的社會環境來看,兒童批判性思維的缺失造成媒介素養較低,無法規避網絡世界的風險。因此必須通過家庭、學校以及媒介三方的共同努力,引導兒童在智媒時代合理運用新媒介。
(一)家校合作:分享與指導雙管齊下
新媒介的出現降低了家庭對于兒童社會化的權威值,但家庭作為兒童社會化的基礎場所始終對兒童發展成長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智媒時代下,家長應當摒棄過去強制限制兒童使用新媒介的方式,而是滿足兒童的求知欲,采取引導的態度幫助兒童合理認識媒介以及媒介中的虛擬場景。另外,針對兒童的年齡制定合理的媒介使用策略,避免兒童對媒介過度依賴,將新媒介使用與書籍閱讀結合起來,培養孩子自主學習獨立思考的能力。
如果說家庭是兒童社會化的第一場所,那么學校便是兒童社會化的第二場所。學校作為教育的場所,對兒童媒介素養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國基礎媒介素養課程覆蓋不全面,無法系統地培養兒童媒介素質。在網絡發達的今天,國家應當重視媒介教育問題,盡早推進相應系統課程的研發。此外,學校可根據兒童年齡認知水平設置相應的媒介接觸課程,教師也可利用豐富的網絡資源對課程進行補充,引導兒童提高學習自主性,增強思辨能力與創新能力。家庭與學校在兒童社會化進程中,承擔好引導與教育的角色,可以較大程度呵護兒童的成長。
(二)媒介制作;把握界限呵護童年
新媒介在技術和內容兩個維度影響著兒童的社會化進程,低門檻與人性化是技術進步的必然,具有不可逆轉性,但內容方面可以進一步優化,生產出適合兒童的產品,盡可能降低負面傳播效果,呵護童年。
首先,媒介產品制作者應當重視兒童這一群體的個性與規律,協調產品內容“教”與“樂”的關系,寓教于樂,幫助兒童在娛樂的同時也能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具體來說,產品設計應當重視傳統美德的傳播,以通俗易懂且有趣的方式弘揚社會正義與社會道德,幫助兒童形成正確認知,規范自我行為。
其次,媒介產品設計之初應當設置相應的青年模式與防沉迷模式。兒童認知能力不夠,無法對自身行為進行限制,過度使用難免會有媒介依賴。比如游戲設置防沉迷的時間長,可以有效減少兒童的過度娛樂。我國不少游戲已經推出了防沉迷系統,可以從根源上降低媒介依賴。
最后,媒介制作者從成人角度思考兒童產品難免會出現主觀與片面的問題。節目可以適當吸引兒童參與媒介內容的制作,鼓勵兒童上傳自己的作品,注重兒童自身的表達,讓兒童能夠感受世界,與同齡人交往溝通,幫助他們發揮自己的創造性與動手能力。
五、結語
童年時期對于個人發展與社會進步的意義是深遠的,是社會化的第一時期。在智媒時代,兒童可以隨時隨地觸網,因而影響著其社會化進程,改變了過去家庭與學校的絕對地位。本文主要關注新媒介對于兒童社會化的消極影響,并對如何降低負面效果提出了建議。無論媒介如何變遷,掌握技術的主體依然在于人,所以發揮人類的積極主動性,整合人力物力技術,正視問題,依然能有效呵護童年,阻止童年的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