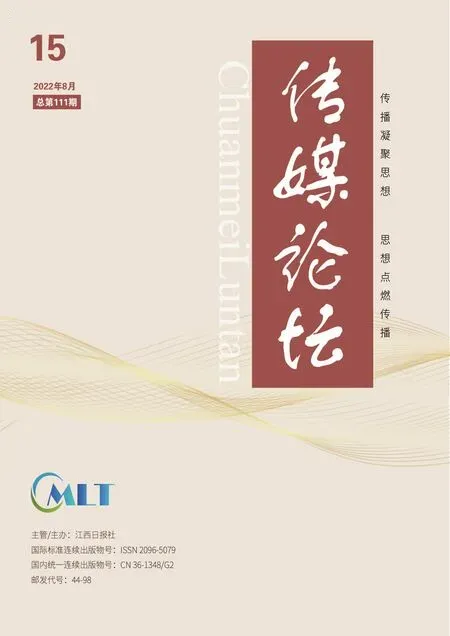論融媒體時代下的活態文創及媒介推廣
丁 潔
2020年河南省博物館文創產品“考古盲盒”系列的火爆銷售和出圈成為媒介融合語境下活態文創的一個成功案例。新興媒體技術拓展了大眾的認知和感官,改變了大眾傳播既有范式,為優秀傳統文化傳播帶來了新的契機。傳統和現代、虛擬和現實、傳承和革新在新興數字化媒介語境下擺脫了其二元對立的桎梏,更趨近于新舊媒介生態融合共生所構建出的多維和交互場景。在新興媒介融合語境下,各種數字化媒介有效助推和共促地方文創產品,增進和凸顯文創產品的精神文化價值,使其引爆受眾注意力和持續自身影響力,并最終成為特色文化品牌或者文化IP。河南省博物館系列火熱售罄的文創產品不僅值得我們對媒介融合語境下文創產品的媒介屬性進行深入思考,更重燃大眾對中原傳統文化的關注和熱情,賦予了大眾全新的維度來審視文創產品與媒介技術的深度融合。
一、媒介融合語境下地方文創產品的破與立
任何媒介技術的興起和發展都和社會環境的變遷、大眾認知和行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信息媒體時代下,地方文創產品不僅打破了原來封閉和單線性地呈現和表述,更迎來了網絡智能化推廣和融合傳播的機遇和挑戰。新興媒介建構了突破時空和現實的虛擬生態場景。媒介成為地方文創產品創意呈現的媒介生態場景。正如戈夫曼的“擬劇理論”和麥克盧漢“媒介即認知”的表述,不同的媒介技術不僅拓展了人類感知和認識,更賦予了大眾不同于真實社交語境的媒介場景。當下空前繁榮的各種媒介技術不僅從各個維度還原再現“在場性”,更塑造他者心中的媒介意象并構建出所謂的“擬象”。新興媒介形態更培養出不同的消費模式和社交方式,從而形成新的人際關系和情感認同。
正是多種媒介技術有效融合和優勢互補賦予受眾豐富和深刻的感知體驗。文創產品的創意不再僅僅局限于包裝設計、符號多模態化呈現、媒介意象的表述和文化內涵傳遞等方面,更反映在文創產品在媒介生態場景中和其他元素的互促和共生關系上。場景時代下的地方文創產品被賦予多元和個性化的表述,文創產品火熱銷售的背后是地方文化品牌和文化IP的媒介建構和傳播系統化工程。可見,媒介融合時代下的生態媒介景觀更側重于關系的連接和融合。
二、融媒體時代下文創產品傳播的新范式:全覺傳受
數字媒介時代下,地方文創產品傳播推廣中的融合不僅體現在各種媒介功能性的整合和互促,更體現在不同產業、技術、網絡平臺和市場等地融合共生。在大數據和移動網絡技術的支持下,地緣及文化的界定和差異性正在逐漸轉變,地方文創產品從設計和展示中每時每刻都呈現出“他者”眼中“自我”的交融。強烈的鄉土歷史情懷和地域特色風情確實是地方文創產品的一個亮點,其在各種媒介技術上得以凸顯,但如何通過消費者的集體記憶和共有認知勾起其對產品關注,更是地方文創產品媒介創意的關鍵。
河南博物館推出“考古盲盒”結合了當下流行的“盲盒”銷售和文物的媒介推廣概念。其打破傳統消費的確定性,消除了傳統文物其束之高閣的嚴肅刻板印象。以體驗性和探索性并存的文物盲盒既是傳統在當下的一種有趣體驗,又是大眾特別是網絡一代對國粹和歷史文物的理解和再詮釋。正如“文物盲盒”,其設計理念中的玩和尋找恰恰勾起了大眾追隨兒時回憶、求新求異的探索心理。融媒體時代下的媒介呈現出擬人化的全覺沉浸式傳播特征。正如萊文森的媒介演化人性化趨勢理論,融媒體旨在通過整合各種媒介所呈現的感官體驗,旨在趨近視覺、聽覺、觸覺、嗅覺等全覺感官的體驗。“人通過時代性技術賦能建構媒介形態,使自己生活在一個擬態的社會環境中,媒介的擬人化延伸人的感知系統,使媒介形態全覺傳受成為可能。”[1]全覺傳受不僅僅是一種沉浸式的媒介感官體驗和呈現,更是一種互文性的媒介敘事。地方文創產品從設計、生產、推廣、銷售和服務等各個環節都處在深度融合之中。
三、地方文創產品的活態文創和媒介推廣
地方文創產品在媒介融合語境下的全覺傳受不僅讓文創產品“活”起來,更讓文創產品“潮”起來。新舊媒介的各種特征的有機整合賦予了地方文創產品呈現和詮釋的全新維度和方式,也讓地方文創在信息呈現、媒介技術表述、傳播方式和組織結構等方面有著新變化和新趨勢。媒介技術已然不僅是中介和傳播工具,而是大眾感知和認知的表述手段和渠道,其已被賦予了媒介生態系統的屬性。在當前的媒介融合語境下,各種媒介的融合共生及其疊替發展是媒介生態景觀的競合,這種競合關系下的媒介景觀是以擬像和媒介再造推進地方文創產品的動態文創和媒介推廣,其呈現以下發展趨勢:
(一)從內容向關系的偏向
自從”考古盲盒”在豆瓣和微博開箱直播后,河南文創產品一下火爆網絡。河南博物館又陸續推出了“壓勝錢”仿古幣和“古幣巧克力”等系列網紅文創產品。電視、報紙、網絡移動終端和各種社交自媒體的推送儼然把河南文創傳播推上了C位。
根據美國學者波斯特的《第二媒介時代》,以互聯網為區別性特征,互聯網以前的媒體時代統劃為“第一媒介時代”。[2]相比于當下的新興媒介,傳統電視和報紙等單一、線性的媒介技術無法給消費者或者觀看者提供完美的全方位多感官的具身性體驗。消費者對文創產品的理解基于一種櫥窗式的觀看和被動地接受狀態中。內容成為第一媒介時代文物創意和傳播中關注的焦點,消費者處于被動接受和缺乏主體性的引導中。地方文創產品很難在第一媒介時代呈現出其活態化特征。隨著互聯網和移動通信數字化普及,第一傳播時代時期的自上而下的、中心的和單向度的傳播模式隨之瓦解。在人人都是自媒體、都有話語權的媒介融合語境下,消費者或者受眾不再僅僅是地方文創產品的觀賞者,而是在互聯網媒介的深度交融下向參與者、創造者和開發者轉變。信息的泛在化和話語權的新分布賦予大眾新的社會關系和身份。網絡造就了圈層和各種亞文化,媒介和文化的關系、人和媒介的關系、媒介和媒介的關系等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地方文創產品的傳播推廣中,關系成為更為核心的要素。
(二)從呈現向擬構的偏向
新興媒介技術和數字化網絡賦予了地方文創產品一個融合互促的媒介生態景觀。地方文創產品中的創造方、生產方、傳播方和受眾方都成為這個媒介生態場景中的一部分。從對地方文創產品的逼真媒介描述和再現,到具有主體性描述及媒介引導的擬像建構,地方文創產品的媒介呈現不再是簡單地復制,其更是通過網絡數據算法的推送介入到消費者媒介行為和信息下的再構。正如媒介融合語境下的《唐宮夜宴》中唐宮仕女的表演,其通過AI虛擬技術和5G網絡等移動端口和傳播平臺讓受眾和媒介場景形成了泛在化的連接。虛擬現實和全覺傳受讓文創產品形成了多維度多時空的立體交互式體驗,媒介再造場景擬構出了具身性和在場感。以《唐宮夜宴》中的唐宮仕女為原型的文創產品,其創作原型也體現了文物和表演人偶形象的融合。網絡和移動終端提供的數據讓消費者的心理和情感偏好都可以在媒介技術和算法中呈現,這些又引導主流媒體和自媒體的系統性多層面的報道推送。一系列地方文創產品的火熱銷售和消費者的持續關注正說明了在這個擬像生態場景中,媒介生態景觀存在的必然性,其不僅架構了地方文創產品的多元呈現的技術可能性,更完善了傳播互動和情感表述的可能性。在國潮和文創活態化的當下,生活在信息網絡的當代年輕人更熱衷于對未知和奇觀的追求,融媒體時代下的地方文創擬像場景正是對其對傳統文化情懷的喚醒和洗禮。媒介融合語境為地方文創產品造就了一個擬態環境,其不再是對現實鏡面式地呈現和表述,在媒介技術的參與和介入下,這種擬態的信息環境成為再加工、再建構的一個媒介生態景觀。其從媒介傳播內容、渠道、交互方式和敘事表達等方面呈現出與以往統媒介不同的特點。
四、融媒體時代下地方文創產品媒介再造的去域性和轉文化傳播
正如梅羅維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一書中對地域的表述,各種媒介的疊替,特別是新興媒介的興起讓地域一詞早已經不僅限于其傳統地理空間的概念。電子媒介拓展了大眾對物理空間和社會場景的界定,更促進了傳統社會行為和關系的變革。[3]在當下新興媒體語境下,看似消失的地域正是對地域一詞當下特征的新詮釋。新興媒介形態培養出不同的消費模式和社交方式,從而形成新的人際關系群。數字新興媒體的非線性、開放性和深度參與性等都讓地域及文化的呈現表述得到了空前的拓展。媒介和技術的興起賦予地域和文化描述、拼接、再造甚至重塑的可能性。基于用戶需求分析的推送式定制化服務是媒介融合時代的地方文創產品創新的發展趨勢。媒介傳播中呈現于受眾的地域必然體現媒介形態下的各種新興人際關系。
在媒介經濟信息一體化時代,地域和文化不再處于局限和對立的新舊和強弱更替的二元發展觀中,多元多向的流動雜糅和融合共生成為常態。合作、共贏和對話代替了經濟文化拓張下的對立、孤立和替代。中國自古以來的“和諧”文化提倡“以何為貴”“和平共處”“合而不同”等理念。[4]正所謂“美美以共,天下大同”。盡管數字傳播下的“數字模因”正以一種先進和更為大眾所接受的方式被復制、再生產和傳播,但其已從文化的異質性和優勢論的關注到對地域和全球化、傳統和當下、傳承和創新等一系列辯證的表述。我們把在兩種或者多種文化交流和對話中產生的文化轉型和變異定義為“轉”(trans)。[5]轉文化的概念成功脫離了文化二元對立的桎梏,正如媒介融合語境下媒介技術的更替和交融同樣是一種共生和再構,其體現了對文化格局和傳播方式差異性的深入思考。鑒于此,地方文創產品的解讀呈現不再是傳統意義上跨越差異和對立,更是基于融合和共生特性的媒介空間信息資源的共享,其提供了重新界定原有社會行為和階層關系的交互,從而形成新的社會交往關系和文化認同。文創活態化是對地域人文屬性和鄉土情懷的多媒介多平臺立體化的呈現,是其對地域人文的原真性的表述和再造,是面向特定消費群體的信息擬像中的媒介意象,表達了媒介技術引導、選擇、再造和不同主體間性的對話和理解。地方文創產品的轉文化傳播正是跨越權威、單一的線性傳播模式桎梏下的媒介生態化競爭整合,是一種融合共生傳播態勢。
五、結論和思考
在融媒體時代下,地方文創產品中的人、信息世界和客觀世界的關系正在重構。其傳播的范式和偏向都呈現出媒介的生態泛在化發展趨勢。地方文創產品的出圈和火爆不僅是各種媒介技術、傳播平臺和組織結構的共贏合作,更是對各種圈層、亞文化和群體關系的重構和再詮釋。依托融合媒介技術和數據終端的地方文創產品不僅僅是對地域人文“象”的追隨,全方位多感知呈現地域人文的物質屬性。其更是對地域人文“意”方面的精神文化價值的呈現和傳播。
融媒體時代下地方文創產品的熱銷帶給我們以下思考:一方面,無論是任何新興媒介技術賦予了何種傳播結構和傳播關系,人作為媒介生態景觀這一系統中符號化的存在,其主觀能動性不容忽略。從地方文創產品的創作到解讀都有著人的交互。隨著媒介時代的變遷,傳播對象也不再是傳統意義上被動和單線接收的“受眾”,而是強調交互和多向性的“與眾”或者“泛眾”。[6]可見地方文創產品中具有符號化意義的泛眾特征、分類和交際消費模式仍有待深入思考,媒介生態場景建構是否需要對其他不同消費人群進行研究值得關注。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知識技術的急速增長和井噴式呈現、信息過度化和碎片化的解讀以及數據模因化地復制同構,地方文創產品不可避免地面臨信息時代下的產品同質性問題。如何避免媒介信息場景傳播中的過度娛樂化和低俗化,如何把握和呈現地域人文的原真性,如何引領時代的審美感知和迎合大眾的人文追求等,這些不僅是傳統和科技的結合、文教和文創的結合,更是民族文化自信自覺和文化外宣的體現,是時代賦予的社會責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