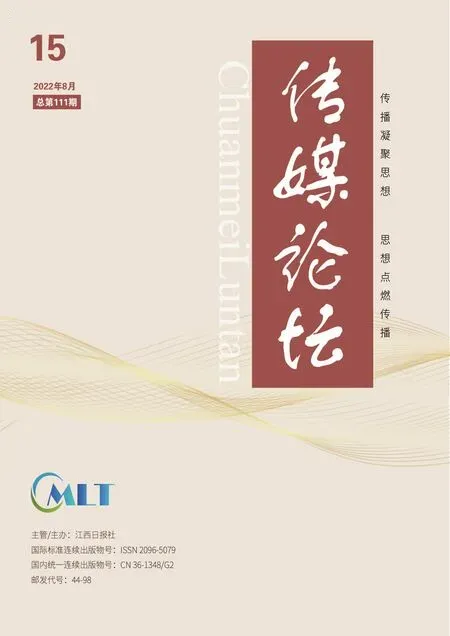移動音頻平臺中傳統文化傳播研究
——以喜馬拉雅APP為例
黃竹子歌 付子琦
社會發展帶來的碎片化先是沖擊了傳統媒體的固定終端,同時也倒逼科技發展催生出移動終端。音頻產業嵌入后,移動音頻產業應運而生。移動音頻產業并不是完全的新生事物,而是為了緩解信息爆炸時代用戶認知負荷與獲取信息之間的矛盾,適配于當下碎片化、場景化、智能化誕生的信息傳播通道。在傳統文化復興的浪潮中,應該借助移動音頻平臺,開拓傳統文化傳播渠道,提高傳統文化的傳播力。
一、聽覺文化回歸:移動音頻產業的興盛
德國后現代哲學家韋爾施曾在《重構美學》一書中對聽覺文化的含義作出簡單的界定:“它可以有一個更為實用的意義。所以它的目標最主要指向聽覺領域本身的培養,即我們文明的聲音領域的培育。”電子時代,以電視為代表的“視覺偏向”媒介對廣播造成了極大的沖擊,聽覺文化漸顯式微。直至互聯網時代初期,人類依然處于以屏幕閱讀為基礎的“讀圖時代”,隨著技術的提升,用戶通過互聯網獲取信息的渠道從PC端向更加便攜的移動端轉移,移動終端的出現為聽覺文化的回歸提供了充分的基礎。
現代社會的發展將大眾的時間割為碎片,內容的呈現也愈發趨向于“短平快”。音頻產業抓住這一特點,使用碎片化內容迎合碎片化時間。以喜馬拉雅APP為例,以某一主題展開,將最具有價值的信息提煉濃縮到十分鐘左右,大大提高了用戶在碎片化的時間里獲取感興趣內容的效率。其次,移動音頻的興盛離不開平臺對場景的感知。基于場景的個性化傳播將會為用戶帶來更佳的使用感受,通過使用LBS技術獲知用戶定位,從而又精準地提供該場景下用戶可能會需要的內容,大大提升了平臺的便捷度以及用戶黏性。聽覺文化以不同以往單一性、模式化的“我播你聽”,轉變為個性化、場景化的“我需要聽”,回歸到我們的生活。
二、移動音頻平臺中傳統文化傳播現狀分析
(一)創新使用PUGC內容生產模式
如今移動互聯網正蓬勃發展,內容生產與傳播分享的成本逐漸降低,越來越多的人能夠參與到內容的生產中,通過UGC模式成為傳播主體。圍繞傳統文化領域的知識性與專業性角度出發,單一的UGC模式會出現內容同質、水準降低的現象。喜馬拉雅創新采用PUGC模式,堅持用戶生產為核心,強調內容的專業性,生產內容的主體也更加細化為專業用戶。[3]一方面,平臺與具有傳統電臺、電視臺從業經歷的主播合作,諸如大力丸兒、謝濤聽世界等在制作環節具有優勢的專業主播;另一方面,平臺邀請在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傳統文化愛好者入駐,在維持內容深度性的同時依靠個人品牌提高用戶黏性。例如觀復博物館館長馬未都主講的《觀復嘟嘟》節目,PUGC模式的運用激發了專業用戶的內容生產能力,保證了優質內容的同時,也為喜馬拉雅引入了更多黏性用戶。
(二)打造層次多樣的優質內容矩陣
在“內容為王”的時代,喜馬拉雅App為迎合大眾的知識需求,創建了多重形式、內容多樣化的產品。其中傳統文化領域的內容產品大體包含歷史、人文、養生、國學、相聲、戲曲6大種類;內容形式涵蓋了原文誦讀、漫談講解和名家集錦3種樣式。為打造有深度、有權威的傳統文化內容,減少對傳統文化的曲解與誤讀,平臺與多位知名學者、作家合作,制作了諸如《易中天中華史》《蒙曼品最美唐詩》等嚴謹權威的優質節目。此外,長尾理論認為,處于“長尾”部分的市場能夠為顧客提供無盡選擇,讓用戶個性化需求的滿足成為可能。[4]為打造差異化內容,喜馬拉雅將“頭部”內容與“尾部”內容相結合,打造多層矩陣。譬如,在喜馬拉雅App內與《紅樓夢》相關的作品中,既有紅學大家馬瑞芳從古代上層社會生活角度品讀的深度解析版《紅樓夢》,也有為青少年制作的,符合少兒理解水平的兒童版《紅樓夢》。這樣多層次的內容滿足了各種年齡階段用戶的需求,使傳統文化能夠做到老少皆宜、通俗易懂。
(三)傳統文化成為知識付費新賽道
根據《2021年中國在線音頻行業發展及用戶行為研究報告》數據顯示,我國在線音頻用戶規模近年來穩步增長,2021年人均文化娛樂消費支出為1119元,占比9.8%。伴隨著移動音頻產業借助場景技術滲透到大眾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用戶在耳朵經濟市場內為知識付費的行為也逐漸常態化。近年來我國著力打造與傳統文化相關的精品內容,以優秀傳統文化為題材的音頻作品也成為付費內容的重要板塊。音頻平臺通過從優質內容端購買傳統文化類書籍版權或與作家、學者簽約合作,再由PGC團隊或PUGC對版權內容進行二次創作生成有聲產品,最后將產品作為付費內容向用戶進行輸出。例如喜馬拉雅買下四大名著版權,在經典名著頻道中設立回響劇場,聯合知名人士推出了張國立解惑《紅樓夢》、張鐵林漫談《水滸傳》、王剛串講《西游記》等付費內容,播放量超過1.2億次。除此之外,還有眾多愛好傳統文化的UGC通過參加喜馬拉雅官方的有聲演播訓練營成長為PUGC,獲得平臺流量支持,將自己的有聲產品制作成為付費內容。
三、移動音頻平臺中傳統文化傳播困境分析
(一)選題同質化造成收聽成本增加
在移動音頻行業迅速發展的今天,大眾可以輕松運用技術生產文化內容,與此同時也可以在海量內容中進行個性化選擇,這本是技術優勢帶給我們的便利。而當文化成為商品被逐漸商業化,熱門傳統文化題材被多次重復使用時,大眾則會被淹沒在各種同質化內容中,反而需要投入更多時間成本進行選擇。例如在喜馬拉雅APP搜索關鍵詞“論語”,在首頁就呈現了20部專輯,其中采用講解形式和原文誦讀形式的專輯各占10篇。除了選材和角度相同之外,作品在標題的設計上多采用“主講人”“播講形式”“播講內容”三要素進行排列組合,譬如《鮑鵬山全解論語》《南懷瑾論語別裁》等。顯然此類作品在選題角度和難易程度上的劃分并不清晰,這使用戶在面對大量的內容時難以找到與自身偏好、理解水平相匹配的內容,既浪費了收聽成本,也消磨了用戶對于傳統文化的興趣。
(二)傳統文化難以融于碎片化時間
我國傳統文化有著諸多自身的特點,源遠流長,世代傳承延續,有著強大的內部凝聚力,形成了一種文化關系整體。[5]而在碎片化傳播時代,隨著各類媒介之間的爭奪,用戶的時間與注意力被分割再分割,在分散且有限的時間內,用戶難以真正了解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與整體內涵。相較于視頻這種視聽媒介而言,音頻能夠爭奪的只有用戶的聽覺,因此這一困境在移動音頻行業尤為突出。
為打破這一困境,各大音頻平臺采取了不少措施,卻也收效甚微。一種方式是通過買下熱銷的傳統文化著作,將其原樣轉換成有聲專輯,這一做法能夠借助其他領域中傳統文化的熱度,獲得用戶的注意,卻沒有考慮到文字直接轉換成音頻后,是否對用戶的接收效果產生影響;另一種方式則是通過在內容中不斷加入刺激點,達到長期吸引用戶注意,獲得更多時間的目的。這種方式使本來應該放在首位的知識與美感逐漸退位,內容的深度與廣度難以達到。
(三)全民共同參與的格局尚未形成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程度不斷深入,全球各地的文化與思潮蜂擁而至,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力受到挑戰。許多人表示,傳統文化在現代生活中接觸得越來越少了,除了一些文化常識,其他傳統內容與自己的聯系并不大。近年來,我國傳媒領域在文化強國戰略方面作出了持續努力,從央視制作的《中國漢字聽寫大會》《中國古詩詞大會》等節目到短視頻中像李子柒這樣傳播傳統文化的主播,都增加了受眾對傳統文化的認識。但目前各個媒介還尚未形成聯合發展的模式,其中移動媒介稍顯弱勢。在移動音頻平臺中,收聽傳統文化類節目的用戶多數都是對傳統文化有了解的愛好者,而信息繭房則讓那些對傳統文化不關注、不了解的人很難在移動音頻平臺接觸到相關內容,從而導致全民共同參與的格局難以形成。
四、移動音頻平臺中傳統文化傳播建議
(一)增設傳統文化專欄,豐富節目內容選題
以“傳統文化”為關鍵詞在喜馬拉雅App搜索欄進行搜索,選擇以播放量進行排序,排名前三的節目均為PUGC,且沒有專門欄目,節目較少。以“歷史”為關鍵詞在喜馬拉雅APP搜索欄進行搜索,選擇以播放量進行排序,排名前三的節目同樣也是PUGC,分別為《聽謝濤·真三國》《中國歷史未解之謎》以及《大力史》,其次在前十名榜單還能看到電視節目《國家寶藏》和《百家講壇》的音頻版。以“國學”為關鍵詞搜索,大多都為PUGC生產的兒童教育節目。筆者通過搜索以及收聽相關內容,發現在喜馬拉雅APP以及其他移動音頻平臺上缺少傳統文化專欄,內容選題,大多集中在歷史講述,而其中對不同朝代故事、著名人物的講述尤為集中。所以在進行傳統文化傳播時既要在平臺上增添傳統文化專欄,同時在內容的選擇上要大膽尋求突破。
增設傳統文化專欄不僅要將內容整理歸類,對內容進行清晰的標簽劃分,而是要通過這一欄目的設置提高平臺用戶對我國傳統文化內容的重視。其次,在內容選題上,應該擺脫趨勢的束縛,尋找更加新穎的角度方向,例如當下的節目都是縱向深入展開,可以將思路轉化為橫向延伸,比較不同時期同一事件的發展結果。找尋新的切入口,突破內容的同質化,提高整體的內容質量。
(二)立足音頻產業特點,引發用戶共鳴
當下參與傳統文化傳播的節目大多都以講述、有聲書以及電視節目的音頻版呈現,筆者通過收聽發現,這些呈現形式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沒有把握好音頻產業的特點。移動音頻產業不能成為電視節目的音頻版存在,同樣也不能將過去廣播的形式傳承下來,而是要把握好互聯網時代音頻產業的新特點,引發用戶共鳴。
移動音頻具有信息性、情感性、娛樂性和陪伴性四個特點。其中情感性與陪伴性是移動音頻產業相較于以往展現出來的獨特特點。情感性體現在不同聲音對音頻情感的演繹和表現,能夠引起用戶共鳴,營造親密的關系,這是聲音媒介的獨特魅力所在;陪伴性體現在音頻不干擾用戶的視覺和觸覺,場景適應性更強,其陪伴性特征可以滿足用戶碎片化收聽的需求。[6]在對傳統文化進行傳播時,“照本宣科”是行不通的,要想在眾多移動音頻平臺中脫穎而出,就要注重對內容賦予情感。例如在對我國優秀傳統文化著作講解時,可以采取對人物配音的方式,還原場景。講述者同樣也要擺脫傳統播音員專業的播音方式,只有對人物賦予情感,所輸出的內容才能喚起用戶的共鳴。其次,利用大數據,平臺基于不同的場景,可以有針對性地推出較高陪伴性的節目,例如駕駛過程、睡前場景中,內容可以松散、簡潔一些,而在通勤、休閑、運動等場景下則可以提高傳播強度,充實內容,節奏也可以稍快一些。在大數據的背景下,根據用戶需求“量身定做”,根據用戶場景將內容場景化,都能夠大大提高傳播效率,從而才能提高用戶黏性。
(三)挖掘傳統文化思想精髓,創新精神內涵詮釋
在人心浮躁的現代社會,越來越多現代讀者面對社交媒體的狂歡無所適從,對于同質化的文化娛樂快消品日漸厭倦,轉而選擇回歸經典閱讀,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收精神養分。[7]單一的對傳統文化進行簡單機械的解讀已經不能滿足移動音頻平臺用戶的需求,而且同時也會使用戶感到枯燥。以《蔣勛細說紅樓夢》為例,《紅樓夢》作為傳統文化中一座巨大的里程碑,有聲書以及其內容、背景的分析在市場上已經飽和,但是蔣勛在講述時從自我出發,對情節、人物的理解都融入了自己生活中的感悟,針對青少年聽眾,更是將其中的思想精髓融入校園生活,提高聽眾對《紅樓夢》的理解。也就是說,在對傳統文化本身的內容進行傳播時,要轉變思路,除了挖掘傳統文化中的精髓外,還要把握當下社會中的核心精神,將二者結合起來,對傳統文化內涵做出創新性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