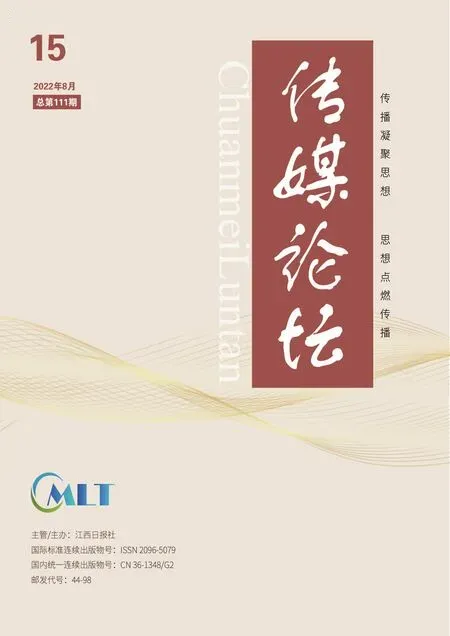互動電影的斯蒂格勒式解讀
徐拂洋 孫一萍
自電影誕生始,觀眾同文本的互動便一直存在,從默片時代銀幕旁的配音員或奏樂者、電影播放完畢演員從后臺走出的謝幕,到今天觀眾在電腦前隨時進行的暫停快進,再到電影評論、評分、在線的“彈幕”,但這些仍然是面對靜態文本在意義或意識層面的互動,這樣的交互不會對客觀存在的電影文本產生影響。數字技術則真正賦予了我們,真正同文本進行交互的可能性,同時也將互動與敘事進行組合,讓用戶的行為對文本產生影響,甚至讓使用者的運動成為敘事的動力。
數字時代電影被賦予了新的創作手段和實踐可能,從傳統電影沉浸式的觀影體驗到如今互動電影可見的交互,觀眾與電影間的聯系更加緊密。技術不僅是電影內容書寫的工具或信息傳遞的媒介,更是影響了電影存在方式的基礎語言,作為電影的內生基因存在。互動性一直是電影研究中的重要話題,數字時代的互動電影借助人機交互相關技術,為觀眾提供了觀影體驗的更多選擇。但數字技術先天的算法框架并不能在現代技術本身的發展中找到突圍的路徑,局限的工具理性也受到質疑,互動電影的未來似乎難以找到出路。斯蒂格勒自胡塞爾處汲取現象學方法,通過對海德格爾、西蒙東技術理論的批判性繼承提出技術義肢論,認為技術作為人的義肢并非一種工具或附加品,而是人的一部分。從意識與時間的相對關系出發,提出技術作為人類的第二起源產生的深遠影響,展開技術本身作為解放的可能性,為電影互動性和交互方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一、人機交互的技術困局
幾乎為人們所公認的是,電影是一種技術的藝術,但首先應該被明確的是,在談論電影時常常出現的“電影技術”概念并非斯蒂格勒口中的廣義技術。被斯蒂格勒視作人類“第二起源”的廣義技術是“techne”,即柏拉圖口中在今天更適合被翻譯為“技藝”——技術與藝術之結合——的“τεχγη”。樂觀的情緒充斥于數字時代的電影研究中,數字電影因為相較傳統膠片電影呈現出的豐富可能為人們帶來了充足的信心,被認為因技術的賦能而具有將想象變為現實的能力。技術決定論悄悄攀上電影前進的馬車,更危險的是科學技術的局限性在一些觀點中似乎只存在于時間維度,一切美好設想同現實世界的落差都被歸因于技術發展的階段性,寄望于未來技術的蓬勃發展,好像面前的困境終將被不斷發展的技術克服。但從根本上將技術本身同科學技術相混淆的片面認知在技術發展的困境前屢屢碰壁。斯蒂格勒不認為問題的解決在于科學技術本身的進步和完善。具備雙面座駕性的廣義技術內蘊著人類世(anthropocene)的解藥,也包含著逆熵的可能,這并不意味著科學技術能夠掙脫其本身的局限性,也不代表現代技術的發展會為一切技術問題提供解決方案。[1]
今天以人機交互為方式運行的互動電影同樣是在靜態作品中進行的有限互動,用戶每一次文本塊的組接、向外投射的每一縷視線都毋庸置疑地處在被預先提供的選擇之內,無法做出被設計路徑之外的選擇。在這一層面上,數字時代的互動電影同傳統電影沒有本質上的差別,敘事層面或觀賞方式的切換背后,基礎技術語言的更迭不能帶來電影文本閱讀的嬗變,意識活動也無法離開技術語言天然的認知框架,甚至在有限選擇的認知框架下的行為本身便是技術對時代掌控的加固,帶來了現代技術作為基礎邏輯對人思維帶來的束縛與規訓。
用戶的體驗是審視人機交互的關鍵坐標,但互動電影所需要的則遠遠不止體驗而已。電影哲學研究者提示我們發掘電影之“思”,而技術作為電影的基因,能夠推動電影為我們創造“思”的更多可能。然而滿足于“體驗”而忽視電影之“思”的局限視野卻時常出現在互動電影的討論中,對技術的片面認知不僅可能將對互動電影的展望引向歧途,而且對技術的應用呈現出一種根源性的矮化。
由內生有限性技術本身帶來的框架至少在目前看來不具備“掙脫”的可能性。觀眾體驗與文本呈現層面,拓寬技術框架的范圍,構造更大的框架以涵蓋更多的選擇,同時增大其密度,讓其具有更小的識別單位以帶來更大的辨識空間,現代技術的進步將帶來人機交互短期的良好發展,但認知的重塑終究是互動電影突圍的前提。
二、互動電影的認知突圍
電影創作的可能性同時代背景下的技術水平有著極大的關聯,不僅是影像技術或更宏觀意義上的聲畫技術,基礎科學更是決定電影形態和發展的可能因素。斯蒂格勒認為技術是并行、甚至重于人類生物性存在的“第二起源”,提供了人類在存在論層面的意義,人類從而得以掙脫生物發展必然的偶然性,并進行有目標、有方向的發展。技術也是電影造境能力的來源,從視聽體驗到沉浸方式,電影世界變得更加立體,空間的組成因而愈加完善,“電影空間”顯出物性的前兆。克里斯汀·戴利認為數字媒介帶來了電影以用戶為中心的轉向,原先靜態存在的觀眾成為“瀏覽者”。[2]作為“瀏覽者”或“用戶”的觀眾具有主動性,在電影文本的閱讀與體驗中或被賦予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用戶同電影的交互創造了觀眾意識活動新空間,這個過程本身也隱藏著互動電影突破桎梏的合理性與可能性。
(一)第三持存的視域拓展
古老的故事欲根植于人們的內心,斯蒂格勒認為這便是電影對人們強大吸引力的根源之所在,我們因此愿意打開書本或走進電影院。這種欲望推動人們探索事件,從各自的視點對事件進行解讀。基于這種故事欲,文本的閱讀者們產生了各自的預期,在閱讀前便對文本建立了各自的前理解。
前理解是理解產生的背景,但文本才是理解的對象,“誰想理解一個文本,誰就準備讓文本告訴他什么”,前理解與現實解讀之間的平衡在此時顯得尤為重要。伽達默爾提出的方法是在讀者認識到自己前見的基礎上進行閱讀,讓文本在前見中被解讀,“表現自身在其另一種存在中”,讓閱讀成為修正前理解的過程,在理解中調整源于前理解的認知。[3]文本被置于信息接收者的面前,意味著閱讀和理解在前理解中的“再生成”,文本同信息接收者的前理解相結合帶來了當下的理解。現代詮釋學將主體閱讀和理解文本的“理解的循環”從文本內部整體與部分的關系拓展至讀者與文本之間。互動電影的體驗與解讀不僅是文本塊同整體之間的循環,更是用戶通過交互行為同文本建立的循環,這個循環中的用戶與文本作為一個更大的整體存在。
用戶當下產生的第一記憶同前理解相重疊,生成了第二記憶,同時用戶在互動電影中讓自己直接同文本產生交互,讓文本包圍自己的當下體驗,理解循環產生了再次重疊,在其中提供了施萊爾馬赫“自身置入”的直觀可能。這個過程中對“自身”的強調拒斥了文本閱讀中丟棄自我的傾向,在前理解的背景下讓自己“置入”文本他者的處境又帶來了文本閱讀的視域融合,是“不僅克服了我們自己的個別性,而且也克服了那個他人的個別性”[4]的文本耕犁,是向著事情本身和文本內在藝術視域的解讀升維。基于用戶“從自身價值立場而不是角色立場出發做出選擇”[5],并因而被所謂“幻覺”蒙蔽主體理性認知的觀點顯然忽略了互動電影為用戶帶來生命體驗的深層次可能。召喚著觀眾強烈情感共鳴的電影本身不應因此而受到指控,進入文本融入角色并不意味著迷失自我,視域的融合和前理解的懸擱以及同文本的碰撞也與主體迷失自我無關。如果對互動電影的質詢陷入了那喀索斯的困局,那表面存在的“自我”也只能淪為冷漠的觀影機器。
源于觀察視點外視域的調整,對相同文本客體差異化的體驗潛藏在文本背后,賦予了文本讀者感受或認知的不斷更新,讓受眾在多次體驗中獲得不同的意識結果,豐富其對作品整體的認知。藝術作品的內在視域是其所呈現的生存體驗世界,觀眾的主觀感受與其認知水平密切相關,因此不同觀眾對文本的解讀也不盡相同,但文本主動為其提供多種觀察的切入點,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讓每一個個體都能因差異化的視點和不同的解讀方向得到多樣化的知覺感受,不僅是完善著自身,更讓受眾認知中的形象更為立體,讓作為“熱媒介”的電影調動觀眾更多的接受器官,拓寬其感受維度、深化其感知縱深。
(二)技術代具與意識延伸
在互動電影與人類意識的關系上,斯蒂格勒的“代具”(prosthesis)理論似乎比他延承自老師德里達的“替補”(supplement)概念更為合適,一方面特別強調對人類而言的技術,另一方面也在表述技術對人類先天不足進行彌補的基礎上突出了延伸的意味。技術作為人類的義肢,拓寬著人同外部世界交往的可能。電影本身便是人類通過技術創造的藝術,人們借此拓展著自己的“思”,畢竟技術的義肢屬性不僅存在于物質層面。陷入困境的互動電影源于作為廣義技術一部分的科學技術,而意識則借助本源的技術(即techne)達成“思”的突破,互動電影從而獲得可觀的發展方向。
海德格爾擺脫技術工具論,將技術視作“解蔽的形式”,技術生產則是“把一個事物從隱蔽狀態變成非隱蔽狀態”的過程,“解蔽”可以是現象學層面不存在于視線之下、光未照射到的存在,也是存在論層面并未向主體展現自身、尚不是此在的存在。正如同電影世界未被目光照亮、由觀眾意識建構而成的、未被揭示存在的“幽靈空間”。[6]以VR為媒介的電影作品通過外置設備設置觀眾同現實世界的隔斷,將用戶的視覺體驗置于電影世界中,通過相同視點不同方向畫面的組接,嘗試將讓觀眾產生身臨其境的文本閱讀體驗,強化其沉浸感受。VR賦予了用戶一定程度上對身體的控制權,用戶對視點的自由選擇意味著空間的完整和存續,通過視角的選擇權體現對身體的控制,讓原本被作為觀眾望向電影世界窗口的攝像機受到挑戰。盡管這種挑戰本身透出VR技術同電影結合過程中,從敘事手段到表現形式面臨的障礙與挑戰,但技術在此過程中行使的“變不在為存在”的“生產”過程卻令人欣喜。與其說被“生產”的是用戶在電影世界中不斷切換的探索視角,不如將其看作對電影世界作為立體“世界”的豐富,為有軌電車帶來離開電線與軌道,自由行駛的可能性。未來的無限可能同樣也存在于其中。
當我們跳出主客二分法,在互動電影的體驗中不再將用戶與電影文本視作不對等的主客關系,或許人與機器間的“自由交互”才具備了實現的可能。人的認知與意識活動往往屈居于現有算法的框架之下,交互中的機器不斷以技術之名否定著人,人機交互因而具有否定性。交互本身不是藝術,但作為藝術的電影通過技術手段不斷肯定著人的意識活動,將先驗的想象不斷變為可見或可被理解的虛擬現實。斯蒂格勒令人振奮地指出,數字技術為個體生產預留了可能,因而具有書寫的性質,可以被視作為我們提供了對肆意發展的大眾傳播媒介的一次糾偏,對其去個體化特質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進行矯正的機會。作為人的義肢,數字技術更加比既往的電影技術更加貼近傳播終端的用戶,代償身體缺憾的延伸不再是宏觀概念下的存在,后天得到的器官讓人更加接近自由。
三、結語
“互動電影”在科學技術不斷取得應用突破的背景下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人們對體驗的熱衷與對新鮮事物的好奇在全新的觀影體驗中得到了釋放。從“VR電影”到“影游融合”,我們不斷探索著電影文本的呈現方式和觀眾的觀影方式,主體從“觀眾”到“用戶”的轉變也讓互動電影的追隨者們趨之若鶩,但現代技術背后的局限性讓我們發現,創造電影神話的數字技術也將互動電影帶入了框架般的困境。互動電影的美好愿景或許終將實現,但一方面技術的發展和完善的確尚需時日,更重要的是我們迫切地需要重新建立對互動電影的冷靜認知,直面技術性本身和技術拓展層面的雙重困局;另一方面電影以強大的可供性將否定性的人機交互同自身的肯定性結合,人機交互從而具有了互動電影這樣一種實現形式。人意識活動的生命力既是互動電影為突破既有之藩籬的動力源,也是電影作為生命體驗“思”的認知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