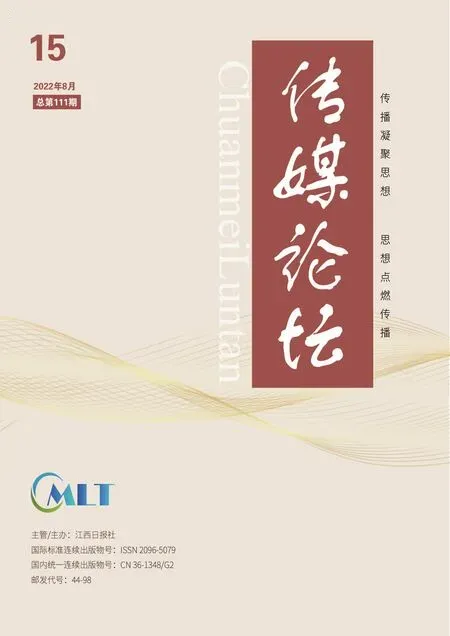論鄉土集體記憶的空間美學建構
——以《大地情書》為例
房奇蕙
一、研究背景
在經歷“娛樂至死”的躁動后,紀錄片作為引領社會價值觀、啟迪心智、塑造國家相冊、推動文化走出的重要載體。由優酷上線的網絡紀錄片《大地情書》正以更全新的姿態擁抱新時代,以坐落于松嫩平原的黑龍江省作為拍攝地點,深耕于東北黑土地上的鄉村生活,書寫了一部頗具地域特色的鄉土中國影像志。全片以精心的構圖、精煉的腳本,將帶有本土氣息的鄉村生活與文化,經由電影美學手法的表達帶入到觀眾的視野。在迎面而來的生產生活場景中,觀眾更加直觀地感受黑土地衍生的自然與人性之美。我們看到了中國電視紀錄片在互聯網時代的創新之路,為當下如何利用紀錄片打造城市IP、建構城市記憶、弘揚中國文化提供了脈絡與方向。
二、鄉土紀錄片中的空間美學建構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的開篇中提出,“從基層上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1]從內容上看,影像是鄉土文化的記憶與重構。地方的鄉土人情與歷史文化是一部鄉土紀錄片創作的根基,既而紀錄片成為傳播地域文化的主要手段。紀錄片《大地情書》立意于“看見東方之美”命題下,將視線聚焦于黑土地和其滋長的世間萬物,借助影像美學用詩一般的鏡頭語言展現了東北大地上的豐饒遼闊,使鄉土紀錄片在空間維度方面呈現出新的美學形態,建構了獨特的美學景觀體系。
(一)地理空間的奇觀表達
作為一部展現東北鄉土文化的紀錄片,《大地情書》選取我國重要的糧食產業基地綏化市作為取景地,以電影美學的手法記錄了山川湖泊、廣袤無際的農田,描繪了一幅寧靜祥和的生活畫卷。十個故事映射了十段人生,飽含了對這片黑土地的熱愛與敬意,將充滿煙火氣的人間呈現在每個觀眾眼前。《大地情書》中的空間建構遵循著從地理空間到社會景觀的邏輯,在時空邏輯、人物譜系、社會環境等多重元素的組合中呈現出空間符號意義:以地理空間為落腳點,將劇中十段平凡人的故事與時代密切聯結,兼顧地域性與普遍性,紀錄片“以‘家’的模式表達國家意志,在表達過程中把‘國’窄化為‘家’,置放于‘家’的范疇內表達”[2]最終實現了社會人文景觀的呈現和精神力量的傳遞,彰顯了紀錄片的熱度與厚度。
《大地情書》中呈現的主要有三個地理空間,一是生活在黑土地上十個普通人的鄉村生活,展現了東北人民的真實生存現狀和生活狀態;二是人們的勞作環境,展現了黑土地的特有生產勞作場景;三是在畫面中所呈現鄉土中國社會空間。其中包括了一望無際的小興安嶺大自然環境,以及大塊又黑又亮的土地展現了大美北林的優質生態環境和東北民俗藝術的發源地。生活、村落、社會三個空間分別代表著都市化進程中這片土地上的人情、精神文化、民生的主要時代主題,這些時代主題影響著一代又一代東北人在黑土地上的生活圖景以及珍惜這片賴以生存的綠色空間是寒地黑土之上每一個人的信條與家訓。他們是一個個微小的音符,構成了紀錄片中展示的四季圖景與時代議題,也促成了地理空間向人文景觀、社會景觀的轉化。正如影片中開篇導引艾青的名言“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全片從對土地的深切情感入手,在飽滿的敘事基調下,通過十段故事定格東北大地的風物之美。《大地情書》從小視角入手,在表現手法、故事呈現、語態表達形式上進行了顛覆式創新,將自然風物、文化自信、鄉村振興、民生等社會主題和宏大敘事,拆解為小故事、小人物、小場景,講述平凡的中國故事。在《“宅男”老丁的故事》中,老丁勤懇地培育生態稻米,積極響應著科技興農的時代號召。在“慶安大米選‘米模’”的故事中講述的是慶安農人畢家英的快樂生活,其中在才藝比拼環節中第一位參賽選手用打快板的方式傳遞出慶安大米特色、慶安的綠色生態環境、國家生態方針等文化理念,靈活地做到了“去政治化”的宣教模式,從新媒體與全球化的角度出發,以真實的藝術方式帶我們走進東北綏化那片黑土地,探尋城市之外“新”的生活可能,提高受眾對本土文化產品的接受,延伸了鄉土紀錄片的高度與深度,讓地域形象和地方品牌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二)鄉土空間中的東方美學
所謂“大地情書”,拆開來看即是“大地”“情”“書”,指涉著空間、人和情感的關系。整部片子以“看見·東方”為主題,借助電影美學成功地顛覆和矯正了很多觀眾對鄉村題材“灰”“土”的歷史觀,這種美學形象的建構是通過一系列地理場所的呈現,從而使之成為一種美學的符號性存在。黑土,是世界上公認的最肥沃的土地,鄉土是帶著情感和溫度的,黑土地養育了中國東北數以億計的中國人。《大地情書》正是從鄉土視角為觀眾講述黑龍江人民最淳樸的人情冷暖,不僅立體化地呈現了東北人民的真實生活,同時細膩而又真誠的鏡頭下將中國農村生活的鄉土氣息和樸實的真性情以及平凡的人生凝練成一封寫給大地的情書。情書的開篇便從對中國人民最為重要的秋收講起,呈現了關于大自然對于人類的饋贈和人對自然的回饋,緩緩勾畫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活圖景。
與語言相比,空間無疑更切合視覺表征邏輯,抑或可以說空間就是視覺活動的產物甚至空間本身就是一種視覺符號。[3]松塔是紀錄片開篇《尋寶小興安嶺》中極具代表性的物像,稀有的野生松塔吸引著很多采山人冒著生命危險挺進小興安嶺探尋這片秘境,尋覓林間至味。為了生活,主人公范立國需要徒手爬到高達七十米的松樹頂部采摘松子,這既是大自然對人類對考驗也是大自然的饋贈。當采摘完后范家父子也留下一些松塔作為松鼠吃食,他們對大自然有所求,亦有所予,人類與自然對和諧共生便是這片黑土地上固有的東方之美。在地大物博的中國,城鄉間的發展不平衡,偏遠山區尤為突出,這一現象也建構了農村紀錄片中人們更好地獲取大自然的資源,從而更好地給予大自然回饋的美好互動。而黑土地只是中國大地的一個側面,在片中所描繪的平凡人物肖像中,東方之美的不同緯度得以詮釋,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人與人間的和諧共處共筑了東方之美。片中的每一個人物,不僅是他們,更是生活在中華大地上十四億中國人的縮影,在有溫度、有態度的鄉土敘事中透視著一個個平凡而非凡的中國人的故事,走進一個真實的東北農村,了解一個真實的中國。
(三)記憶空間的喚醒
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克盧漢認為:“我們的感官器官和神經系統憑借各種媒介得以延伸。”[4]紀錄片《大地情書》里,攝制組在客觀記錄的前提下,更多地選取了具有記憶價值的符號用來建構記憶框架。影片取材從春季到冬季,從森林到湖泊,既有自然風貌地理,又展現了人物、風情、特產,利用文案將風物變成符號來傳承記憶。此外,旁白總是不經意講起故事配合著畫面,形成了一種互文結構,將符號意義注入人們的經驗系統,形成更深層次的記憶。《冰面上的“纖夫”》一集中,特置鏡頭深入冰面之下,特寫鏡頭拍攝鐵制冰镩與厚實冰層的碰撞,這些畫面足以展現了面對極端的采冰環境,他們不屈不撓的韌勁,就像片中解說詞一樣“冬日的黑土地,銀裝素裹,古老的呼蘭河一進入冬季,便猶如作家蕭紅筆下描述的那般,有了別樣的壯美景致”。視聽語音的結合,自然將人們帶入到極為艱苦的工作場景,人們在艱苦的條件下努力的畫面,也從另一個溫度詮釋了東北人堅毅的品格。在寒地黑土之上,他們用自己的奮斗收獲了平凡的幸福,形成了情感上的認同。其次,紀錄片中多次呈現了東北地方美食,如“香噴噴”的稻花香大米、蘸醬菜、酸菜餃子、松花江大魚等,以美食象征黑土地對人的物質饋贈。《老母親的菜園》一集中通過兒子種白菜、母子腌酸菜、女兒做粉條、包餃子、拉秋菜等日常生活的畫面,建構了鄉土文化的符號載體。在影像的編碼中,紀錄片有意識地對生活勞作場景和日常畫面進行特定的重構,激活人們腦海中關于東北人的味覺密碼。在紀錄片中,攝制組將具有“生活”意味的畫面組合起來,對畫面色彩和構圖進行藝術創作,讓畫面更具詩意,加強召喚記憶的力度。此外,紀錄片《大地情書》中選取了承載人們家庭記憶的素材,我們可以從影片中培養水稻的老丁身上看到許多農民的影子,或許從未想過會離開這片土地。兩個騎馬的小伙子,讓人記憶最深的莫過于一個嫉妒對方有女朋友、幽默讓人忍俊不禁,表現了很多東北男人表面上粗獷豪邁,而骨子里埋藏著細膩的一面。四季輪轉、人們辛勤勞作,在極端對環境下,對于生活不屈不撓,在這片黑土之上時代守望、辛勤耕耘,靠自己辛勤勞作撐起一個家。或許這就是平凡生活的真諦,這是這片土地刻在他們血液中的印記,這些是人們共同的家庭記憶,當這些日常生活場景被搬到熒屏時,人們很容易被帶入到紀錄片敘事中,想起自己的那片“大地”。家庭記憶場景的不斷重復,人們心中的鄉愁記憶被打開,古樸的村落、難以忘懷的家鄉味道、層林盡染的山林,人們腦海中一幀幀畫面、一段段鄉土記憶被打開,景觀符號獨特的鄉土氣息引領著人們開始回憶鄉村,回憶過去。
三、電影美學下的鄉土記憶
人們習慣于用“失意”來刻畫如今的東北,社會視角很少聚焦于東北。而紀錄片《大地情書》則嘗試打破這些刻板印象,將帶著“土”氣的和原生態的鄉土生活與電影美學融合,用電影的表現手法去表現真正的農村生活平淡的腳本和詩意的畫面完成了一次美學意義上的創作。在普通的農村生活場景中讓觀眾真正感受到東北農村的自然美和人性美。此封“情書”講述著有一群人是以這樣的方式與態度生活著,不僅是寫給不熟悉這個角落的人看的,也是寫給漂泊在外的東北游子,家鄉或許并不遙遠,這片土地依舊充滿生息,雖然以農民和農村日常生活為拍攝主體,但該片在攝影、腳本等環節都營造出了電影美學的美感和格調。在拍攝手法上,一道酸菜燉粉條和一鍋最為家常的大醬燉魚在特寫鏡頭下,如同專業名廚手下的珍饈天物。潤綠蔥郁的小興安嶺森林收攬于航拍鏡頭下,色塊分明的鄉間稻田如同一幅油畫,多了些歐洲小鎮的即視感。該片在腳本創作上借助了電影的表現手法,給每一位主要人物都安排了幾段以黑幕為背景、近景鏡頭的簡短獨白,并讓人物在獨白中進行自我表達。聚光燈下的人物面部特征及表情一覽無遺,用“真實”展現生活的悲喜交集,整個紀錄片放大片中人物身上堅韌不拔,開朗樂觀的人生態度。同時還有一些精巧設計的橋段來推動敘事。在第五集中,在一場皮影戲演出后,表演者從幕后走向前臺向觀眾謝幕,當鏡頭轉向空無一人的觀眾座席時,這一充滿戲劇性“曲終人散盡”的橋段讓觀眾的情緒仿佛一落千丈。[5]以一種舉重若輕的手法有效地調動了觀眾的情緒,使拯救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方曲藝這一主題更為深入人心。這些鏡頭精心的組合和設計使該片不同于一般的農村題材紀錄片,其本身在電影手法賦能下流露出些許的“匠氣”的意味,脫離了令人興致索然的普通新聞紀實類農村專題片的刻板模式而具備了較高的觀賞性。《大地情書》的畫面構圖、取景角度,打破傳統模式,在4K高清鏡頭下上演視覺盛宴。無論是層林盡染的森林、翠綠綠的稻田、熱火朝天的勞作、白雪皚皚的呼蘭河畔,還是晶瑩剔透的冰雕、沾滿露珠的秧苗等場景,《大地情書》將這些自然風物拍出了一種極致的美感,每一幀和每一個鏡頭極具藝術色彩,極為凸顯出了紀錄片的美學質感。
四、結語
近年來,《鄉村里的中國》《記憶鄉愁》《了不起的村落》等農村題材紀錄片都在試圖較正鄉土中國作為“文化鄉愁”的內涵與外延,使其不再用原來指涉愚昧與文明、先進與落后二元對立的城鄉關系,而趨于將農村形象塑造為烏托邦性質的文化景觀,來幫助緩解高速工業化的進程中產生的一系列人們精神與生態環境的危機與陣痛。也在對外開放的背景下為塑造民族認同感提供新的文化資源。而《大地情書》的精神旨歸與這些前作類似,同樣遵循著正面文化景觀的路徑,為鄉土中國塑造了道德良善、生態健康的面孔。同時,也在美學層面為同題材紀錄片的創作提供了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