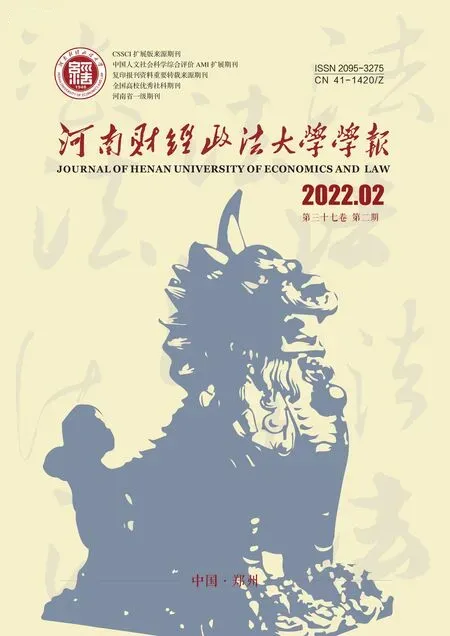《民法典》背景下代位權客體廓清
趙 晶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6)
一、問題緣起——《民法典》施行后代位權客體的爭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頒布實施后,我國民法學研究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傾注在《民法典》條文與制度規則的解釋上,也應驗著史尚寬先生之“民法學本質上是民法解釋學”[1]的箴言。 有關代位權問題的分歧意見,在《民法典》之前已經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債之保全制度的理解與適用。 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以“代位權”為關鍵詞進行檢索①筆者檢索的截止日期是2021 年9 月10 日。,找到各種裁判文書54 926篇;再以“對象”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共有2 480篇文書;再限定“客體”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共檢索到247篇文書。 通過分析這247 篇文書,尤其是通過對2021 年1 月1 日《民法典》開始生效后的24 篇裁判文書的研究,發現有關代位權客體的爭議在《民法典》實施后確實依然延續②目前2021 年的裁判文書是24 篇,考慮到文書上網公開的滯后性,實際的數量一定更多。。 例如,在“楊健、黃婉琳等債權人代位權糾紛”③福建省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2021)閩02 民終1874 號民事判決書。中,被上訴人認為“上訴人主張行使的是撤銷權,并非債權人代位權標的……”;在“中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鄭州農業路支行訴東方鼎盛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代位權糾紛”④河南省鄭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2021)豫0191 民初5246 號民事判決書。中,被告主張,“第三人享有的是請求被告協助其辦理案涉房屋產權登記的請求權,非具有金錢給付內容,原告無權對此行使代位權”;在“錦州濱海新區瑞銀小額貸款公司與王桂英等追償權糾紛”⑤遼寧省錦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1)遼07 民終1187 號民事判決書。中,當事人就“債權人是否有權對債務人怠于主張的物上請求權行使代位權”發生爭議;在“鄂托克旗鑫勝鈑金修理廠訴王二強修理合同糾紛”⑥內蒙古自治區鄂托克旗人民法院(2021)內0624 民初1324 號民事判決書。中,被告主張“原告不能就其對保險公司享有的保險合同權利進行代位”。
這些爭議和分歧,主要圍繞著代位權的客體范圍而展開,涉及代位權是否及于形成權、物上請求權、程序上的權利,乃至可否對保險等新型金融權利進行代位。 訟爭的不同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民法典》的理解與適用效果,甚至可能影響到法治的統一與權威,有必要對其加以澄清。 本文即圍繞代位權客體有關問題進行分析,以期拋磚引玉,求教于方家,并為《民法典》之實施貢獻綿薄之力。
二、追本溯源——代位權客體的歷史發端與理論爭議
根據胡長清先生的研究,代位權制度起源于羅馬法之強制執行法[2]。 羅馬法關于強制執行,是授權總債權人控制債務人的全部財產,總債權人再選定某一主管人或財產管理人將債務人全部財產變現,并分配價金于各債權人。 債務人之財產中有對外債權者,則向第三人收取該債權以清償債務。 此種方法為1804 年《法國民法典》所繼受,《日本民法典》又繼受之。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未設此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第七十三條首次引入代位權制度,《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以下簡稱《合同法解釋一》)對其進行了較為詳盡之規定,再到《民法典》出臺,用第五百三十五條到第五百三十七條3 個條文對代位權進行了規范。 《民法典》實施后,關于代位權的觀點分歧再起,而代位權客體問題就是爭議焦點之一。
(一)法律文本中代位權客體范圍之變遷
債權人代位權之客體,為債務人之權利。 然而債務人之權利,并非均適于代位,不適于代位行使者,自不能代位行使。 所謂適與不適,應依該權利可否為債權之共同擔保來定[3]。 我國《合同法》將代位權的客體限定為“債務人的到期債權”,即債權人代位權行使的對象只是債務人所享有的到期債權,債務人的其他權利,如債務人享有的合同解除權、合同撤銷權等,均不能代位行使。 《合同法解釋一》更是進一步將代位權客體限縮到了“債務人的到期金錢債權”。 相比大陸法系傳統理論,我國《合同法》關于代位權客體之規定本已狹窄,《合同法解釋一》之所以進一步限縮的原因,主要擔心如過分地擴大代位權的客體范圍,會造成“沖擊合同相對性原則”“威脅合同法相關制度”“三方當事人權益嚴重失衡”“損害交易安全”等惡果[4]。
在2005 年9 月最高人民法院給廣東省高院的復函中①《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深圳發展銀行與賽格(香港)有限公司、深圳賽格集團財務公司代位權糾紛一案的請示的復函》([2005]民四他字第31 號)。,最高院再次重申了《合同法解釋一》的立場,即“債權人只能向人民法院訴請以自己的名義代位行使債務人‘具有金錢給付內容的到期債權’,且該債權不能專屬于債務人,代位權的客體也不能擴張至所有權”。
隨著《民法典》的出臺,代位權客體范圍在法律文本上發生了較大變化。 依《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條第一款之規定,代位權的客體是“債權或者與該債權有關的從權利”。 對比《合同法》第七十三條及《合同法解釋一》的相關規定,改變非常明顯:第一,《民法典》所規定的代位權客體不限于“到期”債權,大大擴張了代位權客體之范圍;第二,去掉了《合同法解釋一》第十三條中“具有金錢給付內容”之規定,兩相對照,可知《民法典》明確將非金錢債權納入了代位權客體范圍;第三,《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條增加了“與該債權有關的從權利”之表述,將代位權客體擴張到了學理上無爭議的擔保、違約責任請求權等從權利。 《民法典》在代位權客體方面的這些變更,總結了代位權規則運行的經驗,也很好地回應了理論與實務界的建議。
據全國人大法工委介紹,在《民法典》編纂過程中,如何確定代位權的客體,的確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5]。 一些意見提出:其一,將代位權的客體限定為“債務人的債權”,范圍過于狹窄,不利于保護債權人利益,例如債務人怠于行使為其債權設定的擔保權利,影響債權實現的,也應納入代位權適用范圍;其二,從代位權制度的境外立法例來看,無論是法國、日本、意大利等國家的民法典,還是我國臺灣地區“民法”,都沒有將代位權客體限定為“債務人的債權”,只要債務人怠于行使影響其責任財產的權利,一般都可以由債權人代位行使,建議擴大我國代位權客體的范圍。 《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一審稿和二審稿吸收了這些意見,將代位權客體規定為“債務人的權利”。 在對合同編草案二審稿征求意見過程中,又有一些意見提出,將代位權客體規定為“債務人的權利”,將使債權人對債務人的經濟活動干預過多。尤其是債務人享有的合同解除權、合同撤銷權等權利,究竟是解除或撤銷合同對債務人的整體責任財產更有利,還是不解除或不撤銷合同更為有利,情況比較復雜,債權人不應直接代替債務人作出決定,建議限縮代位權的客體。 經綜合考量,《民法典》合同編最終將代位權的客體規定為“債權或者與該債權有關的從權利”,所謂“該債權有關的從權利”主要是指擔保物權和保證等擔保權利。
(二)法學理論中的代位權客體之眾說紛紜
實際上,關于代位權客體的范圍,學者們主要還是根據相應法律規則進行解釋的。 以我國臺灣地區為例,在民法名宿鄭玉波先生看來,得代位行使之權利,包括以下這些:物權及其物上請求權,一般債權及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價金減少請求權,選擇權,契約解除權,抵銷權,買回權,因錯誤、詐欺、脅迫之撤銷權,對于暴利行為之撤銷權,債權人之代位權與撤銷權,登記請求權,股份公司對股東之股款繳納請求權等[6]。 日本學者將代位權之客體解釋為包涵價款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其他債權、物上請求權等,另外,作為實體法上的權利或利益形式的訴訟上的行為也可代位,如訴訟的提起、強制執行的申請、請求異議的訴訟、第三人的異議訴訟、假處分命令的撤銷申請等[7]。 其主要的依據也是《日本民法典》第 423 條、第 582 條、第 754 條,《日本民事訴訟法》第 545 條、第549 條、第618 條等,以及相應的法院判例。
在《合同法》頒布實施之前,我國大陸學者主要參考域外法的理論與經驗,所認定的代位權的范圍也比較寬泛。 申衛星教授的觀點就比較有代表性,他認為,可以成為債權人代位權客體的主要有五大類權利。 其一,包括合同債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基于無因管理而產生的償還請求權、由于侵害財產權而產生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和違約損害賠償請求權等在內的各種債權。 其二,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土地妨害除去請求權、債務人對第三人財產上存在的擔保物權等各類物權及物上請求權。 其三,各類形成權,包括合同解除權、選擇之債的選擇權、買回權、抵銷權以及對因重大誤解或顯失公平而成立的民事行為的撤銷權和變更權等。 其四,如果債務人本人以第三人之債權人的身份而享有代位權或撤銷權,但怠于行使該權利,并危及其債權人的債權實現的,同樣,該代位權或撤銷權也可以成為債權人代位權的客體。 其五,一些其他權利,如中斷訴訟時效的權利、代位提起訴訟的權利、申請強制執行的權利和各種登記請求權等訴訟法上的權利或公法上的權利,也可成為代位之對象[8]。
《合同法》頒布之后,司法機關的態度雖然謹慎,但學者們對代位權條文及其《合同法解釋一》評論臧否就熱烈多了。 關于代位權客體的觀點大致可以分為窄口徑、中口徑與寬口徑三種模式。 所謂窄口徑模式主要是指恪守《合同法解釋一》之條文,將代位權客體限定為“到期金錢債權”。 不難理解,此種觀點主要集中于審判機關[9]。 寬口徑模式以崔建遠教授為代表,認為窄口徑模式過于狹窄,不符合債權人代位權制度的立法目的,應予以目的性擴張[10]。 崔教授主張,代位權之客體應包括如下幾類:“債權、物權及物上請求權、以財產利益為目的的形成權、以財產利益為目的的讓與權、清償受領權;以及訴訟法上的公權利,如代位提起訴訟、申請強制執行的權利等。”[11]持此種觀點的以學者為主。 而中口徑模式介于兩者之間,影響相對較小,在此不贅述。
應該說,三種模式各有其利弊。 窄口徑模式利于法院對代位權的認定,利于審判與執行,效率相對較高,但弊端在于對代位權客體限縮過緊,使許多應予代位的權利逸出于法律之外,沒有實現對債權人的合理保護。 而寬口徑模式在理論上覆蓋了較廣泛的客體范圍,利于保護債權人利益,但由于自身法理并未厘清,內部亦存在爭議,又無法得到司法實務的認可,終究只是流于呼吁。
有趣的是,《民法典》代位權文本雖已公之于眾,但關于代位權客體范圍的爭議并未塵埃落定,反倒繼續熱烈。 例如,有觀點認為,第五百三十五條的用語是“與該債權有關的從權利”而非“債權的從權利”,這意味著,客體范圍包括但不限于“狹義之債的從權利”,“廣義之債的從權利”也被涵蓋于其中了。 因此,基于合同產生的解除權等形成權也可以作為代位權的客體[12]。 雖然學者已經指出,此種解讀,盡管其擴張代位權客體之努力值得肯定,但有解釋方法上的問題①該解釋存在三方面問題:第一,混淆概念;第二,明顯違背法意;第三,缺乏體系觀。 具體分析請參見韓世遠《債權人代位權的解釋論問題》,《法律適用》2021 年第 1 期,第 33 頁。。 不過,類似分歧和爭議的存在,還是提醒我們,在代位權客體解釋問題上正本清源的重要性。
三、反求諸己——代位權制度之立法目的再認識
代位權客體的范圍界定之所以眾說紛紜,大概是因為論者沒有注意到在確定爭議問題之前,首先應該做的是明晰代位權制度之立法目的,并在此基礎上厘清界定客體范圍的標準。 從代位權制度設置的目的來看,是為了增加債務人責任財產范圍以保護債權人利益,同時又盡量不干涉債務人的私法自治。 因此,在解釋方面,應盡量體現上述之目的,以清晰界定代位權客體范圍所秉持的標準和原則。
(一)保護債權人利益為基本遵循
代位權客體界定的第一位原則,應該是保護債權人利益。 債權人保護的重大意義,在于它是對經濟信用、市場信心、社會信任的根本性支撐,是市場經濟有序運轉的基石,更是淳化社會風尚之經濟風向標。
債權等無形財產的誕生本身就是經濟社會發展、人類智力成果和信用體系制度化的結果[13]。 在前市場經濟的社會中,所有權,尤其是不動產所有權是最重要的權利和財富,在社會生活中占有支配地位。 進入到市場經濟時代之后,債權的作用日益凸顯。 最早是以與所有權相結合的方式,逐漸地,隨著所有權色彩的遞減,債權色彩遞增,直至獲得在近代法中的優越位置[14]。 在現代法中,債權、債更是具有支配性的地位。 債權之所以對于市場經濟運行有無可替代的基礎作用,原因在于,市場經濟運轉的基礎是,交易主體借助彼此之間的信任,促進專業化分工合作,從而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與社會經濟生活的繁榮。 本質上,市場經濟不僅是一種經濟體系,還是一種包括法律、社會、文化價值和體制的復雜體系[15]。 其中,法律是最重要的一環,隨著時間推移,如同混凝土一樣將整個社會凝聚在一起。
市場經濟的主體——現代企業的經營者,其常態是以賒銷、賒購等方式給予交易對手以信用,從而開拓市場與促進市場發展,完成對市場的占領,并最終在整體上實現經濟的正向循環①與農業經濟相對應,市場經濟最大的弱點不在于生產不足,而在于需求不足。 通過擴張信用而擴大市場、增加需求,可以促進商品與服務的供給,拉動經濟的發展。。 與賒銷相伴的則是企業的應收賬款不斷增加。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9 年底,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收票據即應收賬款為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