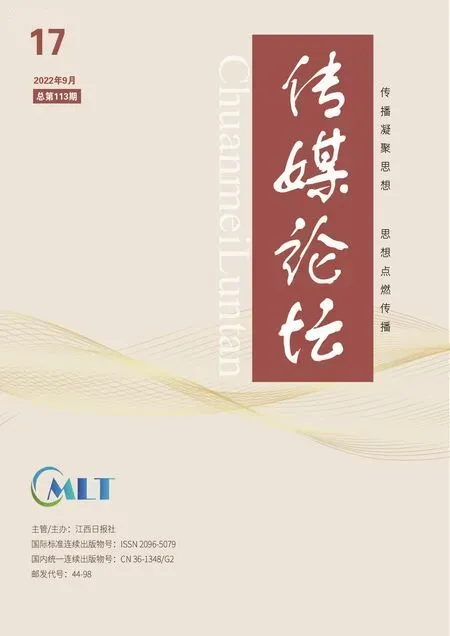從受眾心理的角度分析“她綜藝”火爆的原因
——以《乘風破浪的姐姐》為例
黃心悅
一、“她綜藝”火爆現象
“她綜藝”是指以女性為綜藝節目的主角,從女性視角出發,圍繞女性生活、工作、情感、社交等話題展開討論而量身定做的綜藝節目。近年來,女性向的綜藝節目也更加多元化,女性育兒綜藝、女性婚戀綜藝、女性成長社交類綜藝等多線開花。
但不難發現,過去這些國內的“她綜藝”在節目包裝后的主題上不論有多不同和多樣化,本質上議題的同質化趨勢顯現。不管是親子類節目還是成長類節目,“婚戀” 一直是最終落腳點。這種掛著女性招牌的“她綜藝”,看似找到了女性受眾所關心話題的最大公約數,實則在壓縮女性議題的空間,顯示傳統男權觀念的根深蒂固。
而《乘風破浪的姐姐》節目組另辟蹊徑,邀請了30位優秀的歌手、演員、舞蹈藝術家等姐姐參加“選秀”。但節目組并沒有真正按照選秀的方式來設計節目流程, 更多時候還是讓各位姐姐回歸她們自身,充分展現個人魅力,使淘汰制產生的競爭氛圍被極大地弱化了。所以,《乘風破浪的姐姐》更像是一場“表演類實驗綜藝——姐姐們假裝自己是未曾經過市場檢驗的選手,以女團的規則來重新衡量自己的價值。”這就符合了“她綜藝”最原始的命題了,將女性的多樣人生經歷最終都落腳于其自我價值的實現。
二、《乘風破浪的姐姐》火爆現象的歸因
(一)社會與文化歸因:女性意識的覺醒
1.規避“男性凝視”,女性話語權增強
“男性凝視”作為一個術語使用最初可以追溯到勞拉·穆爾維1975年發表的《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在書中,穆爾維認為在電影中女性不是主體, 往往是被凝視的客體。因為控制攝影機的因素之一來自大多數電影類型的主要觀眾是異性戀男性這一假設上。男性作為觀看者,女性作為被觀看者這個基本概念在如今國內以往的“她綜藝”中也是成立的。
而在《乘風破浪的姐姐》中,這樣一種“男性凝視”都被巧妙地規避掉了。作為這個節目里“男性群體”的代表黃曉明以及“規則制定者”的制作方,他們都有可以改變這一個小小“女性社會”的權力,但是最終他們話語權都被這些姐姐們鮮明的個性和犀利的觀點所消解。在這里女性不在乎男性對她們的評價和觀感如何,用自己的行為方式顛覆以往公眾“凝視”對女人的傳統認知。
2.女性群體的互助性增強
女性意識的覺醒還體現在女性群體之間的互助逐漸增強,也就是西方當代一些女性主義者推崇的“姐妹情誼”理論,這樣的目的在于號召所有女性力量團結起來,共同尋找有效的兩性對話途徑。在她們看來,女性要取得最終的勝利是必須要依靠同性的。而《乘風破浪的姐姐》作為“她綜藝”尊重了“姐妹情誼”這一主題。不同于以往的選秀節目,該節目的影像更加突出姐姐們惺惺相惜的情誼。
(二)經濟與技術歸因:互聯網賦權
經濟社會的發展帶來科學技術的進步, 互聯網的產生為人們帶來了便利。麥克盧漢提出“媒介即信息”的觀點,所以互聯網賦權的一方面就是指, 互聯網的媒介特性能夠讓更多的受眾獲取信息,并對此展開觀點的討論。“她綜藝”的受眾一開始是面向固定的觀眾,但通過互聯網的傳播就吸引了更多的人對這一類節目感興趣并選擇去觀看。其實,不管是出于何種目的來觀看節目, 都屬于互聯網賦權的成功案例。
另一方面,隨著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社會上兩性平等的觀念進步,女性便逐漸想要建構一種屬于女性的話語體系。而網絡化的進程也正給女性群體提供一個好的發展平臺和趨勢。在虛擬網絡中,人們更關注個人的觀點和言論。這就相當于放緩了性別的區分,使得女性能夠遠離社會或男性對其的傳統的期待和“凝視”,擁有了一個更加自由表達自我的空間。
三、受眾心理分析
(一)選秀類型的節目形成偶像崇拜——準社會交往
“準社會交往”概念的提出是在1965年,心理學家霍頓和沃爾在《精神病學》雜志上發表了有關文章。這一概念是用來形容受眾與媒介人物的關系,但它只是一種單向的想象關系。也就是說受眾對于媒介中的人物——明星名人甚至是虛構形象,就像對待身邊社交范圍內的人一樣,會對她們做出認知和情緒反應。由于他們建立的這一種關系類似于現實中面對面交往的人際關系,所以被稱為“準社會交往”近年來該心理最為典型的代表反應就是“追星”,以《乘風破浪的姐姐》為例,背后的“追星文化”就非常值得展開討論。
首先是其獨特的節目模式——選秀類綜藝。 一方面,該節目的基本模式就是“真人秀+線上投票”,不同于青春女團選秀,它不用花錢讓粉絲打榜、做數據,只需要在網上通過鏈接為喜歡的姐姐投上一票,就能為其助力,所以對于大部分受眾來說這是一種“低成本、高收益”的社交付出,他們是愿意并擁護的。另一方面,美國學者亨利額·詹金斯在做粉絲文化研究中提出了參與性文化。《乘風破浪的姐姐》的受眾在觀看節目的過程中參與度就非常高,他們既能夠去公演現場當觀眾參與投票,也能夠通過互聯網根據自己的喜好參與線上投票。同時,官方通過開設多個社交平臺的賬號給受眾提供一個表達自己的平臺,也賦予了受眾自主解讀姐姐們舞臺表演的權利。
其次,準社會交往一個最重要的基礎就是“交往對象的可視性”。許多媒介人物都通過當代的互聯網媒介變得更加具象直觀,引發的準社會交往的對象有社會交往的普遍對象——真實生活環境中的人,轉換為虛擬環境中的人物,這就突破了真實社交環境空間上的接近性和交往對象上的熟識度。《乘風破浪的姐姐》在影像技術上就滿足了這一條件。該節目通過芒果TV線上播出,不僅有正片的按時播放,還會在播出期間安排姐姐們通過直播、參加其他綜藝活動等形式不斷地出現在受眾面前,強化她們在受眾心中的形象,也以此來強化受眾與她們之間的弱關系。正如米蘭·昆德拉在他的小說中提到的,人們越來越從依賴親身經歷向依賴影像進行轉變。而明星又是典型的互聯網時代影像文化的產物,所以“追星”成為一種契合準社會交往心理的自然行為。
(二)尋求信息和共情反思——認知動機
認知動機主要是研究人的認知的內部心理機制的問題,其關注的核心是信息發生在人心理的輸入和輸出之間的過程。認知心理學提倡信息的獲取、存儲、提取、加工和應用的觀點,所以又稱之為信息加工心理學。認知動機是受眾普遍存在的一種尋求信息的心理,而人們對于信息事物的認知在內部心理是有著深淺不同層次的接收效果的。
淺層次的認知動機是受眾停留在事物最基礎的認知層面,包括外形、結構或者是事件的過程。但淺層次認知動機的局限性在于它只是滿足受眾的好奇心,并沒產生更加深遠的實際傳播效果。這對于正在成長的綜藝節目來說是遠遠不夠的。
深層次的認知動機的傳播效果能彌補這一局限性。因為這種傳播效果進一步影響其個性、品質等內在心理。《乘風破浪的姐姐》就通過對姐姐們“臺上表演+臺下訓練和生活”的雙線拍攝模式,推動受眾成為姐姐們成長蛻變全過程的見證者,在這樣的情境下更能激發受眾的自我反省。在節目的不同情境下,受眾也會有不一樣的認知反饋。例如當姐姐們接受采訪輸出觀點時,受眾便會對她們的人生經歷感興趣、被她們獨特的個性和正向的價值觀所吸引,從而來調節自身行為。
另一方面,《乘風破浪的姐姐》不僅僅將節目定位在女性選秀類節目,它作為“她綜藝”,不斷向受眾輸出價值觀、女性生存狀態等,從而刺激受眾的心理,感受女性獨有的魅力和品格的同時,也能急切地去思考女性生存現狀等問題。而且,在深層次的心理動機產生之后,受眾會更加依賴節目價值觀的輸出,他們需要通過進一步接受信息來佐證他們思考的問題,從而在收視率上形成了一個閉環。
(三)女性的尊重需求凸顯——自尊需求
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將人的需求,它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和歸屬感、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實現需求。而“她綜藝”節目廣受歡迎就是女性對于尊重需求—需求理論中的第四層理論的外在表現。女性渴望得到社會對其各方面價值的認同,特別是作為個體,希望擁有像男性一樣平等的地位和權利,從而改變長久以來女性的一種服從地位—既有對于自我尊重的追求,也有對于自由意志的向往。
《乘風破浪的姐姐》相較于其他女性選秀類節目更加削弱了其競爭的尖銳感,嘉賓之間的氛圍也更加自然輕松。通過“公演舞臺+練習日常+生活化場景”三個主要場景轉換的敘事邏輯,從不同維度地構建每一個姐姐的獨特的女性形象。節目制作的重點并不是放在女性依附于某一角色、標簽而帶來的故事上,而只是拍攝這些姐姐們自己單純的作為一名女藝人的臺前幕后。同時,在節目播出時還推出了易立競老師的深度訪談節目《定義》,每周邀請一位姐姐進行訪談。姐姐們自己的故事與易立競老師的問答談話更加柔和,跟正片中的女性形象又有些不一樣, 一方面給女性構建了一個話語場,并通過記錄她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傳遞給更多的人也是對女性需求的一種尊重;另一方面,節目組也再次構建了女性形象的另一個維度, 使得受眾能夠了解更加真實的女性力量和女性魅力。
四、對“她綜藝”火爆現象的思考
(一)規避節目議題趨于同質化
“她綜藝”作為一類再次獲得熱度的綜藝,其在技術和資本的雙重助推下已然在影視行業形成了一套日趨成熟的生產機制。但作為以女性為主的綜藝節目,一旦套用市場化生產的模板就很容易再次落入刻板印象的窠臼。
隨著對女性個體意識與自我情感的關注度提高,《乘風破浪的姐姐》《聽姐說》《姐妹們的茶話會》等綜藝節目出現,不再將女性的議題囿于情感之中。但不難發現,當節目將女性打造成一個又一個精致、獨立、高知的形象,迎合新時代女性需求的同時,似乎將成功女性的模板再次刻畫了出來,讓受眾很難再提起興趣。
好的節目是能夠大范圍地與受眾共情,但當同質化的內容和節目議題扎堆出現時,便容易導致情感的泛濫,從而弱化受眾對該議題的敏感度。所以,女性有關的議題絕對不只是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這些——情感、婚戀、職場。作為節目的創作者,將目光看向其他特質,我們能挖掘到更多的內容。
(二)警惕狂熱推崇“女性主義”的異化
“她綜藝”本質上是一種以女性為主角的綜藝節目類型,但隨著《乘風破浪的姐姐》等類似展現“新時代獨立女性”主旨的節目出現,就有越來越多的自媒體踩著女權主義的熱度兜售“偽女權”的焦慮。
女性主義理論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的本質以及著重在性政治、權力關系與性意識之上。而這些自媒體平臺卻借著“她綜藝”的熱度傳播女性“應有”的“權利”,挑起兩性矛盾。他們本就需要迫切地尋找社會中“因性別不同,從而待遇不同”的熱點,引爆輿論,煽動群眾情緒,而“她綜藝”的產生就帶來了這樣的機會。以至于甚至有少部分缺乏理智的人仇恨男性、叱罵政府。長此以往,女權主義便很容易走上異化的道路,也很難不讓人“提女權色變”。
所以一方面,節目組在推出“她綜藝”時也要注重對社會輿論的影響,要正確引導受眾的觀點輸出和情感表達;另一方面,受眾不能完全沉浸于自媒體或是網絡上的輿論狂歡,在觀看節目后應該有自己的思考,多一份理性,少一份沖動,在健康的輿論環境中真正地實現自我表達。
五、結語
隨著女性的自我意識逐漸覺醒,她們需要借助媒介等來獲取話語權,為自身的權利和價值實現做斗爭。而“她綜藝”的產生和火爆的收視率也都證明了人們性別平等觀念和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對于受眾而言,“她綜藝”的播出也正是滿足了部分女性的尊重需求,在互聯網上構建女性話語場的同時也通過媒介凸顯了女性的多種可能性。而以《乘風破浪的姐姐》為例的新風格“她綜藝”,則是以弱化選秀競技、強調女性個人形象的方式,滿足了受眾的認知動機和準社會交往心理需求,使得受眾在“追星”的同時也能夠自省自勉,達到了較好的社會傳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