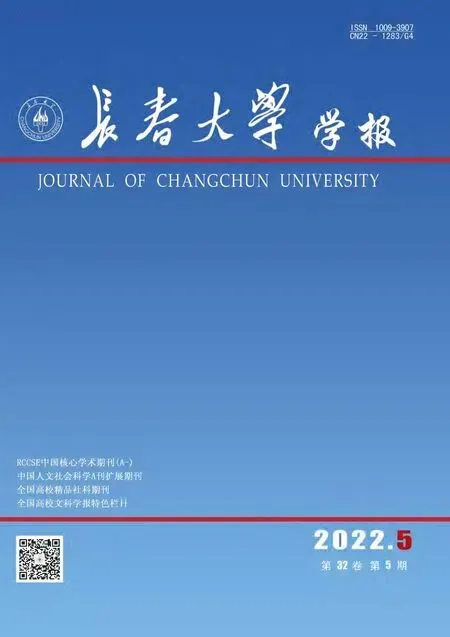武士窮途的侘寂之美:山田洋次的武士三部曲
白 蔚
(沈陽航空航天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沈陽 110136)
日本特有的傳統審美文化有三大基本范疇——物哀、幽玄、侘寂,在日本藝術作品中多有呈現。電影研究者較多注意到了日本電影藝術所表現的物哀之美,而對日本電影文化獨特的侘寂審美相對著墨不多。侘寂之美,更多的在俳偕、茶道、書畫和園林建筑中被廣泛關注。其實,物哀、幽玄、侘寂三者在審美趣味上是有內在共通之處的,在精神深層次上是相互勾連的。“‘物哀’是鮮花,它絢爛華美,開放于平安王朝文化的燦爛春天;‘幽玄’是果,它成熟于日本武士貴族與僧侶文化的鼎盛時代的夏末秋初;‘寂’是飄落中的葉子,它是日本古典文化由盛及衰、新的平民文化興起的象征,是秋末初冬的景象,也是古典文化終結、近代文化萌動的預告。”[1]江戶時代,作為明治維新前封建幕府統治的最后一個歷史時期,恰如日本古典文化向近代文化過渡的秋末冬初,身處其時的武士宛似落葉,注定飄零。日本著名電影編劇、導演山田洋次的武士三部曲①即《黃昏的清兵衛》(2002年)、《隱劍鬼爪》(2004年)、《武士的一分》(2006年)。文中分別簡稱《黃昏》《鬼爪》《一分》。以江戶時代沒落的武士制度為歷史背景,通過描繪日暮途窮的武士的歷史命運和個體遭際,以日本文化特有的侘寂之美消解武士道的殺伐之氣,對武士道精神進行了內在批判和重新詮釋。
一、侘:人在宅中的空間敘事
“侘”(わび)在日語中是一個固有詞匯,它由動詞(わぶ)和形容詞(わびし)轉化而來,不論是動詞(わぶ)還是形容詞(わびし)都有孤獨寂寞、頹喪凄涼之意,帶有負面的消極色彩,表現的是迫不得已離群索居的生活境況與心理狀態。經鐮倉時代和室町時代隱逸山林的文人墨客的提煉,“侘”由一個負面意義的詞,逐漸向正面意義轉化,確立了積極的審美價值。文人墨客給原本貧窮、寒磣、苦悶、殘缺等消極行狀賦予了幽靜、清雅、閑寂、荒寒的審美意味,把他們所面對的物質匱乏、身體殘缺、精神孤獨等物質、肉體、精神的局限轉化為解放的契機,于困頓中求超越,在孤獨中見自性,由迫不得已離群索居的被動消極的生活境況轉化為無所依傍、自在悠游的主動積極的心情意緒。而鐮倉時代和室町時代正是武家政權統治日本的時代,也是武家文化隨著武士階級的成長壯大走向繁盛的時代。之后,在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稱霸日本的安土桃山時代,武家貴族文化走向繁榮,大名為顯示其財富和實力,在造型藝術、建筑藝術包括室內裝飾上,不遺余力錯彩鏤金,引領了當時以富麗繁飾為美的風尚。村田珠光、武野紹鷗、千利休等人卻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侘茶的理念,以“侘”為載體,在茶道藝術上講究在極盡簡樸、狹小的草庵茶室中飲茶,進而提升出一種清貧自守、孤高自許、枯淡質樸的道德境界和審美精神,并將這種簡約之美衍化為禪修的方法。侘茶之侘,暗合了普通百姓的生活現狀,給他們提供了安貧樂道的心靈慰安,很自然就被市井庶民階層接受和認可。另一方面,就武士階層內部而言,武士雖居于士農工商四民之首,不事生產,有佩刀冠姓的特權,但武士階層內部實則等級森然,下層武士俸祿微薄,以儉樸為美更有利于維系武士貴族對整個武士階層的統治秩序(1)在溝口健二1955年執導的《新平家物語》中,武士得勝還朝,貴族卻吝于賞賜,給出的理由就是“武士有錢就變壞了”。。“依據武士道的發展史,通常將平安時代末期、鐮倉時代、室町時代和安土桃山時代的‘武士道’稱為‘本來的武士道’(菅野覺明語)。這個時期的武士是戰場上的戰斗者,因此這個時期的‘武士道’也是以如何直面死亡為主要內容的。而到了‘文恬武嬉’的江戶時代,武士則由戰場上的‘戰斗者’變為了日常狀態下的‘為政者’。這就需要從倫理道德上來提高武士的修養,使其在和平時期也能夠成為普通民眾的楷模。”[2]侘茶之侘,依托日本佛教禪宗文化的背景,適應了武士從戰斗者向為政者角色轉換的需要,符合武士道向士道轉換過程中文武合一的修養要求,給征戰殺伐、紙醉金迷的武士貴族提供了超現實非功利而又簡便易行的道德理想和修養途徑,因而也得到了武士貴族的支持和推崇。在社會廣泛認同之下,侘以侘茶為媒介,逐漸成為日本傳統美學中極富民族特色的一種美學理念。
在古漢語中,“侘”鮮少單獨使用,常與“傺”字合并成“侘傺”一詞,表達的也是失意、憂戚、落魄的敗落蕭條之意與孤獨寂寥之感。日語受到中國漢語文化的影響,不僅將“侘”的意義加以借用引申,還將“侘”這一漢字單獨拈出,直接揭出“侘”作為象形文字標記的“人在宅中”的含義。“人在宅中”之人即所謂“侘人”,也稱“屋人”。
山田洋次的武士三部曲以“人在宅中”的空間敘事表現了侘之空間美學。《一分》中的主人公三村、《黃昏》中的清兵衛、《鬼爪》中的片桐,雖然都是有職責在身的武士,每天要上班工作,但電影將更多的鏡頭對準了他們“人在宅中”的“侘住”狀態,狹窄的室內空間成為主人公最主要的生活空間。主人公也以自己“侘”在家中的“侘人”(屋人)自居自樂,這些帶刀的上班族,并不以上班為榮,更享受宅在家中的日常生活。《黃昏》中的清兵衛每天黃昏下班準時回家,從不參與同僚的娛樂聚會,因而還得了個“黃昏的清兵衛”的綽號,電影一再表現了他歸家后在燭火下與家人一起制作蟲籠的場景(2)制作蟲籠是為了賣錢貼補家用。;《一分》中,三村和妻子、老仆在屋中吃飯聊天的畫面;《鬼爪》中,片桐在屋中讀書寫字的畫面,也是屢次出現。狹窄的室內空間成為武士三部曲中最常見的景觀。千利休將茶室空間縮小至極限,在室內裝飾上也極盡簡化,除了保持原色的茶道具之外,僅余一枝淡雅插花或一幅水墨掛軸,刻意剔除裝飾手段的豐富性以表現空間細部隨時間流逝升華出的自然美感。武士三部曲著意表現了延續自千利休的侘的空間美學。生活空間狹窄,房屋外觀陳舊,室內陳設也簡樸得近乎寒磣……入不敷出的下級武士物質上的匱乏,觀眾一眼可以洞見。
侘的空間美學、人在宅中的空間敘事,不僅表現在狹小局促的生活空間,還表現在因為主人公離群索居而變得更為逼仄的社會空間、人際空間。清兵衛因為妻子早亡、老母癡傻、兩女年幼,忙于家事無暇打理換洗,從不參與應酬,被同僚排斥。三村和片桐都是只有30石俸祿的下級武士,同為武士階層中的邊緣人:片桐父親含冤切腹而死后,家道一落千丈,親戚都與他斷絕了往來;三村本就是一介貧寒武士,中毒失明后更在武士群體中淪為無用之人。清兵衛和片桐都被同僚認為不合群、不上進。物有所不足,人亦有所不足。清兵衛是個鰥夫,身為武士卻因不修邊幅被同僚和上級嘲笑嫌棄;片桐是個父母早亡、大齡未婚的光棍漢,因為父親切腹謝罪的死而使家族蒙上陰影:俱是家庭不完整的煢獨之人。唯一家庭幸福的三村,原本長相英俊,卻因替主公試食而中毒失明,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身體殘缺之人,原有的家庭和睦、夫妻恩愛也因為他中毒后妻子被上級武士欺侮而不復存在,妻子失身使他蒙受了道德和情感上的雙重屈辱。物質上困窘、社會生活上與人疏離、身體上殘缺,武士三部曲中的主人公基本可以被看作是畸零狀態,但他們卻不自棄、不氣餒。清兵衛說,“看著女兒一天天長大,就像看著莊稼或花草的生長,使我很快樂”,自愿放棄提高俸祿的機會,拒絕了親友讓他續弦的建議,因為他既不想拖累別人,也不想隨便找一個身體壯實能干活能生養的女人茍且度日委屈自己,他希望找到一個像自己一樣無怨無怒、甘于貧窮,能在簡樸生活中體味真美的伴侶;三村失明后有一段掙扎過程,最終接受了自己的殘疾和妻子的失貞。“‘侘’就是對不滿足、不完美、有缺陷的狀態(‘不完全美’)的一種積極的接受,就是對缺陷之美的確認。”[3]153知足少欲、隨遇而安、樂天知命,這正是“侘”的真義。如果“因不自由而生不自由之念,因不足而愁不足,因不順而抱怨不順,則非‘侘’,而是真正的貧人”[4]296。武士三部曲中的主人公面對不自由、不完滿、不富足、不順遂泰然處之,在世俗看來落魄寒愴的生活狀態中安享人生的意趣、深昧生命的美妙,“不自由的時候不生不自由之念,不足的時候沒有不足之念,不順的時候沒有不順之感。這就是‘侘’”[4]296。用山田洋次自己的話說:“武士心中有強烈的責任感,面對樸素生活能夠心情平靜,對他們來說,窮困并不是一件可恥的事,不管怎么貧困,都要清潔地生活著。”[5]獨居之時,君子固窮而見“侘”,“侘”之真義更表現在與人相處時固守自己的內心規范,不被世俗所左右。與社會保持距離的孤獨感正可怡情悅性,“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王陽明《詠良知四首示諸生》),內心的堅忍自守仿似自家有無盡寶藏,使他們能夠以精神生活的豐盈充塞貧困的物質生活。連同主人公身邊的人也在清簡的生活中洋溢著安貧樂道、樂天知命的精神。《黃昏》中,一邊編織蟲籠一邊唱誦《論語》的清兵衛的女兒,和兩個小女孩一起嬉笑、觀看農民表演、學唱童謠的朋江;《一分》中,總是被主人三村善意嘲謔而樂呵呵的忠實老仆,一邊清掃或縫補一邊笑看小鳥、靜聽蛙鳴的加世;《鬼爪》中,一邊勞作一邊吟唱和歌的言笑晏晏的希惠。在幕藩更迭、大名混戰的戰國時代,戰亂頻仍使平民百姓深受其害,黑澤明在《七武士》中,借三船敏郎飾演的菊千代的口,說出了平民百姓的苦:“正是你們武士!一打仗你們就燒村莊,糟蹋莊稼,到處征糧抓丁,欺辱女人……有反抗的就給殺了,你們說老百姓怎么辦好啊!”戰爭中,武士的燒殺劫掠造成了農民生活的困苦,而不事生產的武士階層恰恰又是由農民供養的。《黃昏》中,山田洋次也直接通過朋江小姐的口說“仰賴農民的恩賜,武士才能作為武士生活”,清兵衛和女兒到河邊掘野菜時、清兵衛和好友到河邊釣魚時,都出現了早春消融的河面飄浮著餓殍的情景。武士三部曲沒有回避武家政權與平民生活的對立,但山田洋次敘述的重點不再直接表現戰爭給人民帶來的困苦以凸顯階級矛盾,也沒有像傳統的武士電影(劍戟片)那樣濃墨重彩地描繪武士戰斗場面給觀眾營造視覺奇觀,而更多的是將筆墨投向了日常生活中的空間敘事,通過居家煮飯、打掃、針線縫補、砍柴之類極為平淡的日常場景,著力表現了生活不如意、蹉跎不得志的下級武士和底層平民苦中求甘、化苦為樂的侘之美。
二、寂:歷史磨洗的時間敘事
武士三部曲所表達的侘之美,可謂深昧禪宗“孤獨乃真實相”的人生況味,主人公在荒寒的孤獨之境中觀照自己的內心世界,體認生命的價值,感受“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超越之美。這種孤寒的空間美感在電影中因為加入了歲月磨洗的時間敘事,進一步生發出寂之味。
在室町時代之前,日語中的“寂”(さび)基本混同于“侘”(わび),“從室町時代起,‘さび’用‘寂’字來標記,主要指的是存在的時間性、時間感,具有經歷漫長的時間沉淀、歷史積淀之后,所形成的古舊、蒼老,以及呈現在外的灰色、陳舊色、銹色,并以此所體現出獨有的審美價值”[3]150。電影中的食具、臥具、盥洗的木盆、插了枯枝野花的花瓶,都極為簡素樸拙,老舊的外表下透出歲月磨洗的銹色。三部電影的色調都非常素雅,音樂基調也沐浴在深沉寧和的氣氛中,多采用自然聲效,很少有渲染情感的配樂,甚至人物間的對話與情感交流也含蓄蘊藉,整體符合寂之美,在表現寂之色、寂之聲之外,更不乏寂之情。《鬼爪》中,片桐早已喜歡上16歲就到他家做工的希惠,希惠的出嫁,宛如熄滅了家中的最后一盞燭火,在料峭的春寒中,他惦記著給希惠買和服領子,在得知希惠被婆家虐待后,他果決地把她從婆家搶出,并在商人婆婆面前放出“如果有必要,我會豁出我這把刀來保護她”的豪言,卻遲遲不肯表白;《黃昏》中,朋江之于清兵衛一家,也仿佛光耀的燭火,溫暖著主人喪妻、幼女失母的生活,清兵衛對青梅竹馬的朋江早已情根深種,對朋江的情感即便在兩人各自成家后也從未褪色,勇于把朋江從家庭暴力中解救出來,卻怯于愛情,在決戰前夕才敢吐露真情。為了所愛奮不顧身,不懼世俗成見,卻不肯輕易作出愛的承諾,百般克制的苦戀,不是真的膽怯,只為謹守身為武士的責任感。含蓄蘊藉的對話與交流表現了人物情感的克制內斂(克己節制恰是日本武士的傳統美德),既體現了侘之美,也體現了情感經歷了歲月淘漉的時間感。
江戶時代,武士出身的俳句詩人松尾芭蕉承繼了室町時代侘與寂的美學精神,并在他的俳句創作中進一步明確了“寂”這一美學理念:“它不僅客觀冷靜地觀察衰老、孤獨、寂寞等,而且從宇宙的大視野把握人的存在。認為人的孤獨是必然的,與其同孤獨抗爭,莫如投身孤獨,從孤獨中發現美。”[6]15芭蕉本人因此也被稱為日本“寂”之集大成者。芭蕉所提出的“寂”的美學理念,與“侘”的顯著區別在于,“它能夠將孤獨上升到宇宙的高度,指出這是人生永恒的主題。它認為一個對人生短暫無常有充分覺悟的人,是不會害怕孤獨的,相反他們能夠平靜地接受衰老、孤獨、死亡一步步靠近的這個現實,并且從中發現美”[6]15。概言之,侘與寂都指向孤獨超邁的人生境界,但二者的維度不同,侘主要標記主體存在的空間感,寂主要標記主體存在的時間感,而將寂融入侘,則是表現為時間的空間,加強了空間敘事的歷史縱深感,進一步強化了蒼涼寂寥的荒寒之美,如唐人詩句所描摹的“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山田洋次在武士三部曲中巧妙地借用了松尾芭蕉俳句中“寂”的意象。如:《古池塘》“青蛙跳進古池塘,古池發清響”;《螢光》“草葉螢光,閃閃,墜地又開揚”;《枯樹之鳥》“秋日黃昏時,孤鳥棲枯枝”。《一分》中屢次出現了黃昏蛙鳴、螢火蟲飛舞的景象,妻子離家后,鳥籠里的鳥只剩下一只,雖然孤鳥不是棲在枯枝上。《道旁朝顏花》:“我騎行于道上,馬欲嗅食道旁花。”三部曲中頻頻出現道旁花的景象,清兵衛在下班途中看到道旁杜鵑花開,還特意駐足觀賞。
日本古典文學中常見的“黃昏”意象更是頻繁出現在三部電影中。早在平安時代,女作家清少納言就在《枕草子》中這樣寫道:“秋天以黃昏最美。”黃昏秋風起,最易使人生發物哀之嘆、感受侘寂之美。鐮倉時代的和歌詩人藤原定家留下了一首描寫秋日黃昏夕陽西下的和歌:“秋日黃昏,不見紅葉和野花,唯見海邊草庵獨自沐于斜陽下。”這首和歌對日本古典文學的影響力,不啻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之于中國古典文學,后者被尊為“秋思之祖”,前者被后世奉為注解侘寂的經典。在“俳圣”松尾芭蕉的俳句中,“深秋日暮”“暮秋寂寞黃昏”的意象更是俯拾皆是。如《鬼爪》中希惠所唱的和歌“夕陽靄去兮”,暮靄中散去的不僅僅是夕陽,還有行將落幕的幕府制度的殘照、注定凋零的武士生命的余暉。三部曲中的“黃昏”作為視覺隱喻的象征符號,既直接表征了黃昏景象的寂之美,也指稱著武士制度的黃昏、武士家族的黃昏、武士個體生命的黃昏。寂的時間美學通過武士制度的歷史時間、武士家族的傳襲時間、武士個體的生命時間展開敘事。
江戶時代德川幕府統治后期,是即將落幕的武家政權最后的黃昏晚照。三部曲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將武士制度的歷史時間具像化。延續幾百年的武士制度的歷史時間,在電影中以武士家族的傳襲時間的中斷和武士個體的生命時間的終結的方式結束。由于武士身份是家族傳襲的,所以電影中的武士都出身于武士世家。武士家族的傳襲時間在電影中以不同的方式中斷:一是主動的方式。如《鬼爪》中片桐自動放棄武士身份,奉還俸祿自請退出。二是被動的方式,即武士個體的生命時間的終結。終結的方式有:(1)切腹,如《鬼爪》中片桐父親的“憤腹”(憤慨于無實之罪的切腹),《一分》中廚衛長的“引責”(對過失承擔責任的切腹),《鬼爪》中狹間的同伴的“刑死”(因犯罪被責令切腹),《一分》中島田的“名譽”(被失明的下級武士砍傷手臂后為保住臉面切腹);(2)活活囚禁等死的“入鄉”(《鬼爪》中之狹間,后脫逃);(3)被剿殺(《黃昏》中之余吾善右衛門以及《鬼爪》中最后被槍殺的狹間);(4)戰場上戰死(《黃昏》中之清兵衛)。
電影中最具悲劇意味的武士的死都發生在黃昏。在黃昏的火槍聲里,憤然倒下的狹間,被子彈擊斷的手還緊緊攥著武士刀。這是三部曲中唯一具有暴力色彩的鏡頭。在決斗之前,片桐一再勸他切腹以保全武士的尊嚴,他本欲與片桐進行最后的較量,卻被暗處的火槍打掉了右手,自認未死于武士刀是他的恥辱,片桐也深深理解狹間身為武士的生命被火槍終結的不甘。余吾善右衛門曾是被藩主棄用的浪人,帶著妻女流離失所,如喪家之犬乞食于寺廟,妻女相繼病死,他重被任用,卻又不幸淪為藩中高層內斗的犧牲品,死之前一直珍藏著女兒的骨灰,留下的最后一句話是“好黑暗的地獄”。
狹間與余吾善右衛門在臨死之前,都忿忿不平地對武士制度和武士道發出了靈魂拷問——狹間說:我為藩主、為國家謀求更好的前途,何謂不忠?真正不忠的是那些中飽私囊的家老們。余吾善右衛門說:我為藩鎮付出了一切,身為家臣受城主之恩遇,受其恩忠其事,何罪之有?面對這樣的詰問,受命前來執行斬殺任務的片桐和清兵衛無法回答,說明隨著時代變遷,舊有的武士道的價值體系已分崩離析,執守主從關系的愚忠和以殺人為尋常事的悍勇,已不足以支撐武士個體的精神世界。同為武道修為卓越的高手,片桐與清兵衛對以殺伐征戰為己任的武士職責充滿了懷疑,與“殺人勿置于心”(《葉隱》語)的武士規訓更是背道而行,接受藩命不得不去殺人之前盡力抗拒,執行斬殺任務之后沒有“事了拂衣去”的瀟灑從容,而是兔死狐悲、同命相憐的痛惜和悲涼。片桐說,殺人即使對武士來說也是很難的,除非迫不得已,我的武士刀絕不輕易出鞘。清兵衛更直白地表達了對殺戮的厭惡:“經過這么多年艱苦的生活,和老母、病妻、幼女生活在一起,我已經失去揮刀的欲望。殺人者,需要有野獸一般的兇猛和冷血,但現在我兩樣都不具備,也許在深山里和野獸一起生活一個月,我可以尋回它們。”這樣的話無異于直指好戰、嗜殺是野獸之行,令觀眾很容易聯想起發動侵略戰爭、制造野蠻屠殺事件的日本曾招致的尖銳批評——“披著文明外衣有著野蠻筋骨的怪獸”[7]。同時,清兵衛的這一番話也如電影中的點睛之筆,令觀眾看到平淡生活中特有的侘寂之美消解了武士道的殺伐之氣,對武士道進行了內在批判。電影的打斗場面拍攝得十分克制而寫實,因為導演無意渲染復仇的一時之快,而是要著意彰顯主人公的“生”的自覺:盡管生命是短暫的,有諸多缺陷和不足,它仍然是真正的珍寶,“活著才是最重要的”(片桐語)。正因為有“生”的自覺,才有“死”的覺悟。只是這種“死”的覺悟不是建立在忠君獻身、好戰嗜殺的對生命的賤視上,而是建立在平凡生活的侘寂之美上。
與狹間、余吾善右衛門死之前的痛苦不甘顯然不同,清兵衛和片桐、三村作為武士能夠“覺悟到死為常住”(鈴木大拙語),能在關鍵時刻參悟生死,進而超越生死,以向死而生的決心,心無掛礙地面對一切挑戰,包括無可避免的生死對決,正合上文松尾芭蕉所提煉的“寂”的美學理念。所以,雖然清兵衛一生沒有取得與他的才德相稱的地位與財富,與朋江婚后三年就戰死沙場,短暫的人生在旁人看來很不幸,清兵衛的女兒卻認為父親短暫的一生是幸福的,她說:“家父并非苛求功名的人,他絕不會自認為不幸,他深愛女兒,又得到美麗的朋江小姐的愛,他短暫的人生充滿著美好的回憶,我也因這樣的父親而驕傲。”
三、結語
生死之際最能體現武士道的核心精神。傳統武士道以“死”的覺悟為中心,18世紀初根據山本常朝的表述編撰成書的武士道經典《葉隱》開篇即曰:“武士道者,看穿死事之謂也。若于生死擇一,則首選死也。”[8]山田洋次的武士三部曲從生死之際武士個體生命的時間美學切入了武士道的精神腹地,深刻剖析了武士道的核心精神,以“生”的自覺超越了傳統武士道“死”的覺悟。三部曲的主人公用自己的行動對舊武士道進行了顛覆性的重新詮釋:武士絕不會出賣自己的同伴,是謂“義”;正因為身為武士,有的事情決不能袖手旁觀,是謂“勇”;以惻隱之心對待弱者,懲強扶弱,是謂“仁”;在困窮中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利不茍就、難不茍免,是謂“忠”。為了捍衛真正的武士尊嚴,片桐不惜抗命,以下犯上手刃家老,三村以視死如歸的決心敢于以殘缺之身挑戰上級武士。但在大仇得報之后,他們并沒有感到復仇的快感,而是無盡的空虛,片桐因為再也不想殺人而主動放棄了武士身份。與舊武士道卑生重死、賤生親死的傳統截然相反,在他們心目中,“不殺”之仁才是真正的武士道。武士三部曲改編自藤澤周平的武士小說,“真正的男人不會為英雄的榮譽去死,而要為心愛的人活著”[9],既是小說作者藤澤周平的理想,也是山田洋次對武士道精神的新詮。
狹間、余吾善右衛門的死,充分體現了幕末武士無可選擇的悲情命運,清兵衛和片桐、三村也同樣逃不脫武士途窮的悲情。但他們能夠慨然接受悲情,在悲情中堅守自己內心的武士尊嚴,發掘平淡生活中的生命意義。這也是山田洋次所要表達的武士道精神的正面價值。圍繞堅忍內斂的武士所展開的,被時代裹挾不可抗拒的悲劇命運,面對惺惺相惜的同伴身陷歧途的愛莫能助和對終身摯愛的苦苦守候,以及在這種苦況中的道德堅守和審美追求,是武士道的正面價值傳統在日本國民性中的精神延續,也是日本民族在經歷兩次大戰重創后重新崛起的精神根基。
以武士道為外在體現的日本意識形態已內化于日本人的心理深層,如丸山真男所說的歷史意識的“古層”。所謂古層,“是在意識深處貫穿各個時代持續存在的——這種情況下的意識是集團的意識,它在不同時代促進或者限制不同思想的發展并賦予它條件”[10]。深植于日本國民性中的武士道,并沒有隨著武家政權的落幕和武士階級的凋零而消亡,而是一直延續到今天,成為潛藏在日本國民內心深處的集體無意識。正如新渡戶稻造所說,“作為舊日本的締造者和產物,武士道仍然是轉型期的指導準則,并將被證明還是塑造新時代的決定力量”[11]105,“它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無聲無息的。國民的心對自己繼承的精神,雖然不問原因,卻能對其任何召喚都作出回應”[11]109。武士道成為日本民族回應外來挑戰的巨大心理屏障,對本民族的生存與發展而言,它是一把雙刃劍,既是一種自我保護,也是一種自我囿限。武士道精神的每一次勃興,幾乎都或多或少地伴有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和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現實訴求,甚至催生軍國主義。山田洋次通過電影重新詮釋的武士道,無疑是藝術的理想化表達。我們在對電影進行審美賞鑒的同時,必須高度警惕隱匿在武士道這片葉子陰面(3)《葉隱》書名的字面意思即隱藏在葉子陰面。的軍國主義再度現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