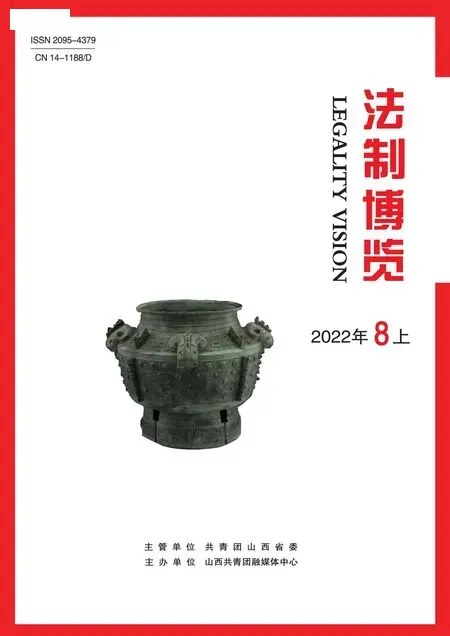量刑輔助系統在我國的發展契機及風險防范
馮雨音 陳妍萍 高 達
廣東警官學院,廣東 廣州 510405
近年來,人工智能開發在諸多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當人工智能的身影開始在我國司法領域活躍時,為我國的司法領域帶來許多新的發展契機。其中,量刑領域的發展契機值得關注,因為定罪量刑是刑事訴訟中對司法公信力極具影響的環節之一。因此,本文將在結合國內外司法人工智能運用情況的基礎上,用理性、審慎的眼光對人工智能在量刑領域的發展前景進行分析。
一、刑事司法領域人工智能運用概述
(一)國內概述
隨著“建設世界科技強國”戰略的推進,我國的智慧法院建設活動在國家政策支持和國家機關的助力下有序開展,司法人工智能的研發是我國智慧法院建設的重要環節之一。在技術人員和司法機關的共同努力下,已有多種人工智能系統在我國司法領域投入使用。目前已在我國投入使用的司法人工智能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1.信息數據化。信息數據化即運用智能轉化系統,將卷宗等紙質化信息,轉化為易于存儲、復制、傳輸的數據化信息,存儲進司法機關的數據庫中。已運用于最高人民法院和多家地方法院的、由上海高院與K公司合作開發的“206”智慧法院庭審系統就搭載了該功能[1]。
2.證據標準化。“206”智慧法院庭審系統在開發時也貫徹落實了“統一證據標準”的理念——該系統屬于我國司法機關以人工智能為手段實現對刑事案件證據的統一校驗的一次嘗試[2]。
3.辦案線上化。廣州市白云區法院在其公眾號中所述的以“云法訟寶”微法院、兩個一站式為主要成果的智慧法院子系統,就基本達到了“全業務網上辦理,全流程依法公開,全方位智能服務”的要求,并且實現了“一站通辦、一號通辦、一網通辦”[3]。
4.量刑公正化。要想刑事訴訟法保障人權的目的得以實現,首先要保證量刑公正。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及貴州、海南的檢察機關于2020年上線運行的全國檢察機關統一業務應用系統2.0版中的量刑輔助系統就屬于該方面[4]。
(二)國外概述
以歐美為例,在美國的司法領域投入使用的人工智能如下:美國聯邦法院的“案件管理和電子案件檔案系統”以及威斯康星等州的法院COMPAS系統等。而根據歐洲司法效率委員會2016年的報告可知,歐洲已有多家法院安裝了用于管理案件的人工智能系統[5]。
二、人工智能在量刑領域的發展契機與優勢
目前,人工智能在量刑領域運用的典型代表為量刑輔助系統。所謂量刑輔助系統,即當一個案件事實認定清楚、罪名確定之后,能夠通過對已知的案件信息進行邏輯推理并提出量刑建議的人工智能系統。以下是該類系統的發展契機及優勢:
(一)司法機關辦案壓力日益增長
隨著基層普法的工作的不斷推進和公安機關偵查水平的不斷提升,法院需要處理的案件也越來越多。以廣州為例,調查顯示,2015年廣州全市法院受理案件數突破30萬件,而到2016年,前三個季度全市法院受理案件總數已經達到2015年全年水平[6]。辦案壓力過大會影響司法工作人員的判案水平甚至是身體健康。同時,案件堆積也會導致部分案件的最佳審理時間因此錯失。由此看來,研發司法人工智能以減輕司法工作人員的工作壓力已勢在必行。在這樣的背景下,量刑輔助系統能夠擁有較好的發展環境。
(二)人工智能可助力提高量刑精確度
目前,司法機關量刑能力培養與提升的速度仍較慢,而司法人工智能可以作為其提速的“助推器”[7]。為提高量刑精確度,在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實施意見(試行)》的指導下,最高院以及地方各省高院都在積極發展包含類案推送功能的智能化辦案系統,例如北京高院的“睿法官”辦案系統,江蘇高院的“同案不同判預警平臺”[8]。但依靠類案推送功能劃定的量刑范圍仍較為寬泛,因此需要量刑輔助系統運用其強大的數據分析能力劃定更精確的量刑范圍,幫助司法機關工作人員更好地積累量刑經驗。
三、人工智能在量刑領域運用的風險分析
我國量刑輔助系統的發展道路看似風平浪靜,實則潛藏著不少風險。針對潛在風險的分析如下:
(一)司法數據缺陷影響運算結果
目前人工智能與法律結合研究的重點放在專家邏輯模型系統之上。該類系統較為常見的運算方式是通過數學邏輯方法來實現人工智能,這一點與法律工作者的思維方式有一定相似性——兩者都可以通過使用三段論推理模型對案件進行分析并量刑[9]。人工智能在獨立運算前,需要對大量數據進行學習,然而我國的司法數據庫中的部分案件的處理過程或結果存在瑕疵,這些瑕疵會對人工智能運算時的邏輯產生一定影響,其對適用法條的選擇可能會因此出現偏差。且由于司法數據中與倫理等常識有關的數據較少,這會導致人工智能容易在與常識有關的問題上產生錯誤判斷。
(二)司法輔助活動影響現有司法體系
我國刑事訴訟的審判程序采用的是混合式模式,法官居于審判中心地位,負責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定罪量刑,最終產生的判決屬于法官及陪審員的智力勞動成果。而一旦量刑輔助系統加入審判環節,其對量刑提出的建議,會對法官的最終判決產生一定影響。這會使法官的審判中心地位產生動搖——法官的最終判決將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人工智能算法運算的結果,而不再是純粹的人類智力勞動成果。而且,一旦人工智能參與審判的案件產生了錯案問題,由于我國現有的錯案問責體系不夠完善,將產生人工智能問責問題。
(三)“算法黑箱”影響司法公信力
目前,由于我國同時精通法律和計算機的人才仍較少,司法人工智能大多是司法機關與科技公司合作進行開發。對于科技公司來說,它所參與研制的人工智能的算法屬于其商業機密,一般不會向大眾公開,這會導致公眾難以了解算法的真正意圖,從而對算法的公正性與合理性產生懷疑。當時盧米斯上訴初審法院將COMPAS系統的評估報告作為量刑依據的行為侵犯其合法權利的理由就與“算法黑箱”有關。由于COMPAS報告提供的數據較為寬泛且不愿公開用于制作報告的算法,盧米斯據此認為法院對COMPAS系統的使用侵犯了他獲得個性化判決的權利[10]。
四、防范風險的措施
(一)對司法數據進行篩選
我國司法數據量多而質不高的問題可以采用對司法數據庫中的案件進行篩選的方法解決。筆者認為,會使案件存在瑕疵的主要影響因素如下:時代背景、社會輿論、主觀色彩。對此,可以研發一款多功能數據篩選系統,讓其先用時間檢索功能對數據庫中受時代背景影響的案件進行篩除,再通過排除個案和挑出典例的方式對剩余案件進行二輪篩選。排除個案即將法院的數據庫中的案件依照案情相似度進行分類后,將與量刑平均值差距過大的案件剔除。其中,量刑平均值最好是通過比對全國各地類案的量刑后得出的,這樣所得出來的量刑平均值可以排除一些地域性影響因素。挑出典例則是將案件中比較典型的挑選出來作為判例,使人工智能能夠根據典型案例中所體現出來的法的普遍性原則對其他類似案例進行量刑。
(二)對錯案問責機制進行完善
完善錯案問責機制需要明確的主要問題是責任歸屬問題。由于根據結果主義的算法問責的觀點,人工智能的算法具有復雜性,進行事后問責時無需考慮算法的具體運算方式,且對人工智能進行懲罰沒有太大意義,所以責任應由人工智能的實際控制者于事后承擔[11]。當審判結果錯誤是由事實認定錯誤造成時,責任歸屬于法官,因為用于量刑的證據一般是經過法官的審核才會輸入量刑輔助系統之中。而當審判結果錯誤由法律適用錯誤造成時,筆者認為,若法官在判決時參考了人工智能的量刑建議,責任應同時歸屬于法官和人工智能實際控制者。因為量刑輔助系統在提出量刑建議時必定會給出其適用的法律,此時法官負有審查法律適用情況的義務,若最終判決的法律適用有誤,則說明法官未盡其義務,需要為此擔責。
(三)對算法進行部分公開
從總體上看,“算法黑箱”產生的原因有二:一是出于維護商業利益的目的,人工智能的實際控制者及設計者不愿將算法公開;二是由于人工智能算法具有復雜性,即使對算法進行公開,其意圖仍難以捉摸。為此,可以采取公開必要部分的方式使算法變得相對透明,無需公布算法源代碼——這是由于一方面算法的源代碼較為復雜,且其設計者會不斷對其進行更新升級,部分算法甚至無法溯源,難以進行公開;另一方面,公開源代碼時一般會使用較多絕大部分人難以理解的專業術語,即使公開也對公眾的權利保護沒有太大意義[12]。只公開必要部分的方式既能維護科技公司的商業秘密,也能提高司法人工智能的公信力。科技公司在公開這部分算法的同時還需要對其功能進行介紹,以便公眾及監督機關進行監督。
(四)對量刑輔助系統的運用進行限制
要想保障法官的審判中心地位,必須保證法官盡到對量刑輔助系統運算結果的準確性、可適用性的“把關”義務,即保證法官將審查與下達最終判決的權利牢牢把握手中。在審理案情復雜或涉及較多法益的刑事案件時,法官應親自綜合多方因素進行量刑[13]。同理,一些需要結合常識判斷的案件也需如此,不然容易產生更多像“天津大媽非法持槍案”這樣的爭議案件。此外,由于認罪認罰案件一般案情較為簡單,涉及的法益較少,且“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所統領性下的制度安排包括認罪認罰從寬,兩者可相輔相成[14],所以可以將量刑輔助系統的運用范圍限制在認罪認罰的案件內,協助法官劃定量刑范圍。
(五)對常識進行選擇性補充
將已固化的倫理規范作為數據的一部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人工智能的常識缺陷。倫理可看作道德哲學對行為目的、原則規范、價值取向進行研究后形成的具有普遍適用性的行為標準,這種符合道德的行為規范,對人與他人、社會以及國家的關系具有調節作用[15],對量刑來說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另外,由于語言具有不確定性,法條也因此具有不確定性。一些詞語在不同的法條中的含義范圍是會出現擴大或縮小的,例如“脅迫”一詞,在搶劫罪中的指是以暴力相威脅,而在強奸罪中其含義范圍擴大,將以非暴力相脅迫也納入其含義范圍[16]。這類詞語的含義范圍只有結合常識才能正確理解。這個問題可以通過給人工智能搭載已經開始在國內的研究中出現的自然語義識別技術(NLP)[17]的方式加以解決。
五、結語
對量刑輔助系統帶來的風險進行防范不僅需要完善司法數據,也需要對我國刑事司法領域的多項機制進行調整與完善。由此看來,量刑輔助系統的出現在帶來機遇和風險的同時,也推動了我國司法模式改進的探索。因此,量刑輔助系統可以視為我國司法改革中不可缺少的量變環節之一,是司法改革創新的動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