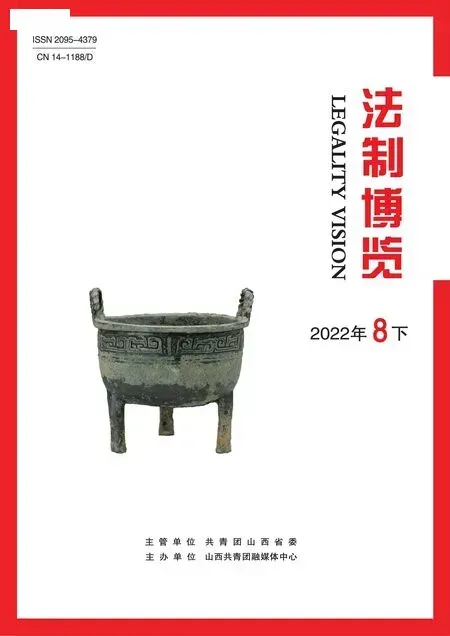風險社會圖景下污染環境罪的法益革新
徐浩源
四川師范大學法學院,四川 成都 610000
一、環境法益在我國刑法中的立法變遷
(一)環境保護刑事法律條文空白時期
在1979年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制定以前,由于受當時社會整體認知水平所限,百廢待興的中國社會幾乎尚未意識到以污染環境的沉重代價換取短期經濟利益將要造成的嚴重后果。1979《刑法》頒布之后至1997《刑法》修訂之前的十余年,立法機關及環保部門在接二連三的經驗教訓中不斷總結與反思,終于逐漸清醒地認識到了環境保護不容小覷。于是,我國關于污染環境行為方面的法律規制開始陸續出爐,不過也僅僅只是零星散見于個別防線薄弱的非刑事法律規范中,環境污染治理依舊是欠缺高效有力的刑事制裁措施。
(二)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對刑法的充實時期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中國社會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發生了巨大變遷,這既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刑法知識體系的重大轉型,也左右了刑法規范體系的大幅調整。1997年《刑法》終于在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了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該罪名即為現行污染環境罪最原始的雛形。此舉標志著刑法作為一種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開始能動地參與到了對生態環境領域的保護之中。然而,這一罪名規范的罪狀實質在當時還僅僅是停留在對人的實害結果層面上。可以說,當時的立法者并沒有樹立起科學的環境犯罪立法理念,因為其立法趣旨僅限于保護以人身利益與財產利益為核心的傳統刑事法益,所謂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完全名不副實。很顯然,這種刑事立法模式對污染環境行為本身視若無睹,其刑事法網也十分稀疏,存在較大的處罰漏洞,根本無法發揮現代刑法對于環境風險日益嚴峻的預防與控制功能。因此,亟須后續頒布的刑法修正案對該條文核心內容作出重大改動,以期實現“環境污染”這一鮮明的罪名標簽的實至名歸。
(三)污染環境罪勃然興起時期
社會轉型導致犯罪形態的遷移,風險社會的迫近更是加速了我國刑法罪名體系的頻繁變動。2011年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簡稱《修(八)》)積極回應社會關切,顯露出了預防型思維的立法跡象。《修(八)》對《刑法》原第三百三十八條“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進行了從形式到實質的全面修改。從形式的罪名上看,《修(八)》將原“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直接簡化為“污染環境罪”,降低了該罪名的冗長性和繁瑣性。從法益的實質保護上看,《修(八)》展現出其法益趨于擴張、預防更加積極、刑罰加速前移的一面。具體而言,第三百三十八條刑罰權的啟動時點不再等到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并伴隨人員傷亡或財產損失這一嚴重結果出現之后,而是行為程度只要達到了“嚴重污染環境的”,即使沒有造成人身財產權利的實際損害也值得動用刑罰。這一變化表明該罪名的行為構造已經由原先純粹的結果犯(實害犯)變成了危險的結果犯(具體危險犯),刑法對污染環境的治理模式開始逐漸從消極懲治的法益保護模式向積極預防的法益保護模式轉變,體現了在基于社會防衛的預防導向型刑法觀的指導下,我國刑事立法已釋放出環境安全保護早期化的強烈信號。不過,《修(八)》對保護生態法益的努力并沒有完全取得成功,時常也會飽受學界與實務界對其量刑畸輕、打擊不力的指責,難逃罪刑均衡、罪刑適應的詰難。
(四)污染環境罪的升級再造時期
刑法修正使刑法立法日趨科學,刑事法網愈加嚴密。[1]如果說,《刑法修正案(八)》在我國環境犯罪的立法修改歷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那么,《刑法修正案(十一)》在我國環境犯罪的立法修改歷程中則具有劃時代式的深遠影響。2020年12月26日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簡稱《修(十一)》)讓我們欣喜地看見新增了許多犯罪化與重刑化條款。特別是本次刑法修正案對污染環境罪的全新修訂徹底打破了過去長期固守的環境保護刑罰輕緩化、輟刑化的一貫傾向,取而代之的是環境治理刑罰適度嚴厲化的基本立場。風險社會時刻面臨的重大風險亟須刑法最大限度地釋放它的強大威力。刑法保障人權和維護安全的雙重面向應當并重,[2]不能死盯著前者而全然忘卻后者。其實安全同樣是一項基本人權,而且正是因為這項人權的存在,所以才證明了由國家所壟斷的刑罰權力作用于國民的合憲性地位。這種安全本位復歸的法益保護立場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環境保護立法理念的重心繼續朝著生態安全保護方向不斷傾斜,以踐行用最嚴格的制度與最嚴密的法治保護生態環境。
二、污染環境罪法益觀念的吐故納新
(一)法益概念的興起與流變
法益作為刑法學基礎性概念,在整個刑法教義體系中始終位居核心。每個時代都有其特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這也決定了刑法中的法益在不同時代的不同圖像。從法益概念的百年學說史來看,這一概念最初是由德國學者比恩鮑姆在1843年對費爾巴哈的權利侵害說進行批判時而提出的財侵害說。[3]及至1872年為賓丁在其著作《規范論》中被重新發現。以賓丁為主要代表的后期刑事古典主義學者對刑法法益概念的進一步發展,其本意就是要將個體權利擴張至社會利益乃至整個國家利益。然而,在古典自由主義刑法語境下,法益僅限于具有實體性指向的客觀存在。隨著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整體變遷,刑法的調控范圍也隨之而日益擴大。越來越多的非物質化法益被納入到刑法保護之中,這迫使法益概念不得不重新再去開辟一條擴張化的道路。法益概念的精神化和抽象化最早是由德國刑事實證主義者李斯特提出的。李斯特指出,法益中的益是指超越于實在法的且具有抽象價值的社會生活利益。李斯特對法益概念的改造對后世法益論的發展走向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例如,繼李斯特之后,在新康德主義價值哲學的作用下,德國學者霍尼希進一步發展了精神化的法益概念,他認為刑罰之所以要保護某種法益,是由共同體的價值觀念所決定的,而法益則只不過是刑法規范目的之體現而已。由此可見,從近代刑法學術史數百年的總體發展歷程來看,法益概念在刑法體系內的引入不僅沒有起到限制國家犯罪化權力的功能,反而在無形之間助推了國家刑罰權的急劇膨脹。[4]
(二)污染環境罪法益觀的學說
無論是在刑法理論還是在司法實務中,環境污染犯罪都屬于一個“舊而新”的話題。盡管現行《刑法》對第三百三十八條在歷經了多次修訂之后總體上的確完善了許多。但是,刑法界對污染環境罪法益的解讀依然分歧較大,未能從根本上達成統一共識。對污染環境罪的法益觀持不同的立場,同時也就意味著對人類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持不同的態度。當下刑法界關于污染環境罪保護法益比較常見的學說主要包括三種:一是狹義的人類中心主義法益觀;二是純粹的生態中心主義法益觀;三是兼顧前兩者的生態學的人類中心主義法益觀(折衷主義)。[5]
1.狹義的人類中心主義法益觀
狹義的人類中心主義法益觀以人類為中心來界定污染環境罪的保護法益。這一觀念特別強調人類是自然界的主宰,認為只有人類的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或者重大財產權利才是環境犯罪保護法益。至于說環境本身最多只能勉強算作是行為所作用的對象而已,并不能成為刑法上具有獨立意義的法益類型。因為自然界自始至終就沒有值得刑法關懷的獨立價值。換言之,刑法對污染環境行為的懲治與其說是在譴責破壞環境的行為,還不如說是在非難通過破壞環境進而影響到人類自身眼前利益與現時利益的行為,如果行為人只是單純地造成了對環境的污染,不論其在主觀方面的表現形式是過失還是故意,只要還不至于傷及人類自身的現時利益,那么刑法都不應當予以規制。作為污染環境罪前身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正好體現了這種法益觀。
2.純粹的生態中心主義法益觀
純粹的生態中心主義法益觀主張以環境為中心來塑造污染環境罪所要保護的法益,并承認一切動植物本身的內在價值。在其支持者看來,立法者制定污染環境罪的目的不是將其用于保護人的人身或財產法益的,而是純粹為了保護環境自身利益。因為自然物享有與人類平等的權利,各有各的刑法特別條款保護,無須將二者在同一刑法規范內混為一談。該學說將法益保護的范疇拓寬至自然物,甚至主張單獨創設出一種與人類利益毫不相干、并駕齊驅的新型法益類型,從而建立起一套以自然為中心的價值體系與評判標準。《修(八)》對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構成要件的實質性變化動搖了純粹的人類中心主義法益觀對環境犯罪刑事立法與司法一直以來根深蒂固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證明我國環境犯罪的刑事法治理念,正悄然出現了從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念向環境中心主義價值觀念發生傾斜的立法新動向。
3.折衷主義
生態學的人類中心主義法益觀又稱折衷主義。該觀點認為污染環境罪的保護法益是雙重的,[6]而不是單一的。它既包括對人的生命、身體、健康等個人法益的保護為中心的刑法條款,又包括將動物、植物以及非生物等生態法益予以保護的刑法條款。主張盡管將環境本身作為刑法中的一種法益類型來予以保護是必不可少的,但也并非是無任何條件限制的,這一限制條件即為人的基本生存與發展需求。即只有當為了滿足人類基本生存與發展需求的特定環境遭受侵害時才是值得刑法保護的。該觀點在域外受到了不少著名學者的廣泛贊譽。例如,今井猛嘉教授指出:“人類與自然之間是一種共生共存的關系,因為人類生活水平會隨著生態環境的逐漸改善而持續提高。”而在我國,通過《修(十一)》對第三百三十八條的二次改動,調和并整合了狹義的人類中心主義與純粹的自然中心主義的核心內容,進而實現了對人與自然的刑法保護在利益平衡中的兼得共融。
(三)學說評析與立場堅守
1.狹義的人類中心主義法益觀之不足
盡管狹義的人類中心主義法益觀在世紀之交為我國污染環境的刑法保護的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在僅隔數年該觀點就日益凸現出其對于環境保護的嚴重滯后性與無效性。雖然李斯特曾言:“一切法律均是為人而制定的,而制定法律的宗旨就是為了保護人的生存利益。”但是強調以人為本的法益理念未必代表肯定狹義的人類中心主義法益論的正當性。[7]
一方面,狹義的人類中心主義法益觀導致所謂環境法益概念呈現出十分嚴重的功能性障礙。該觀點完全將環境自身的內在價值從人的生活利益中剔別出來,并認為可以對其忽略不計,是不折不扣的“唯人類”立場。依照該說法,如果所謂的污染環境罪罪名的成立就是硬要達到對人的人身或財產有形損害不可,那么毋寧直接將行為人以傷害罪、殺人罪或者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論處即可,這樣或許更加大快人心,酣暢淋漓。
另一方面,狹義的人類中心主義法益觀滋生并助長了人類對生態環境的恣意破壞。這種法益觀念極其容易為人類無節制地破壞環境提供形式上的合法借口,使得行為人產生一種只要環境還沒有對人的污染排放行為提出強烈抗議或采取反制措施就可以斗膽試探環境對人的容忍底線的錯覺。一旦人類對環境的破壞突破了一定的限度,那么其所接受的天罰必將是災難性的和毀滅性的。
2.純粹的生態中心主義法益觀之瑕疵
純粹的生態中心主義法益觀盡管是一種建立在尊重自然環境基礎之上對狹義的人類中心主義法益觀片面的認識進行深刻反思與理性審視的進步理論,但是該理論卻徹底拋棄了人類對環境的需求,是典型的從一個極端無意識地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其所存在的重大瑕疵具體表現如下:
一方面,純粹的生態中心主義法益觀會導致法益內容的過度寬泛。任何法益保護都不可能是毫無門檻的絕對保護。環境的好壞本身具有一定的相對性與可參照性,而評價環境優劣的最佳參照標準則是人對環境的基本利益訴求。從嚴格意義上講,人類社會所取得的一切進步都是建立在環境污染之上的,可見,刑法如欲對環境實行絕對保護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因此,只有通過人對環境的基本利益訴求來限定環境法益過于寬泛的保護內容,才能為環境法益的準確界定劃分出一條清晰合理的界限,從而減少刑法對環境治理的無效干預。
另一方面,純粹的生態中心主義法益觀罔顧我國當前的客觀現實境況。在我國現行有效的法教義學話語體系下,個人法益仍然是法益理論的基礎性元素,而所謂的環境法益等超個人法益系屬由無數細小的個人法益匯聚而成的公共利益或集體利益。立法者在對人類利益與環境法益進行權衡時,縱然強調風險社會對環境保護的積極預防,也不宜輕易打破這種運行正常的既定體系。
3.生態學的人類中心主義之提倡
筆者認為,污染環境罪系屬傳統刑法理論中的危害之確定性與風險社會理論中風險之不確定性的共同組合。換言之,污染環境罪侵害的法益既具有人身財產法益的內容也兼具生態環境法益的向度,其對法益的侵害具有復合性特點。在風險社會中,無時無刻不充盈著潛在而可怕的不確定性風險。并且,一個缺乏刑法保護的風險社會中的法益注定是在黑暗中惶恐不安的。由于風險社會在傳統的個人法益基礎之上又產生了新型的超個人法益,因而,耀眼的刑法之光不能對其中任何一方置若罔聞而須將之穿透直射。正如張明楷教授所言,生態學的法益(阻擋層法益)是為保護人類中心的法益(背后層法益)而存在的。[8]本文并不認同純粹的生態中心主義與狹義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法益觀所共同宣揚的人與自然之間的法益無涉或法益隔絕,而是在承認利益終極性的基礎之上,對人類利益與環境利益進行平等的區分與保護,并同時為二者共同尋求一個絕對依賴但相對獨立的法益關聯。
三、檢視《修(十一)》中污染環境罪的法益保護
風險社會圖景下,泛化的環境風險、陡增的治污困境以及龐雜的行為失范合力加快了刑法對環境保護的擴張性與嚴苛性。進而促使變動中的刑事立法對于社會生活的干預愈發活躍而強烈。《修(十一)》在《修(八)》的基礎之上朝著生態學的人類中心主義法益觀的方向逐趨靠攏,主要從兩個方面對污染環境罪進行著重修改。
一是將該罪從兩個罪刑階段上調為三個罪刑階段,并修改了不同罪刑階段分別適用的條件。污染環境罪過去的兩個階段一是基本刑階段,即針對嚴重污染環境的情形,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二是加重刑階段,即對于后果特別嚴重的,處三至七年有期徒刑。如今污染環境罪的三個罪刑階段中較原有的設置而言,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保留了一個,完善了一個,并新增了一個,具體而言,前述第一個基本刑階段被完全沿用了下來,針對前述第二個加重刑階段,將后果特別嚴重變成了情節特別嚴重,同時略微對該階段適用的附加刑條件進行了一定的變動,即附加刑只能夠合并處罰,而不可單獨處罰。此外,剛剛破土而出的第三個罪刑階段則主要是針對特定區域環境(如事關食品安全、糧食安全與飲水安全的核心區域)的嚴重破壞或者致人重傷或死亡等嚴重情形,最高可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誠然,《修(十一)》在此處對本罪的加重處罰規定告訴我們:在風險社會概念早已被提出并證成的當下,盡管人們排斥刑法以血腥鎮壓的“槍桿子”形象出現,但卻并不反對刑法在扮演防控社會風險的角色定位上有所作為,刑法防衛社會的工具屬性被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位置。污染環境罪的刑罰不是越輕或越重就越好,其行為規制也不是越早或越晚就越好而應當是該罪名的司法適用越能夠積極有效地防控社會才越好。
二是新增了三百三十八條第二款,這一款是有關該罪競合形態的規定,即如果行為人在處罰該罪的同時又與刑法分則體系中的其他罪名構成競合關系(例如:想象競合),根據不同的具體情形從一重罪論處。這樣該罪的司法適用就可以從過去一直以來罪名的自我捆綁痛苦中徹底地解放出來,無須就污染環境行為而僅定污染環境之罪,而是可以例外地允許適用其他刑罰更重的罪名,以此彌補或替代污染環境罪刑本身的瓶頸性與有限性。以起到重罪久判、死罪嚴判的罪刑均衡效果進而更好地打擊和預防環境公害犯罪。
然而,我們在充分肯定《修(十一)》的積極意義同時還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在現行法制條件下對污染環境罪的法益保護尚未達到刑法對環境安全的周延保護程度,這還有待進一步立足于生態學人類中心主義法益觀對該罪提出切實有效的立法完善建議。
四、新理念下污染環境罪法益保護的立法展望
(一)適度調整污染環境罪在刑法分則體系中的位置
近二十年來,我國刑事立法無論對污染環境犯罪的刑法條文如何在微觀上趨近完美地加以調適,在宏觀上卻始終將該罪名限定在刑法分則中位置比較靠后的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的倒數第三節“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內。顯而易見,刑法分則體系從一開始在對該罪的編排設計上就是不夠重視的,沒有從根本上彰顯生態學的人類中心主義法益理念。并且在立法者看來該罪保護的法益是國家對環境資源的管理秩序。因而該罪名法益內涵的關鍵詞是所謂的“秩序”。
根據生態學的人類中心主義法益理念,污染環境罪的法益實際上指的是一種環境安全,該罪名法益內涵的關鍵詞是安全,而非秩序。其具體內容包括兩層涵義:表層涵義是指代表個體法益的個人現實生存環境安全,深層涵義則是指代表超個體法益的國家長遠發展環境安全。隨著接連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對該罪法益保護范圍的不斷擴大,以及法定刑的接連加重,《刑法》第六章內部已經再也找不到適合容納該罪的棲息之處了。這就如同高中生的課堂無法為大學生傳授知識一樣,其在刑法分則中所處地位必須要有所變動,至少應當將該罪前移至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內,并緊隨第一百一十五條之后。
(二)增設抽象危險犯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作為風險社會的衍生品自1997年制定并生效以來盡管經歷了兩次大修,然而我國現行污染環境罪的最大缺陷在于其入罪門檻始終沒有超越以結果為要件的古典刑法理念。而該結果就是生態環境遭受嚴重污染的有形結果。包括《修(十一)》對本罪的進一步完善在內都仍然未敢從質的層面上鼓起勇氣打破這道陳舊落后的理論枷鎖,在強化原有結果無價值的基礎之上,必要時擴張對行為無價值的刑法管制。[9]它只是停留在從量的層面上加大了對嚴重污染環境,情節嚴重或特別嚴重的刑罰制裁力度,多少還有些不盡如人意。
本文認為,我國刑法增設污染環境罪的輕罪抽象危險犯十分有必要。因為該立法設置模式在污染環境罪中的運用不僅能最大限度地滿足積極預防與控制環境風險,提前并周延地保護環境安全的迫切需求,而且還有利于減輕公訴方的不必要的證明負擔,加速正義實現的及時性進而不斷訓練與強化人們對法律規范的忠誠度與信賴感。更何況,風險社會中的刑法本身就具有爭當積極參與環境治理的急先鋒和排頭兵的自覺性和主動性特點。基于此,應當在現行《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嚴重污染環境的”之前,再設置一個處管制或拘役并處罰金的刑檔,即“可能嚴重污染環境的”或“具有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可能性的”。當然,此處的“可能”或“可能性”應當以專業人的科學標準而不是以一般人的大眾標準來認定,因為一般人很難察覺和感知或者容易誤判身邊潛在的危險。
(三)科學設置罰金刑
盡管現行《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第一款在各個罪刑階段均已逐一規定了罰金刑的處罰,但是這種罰金刑規定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均值得商榷。具體說,該罪這里的并處罰金十分籠統抽象。這種粗糙立法模式的后果將不堪設想,因為這樣會導致法官擁有過度膨脹的自由裁量權,隨時都能夠將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間,進而形成“今天想收拾誰就多罰一點,明天想饒過誰就少罰一點或一點不罰”的心情司法現象。果真如此,則特別容易明目張膽地滋生司法腐敗現象,進而嚴重損害法律的嚴肅性與司法的公正性。
由此可見,污染環境罪應當摒棄可能導致主觀偏私的抽象罰金制,采用客觀易操作的倍比罰金制。這種模式體現在污染環境罪中,就是以嚴重污染環境之后所造成的或者可能造成的損害數額為基數,以其固定的倍數或約數計算出的數額進行處罰。該模式在我國現行刑法體例中使用廣泛。如:《刑法》第一百四十五至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一百五十八至一百六十條、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一百八十條等。盡管有部分學者會質疑這種罰金刑處罰模式無法準確評估污染環境可能或實際遭受的損害價值,但起碼要比目前毫無制約的抽象罰金制更加科學穩妥。
五、結語
在生態學的人類中心主義法益理念的指引之下,無論是傳統的個體法益安全還是新興的超個體法益安全都應被納入并整合到污染環境罪所該當抽象與擴張的二元一體法益構造范圍之內。本文通過歸納梳理與對比分析我國各個特定立法階段關于污染環境犯罪規定的歷史演進,聚焦污染環境罪法益張弛的規范性探討,明晰了該罪所必須堅守的應然法益理念底色。與此同時,在堅持最新出臺的《修(十一)》立法精神的首要前提下,結合我國當前環境治理近況有待進一步改進的現實背景,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嚴密環境犯罪刑事防控法網,多管齊下,多措并舉的完善建議,以期為我國不斷推進環境犯罪刑事立法先行,更好地發揮刑法在積極參與環境治理過程中的領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