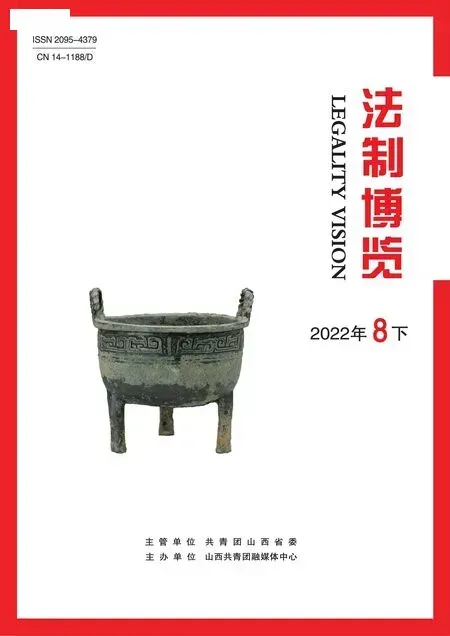支持拐賣兒童“買賣同罪”的法理學研究
胡櫓澤 向永勝
浙江工商大學杭州商學院,浙江 杭州 311500
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三十九條明確規定,禁止拐賣、綁架婦女;禁止收買被拐賣、綁架的婦女;禁止阻礙解救被拐賣、綁架的婦女。滬籍人大代表、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兼職副主席樊蕓認為,如何徹底從法律上根除拐賣婦女頑癥,不僅是民事問題,還需要從刑法上提請全國人大修法。一直以來由于拐賣婦女兒童量刑相對較輕,違法成本低,使得一些拐賣犯罪分子鋌而走險,甚至在部分地區形成產業鏈。樊蕓建議,應加重拐賣、收買婦女兒童罪的刑責,尤其強調買賣同罪,才能增強法律威懾力。上海外國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上海市婦聯兼職副主席黃綺也建議對以暴力威脅等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解救被收買的婦女、兒童的首要分子,給予五年以上的判罰,同時懲治“對向犯”,對阻撓解救拐賣兒童者,體現出法律的威嚴。對于拐賣者在刑法中會給予相應嚴懲,但還應該把懲治力度提高,對買方也應該承擔相應責任。但目前《刑法》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對于“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對其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這有可能變相降低對“買方市場”的打擊力度。縱容買方,只會刺激更多需求,應該把懲治力度提高,買方必須承擔相應責任。
一、文獻基礎
(一)買賣同罪
近年來由于國家對懲處、打擊拐賣行為方面的不斷加碼,一部分法學界和社會反拐人士呼吁對買家實行和賣家相同的罪行進行定罪,實現“買賣同罪”。具體指如果從事人口買入同人口拐賣在法律上是同等罪行。[1]同時給從事相關犯罪行為人提醒,拐賣人口與買入人口是同等罪行。期望從事買入人口的能不給拐賣人口的犯罪分子機會。我國《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同時又指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按照被買婦女的意愿,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因此,在各地司法實踐中,收買被拐兒童的買家往往可以不用承擔法律責任。
(二)買賣同罪的適用可行性
拐賣婦女兒童在當下中國還能如此猖獗,只能說明一個事實,便是中國在立法和司法層面對該犯罪的懲處力度還不夠。一方面,社會輿論導向是偏向于呼吁加大對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懲處力度,甚至認為拐賣婦女兒童罪應當一律判無期或死刑;另一方面“罪刑法定”“罪刑相適應”作為刑法的理論根本,沒有犯罪論的“罪刑法定”和刑罰論的“罪刑相適應”,刑法理論便沒有立身之地,無法在根本上合理解決刑事問題和在法理上說服任何一方。現實中我們之所以遵從“罪刑相適應”的刑罰論原則,在于過重的刑罰可能會導致被拐婦女兒童的人身及生命安全會受到嚴重威脅。“罪刑相適應”的實質是之于“價值”與“價格”的相適應。如果市場上買的東西都統一定一個價,市場秩序也就不復存在。沒有買就沒有拐賣,我們當然知道杜絕拐賣的實質就是杜絕買,而《刑法》規定買方在特定情況下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給了很多人“收買無罪”的錯覺,從而形成了一個“原罪”的買方市場。
二、我國打拐現狀與困境分析
從最近五年最高法判處兒童拐賣的重刑率來看,在懲處人販、打擊拐賣行為方面不斷加碼,情節嚴重的已經判處死刑;但就整體而言,打拐形勢依然嚴峻。截至2021年11月30日,公安機關成功偵破拐賣兒童積案290余起,抓獲拐賣兒童犯罪嫌疑人690余名,累計找回歷年失蹤被拐兒童8307名,其中失蹤被拐人員與親人分離時間最長達74年。“買”,“賣”如何定罪,在定刑上兩者的主觀惡性和客觀危害都是極為嚴峻的。
(一)拐賣兒童犯罪的現狀
中國人對于后代的傳承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對于家族的延續往往需要繼承人來進行,在一些偏遠地區尤為如此。客觀地說,拐賣婦女、兒童不是新中國的產物,是舊社會遺毒,嚴重侵害婦女、兒童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社會危害極大,歷來為中國政府所不容。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人民群眾雖然接受了新興先進思想,但是在法律法規還沒完善的時代大背景之下,存在許久的陋習并沒有很快消散。“重男輕女”“家族根基”“開枝散葉”“養兒防老”這些深深烙印在中國百姓心中的傳統觀念從而催生出了“市場需求”,即商品經濟下的人口拐賣行業,為違法犯罪提供了溫床,拐賣人口犯罪呈擴大趨勢。1983年我國開始對拐賣人口犯罪活動進行嚴打,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伴隨著改革開放,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開始大幅度失衡,拐賣人口的犯罪又重新猖獗起來,1989年拐賣人口的立案數更是超過了兩萬起,被拐婦女兒童數量超過十萬人,并且犯罪區域由云南、貴州等偏遠地區迅速向河南、江蘇等內地省份蔓延。[2]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8年8月8日,全國范圍內被拐賣的青少年達到35812人。
(二)現階段法治上被販賣拐賣兒童的安置問題
對于被販賣兒童,法治上對于被拐兒童的撫養權歸屬問題在實踐中不在少數,其大致分為未成年人的監護決定和成年人的自行決定撫養決定。
1.未成年人的監護決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2021年1月1日生效)第二十七條規定: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監護人。第三十四條規定:監護人的職責是代理被監護人實施民事法律行為,保護被監護人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等。對于被拐未成年兒童,監護人享有法定的監護權利和義務,其不受被監護人的非法轉移而喪失。現實拐賣案件中,大部分被拐兒童在遭受拐賣侵害時往往年紀較小,缺乏民事行為能力,其無法在遭受侵害時進行反抗和維護自身的利益,故監護人在找到被拐兒童后,依然可以繼續履行監護權利,不受限制性行為能力人的意思表示影響。
2.成年人的自行決定撫養決定
《刑法》中明確表示拐賣兒童、婦女是嚴重違法行為,最低量刑可達有期徒刑三年以上,嚴重情節可以判處死刑。法律上對于成年人界定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獨立進行民事活動,并且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在這種情況下,由于生身父母對被拐兒童不需履行監護義務,法律上尊重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的自身選擇。古曰:“生身之恩大于人,養育之恩大于天,百善孝為先。”倘若生身父母棄而不養,那么他們必將受到道德的譴責,枉為人父、人母。不當情況下獲得的撫養權,最終的結果卻由生身父母承擔,國內的大批量拐賣案件宣布告破后,在找到被拐兒童分配撫養權的問題上,卻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予以規范。人販子恰巧利用了這一人性的弱點,在被拐兒童熟悉養父母家中的環境和生活方式時,再想融入親生父母的家庭環境,便難于登天。
三、“買賣同罪”適用性對當前法治基礎的革新與影響
實際上,我國《刑法》已單設了“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并且現行《刑法》中對此行為的處罰力度已經調整加重。調整前的1997年《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同時該條第六款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按照被買婦女的意愿,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其進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3]然而,其中“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免責條款曾飽受詬病,被認為是給了參與拐賣兒童犯罪的買家輕易逃脫法律懲處的空間,也實際成為拐賣兒童犯罪屢禁不止的重要根源。
(一)“買賣同罪”的入刑是現實需要
除了進一步加大對收買人的懲處力度,在立法層面我們幾乎沒有什么改進空間。現行《刑法》中已經對拐賣者規定了適用量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沒收財產。”這幾乎已經是頂格處罰了,所以唯一剩下的改進空間就是對收買者本身進行立法規范。在日本這個以輕量化刑罰為標準的國家,卻對收買者處以較高量刑幅度處罰,也即與拐賣者幾乎相同量刑幅度的處罰。在中國的重刑罰法治環境下,“買賣同罪”更應該可以實施。
(二)“買賣同罪”的立法改進具有合理性
立法技術上,在中國普遍的司法實踐中,基于民法中的民事賠償的填平原則,通常是從受害者角度考慮賠償受害人的損失,卻始終沒有考慮這種賠償或處罰對施害者有沒有實際意義。賠償不能只看絕對量,更著眼于相對量。基于相對性的原理,如果我們將加大的處罰力度放在收買者身上,而不僅僅是放在拐賣者身上,其對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處罰效果可能就要好得多。因為對拐賣者而言,他們在心理意識上就知道他們的行為是在犯罪,而且是重罪。而對于收買者而言,對其的收買行為進行重刑罰處罰,其威懾效果將會大得多。
(三)“買賣同罪”有助于降低買方市場需求
法理基礎上,在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活動中,往往存在著經過幾道手的情況,最后賣出和最終買入的兩者或兩組人之間,一定是成立買賣合意的,即拐賣婦女兒童罪共同犯罪的主觀共同故意。在這個共同犯罪中,買方顯然是花了錢的,而且是明確知道沒有合法手續的;而賣方顯然是收了錢的,而且必是非法轉賣的,所以兩方的共同行為是共同促成拐賣罪的最終成立而無疑的。因為就拐賣行為的實現來說,沒有買就不會有賣,在拐賣罪中的買與賣恰如幣之兩面、棍之兩端成立必然的牽連關系,成立賣就必然會有買。所以即使“拐賣罪”中并不見“買”這個字,“拐賣罪”也實際上是隱含了“買”,即可以合目的地解釋為包括了“買”。
四、研究結論和啟示
(一)研究結論
1.“買賣同罪”的確立是未來發展的必要趨勢,從現實來看對買方市場的打擊是從根本上解決拐賣婦女、兒童問題的必要手段。近年來,針對販賣人口罪的買賣雙方,我國《刑法》立法出現了處罰加重化和范圍擴展化的趨勢。因為基于收買的犯罪違法行為本身就是無效的,甚至是應當受到懲治的。違反當事人的意愿的行為,一開始就必須停止,并且不產生任何與婚姻和收養相關的權利義務。同時,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在打拐技術上,實現跨地域合作以及信息資源共享,加大科技投入,實施“網上打拐”“網上解救”和DNA親子鑒定工作。
2.在立法層面上,提高法定刑不一定能立刻遏制拐賣婦女、兒童類的犯罪,但是提高法定量刑,實現“買賣同罪”,可以有效應對各類犯罪,實現罪刑相當。沒有收買就沒有拐賣,這是一個由需求方導向的“市場”,遏制住需求端,就會減少拐賣犯罪的發生。受多重因素影響,當前滋生拐賣犯罪的土壤尚未完全鏟除,還有一批積案沒有偵破,拐賣犯罪形勢仍然不容樂觀,僅靠運動式打擊,只能管住一時,一旦放松就會迅速反彈。因此,必須考慮到收買方潛藏的多重犯罪行為,以及對受害者和社會所造成的嚴重傷害,大幅度提高收買方的量刑標準,實施“買賣同罪”,讓收買方付出更高的法律代價,以發揮法律的震懾力。當前,社會各界逐漸達成共識,拐賣犯罪是反文明的惡行,必須重罰,希望通過提高量刑標準來震懾犯罪分子,以實現“天下無拐”。
(二)研究啟示
1.“買賣同罪”的可行性在于對出售和購買被拐人口形成了對口的完備市場,出售人口的行為目的在于獲利,獲利的來源在于存在完備市場和相對應的法律漏洞。切斷市場流通,解放需求,便可以阻斷市場。拐騙行為自然成為“無源之水”,“買賣同罪”強調收買方的重刑審判,實現刑法最基本的預防犯罪效果。在當前刑罰判決中,對于拐賣婦女兒童罪的量刑相對寬緩,三年以下刑期無法反映拐賣行為的惡性,也無法回應人民“天下無拐”的期待。
2.現實中“拐賣兒童”中的買方頂著“養父母”光環,免于追責。刑法意義上對于“養父母”的解釋應該用于辦理合法手續后的認養情況。對于一手交錢、一手交人的情況,就是刑法意義上的收買,即為“買家”。通過購買被拐兒童來維系所謂傳宗接代,被賦予角色使命的孩子,表面上得到“養父母”家庭的優待,實際上僅靠“孩子”稱謂構成紐帶。追求“買賣同罪”立法,能夠打破買賣雙方的攻守同盟,從而保護中國新生代兒童的人身安全。“拐賣兒童買賣同罪”具有穩定的現實合理性,買賣雙方的主觀惡性超越了罪刑本身,未來國內有必要對法理意義上和公眾認可的合理正義觀進行考慮,逐步推進買賣人口買賣同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