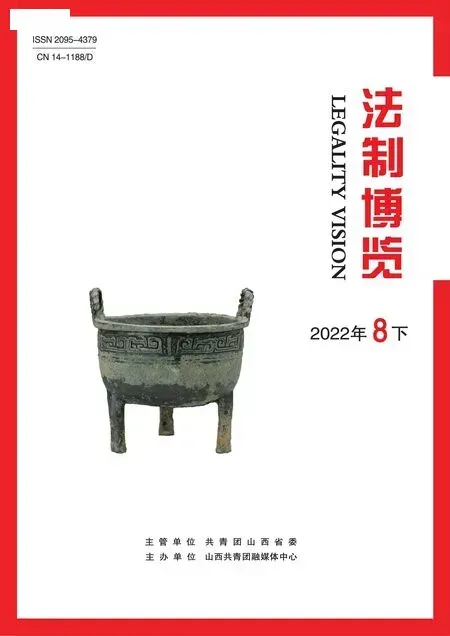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責任與干預保護
袁彥澤
蘇州城市學院,江蘇 蘇州 215104
眾所周知,我國刑法面對的是我國全部的公民。而未成年人,是刑法受眾群體中較為特殊的一類,我國對于未成年人的成長關(guān)注是十分重視的,而未成年人在犯罪違法后所需負起的刑事責任,一方面體現(xiàn)了我國對于“惡”的認知,對于如何規(guī)范未成年行為的標準和對待“人權(quán)”的輕重,另一方面,我國制定《未成年人保護法》與《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從家庭、社會、學校、網(wǎng)絡等多個角度同時承擔對這一龐大群體的教育。所以,面向未成年人的刑法,不但要讓法律條文規(guī)范化,還需要思考案件背后,未成年人的心理與認知概念問題,從而引起社會的注意,從家庭根源出發(fā),規(guī)范未成年人行為。
一、國內(nèi)外針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差異
(一)國外針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措施
美國在1899年就頒布了首部未成年人法律,經(jīng)過時間的推移,一套未成年人法院系統(tǒng)也逐漸變得成熟:設立了獨立的未成年人法院、家庭法院、未成年人及家庭關(guān)系法院、附屬的未成年人法院。法律設定各州略有不同,都以未成年人所犯的行為程度來決定罪刑。而德國針對未成年人推出了教育記錄制度與刑事污點制度,它做到了未成年人心理的平衡,在犯罪者刑滿釋放后,僅有特定的機關(guān)能夠查看其犯罪記錄,這既能夠造成警示作用,也能保證犯罪者的隱私。在世界其他地區(qū)中,以色列、法國地區(qū)刑事責任最低年齡為13歲;土耳其、荷蘭地區(qū)最低年齡為12歲;英格蘭和威爾士地區(qū),最低刑事年齡是10歲;墨西哥、菲律賓地區(qū)最低年齡為9歲;蘇格蘭地區(qū),最低年齡是8歲;新加坡和瑞士地區(qū),最低年齡為7歲[1]。
(二)我國針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措施與預防
以往我國刑事責任最低年齡相比世界各國法律規(guī)定確實偏高,如今發(fā)現(xiàn)很多無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人確已具備了認知能力,并能對自己的行為進行控制,導致了部分未成年人知法犯法卻又不畏懼法律,故意實施法律無法制裁的惡劣行為。如今,《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相輔相成,像階梯一樣逐層上升。前兩者提出,家庭、學校、社會、網(wǎng)絡有義務及責任保護未成年人遠離不良信息,以及不良行為發(fā)生前后的預防與干預措施。后者則在2021年3月1日修正后,由《刑法修正案(十一)》規(guī)定,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對于特定的犯罪經(jīng)過特定的程序,應當負刑事責任,而特定的犯罪是特指一些情節(jié)嚴重的行為。[2]這一修正案的改變廣納世界眾多法系。原本世界法系大致分為樂觀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樂觀主義認為人的理性十分可靠,應當構(gòu)建一個完整的標準框架,在標準范圍以下的是沒有基本判別能力的。在標準之上,則是有能力判別的。在樂觀主義下,人被認為是天性善良的,可以通過教育等塑造方式合理塑造,所以對待未成年人的措施應當以矯正為主。而現(xiàn)實主義以經(jīng)驗為第一基礎(chǔ),它認為,人無論年齡都有其陰暗的一面,脫離了懲罰的矯正,其實是虛偽的人道主義,因為人的本性如果可以通過矯正來徹底改變,那犯罪也會銷聲匿跡。而最初的英美法系擁有無責任能力的辯護理由,通常將7歲以下推定沒有犯罪能力,而7歲到14歲則需具體行為具體分析,因為該年齡段未成年人大概率能夠明辨是非,也是所謂的“惡意年齡補足制度”。而我國的法系,折中了以上的制度,一方面擁有犯罪年齡的明確區(qū)間,另一方面也借鑒了惡意年齡補足制度。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
(一)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分析
近年來,從犯罪的趨勢來看,2020年中國未成年人犯罪人數(shù)為3.4萬人,比2010年減少50.5%;2020年未成年人犯罪人數(shù)在犯罪總?cè)藬?shù)的比重為2.21%,比2010年下降4.57%,但犯罪的低齡化卻在加重。犯罪心理學教授馬皚在整理時發(fā)現(xiàn),2010年以后的未成年人犯罪中,出現(xiàn)了許多惡性的極端案件。2012年,廣西一名13歲女孩,因不滿同班同學比她漂亮,將被害人騙至家中殺害并分尸,但卻因其作案時未滿14周歲,所以僅對這個女孩采取了收容教養(yǎng)3年的措施;2013年10歲重慶女孩摔打1歲女童,并將其從25樓拋下;2017年,江蘇15歲男孩性侵7歲女童,事后擔心事情敗露,將其從25樓推下致死;2016年,大連13歲男孩殺害10歲女童,拋尸灌木叢;2019年3月,四川雅安,3名未成年人截殺小賣部老板娘,其中年齡最大的僅15歲……雖然這些極個別的極端案例不能夠代表整體,但經(jīng)過研究發(fā)現(xiàn),這些極端的案例,很多并非是一時沖動造成的激情性案件,而是有預謀的,甚至是團伙作案,那么對于其中的內(nèi)因就亟需早日發(fā)現(xiàn)并采取措施。
(二)家庭因素
未成年人成長的第一環(huán)境即是家庭。孩童擁有成年人所不及的模仿能力,所以父母的言傳身教就顯得尤為重要。孩子在懵懂時期學習成年人的行為習慣、語句句式,同時潛移默化地被家庭氛圍所影響,這都是今后孩子在人格覺醒時的重要依托。更甚者,家庭中存在缺陷,未成年人缺少母愛或是父愛,都可能會發(fā)展成極端的扭曲心理。人在12歲至14歲中,自我意識的覺醒使其對事物擁有自己的見解,如果此時家庭教育疏忽,孩子對“最基礎(chǔ)的生命或權(quán)利”沒有準確的認同感,那么嚴重者會出現(xiàn)虐殺動物、損壞他人貴重財物、使用危險物品傷害他人等嚴重犯罪行為。
(三)社會因素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的年齡下調(diào),是根據(jù)時代的發(fā)展,社會與科技的進步所進行的修改,說明現(xiàn)今時代的進步對未成年人的影響,相較于早年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目前的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使得未成年人能夠自行注冊種種虛擬的社交軟件,在“看不見”的線上社交中,接觸網(wǎng)絡、接觸信息,在他們心智沒有完全成熟的情況下,有可能無意接收大量易造成其錯誤觀念的污濁內(nèi)容,甚至接觸到違反國家法律的自媒體視頻、犯罪言論和恐怖主義。此年齡段的人往往對父母有叛逆心理,那么更加容易聽信互聯(lián)網(wǎng)污穢的一面。所以國家也為此加大網(wǎng)絡安全管制,幫助未成年人遠離互聯(lián)網(wǎng)陰暗面,建立網(wǎng)絡安全管理技術(shù)。
同時,學校也是僅次于家庭的第二大環(huán)境,孩子處于學校這一社交層面時,“一對多”的教師無法照顧到每一位孩子,那維護好“內(nèi)外”環(huán)境,就是學校所需要下的功夫。“內(nèi)”是指學生自我的心理健康,教導未成年人懂得基本的“人權(quán)”意識,重視自我,尊重他人;“外”是學校整體的大環(huán)境,師德師風的建設、學生風氣的培養(yǎng),是杜絕校園欺凌與暴力的重要地基。
(四)心理因素
回顧往年案件,犯罪講究動機,動機的來源是解決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分析他們?yōu)榱耸裁炊プ龀鋈绱藝乐氐男袨椋麄兪且驗槟撤N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做出違法的事,還是僅僅因為自身的一時暢快,滿足那一刻給他們帶來的歡愉而犯罪呢?埃里克森指出,在12至18歲時,是人形成自我意識的重要階段,在這一時間段中,青少年的重要任務是“完成自我同一性”。他認為,自我成長的環(huán)境、身邊的人和事、自我對自身的定位與認識會同時影響自我同一性的完成度,嚴重的會出現(xiàn)混亂,出現(xiàn)違法犯罪和越軌事件。埃克里森認為,“未成年人如果沒有很好地完成自我同一性的過程,可能出現(xiàn)同一性缺失,拒絕在成人社會中擔任應擔任的角色,甚至否認自己同一性的需要,往往將自己的行為從主流社會的規(guī)范中區(qū)分開來,出現(xiàn)破壞性、暴力性和攻擊性。”此過程沒有完成,未成年人則會出現(xiàn)扭曲的、具有反社會人格性質(zhì)的結(jié)果,倘若在15歲之前沒有對其強制的矯正甚至是懲罰,那么其在成長后極有可能做出更加殘忍的行為[3-4]。
三、社會多方加強對未成年人的保護
(一)網(wǎng)絡安全保護
往年,我國沒有體系式的對待未成年人在網(wǎng)絡方面的保護條例,而國家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辦公室于2019年8月23日發(fā)布《兒童個人信息網(wǎng)絡保護規(guī)定》,這一舉措的誕生,是我國保護未成年人信息安全的里程碑式措施,其中提到了許多重要規(guī)定。同樣的,2020年10月召開的全國人大正式修正并通過了《未成年人保護法》,其中專為未成年人設置了“網(wǎng)絡保護”章節(jié),此次法律修訂立足當前未成年人網(wǎng)絡保護的實際情況,結(jié)合了如今自媒體時代的飛速發(fā)展與消費水平的提高,進一步增強了未成年人處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重要保護對象的地位,更加凸顯未成年人的身份信息隱私的保護力度。
第一,身份認證的關(guān)卡保護。根據(jù)2007年4月發(fā)布的《網(wǎng)絡游戲防沉迷系統(tǒng)實名認證方案》和2011年7月發(fā)布的《關(guān)于啟動網(wǎng)絡游戲防沉迷實名驗證工作的通知》,以及2010年7月原文化部發(fā)布的《關(guān)于貫徹實施<網(wǎng)絡游戲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的要求,體現(xiàn)我國對網(wǎng)絡游戲運營中對未成年人的身份認證有嚴格的審查制度,要求網(wǎng)絡游戲責任方應將其注冊的用戶身份信息完整保留并移交公安部門審核,并用防沉迷系統(tǒng)限制未成年人注冊賬號。同時,消費方面也有類似的舉措,例如,未成年人大額打賞網(wǎng)絡主播、網(wǎng)絡購物、網(wǎng)絡消費過度等事件時有發(fā)生。《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七十六條則對直播平臺進行了限制,不得為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提供網(wǎng)絡直播平臺的賬號注冊服務,這也是對主播以及觀眾做出兩手約束,警示主播正向引導未成年人觀眾的消費觀,不教唆煽動其消費欲望。
第二,信息安全的規(guī)范性文件。工業(yè)和信息化部信息安全協(xié)調(diào)司于2011年2月起草的《信息安全技術(shù)個人信息保護指南》規(guī)定,“個人信息管理者不應要求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提交個人信息,當發(fā)現(xiàn)信息提交者未滿16周歲時,應給出明確提示并停止收集行為,為提供必要服務確需收集其個人信息的,應征得其監(jiān)護人的同意”;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shù)委員會2012年11月出臺的《信息安全技術(shù)公共及商用服務信息系統(tǒng)個人信息保護指南》規(guī)定,“不直接向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或無行為能力人收集個人敏感信息,確需收集其個人敏感信息的,要征得其法定監(jiān)護人的明示同意”等等規(guī)范性文件,非常明確地提到了各種針對未成年人的信息安全保障,但明文條例的頒布需要大眾的共同維護,仍需有法律支持,以作警鐘[5]。
(二)未成年人犯罪干預與保護
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章中寫到,國家會對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進行干預,其中國家機關(guān)、群眾團體、社會性組織、企業(yè)事業(yè)單位、居民委員會、學校、家庭等單位都有責任和義務來保證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同時在管制條例中,矯治可以由家庭、社會機構(gòu)、政府其中之一來進行,通過正向的手段,達到糾正行為歪曲的青少年思想習慣的目的,例如讓其參與社會服務活動,增強其與正能量的交接密度,來達到凈化心靈的作用。同樣的,對待已經(jīng)回到正軌生活的青少年,社會各界也應積極接受,不應有歧視、“穿小鞋”“揭傷疤”等行為,應給予同等對待,他們需要的是正常的生活,而非特殊的對待,多加關(guān)注其心理健康,確保其回到社會中時不與社會脫軌,不與人形成隔閡。
四、結(jié)語
未成年人犯罪這一結(jié)果產(chǎn)生的主要原因,一是成長環(huán)境,二是心理發(fā)育。刑法對于未成年人的懲罰,目的在于“用堅硬的鋼板阻止其樹干進一步歪曲地增長”,而下調(diào)刑事責任年齡意味著孩童的認知能力在提前,分辨是非的速度在加快。一個人的社會化,需要父母、老師、朋友的正向引導和合理管制,才有可能較完美的成功,法律不能夠改變?nèi)诵裕@是現(xiàn)實主義的觀點,法律僅僅能夠約束人性,只有在懲罰的基礎(chǔ)上才有資格談論改造。因為虛偽的人道主義忽略了“具體人”的權(quán)利,縱容了“抽象人”的本質(zhì),盲目地關(guān)注未達刑事責任年齡的人,而忽略了被害者的生命權(quán)利。如果對未成年人自身保持理性的能力十分不確定,那么對未成年人的約束和懲罰、下調(diào)年齡就是必要的,因為自由一旦溢出,剝削必定會無止境地發(fā)生。同時,在犯罪的背后,真正需要加大力度的是針對未成年人的普法教育,是針對未成年人的犯罪預防,是心理健康的正向引導,是整體社會風氣的共同建設,花朵雖需風雨拍打,但其仍是嬌嫩的,易損的,需要保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