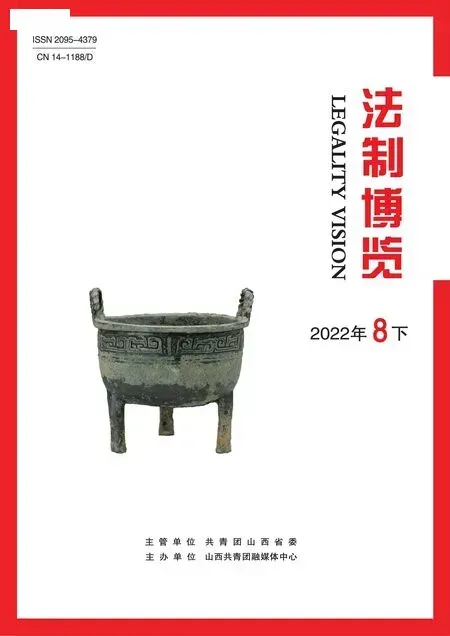“洞穴奇案”引發的法律與道德關系的思考
程慧坤
青島科技大學,山東 青島 266061
一、案例回顧
(一)案件基礎
“富勒的洞穴探案者案”[1]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法律虛構案例,以兩個重要且典型案件(1842年的“美國訴霍爾姆斯案”、1884年的“女王訴杜德利與斯蒂芬案”)演化而來,其共同點是均發生于海難之后,案件都是關于殺人和追訴。
其中,在1842年的“美國訴霍爾姆斯案”中,霍爾姆斯提出扔人下船減重是緊急避難的抗辯。他說,如果殺人對于船上的人的存活是必要的,那在法律上就是正當的,但法官鮑爾溫說,水手是大艇航行所需,但超過數量后,水手和乘客并沒有任何特權,須一起經受命運的考驗,最終以非預謀故意殺人罪判處六個月監禁。案例中,法官的判處是有道理的,從道德層面,似乎我們無法去譴責這個水手,但是在法律層面,他確實是存在過錯,在大艇遇難時,被扔下水的全是乘客,每個人的生命權都是相等的。在這里,水手應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在1884年的“女王訴杜德利與斯蒂芬案”中,同樣是被困在海上的四人,為了活命殺了身體最差的一個人,最后被判處絞刑又被赦免,這同樣是一場道德與法律的博弈。今天我們所探討的洞穴案件,正是在兩個案件基礎上衍生出的一個新的虛擬案件,讓我們對道德與法律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
(二)洞穴案件
探險協會的會員去石灰巖洞里探險時遭遇山崩被困,救援隊伍營救也被不斷發生的山崩所阻斷,且隊伍中的10名人員因此犧牲。探險者僅僅身上攜帶了少量的食物,直到失聯被困的第二十天才與營救人員取得聯系。該情況下,食物匱乏,被救生存的可能性極低,唯有吃掉一名成員的血肉,才能生存。被問可否用抽簽的方式來決定誰被吃掉時,無人回應,于是,其中一名成員威特莫爾提議用抽簽的方式吃掉一個人,其他成員剛開始并不同意,但通過無線對話后,他們同意了用扔骰子的方式殺人,但在扔骰子開始前,威特莫爾決定撤回約定,他認為應該再等一周,其他探險者指責他出爾反爾并且堅持扔骰子,輪到威特莫爾時,其中一名探險者替他扔并且要求他對這種方式的公平性表態,威特莫爾沒有提出異議,不幸的是恰巧選中了威特莫爾作為犧牲者,其他探險者們吃掉他后得以存活。被救援隊伍營救后,他們以謀殺罪被抓。由此,展開了一場法律與道德的探討。
二、從法律與道德角度分析
本文認為被告有罪,就像特魯派尼法官所認為的那樣,法典規定:任何故意剝奪他人生命的人都必須判處死刑。盡管,他們的悲慘境界會讓我們產生憐憫和同情,但是在嚴格的法律條文面前,不允許有任何例外的發生[2]。
看到這里,不禁會讓我們思考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是相互獨立還是相互融合的?我們服從法律的目的是服務于更高層次的道德,人的生命權擁有絕對價值,任何人都不能隨意去剝奪他人的生命,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就可以看出法律和道德是不沖突[3]且相互融合的。被告人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都不能剝奪他人生命,他的行為構成犯罪,應接受法律的懲罰。
唐丁法官被法律和道德之間的矛盾所困擾,他認為,如果饑餓不能成為盜竊食物的正當化事由,怎么能成為殺人并以之為食物的正當化事由呢?但從另一個角度去分析,他還是更傾向于該案件判以有罪判決,這個結論又會顯得很荒謬,因為被處于死刑之人的生命之所以能夠存活至今,是因為有十個英雄用生命來讓他們保存下來的。
本文對于唐丁前半句的表述表示贊同,饑餓不能成為盜竊的正當化事由,當然也不能成為殺人并以之為食物的正當化事由,法律能夠起到良好的威懾作用,如果這些人知道他們的行為會構成犯罪,那么我想他們可能會在執行殺人計劃之前再多等待幾天,那么救援行動就有可能會取得成功。我們應借助法律來保障道德與正義的實現[4]。那么,究竟什么樣的情況可以認定為正義?
三、正義同法律與道德的關系
(一)從道德和法律角度理解正義的理念
對于正義的含義,美國法理學家博登海默用一段恰當的話做出了比喻:“正義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變幻無常、隨時可呈現不同形狀并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當我們仔細查看這張臉并試圖解開隱藏其表面之后的秘密時,我們往往深感迷惑。”雖然正義被視為公民的最高美德和文明追求的基本價值,但正義究竟是什么?
從道德角度而言,正義與人們所崇尚的社會整體道德觀是吻合的,正如每個人的生命權都是平等的,它是不能被量化和比較的,否則會形成一命換多命的錯誤價值觀,它默認將人,作為了一種交易工具及手段[5]。被告為保全自身而傷害了他人的生命權,這是不被社會文明接受的,即使饑餓難耐,也不可用殺人方式延續,這樣會導致我們所確定起來的價值觀和正義理念崩塌,這同樣也是最為基礎的法律和道德義務[6]。因此,正義代表的是一種價值判斷,屬于道德范疇,人們心中的正義原則和向善的道德心理及行為是在人的成長中不斷經過道德教育的洗禮和灌輸中實現的。
法律中的公平正義原則和制度的建立積極促進了社會良好道德和公平正義思想的發展,為人們心中的道德觀念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是正義代表的不是個人道德,而是和社會價值觀相契合的整體道德觀,如果正義反映的是人們的個人道德觀,那么法律將無法發揮作用,也由此喪失了其本身的價值與意義,這同我們所要建設的法治社會便會背道而馳。
從法律的角度去分析,正義應當依法,這是正義能夠得以實現的基礎。我們要對法律保持尊敬,把它當作一種堅定的信仰,從心底去尊重。法律是針對特定的問題對應的解決方案,因此便有多種法律解決各種問題,不同的問題有不同的解決思路,也便有了不同法律間可分享不同的邏輯。
我們不能說法律的規定完全是對的,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它是適用于我們社會生活的。殺人償命是最簡單不過的道理,只不過在這個案件中,情景因素讓我們陷入兩難。從道德上講,簡單會導致無罪判決,從法律的角度而言,簡單也是有罪判決的成因[7],雖然從表面上看,這些之間存在一些矛盾,但是作為法官,其職責就是守護法律,使命就是尊重法律并且維護它。法官是被任命終身之職,是與政治過程完全隔絕,我們應該嚴格依法律規定,行使自己的職責,我們是依法律程序辦事而不是道德觀,否則將面臨人治社會從而給整個國家帶來災難。當我們直擊事情的本質時,我們會發現被告的行為很明顯觸犯了故意殺人罪的法律規定[8],斯普林法官認為探險者們只是預謀不存在惡意,沒有犯罪意圖,然而當時被告的殺害行為是有預謀的,反復討論抽簽的公平性來確定受害者的方法,這都是有意圖的,并且他們是出于維持他們自己生命的目的,導致了他人的死亡,這些都是符合故意殺人罪成立要件的。
就此而言,被告的行為不管是從法律角度去看,還是從道德角度考量,均應當被譴責的,即使以自己生命為代價,也應當克制住,不去殺人,這是人類文明所要求的道德品質的一部分[9],同樣,這也是法律所明確規定的,這是符合正義的觀點的,這也是法律與道德相契合的一個體現[10]。
(二)法律是一種妥協的正義
唐丁法官后半句的觀點,我是反對的,雖然被處死之人的生命的存在是由英雄性命的犧牲換來的,但是這和給被告定罪之間是不沖突的,死去的十個人是在營救過程中遇到山崩不幸犧牲,這和被告后來實施的犯罪行為是沒有因果關系的,所以這并不能成為他們無罪的理由。
那么從道德層面來分析,表面上看,饑餓狀態首先考慮活命,那么殺人的提議經所有人許可并公平決定犧牲一個人保全其他人,的確符合追求最大化的利益的觀點。然而,人的生命是不可以利益化的,它是無價的,應該受到絕對的尊重,我們生活在多元化的社會中,法律在很多時候不同于理想的正義,代表的是妥協的正義,承載每個個體的整體意志。那些以正義之名把法律放在一旁的人,則是假設我們所認為的正義與他們一致,如果我們不顧法律的規定去實行我們個人所認為的正義,就會與道德觀產生沖突,如果依靠我們個人的道德觀念為支撐,并且在數量上成為多數,那么這就會暫時主導政治生活。如果這是現狀,那么將會借以正義名義將法律擱置。僅僅以人民的部分意見去通過法律將造成對人民的踐踏,顛覆民主,那么這是真正的道德嗎?
守護法律才是維護和平、維護正義的必要手段,不能因個人或部分人的道德觀去損害法律。那些在道德上的理想主義者,不理解法律地位,總在法律或者法律外尋求正義,并把他們所認為的正義放到民主程序產生的妥協之上,這是不正確的正義。法律本身就包含了問題的解決方案,我們應該積極承擔職責,履行義務,守護法律,這同樣也是在為我們社會整體的道德觀服務。因此,歸根結底,法律與道德在根本上是一體的,是相互融合不可分割的整體。
四、總結
基于以上分析,結合“蘇格拉底案件”,蘇格拉底為了維護法律即使是不正當的法律,選擇了服毒,這體現了他對法律敬畏的態度和道德觀,他內心把對法律的服從、信仰、捍衛和尊重與他的道德觀融合在一起,他用自己的生命,維護了社會的穩定,這是一種更為高尚的道德觀念。
換句話說,遵守法律的規定一定意義上也是在服從內心的道德。法律是保持社會秩序穩定的最低標準,還需其他因素維護社會秩序,如道德。道德是人們內心的一種自我遵從,錯綜復雜的社會環境中存在誘惑扭曲我們的道德觀,此時便需法律的強制手段來使道德觀各異的人共同維護社會的公共準則,但不意味著法律可替代道德。法律是在充分考慮人性的基礎上,為了保障社會公共利益和人們的根本權益,歸根結底,是為人服務的。
司法具有時效性,這也導致法官時間不足,無法對信息掌握完全,難以實現深思和全盤把握,只能在有限的條件下,做出盡可能正確的判斷。法官需要在司法過程中反思和審視自身,對過去所做的決斷分析,更加審慎地對當下以及未來的案件進行裁決,從社會整體的道德觀出發處理好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系。若將道德主義和法律條文進行結合,將導致司法的職責難以正確履行,不可能嚴格遵守法令條文又私自進行調整篡改。法官的本職便是對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律進行解釋,而不是用自己的道德觀點加之其上,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人民道德觀點的反應。道德與法律,它們之間是一種相互融合且促進的。
用薩伯評價富勒的話說:“嚴密的法律思想既不排斥創造性,也不要求專業的術語表達,更不會讓道德成為與法律無關的獨立變數或事后思考。”因此,法律和道德二者相互影響,相互關聯,道德促使人們更好地理解法律規則與原則,使人們更容易接受法律,提供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法律追求正義的實現,道德亦是如此,只有法律與道德相融合才能更好地理解法律的內涵,發揮法律的作用,更好地實現公平與正義。因此,面對法律與道德的臨界選擇時,既要做到堅守住道德底線,又應當用善用法律維護自身道德堅守,從而走出道德困境,構建和諧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