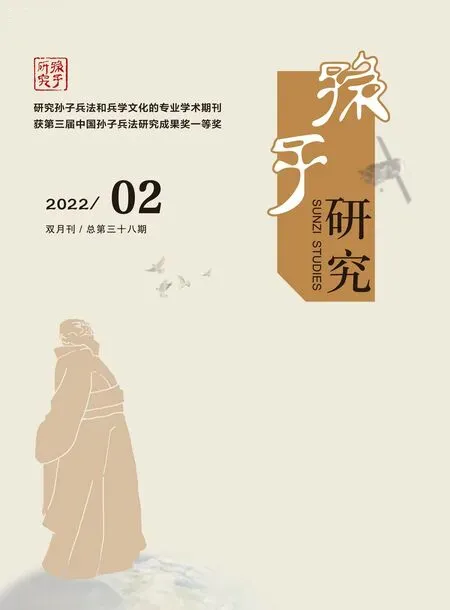結構視角下對《孫子兵法》作戰三篇思想內容的新解讀再建構
黃文偉 王 亮
《形篇》《勢篇》《虛實篇》是《孫子兵法》中集中論述戰場交戰攻防制勝的經典篇章,千百年來注解甚多。當代很多學者也對其做了深入研究,形成了很多極具思想啟發意義和軍事指導意義的成果。但是,學術繁榮往往并不意味著認識的統一,例如“形”與“勢”的內涵到底是什么,兩者之間是什么關系,各篇的邏輯結構又是什么,等等。對于這些問題,學者們都有各自獨到的見解,學術交流上也呈現出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本文嘗試從一種整體的視角——結構視角,來對這三篇的思想內容、邏輯結構再進行一個新的解讀。
結構視角,就是從整體結構、相互聯系的角度看問題。例如宋人張預曾指出:“《形篇》言攻守,《勢篇》說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敵攻守兩齊之法,然后知奇正;先知敵奇正相變之術,然后知虛實,蓋奇正自攻守而用,虛實由奇正而見。”〔1〕再如當代吳如嵩將軍認為,這三篇是講策略學,其中《形篇》主旨是“攻守之道”,《勢篇》是巧妙運用“勢”的力量,《虛實篇》主要講用兵中的“虛實”之勢及應對之策。〔2〕渤海大學的付朝教授提出了整體結構道法術分呈、篇章安排兩元對舉等觀點,其中《形篇》屬于道的層級,主題是戰略部署,《勢篇》《虛實篇》是法的層級,主題分別是軍事勢能和目標選擇。〔3〕上述三種觀點都是結構視角下的觀點,也可明顯看出對這三篇思想主旨在認識上的不統一。無疑,各種觀點都有其合理性所在,本文也是在充分繼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基于“理論創新以批判繼承為前提”和“戰場作戰以基本規律為根本”這兩條論述前提,著眼于古為今用,從結構角度對《形篇》《勢篇》《虛實篇》三篇的思想內容進行現代軍事意義的解讀。
一、《形篇》的邏輯結構
《形篇》的主題是總結戰爭經驗,明確繼承內容,揭示作戰規律。該篇首先對“昔之善戰者”是如何做到“善戰”的,分別從作戰實施角度和作戰全程角度進行分析,從而明確了需要繼承的內容——“勝可知”(戰前要做到先勝),需要批判的內容——“勝不可為”(戰時要等待敵可為我勝的時機),最后總結了以往戰爭的經驗,揭示了作戰力量對于勝敗的基礎性作用這一客觀規律,并引出了下一章主要解決的問題——戰場上如何做到“勝可為”。按照這一邏輯結構,本篇分為三個段落,分別對每一段落內的邏輯結構及思想內容進行分析。〔4〕
(一)從“昔之善戰者”到“故能自保而全勝也”,孫子主要從作戰實施角度(勝敗、攻守)分析了“昔之善戰者”是怎么做到“善戰”的
孫子首先從勝敗角度展開對“昔之善戰者”善戰原因的分析。孫子開篇便提出一個觀點,“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就是說,過去善于打仗的人,先要在戰場上做到不被敵戰勝,然后等待可以戰勝敵人的時機。因為“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即過去在戰場上己方所能做到的只是不可勝,可勝的因素在敵方。“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可勝”,也就是說,所以過去善于打仗的人能夠做到不可勝,而做不到使敵方必然能為我所勝。也正因為如此,孫子提到自古才有“勝可知而不可為”的說法,我方勝利的條件可以提前預知,但這種條件卻掌握在敵方手中,所以“不可為”。
緊接其上,孫子又從攻守角度分析了導致“勝不可為”的原因。“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就是說,不可勝是因為采取了防守,可勝是因為采取了進攻。“守則有余,攻則不足”〔5〕,即防守時各方面條件通常都有余,進攻則總是不足。這一觀點可用漢初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經法·君正》中“以有余守,不可拔也;以不足攻,反自伐也”的論述予以佐證,另外近代資產階級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也提出了“防御是比進攻強的作戰形式”的著名論斷。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防守方通常占據有利的地形條件,且能夠進行充分的作戰準備,以逸待勞。
本段最后,孫子指出了古代善戰者“善戰”的特點。“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就是說,善于守的人,敵方都無法發現,而善于攻的人,則能抓住戰機以凌厲的行動打敗敵方,所以能“自保而全勝”。從邏輯而言,“自保而全勝”是本段一開始提出“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的結果。假如敵方一直沒有暴露出可為我用的可勝之機,最后雙方退兵,當然也就只能“自保”(保全自己)了。只有通過耐心等待,等到了“敵之可勝”的有利戰機,我方才能夠“全勝”(完全勝利)。可見,孫子之前古代的這種作戰方式雖然穩妥,但作戰的主動性并不是很強。這就如同現代戰場上非得掌握確切的信息情報才會有所行動一樣。事實上戰爭的迷霧永遠存在,不可能完全消除。掌握了確切的信息,往往也就意味著已經失去了最有利的戰機。從其后《勢篇》《虛實篇》的論述中可知,孫子對這種消極等待的作戰是持批判態度的。本段至此,孫子從作戰實施角度,完成了對“昔之善戰者”之所以“善戰”,由勝敗到攻守進行倒推的原因分析。
(二)從“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到“敗兵先戰而后求勝”,孫子主要從作戰全程角度(準備與實施)分析了“古之善戰者”是怎么做到“善戰”的
通過上述分析,孫子首先鮮明地提出了“古之所謂善戰者,勝于易勝者也”的觀點。孫子采用類比論證方法,以“舉秋毫”“見日月”“聞雷霆”等日常經驗為例,闡明為什么“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戰勝而天下曰善”都不是所謂善于打仗的人;進而鮮明地提出“勝于易勝”的觀點,指出古代所謂善于打仗的人,就是能夠戰勝那些易于戰勝的敵人,并指出“善戰者”在外界名利方面的兩個特點:“無智名”“無勇功”,沒有智慧的名聲,也沒有勇猛的功勞。
然后,孫子重點闡述了“昔之善戰者”是怎么做到“勝于易勝”的。答案就是“戰勝不忒”,主要有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從作戰準備角度來講是“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就是說戰前所計劃采取的措置必然勝利,因為敵方的各種行動已在戰前被我充分預料到,這也便是“勝可知”;另一方面從作戰實施角度來講是“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這一點也就是第一段所論述的“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兩方面相結合,這便是以往戰爭“勝可知而不可為”的根本原因。這里,孫子通過分析得到了以往戰爭的一條重要經驗,即“勝兵先勝而后求戰,敗兵先戰而后求勝”,這是需要繼承下去的內容。
(三)從“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到“若決積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孫子主要總結了以往戰爭勝敗的經驗,并引出了下篇主題
首先,孫子指出善于用兵的人“修道而保法”,才能成為戰場勝敗的主宰。結合《計篇》所述,這里的“道”主要指的是“令民與上同意也”,但《計篇》之“道”主要是指君王之道,而這里的“道”是指將帥之道,即身處戰場的將帥要與兵眾上下一心、眾志成城。“法”則是指通過第二段分析所得到的一條重要經驗:先“見勝”而后“戰勝”。古往今來很多注家均將這里“法”的內涵進行了擴展,如理解為“曲制、官道、主用”等孫子在《計篇》中提到的內容。但是,《形篇》的著眼點是作戰力量在戰時的使用,而不是平時的建設。從結構上來分析,這里的“法”應該承接上文所提到的作戰要先“見勝”后“戰勝”,同時也應與下文中“兵法”的內容相銜接。“見勝”是戰前要預見能夠取勝的條件,“戰勝”則是戰時當具備這種條件時要贏得勝利。戰時“戰勝”的敵人是早已在戰前“見勝”中失敗的敵人,只有先“見勝”才能“戰勝”。這一法則即作戰的指導原則是需要繼承下去的,不應隨時代變化而變化,所以要“保法”。
然后,孫子引用古代兵法,給出了“見勝”的方法。“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常見的釋義是將地、度、量、數、稱、勝譯為國土面積、土地幅員、物產資源、兵力數量、力量對比、勝敗結果。但是從《形篇》是立足于作戰過程這一角度來看,孫子在這里給出的主要是在作戰層面評估勝敗的方法,而不是更高的戰爭層面的內容。戰爭勝敗的評估方法孫子已在《計篇》的“五事七計”中說明〔6〕,這里重點對比的是在某一場具體的交戰中敵我的實際力量,給出的是一種在戰前評估勝敗的方法,即“地生度”是結合特定的戰場環境列出需要評估的方面(如步兵、車兵、士氣精神、將領素質等),“度生量”是對敵我雙方這些方面的情況進行量化(如步兵多少、車兵多少、士氣如何等),“量生數”是對各方面的數量統一標準化為某個數值(因為評估過程中會涉及到不同質的事物之間的量的換算),“數生稱”是對雙方的綜合數值進行比較,“稱生勝”是最后得到勝敗的結論。此外,孫子還強調了勝敗的對比一定是要“以鎰稱銖”的。這樣做的原因,一方面是要保證確實形成絕對的優勢,另一方面也是盡量減少評估過程中的誤差〔7〕。
最后,孫子運用類比方法揭示了作戰規律,點明了本篇主旨,并引出了下篇。“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就是說勝利者的用兵就像決開“千仞之溪”的積水一樣。這里“千仞之溪”的積水主要是指在戰前作戰準備階段,對敵已形成絕對優勢的力量,這是一個蓄勢待發的過程。“決”則是指戰時作戰實施階段“戰勝”的行動。作戰力量的強弱是戰場勝敗的基礎,這是一條亙古不變的作戰規律。但這還不是戰場勝敗的關鍵,“基礎”只是提供了勝敗的可能,“關鍵”才能將這種可能轉變為現實。在原文中,“決”便是這個關鍵。在孫子之前的時代,這個“決”主要取決于“以待敵之可勝”的戰機,就是需要等待。如果孫子的論述僅限于此,那孫子最多也只是對以往戰爭的經驗進行了一個梳理總結,但《孫子兵法》之所以被譽為武經冠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孫子要把這個“決”的時機牢牢掌握在己方手中。敵方即使現在還沒有出現“可勝”之機,己方也要致敵形成這種“可勝”之機,這也便引出了《勢篇》所要論述的內容——如何使作戰由原來的“勝可知而不可為”轉變為“勝既可知又可為”。
二、《勢篇》的邏輯結構
承接《形篇》的論述,《勢篇》的著眼點便是如何在戰場上實現“勝可為”,主題是創新作戰理論,掌握戰場主動權,揭示作戰規律。該篇先是提出了作戰中“任勢”的四個基本要素〔8〕,然后對勢做了形象化的說明并提出了戰場上“任勢”的一般方法,最后明確了“任勢”的基本要求,揭示了作戰力量的行動對于勝敗的關鍵性作用這一客觀規律,并引出下篇主題。按照這一邏輯結構,本篇分為三個段落。
(一)從“凡治眾如治寡”到“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孫子提出了“任勢”的四個基本要素,并重點闡釋了奇正
分數和形名分別是作戰的編組與指揮活動,是“任勢”的基礎。傳統釋義將分數與形名分別解釋為組織編制和指揮工具,而從《勢篇》的論述是立足于戰場作戰的語境中來看,這并不完全貼合孫子的原意。組織編制和指揮工具在平時都是要有的,是軍隊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具有殺傷力功能的組織的基礎,不可能平時是一盤散沙,到了戰時才予以明確。實際上,古往今來每次作戰,指揮員都要根據情況靈活區分兵力、明確數量,這便是“分數“;而“分數”明確后,相應兵力也便具有了“形”與“名”,所謂“有形之徒,莫不可名”(《孫臏兵法·奇正》)。如果以現在的軍語來解釋,那么分數便是作戰中的編組。編組建立在平時組織編制的基礎上,是戰時針對具體任務對部隊所做的兵力區分。編組明確后,指揮員的指揮也就有了對象,所以才能“治眾如治寡”。形名是作戰中具體的指揮。編組后每組兵力都有相應的名稱、代號,有了這些名稱、代號,才能對特定兵力實施下令等具體的指揮活動,也才能“斗眾如斗寡”。
奇正和虛實分別是作戰的方法與指向,是“任勢”的關鍵。孫子在《勢篇》原文中只強調了奇正,原因是分數和形名是“任勢”的基礎,是在與敵展開正式交戰之前必須確定下來的;而奇正與虛實則是關鍵,是需要在戰場上著眼于敵情變化,不斷需要調整變化的。所以在《勢篇》中孫子主要論述了奇正,而將虛實單列一篇進行重點闡述。“奇正”是作戰方法,“正”通常解為“常規戰法”,“奇”通常解為“非常規戰法”。這種解釋并不切合戰場實際,也不利于指揮員實際運用。比如“常規”怎么界定?己方認為的“非常規”卻被敵方以為是“常規”,那還是“奇”嗎?實際上,“奇正”的立足點是在己方,兩者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己方對所用戰法的判斷,即己方預計敵方能料到的便是“正”,己方預計敵方料不到的便是“奇”,由此才能著眼于戰場具體情況而“循環無端”。孫子在本段論述最后引入了“勢”這一概念。“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就是說,作戰中的勢不外乎是由奇正形成的,奇正無窮暗含的意思也就是勢也無窮。那什么是勢呢?這便引出了第二段的內容。
(二)從“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到“以利動之,以卒待之”,孫子對勢進行了形象化說明,并提出了“任勢”的一般方法
孫子首先以兩個類比來說明勢與節的關系,旨在說明勢的強大威力。湍急的流水能把石頭沖起來,是勢;迅疾的飛鳥能夠毀折,是節。勢是險峻的,節是短促的。勢就像滿弓,節就如弩機。由此可見,勢在爆發時是一種無法抗拒的沖擊力量,能夠“漂石”,而在未發時是一種無形的威懾力量,就如“弩”。節便是勢在由未發變爆發時控制其爆發的關鍵環節,以現在的軍語而言,節便是對于作戰關鍵時節的作戰控制。無論是未發還是爆發,勢的威力是很大的。打比方很好理解,但問題是戰場上怎么形成這種險峻的勢呢?
緊接上文,孫子便結合戰場上的一般情況,提出了戰場上“任勢”的方法。孫子先是描述了戰場上的一般情況,并提出了如何不敗的總原則。“紛紛紜紜”是形容戰場上敵我交織的混亂情況,“渾渾沌沌”是形容戰場信息不明的模糊情況。交戰雖然混亂但己方部隊不能亂;戰場情況雖然不明,但只要己方能做到“形圓”就不會敗。這里的“形圓”強調的是己方兵力內在結構上的無懈可擊,例如采取某種攻防統一的陣型。結合《形篇》的論述,古代作戰在敵我交戰前己方要先立于不敗之地,孫子在這里將其進一步凝練為要保持“形圓”,這樣就不僅在戰前立于不敗之地,在交戰過程中也始終立于不敗之地。“形圓”也便是戰場作戰的一條總原則,是“任勢”的前提。以往的戰爭是“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而孫子這里的作戰理念則是先“形圓”、再“任勢”。在這種紛紜、渾沌的戰場情況下,要“任勢”,就必須采取“動敵”的方法。
接著孫子便論述了“動敵”的原理。“亂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強”,即己方整體的治當中可故意產生局部的亂,整體的勇當中可故意產生局部的怯,整體的強當中可故意產生局部的弱。“治亂,數也”,治亂通過數來明確。多少兵力嚴整待機,多少兵力示敵以亂,須明確數量。“勇怯,勢也”,勇怯可由勢來展現。嚴整兵力的勇敢,混亂兵力的怯懦,可通過兵力的行動來體現。“強弱,形也”,強弱要以形為根本。勇敢兵力的強悍,怯懦兵力的虛弱,要以保持“形圓”,即保持內在結構穩定為根本。
最后孫子給出了“動敵”的方法。善于“動敵”的指揮員,在“形圓”的前提下,通過“形之”即靈活調整兵力結構,例如以一部兵力示弱佯北,另一部兵力埋伏于預設戰場,敵人就必然會跟從;給敵以小利,敵便必然會奪取。以小利調動敵人,而以大部兵力待機破敵。傳統釋義將這里的“形之”解為呈現、暴露。這一解釋較為寬泛,要暴露給敵的兵力通常只是部分兵力,那么這個“部分”究竟是哪一部分,有多少?這便涉及到一個結構、數量的問題。另外,本段一開始孫子便提出了“形圓”的總原則,所以這里的“形之”應解為在保持整體“形圓”的前提下,根據情況靈活調整兵力結構。內在結構的調整必然導致外在形態的變化,由此敵方在偵察到后,才會“從之”上當受騙。
孫子的以上論述,用現在的軍語來說,其目的就是掌握戰場主動權。要在混沌不清的戰場情況中,主動地再給敵方制造一些“戰爭迷霧”,使敵方行動按照我方構想的實施,而不是像古代作戰那樣只將己方立于不敗之地,然后甘等戰機出現,那種作戰方式無異于守株待兔。這里孫子給出“動敵”的方法與《計篇》中的“詭道十二法”主要區別在于,本篇的方法著眼于戰場作戰常用的方法,而“詭道十二法”則著眼于整個戰爭的層面。
(三)從“故善戰者,求之于勢”到“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孫子提出了“任勢”的基本要求,并引出下篇主題
首先,孫子指出要根據敵軍具體情況“任勢”。“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傳統釋義多將這里的“擇人”解為“量才選將”,但通觀《孫子兵法》全文,“人”在很多語境下均指敵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故形人而我無形”“致人而不致于人”“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等等。從本篇上下文角度來看,這里的“人”也是敵軍之意〔9〕。以往作戰“以待敵之可勝”便是“責于人”,期望敵軍自發產生能被我勝的條件。而在孫子提出“任勢”這一概念后,便可以“不責于人”,可根據敵軍的情況(“擇人”)通過“任勢”取得勝利。自然,如何根據敵軍情況“擇人而任勢”也就成為一個需要解決的理論問題,由此也便引出了下文。
然后,孫子類比描述了“任勢者”指揮作戰的前提。“任勢者”雖然“不責于人”,不期望敵軍會主動為我產生有利于我戰勝的條件,但一切行動的前提必然是要清楚了解敵軍的情況。“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木石的本性是在安穩時靜止、陡險時運動、方形時不動、圓形時滾動。而敵軍的“本性”是什么呢?戰場上又如何根據敵軍的具體情況去“任勢”呢?在這里孫子并沒有直接給出答案,因為這些問題將在《虛實篇》進行重點闡述。
最后,孫子運用類比方法揭示了作戰規律,點明本篇主旨并引出下文。“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圓石從千仞之山滾下,結果必然是粉碎;敵人在我的勢里,結果也必然是失敗。由作戰力量行動所形成的勢,是戰場制勝的關鍵,這也是一條亙古不變的作戰規律。孫子在本篇創新提出了勢的概念,但勢所蘊含的規律卻是自古以來存在著的。“昔之善戰者”也是因勢才能制勝,但以往善戰者的“節”卻掌握在敵軍手中,戰場上只能被動等待敵軍出現可被我勝的戰機。而孫子是要將這個“節”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這便是“任勢”。那么假設敵人現在是“方石”,問題在于如何使敵像“圓石”一樣呢?本篇第一段提到“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便是使敵由“方石”變“圓石”的方法。但是使用奇正方法的著眼點在哪呢?戰場上又怎么根據敵方具體情況“任勢”呢?這便引出了下篇的內容——虛實。
三、《虛實篇》的邏輯結構
《虛實篇》前半部分是對戰場上如何使敵由“方”變“圓”問題的回答,后半部分是對《形篇》《勢篇》《虛實篇》三篇的總結與升華。戰場交戰是一個敵我雙方互動的過程,分數和形名主要是我方的編組與指揮行動,奇正則要著眼敵情靈活變化,這一著眼點便是敵方的虛實,也便是敵方的本性(與前文“木石之性”相對)。《虛實篇》的主題是提出創新觀點,總結升華認識。篇中孫子先是分別從走和打兩個方面,著眼敵方虛實情況,提出走要“致人而不致于人”、打要“敵不知其所攻守”的觀點,然后分析了善攻善守的根本原因,提出了關于作戰“勝可為”的核心觀點,在此基礎上孫子歸納了用兵作戰的一般方法,即先要“勝可知”然后再“勝可為”,最后,孫子將其對作戰的認識升華到了哲學高度。
(一)從“攻而必取者”到“故能為敵之司命”,孫子分別從走和打兩個方面,著眼于敵方虛實情況,提出走要‘致人而不致于人’、打要‘敵不知其所攻守’的觀點
走和打是作戰的兩種基本活動。〔10〕戰場上敵軍不會自覺按照我方設想實施行動,不會自覺地由“方”變“圓”。要形成勢的威懾力和沖擊力,首先就必須著眼于敵方虛實情況,充分發揮我方主觀能動性,積極地調動敵人,靈活地打擊敵人。由此,孫子在本篇首先從走和打兩個方面提出了其基本觀點。
對于走,孫子提出要“致人而不致于人”。孫子先是總結了以往的戰爭經驗,“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后處戰地而趨戰者勞”,佚勞便是一種典型的虛實情況。然后提出了“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的觀點,善于打仗的人,要能夠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所調動。接下來分別從“致人”和“不致于人”兩個方面展開對原因的分析,“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致人”是因為能夠使敵以利害,所以能讓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不致于人”是因為“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所以己方才能夠“行千里而不勞”。
對于打,孫子提出要“敵不知其所攻守”。孫子在文中先是從攻與守、進與退、欲戰與不欲戰三種正反相結合的角度,論述了戰場上如何能掌握主動權。然后提出其對于打的基本觀點“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這便相對于以往戰爭“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更進一步強化了戰場作戰的主動性,是孫子的一大理論創新。最后,孫子對這一認識進行了升華。無論是攻守還是進退,這些都是有形的。只有根據戰場情況、敵情靈活快速變化,達到無形、無聲的境地,那我方才不僅僅是戰場勝敗的主宰,即“勝敗之政”(《形篇》),也便成為了敵軍命運的主宰(“敵之司命”)〔11〕。
(二)從“故形人而我無形”到“可使無斗”,孫子分析了善攻善守的根本原因,提出了“勝可為也”的核心觀點
相較于以往戰爭“勝可知而不可為”,“勝可為也”這一觀點是孫子對戰場作戰最為深刻的見解。孫子得出這一結論主要采用了演繹的方法。孫子先從一般性的角度,分析了善攻善守的根本原因。“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傳統釋義是使敵方暴露形跡而我方不暴露,這樣便可做到我兵力集中而敵分散。從上下文語境來看,“暴露形跡”這種對“形”的解釋,一方面與前面“敵之司命”不匹配〔12〕,另一方面與后面“深間不能窺”相矛盾〔13〕。這里的“形”更多表示一種作戰力量的結構,“形人”即我方能控制敵方的結構,如前述“動敵”之法,這樣才能成為“敵之司命”;“無形”則是指我能因敵而變化,靈活快速調整我方結構,敵變我變,快到極致也便無形了,自然“深間”也難以窺探。只有在戰場上做到我方能控制支配敵方的結構,才能“我專而敵分”,進而以我眾擊敵寡,取得勝利。這也便是善攻善守的根本原因。
在上述一般性論斷的基礎,孫子依次加上了戰地、戰日的具體條件進行論述,最后提出了“勝可為也”的核心觀點。當我方進攻時,敵方由于不知我所要戰之地,所以防備就多,前后左右不能兼顧,這樣便可造成我以眾擊寡的戰場態勢。加上戰日的條件也同樣如此。基于上述論述,孫子聯系實際,得出了“勝可為也”的結論。孫子認為己方若能做到知戰地、知戰日,便可奔襲千里與敵會戰,即使越人兵眾多,也無濟于事。“勝可為也”這一結論既是孫子關于作戰的一般性結論,也可看成是針對吳越戰爭所做的戰略預判,是孫子最為核心的觀點。從歷史角度來說,這也應該是當時孫子最能打動吳王闔閭的一個理由。
(三)從“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到“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于無窮”,孫子歸納了用兵作戰的一般方法,即先要“勝可知”再“勝可為”
用兵作戰的前提還是“勝可知”。除了在《形篇》中提到的要“修道而保法”這一傳統做法,還要知敵虛實。本段一開始孫子便給出了知敵虛實的方法,即“策之”(己方籌策分析)、“作之”(己方兵力調動)、“形之”(己方示形動敵)、“角之”(己方戰斗偵察),以知敵“得失之計”(敵方作戰企圖)、“動靜之理”(敵方行動方案)、“死生之地”(敵方利弊條件)、“有余不足之處”(敵方部署虛實)。策、作、形、角,是從作戰準備到作戰實施階段;從概略到詳細、從分析到驗證的一套完整的知敵虛實的方法。作戰準備階段,己方通過籌策分析、兵力調動可對敵方作戰企圖、行動方案有個初步的判斷。作戰實施階段,己方通過示形動敵之法、調動支配敵軍,可知敵方作戰的利弊條件。當敵方已在我的控制支配下由“方石”變為“圓石”時,最后通過戰斗偵察進行驗證,以保證我方對敵判斷的正確。“策之”主要指的便是《形篇》中提到的度、量、數、稱、勝。相較于傳統的分析方法,這里孫子又創新地提出“作之”“形之”“角之”三種注重實踐的探敵虛實的方法。這樣既能評估“策之”的有效性,也能更為全面地掌握敵情虛實。
用兵作戰的關鍵要做到“勝可為”。“勝可為”的方法,便是靈活運用“任勢”之法——“形兵”。如前文對“形人而我無形”的分析,這里“形兵”的含義,也并非僅僅是偽裝、佯動這些表面的兵力行動,而是指的運用分數、形名、奇正、虛實等“任勢”的基本要素調整兵力結構,實施作戰行動。即著眼于敵情虛實,確定兵力分數,運用奇正之法,下達形名指令,實施兵力行動。這四個“任勢”要素便形成了一個現代所謂的“OODA 循環”,只不過更為具體。戰場上敵情變化迅速,我因敵而變化也迅速,唯有如此快到極致才能達到“無形”的境界。“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就是說,人們都知道最后我取勝時的形態,卻不知道我是怎么形成這種形態的,也就是在作戰過程中我是怎么因敵而無形的。這里“制勝之形”實質上就是“任勢”,即指揮員靈活運用分數、形名、奇正、虛實指揮作戰的過程。
(四)從“夫兵形象水”到“月有死生”,孫子總結了其對用兵作戰的認識,并將其升華到了哲學高度
本段是對《形篇》《勢篇》《虛實篇》三篇的總結和升華,主要揭示了客觀事物始終是運動變化的這一唯物辯證法基本原理。首先,孫子以水形喻兵形,闡述了用兵要因敵制勝的基本規律。兵形與水形的共同點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非靜止,兩者都是運動的。“避高而趨下”“避實而擊虛”分別說明了水形和兵形的運動趨勢,因為有這種趨勢在,所以就不會停止。二是無定形,形態都是變化的。“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就是說,兵形之所以象水,是因為兵形要根據敵情變化而不斷變化。因此,孫子得出了“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的結論。在對三篇內容進行總結的基礎上,孫子將其對用兵作戰的認識升華到了哲學高度。“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孫子之所以最后將五行、四時、日月這些看似與用兵作戰毫無相關性的事物羅列在一起,其本意就是要說明事物都是運動發展的這一基本道理,世界上萬事萬物莫不如此,這便體現了孫子樸素的唯物辯證法思想。
結語
從作戰三篇的整體邏輯結構角度來看,《形篇》言繼承,《勢篇》談創新,《虛實篇》上半部分是《勢篇》的下文,下半部分是對三篇的總結和升華。通過三篇的論述,孫子批判繼承了其之前時代“勝可知而不可為”的作戰思想,創新實現了“勝可為也”的理論突破。其中,《形篇》通過分析總結以往經驗,揭示了“作戰力量的強弱是戰場勝敗的基礎”的規律。《勢篇》通過創新作戰理論,揭示了“作戰力量行動所形成的勢是戰場制勝的關鍵”的規律。《虛實篇》通過對三篇內容進行總結,孫子將其對用兵作戰的認識升華到了哲學高度:任何事物都是運動發展的。
基于全文對作戰三篇思想內容的詳細分析與重新建構,可對“形”與“勢”的本質內涵和相互關系提出以下觀點:孫子所謂的“形”是作戰力量本體內在結構與外在形態的辯證統一,具有外顯性(能夠看到外在形態)、可變性(通過調整結構改變形態)、強弱性(是一種客觀實在的力量,有強弱之分);孫子所謂的“勢”是作戰力量功用在特定時空環境下的發展趨向,具有內隱性(依附于作戰力量、內隱于其作戰行動)、主導性(決定作戰力量戰場勝敗的趨勢)、優劣性(是敵我之間與戰場環境的綜合態勢,有優劣之分);“形”與“勢”是作戰力量的“體”與“用”的關系,強勝弱敗、優勝劣汰,“形”是戰場勝敗的物質基礎,“勢”是戰場勝敗的主導關鍵。
【注 釋】
〔1〕黃樸民,趙海軍:《孫子兵法集注》,長沙岳麓書社2002年版,第101 頁。
〔2〕吳如嵩,蘇桂亮:《孫子兵學大辭典》,沈陽白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19-20 頁。
〔3〕付朝:《孫子兵法主題研究述論》,載《濱州學院學報》2014年第1 期。
〔4〕本文所依據原文總體上采用《十一家注孫子》本的內容,參見吳如嵩、蘇桂亮:《孫子兵學大辭典》,沈陽白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44-45 頁。
〔5〕《十一家注孫子》本中,該句為“守則不足,攻則有余”。本文采用時間更早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中原文,即“守則有余,攻則不足”。
〔6〕由國土幅員等決定的國家兵力數量規模,在兩國開戰前必然是已經大致明確了的。而在具體的某一場交戰中,當面之敵與我的力量對比,卻是需要詳細評估的內容。這一點即使到了現在也一樣,作戰評估是古往今來作戰中的一個共性活動。
〔7〕評估過程中誤差不可避免。例如在“量生數”這一環節,即使在21世紀的今天,要得到一個較為合理的數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主要困難有兩個方面:一是士氣精神等很難量化;二是不同質的事物的量之間很難找到一個統一的換算標準。
〔8〕“任勢”取自“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實質是指揮員著眼于勝勢指揮作戰的過程。其基本要素是:分數、形名、奇正、虛實。關于“為什么是‘任勢’”的問題,本節第三部分會給出詳細解釋。
〔9〕對于“人”是指敵軍的這一觀點,國內有學者亦持此見,參見汪柳:《〈孫子·勢篇〉三議》,載《漢中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2 期。
〔10〕毛澤東同志曾在上世紀60年代談將來如何打仗時說:“打仗沒有什么巧妙,簡單說就是兩句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11〕戰場勝敗的主宰和敵軍命運的主宰,這兩種主宰的區別,主要在于前者是在交戰之后我能決定勝敗,因為這種勝敗是建立在我方終于等到敵方產生了有利于我勝的時機。而后者則是不管是戰中還是戰前,不論是敵我勝敗,還是敵方一切進退攻防行動,都由我掌握控制。
〔12〕不匹配:僅僅是敵方暴露我方不暴露、敵明我暗,不足以能使我成為“敵之司命”。因為在戰場上敵我不可能始終處于這種狀態,我方也很難因此就做到“我專而敵分”。
〔13〕相矛盾:“深間”必然是敵方派入我方內部的間諜,若“形”僅僅是指暴露行跡的話,那在我內部的“深間”又怎能不知道當前我方的位置、形跡?又怎能不把這種攸關勝敗生死的情報想方設法通知敵方?既然是“深間”,那我方兵力部署這些表面上的信息是很容易掌握的,這便與“不能窺”產生了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