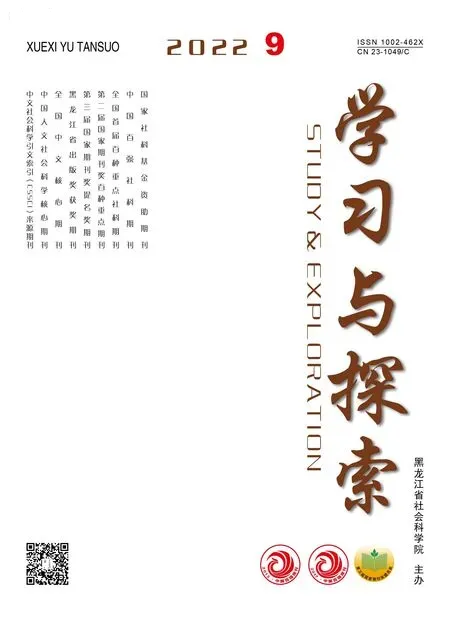世界歷史與中國式現代化
吳 曉 明
(復旦大學 哲學學院,上海 200433)
隨著現代性的權力——一種無遠弗屆的權力——開辟出“世界歷史”,現代化就成為每一個民族的普遍的歷史性命運了。但是,任何一個民族的現代化道路與進程,都是由其特定的社會條件和歷史環境來決定的。在這樣的意義上,中國的現代化就必然要在其歷史性的進程中發展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實際的現代化,即“中國式現代化”。而在新的歷史方位上,中國式現代化不僅取得了史無前例的發展成就,而且開啟出中國與世界發展的新途徑。當中國式現代化日益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時,對這一現代化實踐的理論考察就變得很有必要了。因此,本文試圖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性進程作出要點上的探討,以便在“世界歷史”的基本處境中揭示中國式現代化的現實起源、當代意義和未來籌劃。
一
1840年以來,中國遭遇到了極為嚴峻的挑戰和危機。與以往任何一種嚴峻局面完全不同的是,這一次的挑戰和危機歸根到底起源于現代性(現代世界的本質—根據)在特定階段上的絕對權力。這種絕對權力史無前例地開辟出“世界歷史”,從而使原先地域性的歷史或民族性的歷史都被納入到世界歷史的總體進程之中。不僅如此,現代性的權力在開辟出世界歷史的同時,還為之布局了一種基本的權力關系,即支配—從屬關系:“正像它[資產階級]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1]27這意味著,世界歷史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到現代資本主義文明中來,并因此而使現代化成為每一個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普遍的歷史性命運。海德格爾把這種歷史性命運稱為“地球和人類的歐洲化”。這種情形深刻地表明:中國所面臨的現代化任務是歷史的必然的,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和愿望為轉移的。
然而,盡管在“世界歷史”的基本處境中,現代化普遍地成為每一個民族的歷史性命運,但對于不同的民族來說,其現代化道路的開辟,其現代化的任務、進程與方式卻是非常不同的。我們可以很容易觀察到,直至今天,現代化的歷史性進程,不僅在基督教世界、伊斯蘭世界、東亞、南美以及非洲等各個區域的展開方式非常不同,而且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個領域,也都有其獨特的表現形式。無論其展開方式是順利的還是艱難的,也無論其表現形式是這樣的還是那樣的,總而言之,它們都實際地采取著相當不同的發展道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每一個民族都處在非常獨特的社會—歷史的現實中。正如馬克思在致《祖國紀事》編輯部以及致查蘇利奇的信中所指出的那樣,一個民族的現代化道路與進程,完全取決于特定民族處身其中的“社會條件”和“歷史環境”——這樣的社會條件和歷史環境乃是非常獨特、非常具體的[2]770-772。如果把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轉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公式”,并把這種“超歷史的”公式先驗地強加給任何一個民族,就只會得出完全無頭腦的荒謬結論[2]340-342。例如,在講到俄國的道路時,馬克思指出,俄國農村公社的歷史環境是獨一無二的,即使從經濟的觀點來看,俄國也能夠通過本國農村公社的發展來擺脫它在農業上所處的絕境;而“通過英國式的資本主義的租佃來擺脫這種絕境的嘗試,將是徒勞無功的,因為這種制度是同俄國的整個社會條件相抵觸的”[2]771。
由此可見,現代化任務的普遍性,只有通過每一個民族在其社會—歷史中的具體性,才可能得到現實的展開和特定的完成。黑格爾就曾在哲學上論證過,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體的;真正的普遍性絕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深入于具體之中并且能夠把握住具體的普遍性。所以在《歷史哲學》和《法哲學》中,黑格爾多次批評拿破侖說,這位軍事天才和政治天才想要把法國的自由制度先驗地強加給西班牙人,結果卻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并且是不可避免地失敗了。這種失敗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為“如果要先驗地給一個民族以一種國家制度,即使其內容多少是合乎理性的,這種想法恰恰忽視了一個因素,這個因素使國家制度成為不僅僅是思想上的事物而已,所以每一個民族都有適合于它本身而屬于它的國家制度”[3]。
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開辟出來的,是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展開其前進運動的,這就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現實起源或本質來歷。離開特定的社會條件和具體的歷史環境,就不可能有中國現代化實踐的獨特道路和實際進程,因此也就不可能在中國實現現代化。那種以抽象普遍性(實際上只是來自于近代西方的某種觀念)來先驗地強制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種種設想與方案,不過是一些純粹的夢想或幻覺而已,在哲學上不過是局限于“外在反思”的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表現而已。馬克思曾把這種設想或方案稱為“社會新棟梁的文壇奴仆”的虛假觀念;而黑格爾則把這種思維方式稱為“詭辯論的現代形式”,稱為“浪漫主義虛弱本質的病態表現”。
在中國獨特的社會條件和歷史環境中,并且在經歷了多方的探索和嘗試之后,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本質特征最為突出地表現為:這一進程與馬克思主義建立起本質的聯系。這樣的聯系對于中國的歷史性實踐來說,同樣是必然的,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和愿望為轉移的。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必須經歷一場徹底的社會革命來為它奠基,而這場社會革命歷史地采取了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定向。我們知道,任何一個大規模的現代化進程都需要特定的社會基礎,這樣的基礎只有通過特定的社會革命才可能建立起來。歐洲的現代化進程同樣需要通過社會革命來為它奠基;而這樣的社會革命采取怎樣的路徑,在政治斗爭上以何種方式展開,以怎樣的激烈程度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并得以完成,則完全取決于不同民族的社會條件和歷史環境——因此英國1640年的革命和法國1789年的革命就是相當不同的。對于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整體來說,同樣必須經歷一場徹底的社會革命來為它奠基。如果說這一社會革命的定向是由當時中國的社會條件及歷史環境來決定的,那么,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與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聯系就在于:除非中國革命歷史地采取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定向,否則這場革命就不可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并得以完成;除非中國的歷史性進程將革命的領導權最終托付給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否則它就不可能完成其社會革命的任務從而為整個現代化事業真正奠基。
五四運動是一個突出的轉折點,它意味著中國革命從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的決定性轉折。但在理解這一轉折點時必須充分意識到:五四運動不僅僅是一般的觀念(現代性的價值目標或所謂“啟蒙”),而且是現實的歷史運動(即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斗爭);尤其需要充分把握住的是:在這一現實運動中正在展開出來的歷史性趨勢,因為歷史發展的總體趨勢比既成的歷史事實具有更高的現實性。
這種總體的歷史性趨勢是怎樣的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五四運動就不能不成為當時世界革命的組成部分;而當五四運動成為世界革命的組成部分時,它就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好了準備,從而為中國的現代化事業與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聯系做好了準備。“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4]699-700由此可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與中國革命具有本質的聯系,而中國革命又在特定的歷史轉折點上同馬克思主義建立起本質的聯系。即使是稍有識見的西方歷史學家也清晰地看到了這種歷史的必然性。例如,費正清在《偉大的中國革命》一著中這樣描述道:就像軍閥制度與現代教育不可能并行不悖一樣,美國式的自由主義和中國革命也不可能并行不悖。“杜威于1921年7月11日離開上海時,中國共產黨剛好要在那里成立。最為進步的教育[指杜威在中國關于現代教育的演講]剛剛展示在革命的中國面前時,她卻轉到馬克思和列寧那邊去了。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在共產國際的陽光照耀之下變得黯淡無光。顯然,美國的自由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雖然它作為主流思潮后來又茍延了15年。”[5]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決定性地標志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與馬克思主義建立起本質的聯系。自此以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同時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在這樣的歷史性進程中,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的,是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為本質特征的。在現實起源的意義上,中國式現代化的形成過程,同時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過程。因此,如果說,在“世界歷史”的基本處境中,中國最初是被動地卷入到現代化進程中去的,那么,“在近代以后中國社會的劇烈運動中,在中國人民反抗封建統治和外來侵略的激烈斗爭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過程中,1921年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從此,中國人民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斗爭就有了主心骨,中國人民就從精神上由被動轉為主動。”[6]
二
在“世界歷史”的基本處境中,中國的歷史性實踐不僅展開為一個以現代化為主題的前進運動,而且在特定的階段上使這一運動與馬克思主義建立起本質的聯系。然而,與中國的歷史性實踐建立起本質聯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抽象的馬克思主義(抽象的馬克思主義與這一進程至多只有偶然的、表面的聯系),而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的歷史性進程與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聯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現實的歷史行程中建立起來、發展起來和鞏固起來的。而這樣一種本質聯系的建立、發展和鞏固,又是唯賴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與中國的歷史性實踐相結合才成為可能的,也就是說,是唯賴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才成為可能的。在這個意義上,沒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本質聯系。
我們之所以要突出地強調這一點,是因為對于當時的先進知識分子和早期共產黨人來說,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并不是能夠被現成地給予的東西,而是需要經過一個艱苦鍛煉的過程才能被鍛造出來的。在早期的“學徒狀態”中,抽象的觀點往往容易占據上風。中國革命時期就有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被恰當地稱為“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很熟悉的一個例證是,教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和俄國的經驗當成抽象的原則來加以運用,特別是試圖把“中心城市武裝起義”這一原則先驗地強加給中國革命的進程。由之而來的結果同樣是我們很熟悉的,它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革命遭遇到一連串嚴重的挫折,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很明顯,這里導致挫折和失敗的根源,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本身,也不是俄國革命的經驗,而是局限于抽象原則的教條主義。只有當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的過程中終于意識到,中國革命的道路不是“中心城市武裝起義”,而是“農村包圍城市”時,他們才開始在武裝革命的主題上擺脫了執著于抽象原則的教條主義,也就是說,才真正使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這種結合的要義是,深入地把握中國特定的社會現實,并根據這一現實本身的具體情況來制定革命的綱領。
“農村包圍城市”的綱領,說到底是與中國的社會現實相結合、與中國革命的歷史性實踐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而這種結合所要求的理論上的具體化,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題中應有之義,是這一學說的“生命線”和“活的靈魂”。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這種依循特定的社會條件和歷史環境而來的“具體化”,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原則或原理的“中國化”。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絕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4]707。
這樣一種根據特定社會條件和歷史環境而來的具體化,適用于中國的整個現代化進程,也就是說,不僅適用于為現代化事業奠基的中國革命,而且同樣適用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為了完成現代化任務,中國自近代以來就進行了多方面的工業化嘗試,并且也相應地開展了大規模的對外學習。但是,通過這種學習所獲得的關于現代化的外部理論和外部經驗,只有經過必要的中國化,也就是說,只有根據中國的社會條件和歷史環境來加以具體化,才可能具有真實的效準并取得積極的成果。從具體化的原則來講,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和任務必須立足于特定的社會條件和歷史環境來加以確定,必須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實際的現代化,也就是說,必須成為中國式的現代化。從歷史性的實踐來講,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探索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性進程就大規模地、積極地開展出來了。毫無疑問,這一探索的成就是主要的,其意義是無比深遠的。就像年鑒學派的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在1963年的《文明史綱》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的實驗”取得了無與倫比的、令人信服的成功——它在1945年還造不出摩托車,但現在已馬上能夠制造原子彈了。“在非常短的時間里,這一活著的最古老的文明就變成了所有欠發達國家中最年輕、最活躍的力量。”[7]
不消說,正是這一歷史性進展為新中國奠定了最初的工業化基礎。同樣不消說,在這一現代化建設的探索過程中,也存在著曲折、失誤和教訓,因而在某種程度上遲滯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干擾了現代化任務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進程。為了糾正這樣的遲滯和干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不僅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而且“指出經濟建設必須適合我國國情,符合經濟和自然規律;必須量力而行,循序前進,經過論證,講求實效,使生產的發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相結合;必須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8]。在這里得到明確體現的是:進一步重申并強調了我們所面臨的現代化建設任務,并且尤為突出地要求將這一現代化建設任務同中國的國情和實際緊密地結合起來。由此可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現代化探索,無論是其成功的經驗還是其失誤的教訓,都越來越清晰地表明,中國只有最堅決地完成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中國只有從自身的現實或具體的國情出發,才可能真正推進并完成現代化建設任務。由這一明確的立腳點開辟出來的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這條道路也就是更高階段上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中國式現代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同一個歷史性進程,而中國式現代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當代形態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它是由中國革命為之奠基,承續著新中國的發展成就與脈絡,以改革開放為起點而開辟出來的道路。這條道路在今天展現出怎樣的歷史性意義呢?為了充分理解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當代意義,我們需要回到改革開放之初,回到20世紀的最后十多年。回顧往事,最深刻的歷史性記憶是:當時中國的現代化水平還很低,人民的生活還很不富裕(還有大量的貧困人口),而當我們剛剛踏上漫漫改革之路時,世界社會主義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災難性挫折。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一場又一場的顏色革命,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改旗易幟,以至于當時一般的意識形態和知識界的普遍氛圍都認為,馬克思主義這次是被送進了墳墓,而《共產黨宣言》的結論是最終破產了。福山的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迎合了這種流俗的意識形態氛圍。按照這部著作的觀點,歷史是終結了:它終結于現代性之中,終結于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基本建制之中;而這同時也意味著:世界歷史已不再具有其他的可能性了。
雖說這種輕佻的、偽黑格爾主義的觀點遭到了一些理論批評(例如德里達的《馬克思的幽靈》),但對這種觀點的真正歷史性反駁,卻來自中國:一支現實的、有肉體的馬克思主義正在生機勃勃地成長和發展起來——它就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引領下的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不僅強有力地推進著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而且使中國式現代化的整個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如果說改革開放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開啟,那么這條道路迄今大約40多年的發展,或許可以簡要地概括在建設“小康社會”的廣闊實踐中,概括在這一目標的提出、展開、深化和實現的歷史性進程中。改革開放之初提出的目標是“四個現代化”,它同時也被明確規定為“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回顧這40年來的發展進程,大體可以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徹底消除貧困,以及作為并聯式過程的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疊加發展,所有這一切都使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此可以說,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就不可能歷史性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發展,就不可能在這一新發展的基礎上去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在經歷了數十年的發展之后,我們現在能夠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當代意義作出充分的歷史性估量。這是因為我們不僅獲得了相應的歷史縱深,而且尤其是因為當今中國的歷史性實踐已經抵達新的“歷史方位”。因為只有站到新的歷史方位之上,我們才能夠獲得清晰的尺度來衡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取得的巨大進展,才能夠依照真正的歷史性來評估中國式現代化對于當代世界來說的非凡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新的“歷史方位”上展現出以下三重意義。
第一,它對于中華民族來說所具有的歷史性意義: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第二,它對于世界社會主義來說所具有的歷史性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其自身的積極創新和發展壯大,從20世紀末社會主義普遍遭遇的巨大挫折中決定性地站立起來,它在成為科學社會主義偉大印證和偉大實踐的同時,歷史性地開拓出世界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積極前景。
第三,它對于人類整體發展來說所具有的歷史性意義:它敞開出一個無比廣闊的實踐探索領域,它拓展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新途徑新選擇,為人類的整體發展和整體進步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因此,概括起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史上、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義。”[6]
由此可見,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它的發展進程中抵達新的歷史方位時,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式現代化才會在對我們民族自身具有重大意義的同時,開始對“世界歷史”的整體進程具有重大意義。這樣的意義是在何種程度上并具有何種性質呢?回答是:它是一種“世界歷史意義”。這里所說的“世界歷史意義”,是在黑格爾大體規定的那種含義上來使用的。它意味著:特定的世界歷史民族,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上,承擔起新的歷史任務,由于這種任務在“世界歷史”中具有更高的普遍性,所以便展現出它的“世界歷史意義”。因此,正像當今中國的歷史性實踐是中國式現代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愈益加深的本質聯系一樣,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定向的現代化事業,已經開始建立起與人類社會的整體發展、與世界歷史之未來走向的本質聯系。正是由于這種本質聯系,當代中國的歷史性實踐才在特定的轉折點上展現出它的世界歷史意義。
在新的歷史方位上,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基本引領的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不僅極大地顯示出它的獨特性和優越性,而且不斷地展現出它正在積極生成的全新內涵。從社會—歷史的現實來說,中國式現代化是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實際的現代化;從發展的方向來說,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9]。如果沒有現代化,中國就不可能在現代世界中生存;如果沒有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巨大的現代化成就,并通過這樣的成就在發展進程中站到新的歷史方位上。雖說在現代化的一般觀念中,某些共同點是確實存在的,但對于任何一個民族的現代化任務和道路來說,其現實性總是植根于特定的社會條件和歷史環境。即使是西方原生的現代進程,同樣是在其特定的社會條件和歷史環境中展開的。如果抹殺這一現實基礎本身的具體性,而是試圖把來自近代西方的抽象觀念先驗地強加給任何其他民族,那么在這里表現出來的,不過是完全無頭腦的主觀幻覺罷了。
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在新的歷史方位上展現出它的“世界歷史意義”,是因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在于它將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而且還在于:它在完成現代化任務的同時,在占有現代文明積極成果的同時,正在開創人類文明的新形態。這意味著,在新的歷史方位上,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建立起非同尋常的歷史性聯系。如果說,中華民族的復興僅僅是成為一個如英、美、德、法等的現代強國,那么,這一發展就不具有新的世界歷史意義;毋寧說,它只是作為某種特例、某種表征而從屬于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及其被規定的意義范圍罷了。只有當特定的歷史性進程在消化和吸收現代性成果的同時,能夠超越現代性本身,它所具有的世界歷史意義才開始積極地展現出來。
按照馬克思歷史理論的基本觀點,人類文明的新形態必定具有兩個最基本的規定。第一,完成現代化任務,從而充分占有現代文明的積極成果。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就只會有“貧窮的普遍化”,并會“使一切陳腐的東西死灰復燃”。所以馬克思在講到俄國革命的時候說,根據俄國具體的、不斷變化著的社會條件和歷史環境,它的現代化道路的可能性是多重的——可能走這條道路,也可能走那條道路,但是,無論它走哪一條道路,都必須能夠現成地占有現代文明的積極成果。第二,揚棄并超越現代性本身。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就意味著依然從屬于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從屬于這一文明的本質規定,因而就不可能開啟人類文明的新形態,并從而展現新的世界歷史意義。因此,馬克思非常嚴格地把揚棄了現代性本身的人類文明形態稱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 。
自黑格爾將歷史性引入哲學以來,特別是自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開展出真正的歷史性批判以來,將現代文明——以現代性為本質—根據的文明——看作是永恒事物的觀點(并因此“祝福它的永垂不朽”),就已經是時代錯誤了。馬克思的學說所要表明的是:現代—資本主義文明是歷史的事物(“歷史的過渡形式”);而只要它是歷史的事物,就有它的出生和成長,有它的鼎盛時期和文明貢獻,也有它的衰老和死亡。在這樣的意義上,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歷史性批判無非意味著:揭示其歷史的前提并把握其歷史的界限,從而歷史地肯定它并且也歷史地否定它。這種批判絕不是一味的否定(如阿倫特所說,在資本主義的批判家中馬克思是對資本主義肯定最多的人)。馬克思不僅明確地指出了“資本的文明的一面”,而且突出地強調,對于現代性的任何一種積極揚棄,都以充分占有現代文明的成果為基本前提。因此,就歷史的肯定方面來說,“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10]。就歷史的否定方面來說,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或文明形態,包括現代—資本主義文明,都有其自身的歷史限度;而當世界歷史的進程抵達這一限度,從而展現出新文明形態的現實可能性時,舊的形態就必然要被新的、更高的形態所取代。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1]284。
當今中國的歷史性實踐之所以能在新的歷史方位上展現出它的世界歷史意義,是因為它堅持不懈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因為這一現代化進程在占有現代文明積極成果的同時,正在突破并超越現代性本身。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把握這樣一個發展進程,以便深入理解中國式現代化向著未來的歷史性籌劃(未來籌劃)。首先是我們的發展目標。當今中國歷史性實踐的戰略目標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目標作為未來籌劃清晰地表明:第一,它是高度現代化的,它要求充分而全面地實現現代化;第二,它是以社會主義為定向的,也就是說,是以揚棄現代性本身為定向的。正是這兩個方面的通同一體,意味著中國式現代化在特定的歷史轉折點上與人類文明新形態建立起本質的聯系。換句話說,在我們的戰略目標即未來籌劃上,中國式現代化在持續不斷向前推進的同時,正在為人類文明新形態開辟道路。
不僅從戰略目標上來講是如此,而且在我們當今的歷史性實踐中,與中國式現代化本質關聯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諸多理念和要素正在積極地生成,正在我們眼前到處呈現出來。舉例來說,“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只有在突破以資本為原則的現代性本身時,才真正成為可能;“共同富裕”的理念,只有在超越馬克思所謂“猶太精神”或“猶太本質”(唯利是圖)的現代性原則時,才具有真正的現實性。同樣,“新型大國關系”只有在突破并超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這一現代性國際關系的叢林法則時,才可能得到整全的理解和積極的實踐;“文明互鑒”也只有在現代性的權力所設置的支配—從屬關系被突破、被超越的地方,才可能真正發展起來并迎來它的繁花盛開。事實上,這樣的例證還可以舉出很多,“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亦是如此,“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理念更是如此。
而所有這些實踐要求和實踐主張,無非意味著通過揚棄現代性本身而開展出一種現實的可能性,一種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可能性。如果說,當今中國的歷史性實踐仍然必須更廣泛、更深入地推動其現代化進程,那么,這一進程同時也將更多地展現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可能性,并且更經常地將這種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
因此,在我們向著未來籌劃的歷史性實踐中,中國式現代化同時就意味著開啟人類文明新形態。“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11]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引領下開辟出來的,而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在其歷史性的展開過程中,將建設性地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正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創造和展開,使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局成為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最重要的積極變量,使得我們能夠在自身發展的基礎上,有效地回應人類社會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中國式現代化的深遠意義,不僅在于它實現了對西方現代化的歷史性超越,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而且還在于它積極地開啟著人類文明新形態,從而展現出人的全面發展的新境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式現代化不僅使得中華民族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能夠為人類作出更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