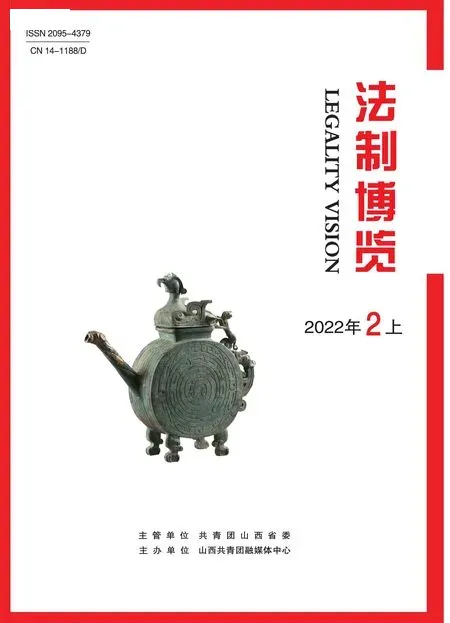感知智能階段人工智能創作物的可版權性及權利歸屬研究
徐浩程
沈陽工業大學,遼寧 沈陽 110870
一、人工智能及發展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縮寫為AI),1956年在美國達特茅斯學院召開的“人工智能夏季研討會”上由麥卡錫教授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這個概念,艾倫· 紐厄爾和赫伯特· 亞歷山大· 西蒙則展示了編寫的邏輯理論機器。[1]人工智能通常是指通過計算機模擬人腦產生思維過程和智能行為的技術。受制于芯片算力,人工智能技術很長一段時間一直處于初始的“計算智能”階段,即人工智能只能像人一樣記憶和計算,幫助人類快速儲存和處理海量的數據。近年來,芯片技術在納米制程上的突破,使算力實現了量級的跨越,人工智能跨入了第二階段,即“感知智能”階段。例如蘋果公司研發的神經網絡引擎,即是通過對人腦的基本單元神經元的建模和聯接,探索模擬人腦神經系統功能的模型,是一種具有學習、聯想、記憶和模式識別等智能信息處理功能的人工智能系統。該類型的人工智能技術區別于計算智能階段的人工智能技術,可以通過模擬人腦神經系統開發出一套“神經網絡”算法,模擬人腦的思維形成模式,再通過采集大量數據進行的學習和訓練,輸出最優數據特征。微軟設計的人工智能“微軟小冰”(以下簡稱“小冰”)創作的詩歌集《陽光濕了玻璃窗》即是“小冰”在對大量詩歌集的學習(即采集信息)及詩歌詞句的拓展(即人腦思維模式模擬)后,通過“神經網絡”算法創作出的。人工智能的第三階段是認知智能,即讓計算機開始像人類一樣能理解、思考與決策。該階段也是人工智能技術的最終形態——“強人工智能”。對人工智能發展過程的認識及現階段人工智能創作機制的了解便于展開對人工智能創作物能否認定為作品以及確定創作物權利的歸屬討論。
二、人工智能創作物可版權性研究
在人工智能處于計算智能階段時期,人工智能技術是人為控制數據輸入、變量控制及數據輸出的產物,人工智能技術不過像是筆、打印機一樣機械性的輔助工具,離不開人意志的左右,其創作物體現的是人的創作意圖。近年來,人工智能技術跨入感知智能階段顛覆了學界對人工智能技術的傳統認知,使得學界對人工智能創作物性質的認定逐漸發生變化。界定人工智能創作物的性質,避不開對人工智能創作邏輯的拆析,只有對創作過程的具象化才能對人工智能創作物可版權性加以認定。
(一)人工智能創作過程
在人工智能及發展部分,筆者介紹了感知智能階段人工智能模擬產生類人化思維過程和智能行為的技術架構,人工智能創作逐步出現了由“自動性”向“自發性”的轉變。
以人工智能“小冰”創作詩歌的產出邏輯為例。通過給定“小冰”一個圖像抑或一段視頻進行數據采集,從圖像中提取出若干表示對象和可能的情感的關鍵詞,從關鍵詞與人類詩歌的關聯(深度學習),擴展到相關的新的關鍵詞,接著以每個關鍵詞作為每行詩的核心,使用雙向語言模型逐步向左右拓展生成整句,這個過程模仿人類由景生情創造詩歌的過程。神經網絡算法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保證句子之間的流暢性、整體性、與圖片的匹配性以及符合人類表達習慣,其生成詩歌的形式、內容在開始時是無法預測的。這種收集數據—關鍵詞提取與過濾—深度學習—生成文字的模式的變量在于“提取與過濾”以及“深度學習”,而兩者又是相互促進的關系。兩變量的存在決定了人工智能生成物不是簡單的提取后套用算法生成固定內容的機器,而是一個模擬人觸景生情創作的過程,即便情景、算法相同,也可能創作出不同的作品。
(二)人工智能創作物的獨創性
“獨創性”作為作品必須具備的構成要件是各國法律對其著作權或者鄰接權進行保護的基礎,人工智能創作物獲得《著作權法》保護也需滿足“獨創性”的要求。
傳統法律制度下的“獨創性”源于人類的智力勞動,是與作者密切聯系的,即作者中心主義。實踐中,對作者內心的創意是否有獨創性的衡量標準是極難界定的,于是學者們逐漸將衡量標準從主觀衡量作者內心創造意圖的創造性轉向客觀衡量作品之間的差異化表達,即作品中心主義。這一轉變減弱了作品與作者之間的聯系,同時也賦予人工智能創作物享有著作權的法理基礎。根據作品中心主義對獨創性的要求,人工智能創作物只要在客觀上與其他作品形成差異化表達即可認定具有獨創性。
在人工智能技術運用神經網絡算法創作的過程中,其差異性主要來源于通過深度學習使各神經元連接之間權值不同導致的輸出結果不同。一個神經元活動可能增強其與第二個神經元連接的強度而削弱其與其他神經元連接的強度,這種神經元之間的連接強度是隨著深度學習訓練而不斷變化的。權值的變化引起人工智能創作過程中對自身數據提取與過濾傾向的變化、對提取過濾后數據的編輯輸出的變化。[2]
部分學者認為,人工智能創作過程離不開人類作品數據庫的基礎,其創作實質上是運用算法對現存作品模仿的過程,因此不具有獨創性。該類主張片面地立足計算智能階段,否定人工智能創作物的獨創性是錯誤的:其一,人類的創作同樣離不開對現有作品的學習、思考以及模仿,在這個過程中作者逐漸形成不同于以往的特有風格并以此創作出新的作品。風格化的形成過程也即神經網絡算法中的權值變化過程,此過程是一個存在大量差異性、隨機性和偶然性的變化過程,并不受人類意志的左右,同一算法同一數據庫輸出的內容并不是唯一的。因此內容的差異化表達使得人工智能創作物與人類創作物同樣具有創造性而非機械性模仿。其二,人工智能算法自動學習過程中能夠按照人類思維模式生成創作規律,在不借助人類作品數據庫的情況下,獨立完成符合人類表達習慣或審美的創作。
盡管人工智能創作物仍符合人類的語言、藝術風格,但其每一具體的創作物的表達,又是有別于現存任一作品的創作,結合作品中心主義,作品不必然地因缺少人的智力勞動的參與而否定其為法律認可的作品的性質。因此,應認定人工智能創作物具有獨創性,屬于版權法意義上的作品。
三、人工智能創作物的著作權歸屬
學界對于人工智能技術本體的著作權應歸屬于軟件設計者本人并無爭議,但在現行法律制度框架內對人工智能創作物產生的權利歸屬問題存在較大分歧。在感知智能階段,人工智能并不具備意思表示能力、行為能力,也當然地不能成為責任的主體,故此人工智能著作權的歸屬問題最終要通過尋找一個與人工智能創作活動相關的、具有法律主體資格的“人”來解決。[3]
(一)著作權歸屬于設計者
部分學者認為,人工智能創作的作品離不開人工智能技術設計者的智力勞動,正因為人工智能技術設計者對人工智能技術創造性的開發和改進,人工智能才能創作出作品。如果人工智能創作作品的著作權無法為設計者享有,那么設計者可能將人工智能技術作為商業秘密加以保護并將人工智能創作作品以自己的名義獲得著作權。也有學者主張人工智能創作作品可以視作人工智能技術的演繹作品,由作品(人工智能技術)的原作者享有演繹作品的著作權。
上述兩種主張均存在不足以支撐設計者作為人工智能創作作品的權利人的缺陷。第一,人工智能技術設計者付出獨創性腦力勞動的目的在于開發和改進人工智能技術,故法律賦予其對人工智能技術作品的著作權。對于人工智能創作作品,實際是由人工智能獨立運作的產出物,技術作者的創造性腦力勞動并沒有應用于人工智能的創作過程,因此不能將設計者視為人工智能創作作品著作權人。第二,演繹作品是在原作品的基礎上,附加自己創造性勞動而產生的作品,區分演繹作品與原作的界限在于演繹作品中保留原作內容的多少。而人工智能創作機制的偶然性和不確定性以及人工智能程序內嵌檢索模塊的重復率檢索保證了人工智能創作作品是有別于現存任何作品的新作品。此外,人工智能軟件的演繹作品,應是在原軟件核心代碼的基礎上派生而來,而人工智能軟件創作的作品中并沒有包含原軟件核心代碼的表達,兩者不可混作一談。
(二)著作權由使用者享有
主張著作權由使用者享有的學者認為人工智能創作作品是由使用者對人工智能軟件發出指令,由人工智能軟件通過算法生成有形的作品,發出指令行為帶有使用者的創造性思想,成為人工智能創作作品獨創性來源,因此其著作權應由使用者享有。此外,使用者對人工智能創作作品有著第一時間的控制力和傳播力,將著作權歸屬于使用者,使得使用者為人工智能軟件許可使用支付的費用得到補償,有利于鼓勵對人工智能技術使用以產出更多更豐富的作品,符合著作權法鼓勵創作和傳播的精神。
將著作權歸屬于使用者的理論貌似合理實則不然。其一,人工智能創作作品的獨創性來源于其技術本身的創作機制,并非像打字機一樣作為人類將創造性思想固定為有形作品的輔助工具。使用者為獲得人工智能創作作品對其發出的指令并非人工智能創作作品的獨創性的根本來源,因此不應將人工智能創作作品著作權歸屬于使用者。其二,對使用者為人工智能軟件支付的許可使用費用的補償,應在人工智能軟件所有者對其授權時約定,將使用過程中人工智能創作作品的著作財產權部分或全部轉讓與使用者享有,以此方可補償使用者支付的許可使用費用,同時鼓勵對人工智能技術的使用。
(三)著作權由所有者享有
主張著作權由所有者享有的學者認為,人工智能軟件的原始所有人是為人工智能軟件的開發和改進投入大量資金以及專業技術資源的主體,原始所有人期待獲得的利益不僅僅是取得人工智能軟件的著作權,其主要目的是追求人工智能創作作品所能帶來的利益。此外,在通過交易使人工智能軟件為買受人享有所有權的情況下,繼受所有人變相承擔了人工智能軟件開發過程中的資金投入及技術投入的對價,也理應繼受取得人工智能軟件及其創作作品的著作權。
人工智能創作作品實質是由人工智能自身創作出來的,無論是原始所有人還是繼受所有人,都不是人工智能創作作品的實際創作者,無法直接將著作權歸屬于所有者。
(四)虛擬法律人格理論下著作權歸屬
在現行法律規范體系內,人工智能創作作品的著作權無法直接歸屬于生物學意義上的人工智能軟件設計者、使用者或所有者,于是,美國學者蒂莫西· 巴特爾提出了通過賦予人工智能以虛擬法律人格,來解決著作權的歸屬問題的理論。根據作品中心主義的要求,人工智能創作作品可以視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通過賦予人工智能虛擬意義上的法律人格,使其成為人工智能創作作品著作權的主體。[4]但是,根據權利和義務對等原則,賦予人工智能虛擬法律人格仍不能解決主體承擔法律責任的問題,責任的承擔最終仍需確定一個生物學意義上的人。既然感知智能階段的人工智能并不具有意思表示能力、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那么我們可以通過為其尋找一個法律承認的、具備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的與人工智能軟件創作相關的主體,賦予其“代理人”的角色,由其代為行使權利或承擔責任。
對于代理權授予人工智能的設計者、使用者還是所有者享有,筆者認為授予所有者享有更為妥當。一方面,人工智能軟件的原始所有者一般是投資完成該人工智能軟件開發的主體,對人工智能軟件的開發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匯聚了大量的人類智力資源,人工智能軟件的原始所有人寄期望于通過軟件的開發獲取人工智能創造性的產出物,授予其代理權符合原始所有者在開發改進人工智能軟件之初追求人工智能軟件產出物利益的目的。另一方面,繼受所有人通過交易行為取得人工智能軟件的所有權的情況下,繼受所有人因支付了相應的對價,并且其目的通常與原始所有人相一致,因而也應繼受取得代理權。最后,對于使用者而言可以通過所有者的轉讓獲得人工智能創作物的著作財產權,亦可以通過購得人工智能軟件成為新的代理人。
四、結語
感知智能階段,人工智能創作作品的可版權性和著作權歸屬問題亟待尋求一種法律上的解決方式,按照作品中心主義承認人工智能創作物的獨創性進而認定其可以成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同時,在其著作權無法直接授予生物學意義上的人的情況下,通過賦予人工智能以虛擬法律人格的方式授予其著作權,并許可人工智能技術所有者代為行使人工智能創作作品著作權或承擔相應責任的方式,既能解決人工智能創作作品的著作權歸屬問題,同時代理人代為行使該類著作權也與著作權法鼓勵創作和傳播的價值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