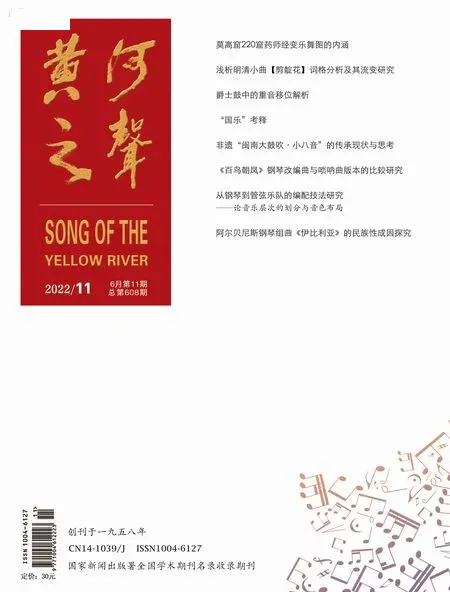論《火焰在燃燒》中音樂手法對戲劇性的構建
張建蕓
一、歌劇《游吟詩人》中的音樂手法
威爾第是19世紀中下葉歐洲最偉大的歌劇創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使意大利的歌劇藝術散發出了閃耀的光芒。本文所闡述的歌劇《游吟詩人》,被普遍認為是威爾第歌劇作品中情節最為復雜,情感上的設計最具戲劇性的一部,威爾第在這部歌劇中,通過運用不同的音樂手法,使得音樂與故事的戲劇性完美融合。
在歌劇《游吟詩人》中,威爾第采用了一種較為獨特的音樂形式,即加入帶有真實主義的民族旋律,對劇中每一個人物的形象特征進行了完美的刻畫。第一幕“決斗”。每到夜半的時候,伯爵總是被一個喜歡唱歌的游吟詩人深深地吸引,在守衛們感到困惑時,費南多就演唱了《黑暗與恐怖》,來給他們講述伯爵的往事,這首男低音詠嘆調作為歌劇開場的第一個唱段,它用瑪祖卡音調和大量的低音,渲染了一種陰森、緊張的氣氛,將聽眾帶到劇情之中,毫不枯燥。第二景,萊奧諾拉向仆人訴說自己的愛情故事,演唱了《寂靜的夜》,這也是女主角第一次表露自己內心時的重要唱段,為了突出萊奧諾拉的愛慕之情,這首女高音的詠嘆調全曲為降a小調,8/6拍,行板,多用頓音記號和無限延音記號,來描繪她在夜晚傾聽琴聲時的神情,在歌曲的高潮部分速度轉為快板,將萊奧諾拉內心濃烈的愛意宣泄了出來,為男主角曼里科的登場進行鋪墊。
第二幕“吉普賽人”。開場的《鐵砧大合唱》鏗鏘響亮,烘托了整個歌劇舞臺的熱烈氣氛,曼里科在這場激烈決斗中不幸受到了重傷,在小屋里阿蘇切娜把她的親生父母經歷了一場大屠殺被大火燒死的真實故事告知了兒子曼里科,并向他說明自己不是他的親生母親。這首合唱是帶有再現的復三部曲式,從e小調轉到G大調上,音樂技巧非常豐富,多次運用前倚音、三連音和跳音,音樂速度為快板,整首歌曲風格活潑且具有跳躍性,這與第一幕的音樂風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緊接著就是女二號阿蘇切娜的女中音詠嘆調《火焰在燃燒》,這也是第二幕中最為突出的一個唱段,這首詠嘆調直接將劇情推向了高潮,其復二部的音樂結構與《黑暗與恐怖》有異曲同工之效,同樣是全曲采用小調曲式,從f到pp的強弱變化與長達十三拍的高音抖動設計,將阿蘇切娜內心洶涌的復仇之情表達得淋漓盡致,真正做到了通過音樂手法將歌曲與歌劇的戲劇性完美融合,不斷推動劇情的發展。
二、《火焰在燃燒》中音樂技法對戲劇性的構建
(一)《火焰在燃燒》中阿蘇切娜的戲劇性分析
威爾第通過對主旋律的編創、對伴奏的編創和演唱技法的設計,成功地塑造了阿蘇切娜這一重要的傳奇女性人物,運用她優美的女中音寬厚且濃郁的旋律聲調和音色,把她的種種愛恨恩怨表現得淋漓盡致。使觀眾既希望阿蘇切娜為了母親而讓曼里科幫她復仇,又特別地希望阿蘇切娜能夠給予曼里科母愛和關懷,這種矛盾的情感從阿蘇切娜與曼里科的角色內心出發,形象地把人性的復雜刻畫了出來,而威爾第在這首詠嘆調中所運用的民族歌劇創作手法也一直被認為是貫穿于他歌劇作品的一個重要線索。
(二)《火焰在燃燒》作曲技法的戲劇性構建
在不同的段幕,不同的人物角色,不同的情節背景中,為了使情節更加流暢,使角色和唱段能夠很好地結合,威爾第以其極具戲劇性與極富戲劇情感的主題音樂表現力,根據角色的人物個性來編創歌曲,《火焰在燃燒》里的阿蘇切娜這一角色的定位就是一個出色的女中音,所以這首歌曲的音域與音樂符號都遵循了這一特點,用渾厚的嗓音成功地塑造了阿蘇切娜這一獨特的女性形象。
《火焰在燃燒》這首詠嘆調的結構為復二部曲式,全曲定為e小調,節拍為3/8拍,速度采用小快板,其中第一部分為A-B-A1,是一個再現三段體,第二部分與第一部分相似,從這些歌曲結構的創作上就可以大致了解這首作品的風格類型:首先調性定為小調,就給整首歌曲營造了一種較為陰暗的氛圍,從而突出角色人物是以復仇和極大地怨恨為主要基調的。接著,作者采用三拍子,使歌曲在旋律節奏上給聽眾一種連續不斷,此起彼伏的感覺,就仿佛是阿蘇切娜的內心活動是生生不息永遠沒有盡頭的,而強弱弱的三拍子特有節拍風格也是這首歌曲在刻畫角色人物戲劇性的方面更上一層樓,將人引入到歌劇情節當中。其次,小快板的節奏定速,更是使這首詠嘆調作品如虎添翼,稍快的速度就像在表現阿蘇切娜內心的熊熊烈火,不可能是平靜的,更不可能是舒緩的,將一股接一股的復仇的恨意不斷地傳給聽眾。第一部分1-55小節:A第1-18小節,B第19-34小節,A1第35-55小節,運用了很規整的圓柱式伴奏旋律和弦形框架,從主旋律來看,旋律上是有一定的主題性的,作者通過對這一主題旋律的反復來確定第一部分的情感,是在一個較為激昂的情感之下進行的,而且“tr”這一音樂技巧反復多次出現,用在小節重音上,更加吸引聽眾的注意力。還有連音線的恰到好處的運用,也是歌曲在紛亂的節奏之下能夠保持連貫的關鍵。第二部分則是在歌詞與演唱情感方面與第一部分進行對比,來達到更深一層次的情感表達與增強劇情的戲劇性。整首歌曲就是在這樣的旋律創作的濃烈且激情的氛圍中進行的。
隨著兩小節的三拍子柱式和弦伴奏,阿蘇切娜在開始演唱時,以較強的爆發力開場并隨著三拍子的節奏不斷訴說著內心的仇恨,每一個小節的第一拍重拍都會出現一個重音記號,威爾第通過對音樂的強弱控制和對節奏的精密把握,將阿蘇切娜心中的怨念仇恨和無數次想要復仇的情緒充分地表達了出來。阿蘇切娜的第一句歌詞是整首詠嘆調的靈魂,所以,在演唱中就需要充分地掌握力度的變化,通過從f到pp的明顯強弱對比,把那些去看熱鬧的人們和等待被執行死刑的犯人之間強烈的對比氣氛給烘托了出來。如下圖所示。
在十三拍的長音中,將b1這個音加以顫音技巧,然后以一個較快的節奏連續爬音,達到了這首詠嘆調的最高音g2,將聽眾帶入整個音樂的強烈情感之中,并將歌劇的劇情發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休止符的運用巧奪天工,這也正是描繪阿蘇切娜這一人物形象所要用到的最具強烈感染力的音樂創作手法,即音高與節奏與伴奏的三方配合,這才是阿蘇切娜內心的真實聲音,在悲傷和無助的復雜情感交融之中,阿蘇切娜才能得到真正的釋放,這個在十三個拍子的顫音之后爆發的最高音,就像是歇斯底里地尖叫。如下圖所示。
威爾第對這首詠嘆調運用的音樂創作手法充分地表現了阿蘇切娜這一充滿戲劇性人物的特點,他在需要演員運用歌詞演唱的主旋律中將變化音#c2和#d2與柱式伴奏中的#c1和#d1巧妙地結合,用伴奏來引導聽眾,這樣也使得高音不會那么突兀,反而是恰到好處的作為情感的爆發點,在節奏編創中多次將八分音符與休止符聯系起來,或將四分符點與連音線進行結合,使歌曲更加富有戲劇性,更加引人入勝。
(三)歌劇《游吟詩人》演唱技巧的戲劇性構建
歌劇《游吟詩人》中的唱段大都需要演唱者具有較為扎實的演唱功底,不僅如此,在演唱不同的作品之前,還要加強對這部作品人物的認識和理解,也同樣是因為這類歌劇中的角色對表演的藝術要求和技巧要求較高,在對氣息、共鳴、發聲、起音三個方面的表現能力與聲音技術上的要求也很高。首先,氣息對歌唱是十分重要的。在我們進行音樂演繹時,要提升對聲音的協調控制,從而表現出人物角色的戲劇性情感。這就要求每位演唱者在歌唱時首先做到吐字連貫、清晰,演唱者在歌唱時需要留出足夠的空間和氣息來進行支撐,使頭腔、喉嚨、胸腔形成一條管子,將強大的氣息作為支撐,比如《火焰在燃燒》中的結尾幾小節,就是以一段長達13拍的三個音階旋律作為結尾主題,這是一個精彩的時刻和高潮,是阿蘇切娜把自己整個內心緊緊壓抑的那股強烈復仇之心與怒火迅速性地在歌聲中釋放出來的一個極富戲劇性的時刻,這里運用顫音這一音樂歌唱技巧,需要歌唱者用渾厚的嗓音和強大的氣息來完美呈現,并充分突出阿蘇切娜內心的悲憤與深深的怨恨,將阿蘇切娜親眼看到她的媽媽被巨大的火焰重重淹沒時的絕望和心里充盈著復仇的那種感覺表達出來,將整首歌曲中最具戲劇性的感情表現出來。
其次,只要是具有戲劇性的音樂作品,就需要我們具備華麗、豐富的歌唱技巧和強烈的情緒,這也就需要我們在進行演唱的關鍵時刻能夠協調好且大膽地運用我們的頭部與胸腔的聲音共鳴、頭部腔體的聲音共鳴和口腔的聲音共鳴。《火焰在燃燒》這首作品在音樂演唱技巧方面重要性尤為突出。比如,在我們需要表現一個具有大量重音與爆發音的歌曲作品時,需要用爆發力或較強力度來演唱,使作品的戲劇性得到充分的展現,要做到很好的凸顯人物角色的真實內心情感與性格特點,才能充分地將歌曲的戲劇性表現出來。此外,在演繹《火焰在燃燒》這首詠嘆調時,需要在充分運用演唱技巧和音樂情感的基礎之上,加強對該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歌詞和句子特點等方面的研究與分析,結合自己所學的知識進行理解,二度創作。
對歌劇作品的表演必須是在對劇中一個人物的心理、情緒等各方面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后才能進行的,如了解角色內心戲劇性的矛盾,這樣在演唱時才能從力度、速率、節奏的變化和歌曲的結構、音調和風格特點上有更好的演繹。威爾第通過對人物角色的唱段進行作曲技法和演唱技巧的恰當創作,來塑造歌劇的人物形象。威爾第在這部歌劇中使用了民族音樂創作方法,來促使角色和歌曲完美融合并表現出強烈的戲劇性。《火焰在燃燒》可以說是獨樹一幟的,為了使歌曲能夠準確地描述人物形象和充分地表現出人物內心戲劇性的矛盾,就必須要求歌曲具備華麗的旋律與獨特的音樂語言,在作曲和演唱上一定要表現出較強的爆發性。《火焰在燃燒》中濃厚的音調、滑動抖音帶來的驚人效果,以及六度、八度旋律上下行的跳進、三連音所烘托的氣氛,都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音樂創作手法。它的現場演唱也一定是要充滿吶喊感的,就是說,聲音必須盡可能地保持柔韌,聚焦,和連貫,要用璀璨、豐滿、具有高度藝術質感的聲音,它在重音、高音的具體演唱時都需要聲音的爆發力,來抒發人物內心的情感,表現這部經典歌劇中強烈的戲劇性。
三、音樂表現手法對歌劇戲劇性的構建
音樂要有“情”,即感情。所以故事中的悲劇色彩充分地釋放了人物角色唱段的戲劇性。威爾第為每個角色“定制”的詠嘆調都被認為是最完美的,不會讓任何人覺得唱段拖了角色的后腿,或使角色變得呆板乏味,隨著歌劇劇情的改變與發展而創作出來的任何旋律和特定設計的音樂符號都是那么的恰當,突顯了每一個人物角色內心的戲劇性矛盾:痛苦與掙扎、愛情與美好。
合唱、齊唱和男女對唱的這種綜合音樂演唱形式,在《游吟詩人》這部歌劇作品中都進行了展現,它們可以更好地凸顯主要人物角色,這使得歌劇作品中的每一個重要人物都深深地刻在了觀眾的頭腦之中。對于一個角色的形象塑造不僅要注重對角色本身形象個性的描寫,同時需要通過特定的唱段來加深觀眾的印象,在演唱作品時對動作、表情等諸多因素上都給予一些新的注釋,這樣不僅能夠很好地幫助我們來表現角色的整體形象,又能夠很好地幫助我們理解音樂手法對人物戲劇性進行的構建。在威爾第的眾多歌劇作品里,在不同人物角色的唱段創作上都具有極高的學習價值,加上他那種極富戲劇性的音樂創作風格,使他超越了許多著名的歌劇創作家值得我們學習。
結 語
威爾第歌劇《游吟詩人》的主線劇情通過對音樂的旋律、技巧、伴奏的創作,來表現歌劇劇情的復雜多變,主要人物的唱段都有著極強的沖突與矛盾,從而形成鮮明的對比,突出戲劇性。其所創作的音樂演唱技法也蘊藏著極高的聲樂技能,需要我們深入地分析音樂曲式結構等特點,加強對作品中人物性格與故事情節等因素的了解,同時還需要結合具體的音樂作品來進行演唱,通過對氣息的控制、運用歌唱的技巧,來表達藝術情緒。也唯有如此,才能將音樂中的人物表現的有血之肉,更準確地詮釋這部經典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