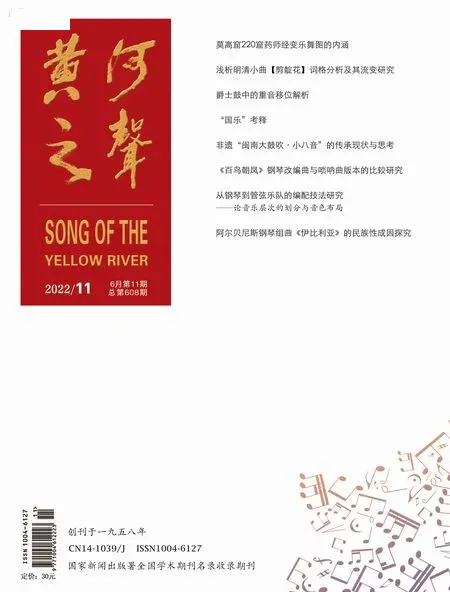探析歌曲《絨花》創作風格與演唱特點
趙若普 / 李春鵬
《絨花》具有別具一格的藝術特色和豐富的情感表達,雖然這首歌曲在音樂結構上面比較簡單,音域跨度小,但是要想演唱好這首歌曲,還需要深入的分析其情感表達,創作風格以及在演唱時需要注意的細節,對整首歌有全面的了解才能更好地演繹。
一、作曲家及創背景概述
(一)作曲家介紹
歌曲《絨花》是由劉國富、田農作詞,王酩作曲。王酩于1934年出生于上海,受到環境的影響,他從小便會唱一些京劇的唱段,之后在青年文工團所開辦的文藝學習班中學習樂理、作曲、指揮等[1],對于音樂的熱愛和在知識儲備不斷豐富的情況下,他逐漸開始走上音樂創作的道路。1950年,他創作了自己的第一部音樂作品《南下參軍歌》,這首歌曲的成功更加堅定了他走藝術道路的信念。后來考入上海音樂學院跟隨丁善德學習,創作風格、創作理念受到了丁善德的影響,喜愛民間音樂,在音樂作品中融入許多民間音樂元素,他還大量觀摩昆劇、豫劇等各種形式的音樂,巧妙地將戲曲等元素運用到音樂創作中。王酩還擅長借鑒西方音樂作品的風格、體裁,進行創新創作。
(二)歌曲《絨花》的創作背景
歌曲《絨花》是為電影《小花》創作的音樂配樂,為了能創作出貼合電影主題的音樂,作曲家王酩跟隨攝制組一同體驗生活,最終創作出了《絨花》這首歌曲。電影《小花》講述了三兄妹之間血濃于水的親情,歌頌了勇于為共產主義獻身的精神。作為電影的插曲,《絨花》以優美的旋律、飽含情感地歌頌了主人公堅強勇敢的精神[2]。
二、歌曲絨花的創作風格
(一)歌詞特點分析
從兩個方面來分析歌詞的特點,一是在歌詞的創作中使用了多樣的表現手法,一方面托物言志,所托之物便是絨花樹。創作的靈感來源于電影《小花》故事原型《桐柏英雄》的故事發生地,絨花樹是當地常見的樹種,樹形優美,粉紅色的花絲聚成球狀,與電影中出現鮮血的場景相稱,加之絨花是一種耐寒、耐干旱的植物,在惡劣的環境下也能生長,與電影中革命戰士堅韌不拔、奮勇向前的精神相呼應。另一方面使用了許多修辭手法,如“比喻”的修辭手法,將美好的青春比喻成美麗的花朵,“擬人”的修辭手法將絨花樹比喻為主人公何翠姑。多種創作手法的使用樹立了更加鮮明的音樂形象,使得歌詞表達的情感更加真實細膩,豐富了作品的內涵,讓人在生動的意境中產生情感共鳴。二是歌詞的情感表達,通過塑造絨花這一文學意象,歌頌了主人公勇敢、舍己為人的精神,之后使用了一長段的“啊”詮釋情感,給聽眾留有想象的空間。歌曲在歌詞的使用上也十分的巧妙,比如“芳華”一詞,其又可以理解為“芳花”,美麗的花朵,美好的青春都在這個詞中體現,歌頌了將青春獻給革命的先輩,與何翠姑跪地為隊友抬擔架的情景相呼應。“一路芬芳滿山崖”花朵漫山遍野,花香撲鼻,表現了革命戰士的精神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人。
(二)曲式結構分析
從主題和副歌兩部分分析歌曲《絨花》的曲式結構。一是主題部分,主題部分又可以分為兩個大樂句,分別是第一大樂句(第10-18小節)和第二大樂句(第19-28小節),在第一大樂句中使用了級進的旋律,在起音和尾部都使用了G宮音,第二個大樂句中19-23小節重復了第一部分的10-15小節,有所不同的是在第二大樂句中第15和23小節的尾音,第15小節的尾音落在宮音,第23小節的尾音落在商音[3]。總體來說,主題部分較為平緩,上下句的節奏相對統一,適時的使用切分音又在舒緩的旋律中增添了律動感,呈現出一詠三嘆的音樂效果。西洋大調和中國民族五聲調式的巧妙結合,使得歌曲展現了民族特點。二是副歌部分,副歌部分的民族特點更加鮮明,使用了包含16個小節的非方整的對比復樂段,也分為第一大樂句(第28-36小節)和第二大樂句(第37-46小節),第一大樂句共8小節,比較特別的是第28小節,由于第27小節的尾音使得第28小節是一個弱起節奏,第二大樂句中,第37-40小節為29-32小節的重復,這兩部分都沒有歌詞,是指在用“啊”烘托氛圍,抒發情感。在副歌部分多處使用三連音,將音樂逐步推向高潮。歌曲的曲式結構的設計和故事情節相呼應,更加烘托了電影的氛圍,使得在聽歌時也更有電影的畫面感。
(三)旋律特點分析
總的來說,歌曲《絨花》的旋律特點非常有敘述性,給人以娓娓道來的感覺,講述了一個故事,并且極具民族特點,巧妙地結合了戲曲的元素。在旋律的創作上,作曲者王酩注重“點”和“線”的結合[4],“點”指的是緊湊密集的節奏,“線”指的是旋律的流暢感、延展感。在流暢的旋律中加入了具有節奏性的切分音,增強了整首歌曲的音樂表現力。具體來說,歌曲《絨花》調式的使用,采用了民族的七聲音樂調式,旋律上運用了四種方式,分別是級進式、跳進式、模進式和環繞式,這幾種方式根據歌詞所要表達的情感靈活的出現,使得歌曲更加悅耳。就曲式結構來說,第10-27小節這部分的旋律較為平緩,似乎在講述一個故事,在第27-36小節,這部分律動性較強,三連音的使用使得音樂不斷起伏,36小節之后重復了27-36小節的旋律,進一步的推進了情感,使得情感得到了極大的釋放。
三、歌曲《絨花》的演唱特點分析
(一)在演唱中對于氣息的把握
聲樂作品就和我們欣賞的一幅畫作一樣,作品體現在畫作中就是各種圖形或者形狀,演繹人員的處理就是作畫者手中的各調色板一樣,只有將顏色進行組合搭配才能創作出讓人滿意的作品。而在聲樂演唱中,氣息是最基礎的也是最根本的,也是能夠體現演唱者演唱功底的存在。良好的氣息運用至關重要,是決定演繹作品質量的關鍵與基石。從前面對《絨花》的旋律分析可以知道,這首作品的旋律是舒緩的、是具備較強的流暢感、流動性的。整首歌曲的每一句歌詞與其他歌曲相比都是比較長的,作者在作曲時運用了大量的、較大的拉伸度的旋律線條以及錯綜交錯、張弛有度的節奏,讓整個作品具有更強的觀賞性,這對演唱者的氣息運用也提出了較大的要求。
演唱者在演唱準備的時候可以采用胸腔與腹腔進行聯合和呼吸的方式進行,在進行呼氣的時候應當讓自己的橫膈膜處于擴張的狀態,盡量將其打開;用近似聞花香的狀態去演繹歌曲,當準備完進行演唱的時候需要在這方面進行特別的注意,收尾音的時候一定要控制得既干凈又利索,將尾音的干脆感表現出來,在唱到作品的長音的時候,一定要保持長音的穩定性與持續性,讓自己的氣息足以支持對長音的演唱,讓演唱可以持續進行下去,不能讓自己的氣息一次性用完[5]。特別是在演唱跳音的時候,演唱者需要借助自己對氣息的控制實現高音的演繹,讓身體本身對自己的氣息強弱、長短進行控制,避免聲帶上產生聲音的落點與支撐點。一旦聲音的支撐點是在聲帶上出現的,就會產生聲帶的擁擠與卡頓,讓聲音聽起來缺乏舒緩感與從容感。在歌曲的高潮部分,應當讓共鳴保持在頭腔部位,讓共鳴的流暢轉化和氣息的變化實現情緒的表達。
演唱者還應當注意到歌曲本身是很抒情的、婉轉優美的,因此在演唱時應當將歌曲的穩定性、連貫性的特點最大限度地表現出來,用藝術歌曲的演唱標準對自己進行衡量,在進行呼氣與換氣的時候應當是自然進行的,避免出現大幅度的換氣動作,讓歌曲的已經可以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讓聽眾沉浸其中盡情地感受與體會,跟著演唱者感情的變化而變化。
(二)在演唱中對咬字的處理
《絨花》的歌詞承載著藝術美的特征,作詞者具備深厚的文學功底讓作品具有了獨特的文學美感與特點。在演唱這一類優秀文化作品的時候,演唱者對行腔與咬字的處理是非常重要的演唱技巧之一,只有讓自己在演唱時的吐字保持清晰才可以將作者的感情完整地演繹出來,才可以將作品的意境美如實地呈現在大家面前,觀眾才可以更好地理解作者想要表達的意圖與目的,進而通過自己的共情能力感受身受、引起共鳴。與國外的咬字不同,我國具有自己獨特的咬字行腔經驗與方法。
演唱者在演唱《絨花》這一作品有時是使用美聲唱法的演唱者在進行演唱的時候,由于長時間使用美聲唱法進行歌曲的演繹,往往會將聲母的腔調不自覺地忽略掉,讓自己的聲音在喉嚨稍微靠后的位置上進行共鳴。如果使用這種演唱方法演唱《絨花》,會導致演唱者在演唱時的發音與吐字出現模糊的現象,甚至出現有聲無字的情況。如果是使用民族唱法進行演唱,則會因為對于咬字的過分重視而出現歸韻的失衡。為了避免這兩種情況的出現,演唱者必須對咬字有明確清晰的把握,讓自己清晰的咬字與對氣息的運用可以對歸韻起到較強的支撐作用,保持歸韻的平衡感與節奏感符合演唱的要求。這樣才可以讓聽眾可以清晰地聽到每一句歌詞、歌詞的每一個字,才能更好地感受其中的美感與情感,還可以幫助演唱者保持良好的聲音演唱狀態,以便自己可以更自如地對聲音的強弱進行處理。
在演唱的時候需要將歌詞的字頭部分清晰地進行咬字,要做到咬字的干脆、清晰又不失準確性,同時保持咬字的有力感,還應當注意咬字的著力點的變化,并根據聲母的不同進行著力點的調整;對于歌詞的韻母部分的發音也是同樣的道理,演唱者需要具備根據韻母變化及時調節自己口腔形狀的能力與應變能力,讓自己的發音可以對喉嚨位置產生的共鳴與氣息的強弱進行強有力的支撐[6]。比如《絨花》歌詞中的會出現聲母“sh”,韻母為“eng”,在演唱的時候需要讓自己的口腔開度較小,在口腔的前面進行用力,讓自己的氣息從縫隙中自然地擠出,然后稍微打開口腔,讓清晰的咬字與優美的發聲順暢地演繹出來。
(三)對作曲家的創作進行充分挖掘
作曲家在對某一首音樂作品進行創作時會將自己的情感寄托在曲譜上面,演唱者在演唱時根據這一規律進行演創作與演繹,這樣可以確保將作者想過表達的情緒更好地展現出來。《絨花》的曲作者雖然沒有在曲譜上進行過多符號的使用與標記,但作者在節奏上運用、旋律走向上的規律、對于曲式的排面布局以及寫作手法上都可以給演唱者一定的啟發與提示。在演唱樂曲的B樂段的時候可以發現,作者在這一樂段的每一個樂句的開端都進行了弱起小節的設計,在唱到整個歌曲的最高音的時候,演唱者往往會因為過多強調這一部分在高音上的變化而將開端弱起小節的連音唱出的聲音特別強,或者是在唱到此曲最高潮的時候,由于過于重視對于情緒的把握而將本來該使用重音的地方唱得更加弱,無法給觀眾傳遞出作者想要表達的意境與感情的起伏變化。在演唱時需要根據每個樂句開端弱起小節的變化規律進行把握,在唱到節奏上的重音的時候將自己的聲音強有力地表現出來,達到應有的效果。
在音色的表現方面,這首極具柔美的歌曲一方面表達了人物頂天立地、不屈不撓、錚錚鐵骨,又表現了人物的無限的柔情與優美。演唱者在演唱時需要將音色的虛與實的對比鮮明地表現出來,將歌曲的柔美與明亮干凈的特質展示出來,即使使用一種音色演唱整首歌曲,但也要有動態的變動調整。
結 語
距離《絨花》第一次出現在大眾面前已經有三四十年的時間,但今天依然受到大家的歡迎,成為傳唱度非常廣的歌曲之一,是經典歌曲的優秀代表。整首歌曲既具備了豐富的藝術性特征,又具備完整的文學特點,是藝術感與時代感完美結合的典范。《絨花》的曲調簡單卻不失柔美性,優美動聽,簡單的曲譜上蘊藏著曲作者的創作巧思在里面,作曲者還投入了大量的感情。演唱者通過對歌曲演唱時氣息的運用、吐字的特點以及曲作者在曲譜上面加入的情感與希冀之后,再加上自己的創作一定能夠將歌曲完美地呈現在聽眾面前,讓大家大飽耳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