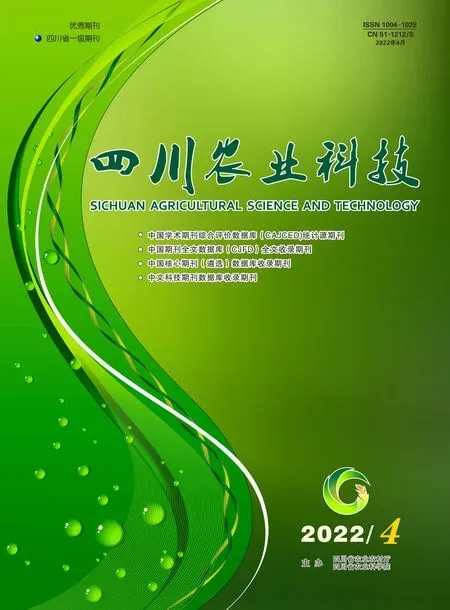麓湖生態(tài)城社區(qū)互動性景觀設計研究
常梓渝,李光躍
(四川旅游學院藝術(shù)學院,成都 610100)
1 引言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人們對于生活環(huán)境質(zhì)量要求也越來越高,城市公共空間的構(gòu)建也越來越受到各大城市的重視。傳統(tǒng)居住區(qū)設計的公共空間營造的短暫視覺效果在智慧景觀和科技浪潮中愈顯單薄乏味,許多公共空間的設計在越來越漂亮的同時逐漸失去內(nèi)核,變得索然無味,趨同化嚴重。而公共空間在這種信息發(fā)展迅速,多元化的時代更需要承載更多的功能,例如科普教育、地域文化的展示等。基于互動式的多感官體驗景觀能很好地順應這種發(fā)展,將被動式欣賞轉(zhuǎn)變?yōu)槟軇邮絽⑴c,有利于促進人與環(huán)境的良性認知。因此,文章以成都麓湖生態(tài)城社區(qū)互動性景觀為例,研究并理解公共空間互動性景觀的營造方法,有助于城市公共空間景觀的營造,進而實現(xiàn)精神面貌再塑造的根本目的。
2 互動性景觀相關(guān)概念及發(fā)展現(xiàn)狀
2.1 相關(guān)概念
2.1.1 互動性景觀 “互動”在漢語詞匯中是指彼此聯(lián)系,相互作用。在現(xiàn)代景觀設計中,設計的主體往往就是人與環(huán)境。“互動性景觀”即更注重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相互作用的景觀。人對景觀的文化、內(nèi)涵等產(chǎn)生共鳴,而景觀又對人產(chǎn)生吸引,這樣就形成了人與景的相互作用。其設計手法也是多樣的,廣泛來說,除了對環(huán)境、設施、意境的設計外,可以實現(xiàn)人與景的相互作用,滿足人的物質(zhì)需求和引起人精神共鳴的景觀都可以被認為是互動性景觀。
2.2.2 社區(qū)公園 社區(qū)公園是城市四大類公園之一,主要直接服務于周邊居民日常的休閑及社交活動,包括居住區(qū)公園和小游園等,具備多元功能、共享空間的特點。2017年住建部將社區(qū)公園從其他類別中單獨劃分為一項公園類別,2020年起更是強調(diào)了改善人居環(huán)境、提升人文品質(zhì),由此可見,社區(qū)公園的建設方興未艾,需求甚廣。
2.2 發(fā)展現(xiàn)狀
2.2.1 趨同化嚴重,缺少地域性文化 我國房地產(chǎn)發(fā)展迅速,許多居住空間空間設計千篇一律甚至采用快捷低成本的“拿來主義”,傳統(tǒng)的批量流程化的設計生產(chǎn)導致有的景觀隨處可見,識別性和地域特色大大下降,缺乏個性化,許多設施都是同一個廠家生產(chǎn)的。其本質(zhì)原因是在設計時欠缺對場地條件和文化關(guān)系的考慮,設計的景觀與當?shù)匚幕兴鋈耄O計好后買來安裝草草了事,設施與場地條件可謂是方枘圓鑿,人與景觀之間自然難以共情。
2.2.2 以人為本思想的式微 位于法國巴黎的喬治·蓬皮杜國家藝術(shù)文化中心是優(yōu)秀的建筑及景觀空間結(jié)合的代表,它的設計師R.羅杰斯認為設計應使人在室內(nèi)和室外都能自由自在地活動。我國城市化發(fā)展迅速,許多公共空間著重于交互式裝置的設計,而僅憑幾個智能裝置所體現(xiàn)出的場所精神和人文關(guān)懷是有限的,當今景觀設計不僅僅關(guān)注于基本功能的設計,更應該考慮不同人群在不同場景下的行為特征和在智能化數(shù)字化背景下居民生活方式的轉(zhuǎn)變。
2.2.3 情感空間的缺失 在快節(jié)奏的生活中,填鴨式住宅無疑讓現(xiàn)代人更缺乏情感釋放的空間。如何合理利用空間,增強人與人之間的聯(lián)系,讓人們進行情感表達,正是現(xiàn)代景觀設計應該思考的方向。社會心理學表明,人有聚集效應,而人們良性的交流又對聚集產(chǎn)生了正反饋,增加了場所的凝聚力和吸引力。讓空間引導人自發(fā)地交流互動,也正是互動性景觀研究的意義所在。
3 成都市麓湖生態(tài)城公園互動性景觀設計分析
麓湖生態(tài)城位于成都市天府新區(qū)天府大道兩側(cè),是一座以水為生態(tài)基底,綜合現(xiàn)代制造業(yè),高端服務業(yè),休閑娛樂產(chǎn)業(yè)和居住區(qū)為一體的國際新城區(qū)。總占地面積約為1100hm2,建設用地573hm2,其中景觀用地近333hm2[1]。美國心理學家唐納德·諾曼的設計心理學將人的認知水平分為感官互動,行為互動,情感互動,這三者的關(guān)系是層層遞進的,國外互動式景觀的設計方法也是由此發(fā)展而來,國內(nèi)互動式景觀的打造在前兩個層面已經(jīng)趨于成熟,但在情感互動方面仍有待提高[2]。麓湖生態(tài)城互動性景觀依據(jù)該理論的具體營造方法總結(jié)如下。
3.1 感官的互動
感官互動是最初級的體驗互動,互動式景觀同時應該充分考慮人的心理和生理需求,滿足多種人群的多種需要。可以通過不同的材質(zhì),顏色,大小等進行變化組合,形成內(nèi)涵統(tǒng)一而形態(tài)風格各異的系列景觀,多重感官的沖擊能使人對場景的記憶更加深刻。
3.1.1 多重感官體驗的設計 人對外界認知的第一直覺來自感官體驗,麓湖生態(tài)城中對于多感官的景觀設計也是匠心獨運。例如云朵樂園的目標群體是兒童,有趣的多感官體驗設計很好地調(diào)動了小朋友的參與性。例如坐上去就有音樂響起的秋千,多面鏡一樣的冰川峽谷,在探尋倒影鏡像的同時能聽到水滴在山谷中的回響都是運用了聲景。外形如云且彈性十足的跳跳云又帶給小朋友柔軟的觸感。冰凌拱橋則會有柔和的燈光隨著人的遠近而明滅,帶給人不同的視覺感受。這些互動性景觀的設計一方面憑借多元的外觀設計增添了景觀的敘事性和層次感,另一方面又從聽覺、視覺、觸覺等多方面的感官豐富了人對空間的體驗感。
3.1.2 人性化景觀小品的設計 麓湖生態(tài)城的小品基于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設計理念,在滿足基本形態(tài)設計的基礎上加入了文化和互動性。例如云朵樂園的互動噴泉,阿基米德取水器等都采用人參與使用才會出現(xiàn)豐富的景觀變化的設計。這些互動性設施不僅在保證安全的基礎上激發(fā)了人的探索心,而且科技環(huán)保,不需要人工管理。
3.2 行為的互動
優(yōu)秀的互動性景觀不僅要提升人對景觀的感覺,應更進一步增強人的主觀能動性,讓人愿意參與到設計的場景中,提升景觀的使用頻率。這就要求景觀設計有足夠的預見性,從而調(diào)動人的參與積極性。
3.2.1 人與動植物的互動 植物是景觀要素之一,展示植物的自然特性和本身特征能充分展現(xiàn)不同季節(jié)的特色,能讓人感受到時間和環(huán)境空間的變化。植物在麓湖不僅僅是一種裝飾元素,更多的是作為一種空間情感傳達的媒介。麓湖生態(tài)城的整體環(huán)境接近于一個濕地生態(tài)區(qū),很多景觀都真正做到了人與自然的融入。以紅石公園為例,其中竹林掩映,道旁種植有繡球、香樟、紅楓、雞爪槭等,林下空間的微地形搭配多彩的花境。水邊栽植水杉,蘆葦,兒童樂園中的陽光大草坪,社區(qū)蔬菜圃等都有科普教育的作用。園內(nèi)有許多木棧道與小徑,汀步相連,使人行之富有自然野趣,游覽途中自然會融入其中。動物也是景觀構(gòu)成的自然要素之一,麓客島的小動物農(nóng)場的設計就很有特色,其中的羊駝,荷蘭豬,可達鴨等小動物深受大家的喜愛。農(nóng)場中的網(wǎng)紅草垛區(qū)、網(wǎng)紅紗幔露臺、農(nóng)場雜貨鋪等成為網(wǎng)紅拍照打卡地,結(jié)合當下的網(wǎng)紅經(jīng)濟,吸引了更多的人參與到景觀互動中來。
3.2.2 人與人的互動 人與人之間自發(fā)愉快的交流,感受身邊的生命力和社群生活,也是多主體互動性景觀設計的內(nèi)在要求之一。公園中的景觀小品例如互動自行車、水晶漩渦、跳跳蛙踏板噴泉等一改傳統(tǒng)的兒童玩耍,家長只能在一旁看護的情況,鼓勵家長參與其中,增進親子交流[3]。另外麓湖生態(tài)城經(jīng)常開辦一些活動,讓居民對自然的融入感更強烈,在體驗自然野趣的生活環(huán)境之余增強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交流和互動。例如麓客島開辦的花島生活節(jié)基于庭院花園打造的景觀交流活動,引導居民增加與自然共生的生活理念。美食節(jié)也是貼近人們生活的一種活動,有鬧市的音樂啤酒和自然的湖光山色,為社區(qū)生活增添了人情味。
3.3 情感的互動
場所精神是挪威城市建筑學家諾伯舒茲在 1979 年提出。“場所”一詞在廣義上可以翻譯成“土地”,可以解釋為“對一個地方的認同感和歸屬感”[4],場所精神內(nèi)涵和中國常說的“人杰地靈”不謀而合,基于人與自然的和諧,注重人、環(huán)境、物三者之間的關(guān)系,為游覽者提供一個情感交流、精神寄托的地方是現(xiàn)代復合型景觀打造的更高級要求。互動性景觀對地域性文化的塑造會更明顯地放大人們對場所精神的感受。
3.3.1 “水”文化的塑造 成都平原自古為富饒之地,故有“巴山蜀水”之稱,水網(wǎng)密布,河渠縱橫。成都2000多年歷史中關(guān)于修河治水的故事數(shù)不勝數(shù),其中以都江堰最為聞名遐邇。隨著城市工業(yè)化進程,人們在景觀營造過程中發(fā)現(xiàn),水才是現(xiàn)代景觀中最寶貴的資源。自80年代起,成都的河道受到不同程度的淤塞、污染,城市道路的擴張導致水系不通,局部斷流。因此,為“將水還魂于蜀地”而重新清理設計的水成為了整個場地的設計主題,每個公園及居住區(qū)都有不同形態(tài)的設計表現(xiàn)。例如紅石公園的彩虹橋,云朵樂園的云、冰、水外觀的景觀裝置設計,生動表現(xiàn)了水的固、液、氣三態(tài)特色。美食島、黑珍珠等各個居住區(qū)都臨水而建,力求打造融入自然,與水共生的生態(tài)景觀。紅石公園雨洪管理系統(tǒng)的設計更是獨到地演繹了水的主題,凈化后的雨水可循環(huán)利用至周圍的社區(qū)公園。在整個麓湖駁岸也隨處可見水草、蘆葦、鴨群等水生動植物,展現(xiàn)出濕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活力。
3.3.2 紅砂巖的文化運用 紅石公園坐落于麓湖生態(tài)城中心區(qū)域,設計借鑒加拿大布查特花園,結(jié)合原生地貌的紅砂巖,充分尊重場地條件,將紅砂巖作為主要的景觀要素巧妙地貫穿于整個場地的設計,形成了獨特的地域文化,延續(xù)了空間記憶,因此得名“紅石公園”。兒童七彩樂園里的紅砂巖鑲嵌在中間下陷四周略高的微地形中,中心的凹陷地形用于營建兒童樂園,能讓兒童在活動過程中對紅砂巖產(chǎn)生場所印記,寓教于樂。四周的高地和開闊的草坪方便鄰里交流休閑,形成了互動空間,并方便觀察場地中心孩子們的活動情況。在飄香澗和香樟棋語林隨處可見紅砂巖與玻璃材質(zhì)的桌椅,滿足了各個年齡段人群的活動需求并讓人們在聊天或游覽等過程中逐漸形成場景記憶,激發(fā)人們對社區(qū)公園的探索熱情。
4 互動景觀營造的探索
我國人口基數(shù)大,城市規(guī)模不斷擴大,人們對于居住區(qū)環(huán)境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在城市更新的過程中社區(qū)建設是提升居民生活體驗的重要內(nèi)容,設計是解決居住環(huán)境問題的重要工具,注重精神內(nèi)涵的打造比空間的設計更重要。
4.1 “互動性環(huán)境”景觀設計
優(yōu)秀的互動性景觀除了好看的外觀,其內(nèi)在也應當豐富有趣,不僅能體現(xiàn)人文關(guān)懷,而且讓人愿意花時間主動去了解其中的內(nèi)涵。
首先,應該通過多感官體驗設計讓人主動參與到景觀當中。其次,通過空間的設計引導人的行為互動。最后,將地域性文化滲透到景觀設計中,進一步塑造景觀的情感互動。互動性景觀不僅美觀且將人、環(huán)境、物三者結(jié)合,增加了社區(qū)活力,真正讓社區(qū)成為居民放松身心和活動交流的地方。
4.2 “人與人”的互動設計
場地動靜結(jié)合的設計與科學的功能分區(qū),讓家長可以帶兒童進行游玩與科普活動,年輕人可以打卡拍照,老年人可以放松身心。多層次結(jié)構(gòu)的景觀方便多種人群的使用與體驗,打破了傳統(tǒng)社區(qū)景觀設計單一化而導致的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壁壘。
5 結(jié)語
本文以成都麓湖生態(tài)城項目為支撐,探討了互動性景觀如何更好地融入社區(qū)公共空間。由于互動性景觀具有包容性,新穎性,很多新興體驗式景觀進行了大量的實踐應用,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游覽者,但目前互動性景觀的實際營造大多集中在人的感官體驗與行為互動上,對于情感的互動在社區(qū)空間中的運用較少,研究尚不完善。希望本文通過對麓湖生態(tài)城中互動性景觀營造的3個層次的總結(jié)能夠為該領域的研究添磚加瓦,讓互動式景觀設計更好的服務于社會大眾。
——《勢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