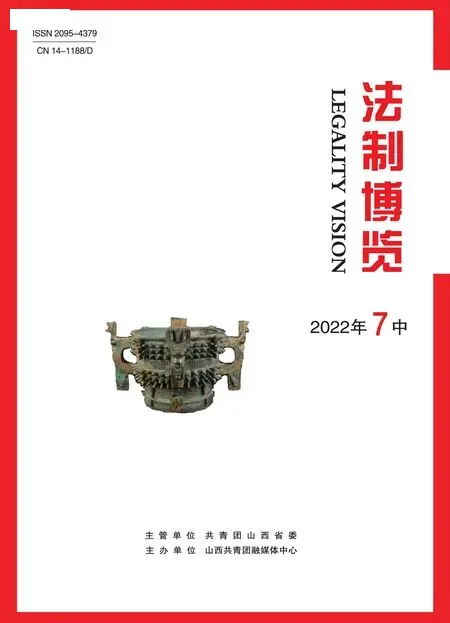商業秘密的認定與保護相關制度新趨勢的研究
——以從業自由原則為視角的反思
王 鵬 徐曉光
1.江蘇師范大學,江蘇 徐州 221000;2.貴州師范大學,貴州 貴陽 550000
一、商業秘密認定與保護的制度歷程
(一)商業秘密概念的變遷
商業秘密的概念最早被刑法所認可和接納,但是刑法所認定的商業秘密相較于民事立法的相關規定存在差異,這也是商業秘密相關制度發展的趨勢所決定的。最早在《刑法》之中出現的商業秘密的概念是“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并經權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分別并列的四個概念要件:區別于公眾可以簡單獲取的信息、實用性、具有經濟效益、權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然而在這個概念的實際內容在2007年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司法解釋》之中被簡化了,其中通過該司法解釋的第十條①《反不正當競爭法司法解釋》第十條:有關信息具有現實的或者潛在的商業價值,能為權利人帶來競爭優勢的,應當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條第三款規定的“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的內容將后兩個要件的實際認定條件擴大解釋為:至少具有潛在的商業價值,即可滿足后兩者的要件。這樣的解釋觀點被2020年9月頒布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商業秘密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1]》(以下簡稱《侵犯商業秘密規定》)所繼承,分別體現于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中表達的不為公眾所知、至少具有潛在的經濟價值、采取了相應的保密措施。
關于商業秘密構成要件的法律概念的變遷呈現出越發簡化、可包含范圍擴大化的變更趨勢[2],這一點在2007年之后的民商事審判之中成為了法院傾向于認可存在符合構成條件的商業秘密信息從而進行保護的趨勢的依據。而在這些要件之中,引發更多爭議的還是關于非公眾性(或者說秘密性)和實施了相應的保密措施這兩個要件。下文將舉例來專門闡釋為何在適用司法解釋判斷是否具有秘密性這個問題上一直爭議巨大,上下級法院意見差距巨大。
(二)保護商業秘密的制度變遷
最早在法律中規定侵犯商業秘密罪的是《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①2020年《關于商業秘密法律適用的司法解釋》第四條:(一)以盜竊、利誘、脅迫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以前項手段獲取的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三)違反約定或者違反權利人有關保守商業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業秘密的。明知或者應知前款所列行為,獲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業秘密的,以侵犯商業秘論。,存在三類侵犯行為:1.以違法手段獲取秘密;2.以違法手段獲取秘密后讓他人使用;3.違反保密協議或者權利人保守商業秘密的要求而泄密,并且本條對于第三人單純使用信息構成犯罪的情形明確了故意心態作為主觀要件:必須滿足明知或者應知前款所列行為,仍然獲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業秘密,以侵犯商業秘密論。因此除去泄密人、竊密人之外的獲取秘密的第三人要認定為侵犯商業秘密需要主觀上“明知”的嚴格的主觀標準,但是在2007年和2020年的兩部司法解釋之中這兩者均被做出了擴大解釋。
首先在2007年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司法解釋》之中,通過司法解釋擴大了侵犯秘密信息的范圍,將客戶與職工通過個人信賴關系共享的信息,設置了附條件的保護,如果單位禁止員工單獨(以單位商業往來之外的原因)與客戶接觸,那么這樣的個人信賴的信息往來也屬于對商業秘密的侵權行為。具體表述如下:在原單位進行的交易是基于雙方的個人信賴而進行的,同時在職工離職后,職工或者交易相對人能夠證明新的交易關系仍然是基于客戶的自主意愿選擇,則應當認定沒有采用不正當手段,但職工與原單位另有約定的除外②《反不正當競爭法司法解釋》第十三條商業秘密中的客戶名單,一般是指客戶的名稱、地址、聯系方式以及交易的習慣、意向、內容等構成的區別于相關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戶信息,包括匯集眾多客戶的客戶名冊,以及保持長期穩定交易關系的特定客戶。客戶基于對職工個人的信賴而與職工所在單位進行市場交易,該職工離職后,能夠證明客戶自愿選擇與自己或者其新單位進行市場交易的,應當認定沒有采用不正當手段,但職工與原單位另有約定的除外。。
而2020年的《侵犯商業秘密規定》則更進一步針對第三人獲取被侵犯的商業秘密信息的情形,做出了擴大解釋,將獲取商業秘密的不正當手段行為擴大解釋為:“被訴侵權人以違反法律規定或者公認的商業道德的方式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行為。”只要第三人獲取信息的途徑從客觀角度分析屬于違背法律或者社會商業道德便屬于侵犯行為。
(三)秘密性與保密措施在司法實踐中的爭議
上文所展示的法律發展的趨勢體現了國家通過立法擴大對于商業秘密保護的趨勢,但是這樣的趨勢也引發了許多問題和爭議。以2016年典型案例之一③2016南京法院知識產權10大案例之十:被告單位某A公司及被告人梁某某、龔某某侵犯商業秘密罪案。以及2015年典型案例④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定被告王某、張某、劉某違反保密義務,允許被告麥達可爾公司使用其所掌握的商業秘密,麥達可爾公司在明知的情況下使用涉案43家客戶信息牟利,屬于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判令四被告停止侵權并連帶賠償60萬元。分別說明。首先舉出2015年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的商業秘密案件為例,關于案中客戶信息是否具有秘密性,一審、二審、再審的中院、高院、最高院分別給出了不同的解釋方法,其中一審法院依據《侵犯商業秘密規定》的第三條認定:公司主張的客戶的信息包括客戶名稱、品名、貨品規格、銷售訂單數量、單價、聯系人、電話、地址。這些信息除客戶名稱之類的基礎信息外,還記載有產品類型、交易價格與數量等深度信息。雖然部分客戶的名稱、電話、地址等信息可以通過公開途徑查詢得知,但是客戶名稱、電話、地址與交易內容等深度信息結合后形成的新信息,并不為其所屬領域的相關人員普遍知悉和容易獲得。基于對“非公知性”的認定理由,一審認定具有秘密性重點在于是新信息就認定不是容易獲得的,對于新信息的“加工整理改進”的條件沒有做出要求,二審維持了這樣的判斷⑤二審法院認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第一款:“商業秘密中的客戶名單,一般是指客戶的名稱、地址、聯系方式以及交易的習慣、意向、內容等構成的區別于相關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戶信息,包括匯集眾多客戶的客戶名冊,以及保持長期穩定交易關系的特定客戶。”因此,華某公司主張的43家客戶信息符合上述法律的規定,具有秘密性的特征。。但經過最高人民法院再審之后改判“因為不具有非公知性而不構成商業秘密”,其中認為本案中所爭議的商業信息,在當前網絡環境下,相關需方信息容易獲得,且相關行業從業者根據其勞動技能容易知悉。另外,關于訂單日期、單號、品名、貨品規格、銷售訂單數量、單價、未稅本位幣等信息均為一般性羅列,并沒有反映某客戶的交易習慣、意向及區別于一般交易記錄的其他內容。在沒有涵蓋相關客戶的具體交易習慣、意向等深度信息的情況下,難以認定需方信息屬于《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的商業秘密。這樣的認定方式改變了原本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司法解釋》第十三條第一款中秘密性的形式需求,轉而探究該信息本質上是否是公眾難以獲取的、經過整改的新信息,這樣的觀點被2020年的《侵犯商業秘密規定》①《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商業秘密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權利人請求保護的信息在被訴侵權行為發生時不為所屬領域的相關人員普遍知悉和容易獲得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四款所稱的不為公眾所知悉;第四條第二款:將為公眾所知悉的信息進行整理、改進、加工后形成的新信息,符合本規定第三條規定的,應當認定該新信息不為公眾所知悉。所繼承。
綜上可知:司法解釋中所提到的秘密性信息和公眾可以知悉的信息的區別的要件——“整理加工改進”——可以判定的范圍過于巨大。在案件中一審認為“經過一定結合的新信息”就滿足“整理加工改進”的要求。二審之中勉強認定具有體現交易習慣和意向的功能,但是仍沒有采取鑒定等等手段對于信息和公眾公開渠道可以獲取的信息進行對比。直到再審申請人舉證網絡搜索證明,權利人所主張的信息都是網上可以獲取的信息的簡單羅列,并沒有自己“加工改進”的實質上的新信息。2016年案例也屬于同樣的特點。
二、從業自由原則面臨的阻礙
(一)從業自由面臨的制度阻礙
對于上文中的案例,原被告雙方沒有關于競業限制義務的約定,王某、張某、劉某的行為在不構成侵犯華某公司商業秘密的情況下,被告僅運用其從業期間在原用人單位學習的知識、經驗與技能,無論是從市場渠道知悉相關市場信息還是根據從業經驗知悉或判斷某一市場主體需求相關產品和服務,可以在此基礎上進行市場開發并與包括原單位在內的其他同行業市場交易者進行市場競爭。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合理的做法應當包括兩方面價值:首先應當依法加強商業秘密保護、制止侵權行為,為企業創新、投資創造安定的法律環境;其次也要妥善保護勞動者自由擇業、進行自發性的學習創新和人才合理流動的自由,進而維護勞動者正當就業、創業的合法權益,依法促進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和自主擇業。可見在保護商業秘密權利的同時容易與從業者的從業自由產生沖突。
(二)二者沖突的理論探討
誠實信用原則是民事活動的基本行為準則,這正是民法調整平等民事主體間的人身和財產關系的應有之義。而從業自由原則,是指從業者在不違反法律強制性或者禁止性規定的前提下,可以基于雙方的意思表示形成權利義務關系,設定具體的權利義務內容供雙方遵守。權利與義務是硬幣的兩面缺一不可,沒有無義務的權利,反之亦然。權利的行使也不是沒有任何限制的,禁止權利濫用本身就是法治的理念之一。除此之外,為了某些特定的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也需要對某些權利做出一定的限制,基于憲法的自由擇業權也不例外。
在競業禁止制度中,為了保護雇主的商業秘密,合理限制了離職雇員的再就業權,即在一定期限內不得從事與原雇主具有競爭關系的行為。此競業限制的約定因為是保護商業秘密的合理需要而具有了正當性,即“因競業禁止的需要所作出的限制是合理的[3]”。我國通過《勞動合同法》第二十三、二十四條明確了這種權利限制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當然這種限制也是有一些預設前提和限度的,例如適用的對象是特定的雇員,還有明確的期限、范圍以及出于保護商業秘密的目的等。
自由擇業權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非法律特別規定無例外情形,而就在競業禁止適用時出于權利沖突的協調和平衡,此時自由擇業權因商業秘密保護的需要而被合理限制,這就是自由擇業權的例外原則。
(三)司法實踐中從業自由面臨的阻礙
關于工業技術商業秘密如果屬于通過簡單觀察就能夠掌握的技術,應該屬于從業人員日常工作之中合理研究就應當掌握的基本從業技巧。但是許多案件在一審的時候由于將司法解釋中“公眾容易知悉獲得信息”的認定門檻設置得過于簡單,造成了本應當屬于從業者日常工作中應當掌握的基本技術進而使用的行為,也被認定為侵犯商業秘密而違法。幸而在隨后的案件判決、其他案件的解釋適用中存在克服這樣問題的探索。
例如“蔣某輝、武某軍侵犯商業秘密案”與2016南京法院知識產權十大案例之十:“被告單位某A公司及被告人梁某某、龔某某侵犯商業秘密罪案”,兩個案件中的一審都以“直接觀察不能夠獲得信息”為理由認定該信息具有秘密性。對于生產技術指標“容易獲得的”條件不同的認定:一審法院認為對于一經公開銷售的產品生產參數的部分信息并沒有公開、通過簡單觀察無法直接獲取便足以滿足條件,并沒有參考和驗證相關信息能否通過對于產品(一經公開銷售)合理測量觀察后能否獲取。
而二審之中加入了對于信息本身獲取難易程度的判斷,并且最終改判無罪,有力地保護了從業自由原則的價值。在一審之中以相關信息組合沒有經過出版物公開發表為由,認定“其整體及關鍵信息并未公開。而且除了出版物公開外,其他方式公開僅具有公開的可能性,并不必然導致被公眾所知悉,且知悉不能僅僅是一知半解”而具有秘密性。二審之中則認為“因此,要認定系爭技術非公知性時,既要排除出版物公開的情形,又要排除使用公開等已公開情形”,由于相關秘密信息可以通過簡單的測繪、拆卸、付出一定簡單代價就能夠獲得,但由于不能排除涉案兩項技術信息已經被公開使用的合理懷疑,原審判決認定涉案技術信息屬于商業秘密繼而認定蔣某輝、武某軍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罪有誤,應予糾正。這樣的司法實踐成為了趨勢,被如今2021年前后的最高院相關判決所繼承。
三、對于從業自由進行保護的制度與司法探索
(一)保護從業自由的制度探索
2020年9月頒布的《審理商業秘密的若干規定》之中存在明確的對于從業者基于個人信賴而使用所獲取的客戶信息以及技術從業人員可以通過自主研發攻破商業秘密的反向工程手段。
其中第二條第二款:客戶基于對員工個人的信賴而與該員工所在單位進行交易,該員工離職后,能夠證明客戶自愿選擇與該員工或者該員工所在的新單位進行交易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該員工沒有采用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體現了對于客戶信息進行使用過程中的從業自由的價值。
而第十四條第一款:通過自行開發研制或者反向工程獲得被訴侵權信息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不屬于《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規定的侵犯商業秘密行為。該條款是對于從業者利用學得的知識,進行合法自主創新的自由權益的承認,因為反向工程是指通過技術手段對從公開渠道取得的產品進行拆卸、測繪、分析等而獲得該產品的有關技術信息,因此該條款表達了技術行業的從業人員可以通過自主研發、破解來使自己獲得對于商業秘密信息使用的正當權利。
(二)相關司法實踐的保護探索
在2021年9月最高院的案例①北京零極中盛科技有限公司、周洋等侵害技術秘密糾紛民事二審民事判決書。之中,結合上述規定第三條、第四條對《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規定的商業秘密構成要件之一“不為公眾所知悉”作出規定:“不為公眾所知悉”的判斷主體是所屬領域的相關人員,判斷的標準是既不能“普遍知悉”,也不能“容易獲得”,認定的時間點是“被訴侵權行為發生時”。此外,市場流通產品屬于外部載體,某B公司為實現保密目的所采取的保密措施,應能對抗不特定第三人通過反向工程獲取其技術秘密。此種對抗至少可依靠兩種方式實現:一是根據技術秘密本身的性質,他人即使拆解了載有技術秘密的產品,亦無法通過分析獲知該技術秘密;二是采取物理上的保密措施,以對抗他人的反向工程,如采取一體化結構,拆解將破壞技術秘密等。據此,原審判決認定,涉案技術信息通過去除覆膠、拆解后,使用常規儀器測量可以獲得,構成所屬領域的相關人員容易獲得并無不當,最高院予以確認。
并且該案審判之中也依據由于產品可以通過測量獲取相關的商業信息這一點,認定對于信息的載體,即產品,由于已經在市面上公開發售就會導致不能夠認定存在“相應的保密措施”。根據原審查明事實,某B公司根據其技術圖紙制造的產品在爭議發生前均已進入市場流通,因此,本案中涉案技術秘密的載體為相應進入市場流通的電源模塊產品。而產品一旦售出進入市場流通,就在物理上脫離了某B公司的控制,故區別于可始終處于商業秘密權利人控制之下的技術圖紙、配方文檔等內部性載體。某B公司主張的與前員工的保密協議、技術圖紙管理規范等對內保密措施,因脫離涉案技術秘密的載體,即在市場中流通的電源模塊產品,故與其主張保護的涉案技術秘密不具有對應性,不屬于本案中針對市場流通產品的“相應保密措施”。
通過上述的最高人民法院對于“秘密性”和“相應的保密措施”的闡述我們可以發現,目前司法實踐的態度對于商業秘密認定的門檻越來越高,因此從業者的從業自由也會從相關最新司法實踐之中得到進一步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