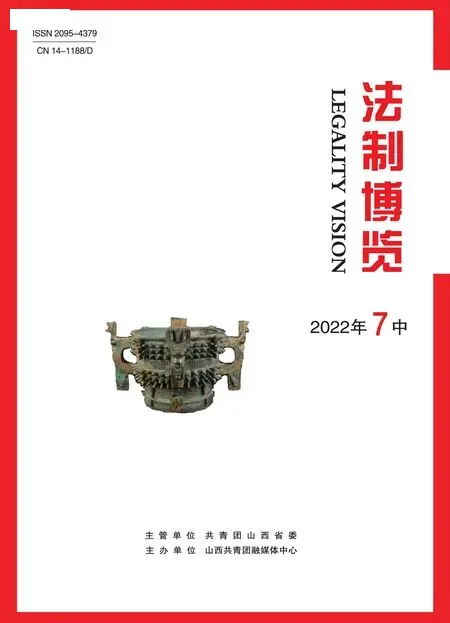智慧法院:現代科技應用于司法的思考
——基于中國裁判文書網近十年數據的實證分析
孫玉寶
揚州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江蘇 揚州 225001
一、智慧法院建設的實踐探索
“當某一新學科在現階段表現出突破性進展的時候,就會有很多科研探索者幻想可以適用于所有問題。”[1]達特茅斯會議上約翰·麥卡錫首次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但是從科學角度并未實質界定“人工智能”一詞,因此導致至今對“人工智能”的基礎性認識分歧。但是,關于人工智能融入司法,“中國經驗”的智慧法院規劃在我國已經出現近五年了。
七年前,最高法為了將科技實際運用到司法審判和執行全過程,充分應用現代科技來保障司法的公開、公平、公正,首次提出了“智慧法院”這一概念。[2]在之后“智慧法院”推進的過程中,為保證司法與人工智能相輔相成,2016年11月10日,人民法院信息技術服務中心與中國電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天平司法大數據有限公司,周強院長多次指出成立該公司就是要圍繞成為世界一流的司法大數據管理者、服務者和研究者的目的,使司法大數據更好地服務司法審判執行,服務人民群眾多元化司法需求;同年11月,《烏鎮共識》發布,表達了國家全力建設智慧法院的決心和毅力;2017年4月,為了加快智慧法院的建設進程,最高法發布了相關指導意見,對各省市地方建設人工智能平臺提出相關指導,以此為基礎接下來的幾年我國各地人民法院的人工智能建設取得顯著提高,成效顯著,如北京“睿法官”智能研判系統、蘇州法院的“智慧審判蘇州模式”等。
二、智慧法院存在的實踐困境
“中國經驗”在中國的智慧法院建設中起到了突出的貢獻作用,地方試點主義政策的出現帶來了如江蘇法院“12368”智能語音系統等優秀的智慧法院建設成果,但就像推進全國共同富裕一樣,雖然全國智慧法院的建設在全國全面展開,但并沒有擺脫中國地域導致的發展創新不平衡的矛盾。遍觀全國三級法院,智慧法院的建設成果及現狀與理想狀態存在著不小的鴻溝,同時各家法院深入研究的成果以及全面推進所取得的成效均無法滿足實際智慧法院運行的需要。[3]本文因篇幅有限,以類案檢索機制為角度,簡要闡述智慧法院建設中的實踐困境。
(一)平臺推送問題
通過查閱中國裁判文書網相關文書筆者得出,現階段生效裁判文書類案檢索系統的內在算法黑箱主要是通過對案件的定性和定量兩方面。同類案件的定性可有效地分辨案件性質類別,但同時也會導致沒有考慮不同案由或事由問題,此種事先宏觀歸類方式會遺漏很多案件;同類案件的定量是在定性的基礎上依照法律規范的內容對案件的一些基本要素進行量化,通過要素式分解這一抓手解決達到檢索這一目的。無論是定性還是定量最終都是對生效判決文書關鍵字、關鍵詞或語義結構相似度的抓取問題,如中國裁判文書網類案檢索系統相似度的抓取方法就是關鍵字、關鍵詞的出現頻率,以此為抓取基礎統計出高頻關鍵詞,另外如知網等則往往通過對整段文字的結構為抓手,截取整個裁判文書中結構體系,以此層次結構體系作為抓取方法。[4]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司法案例數據庫中,筆者以“買賣合同”和“房屋”作為裁判文書搜索的關鍵詞,檢索得到案件數量超過2000件。而且通過快速篩選所檢索得出的案例,筆者發現通過關鍵字得出的判例,并沒有真正意義上做到“類案”,有接近三分之一為毫無任何實質關聯的相同詞句,或者不同判例中援引了同一法條。之后筆者繼續輸入關鍵詞“所有權”,依然還是會有上百條案例,逐一查閱獲取想要的類案其實并沒有想象中的簡單,反而耗費了大量的精力。[5]目前我國文書上網工作還在日益完善,這就導致中國裁判文書網上的類案檢索案例數量將繼續增多,同時不能快速檢索到相關度較大的案例問題將日益凸顯。其實,作為法院人都明白,承辦法官最想看到的是數量不多的精品案例,保證類案有跡可循,而不是通過大量閱讀得來的不符合需求的類案。
(二)司法數據庫問題
筆者通過調研中國裁判文書網數據,自2002年至2017年的十五年間,我國刑事一審判決書數量與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該年度工作報告刑事一審結案數量對比:該年度裁判文書網公開的一審刑事判決案件與案件實際結案數量比例在0.08%~79.71%之間,各省市之間差距也比較大,綜合分析,在2012年之前,數據庫中收錄案件數量不足實際結案數量的10%。雖自2013年開始至今所占比例有較大幅度的提升,但占比仍然不到50%,通過對比不難看出2013年與2017年的比例相差多達20%。由此可見,算法計算所依靠的大數據與實際結案數量之間差距很大,不能有完整的原始數據作為支撐將必然導致算法誤差的出現。縱觀全國各級法院不難看出,文書的上傳都是經過選擇的,數據從最初就已經不夠客觀,充滿了主觀因素的干擾。
(三)類案裁判規則供給不足
“同案同判”一直是人民群眾一直希望的司法公正,類案檢索機制出現的根本價值就在于在法官處理待決案件時能夠有一個在性質上接近于司法領域持續一致的見解,這一見解已經通過時間的沉淀以及實踐的檢驗。當然過分強調同案同判是有瑕疵的,承辦法官能夠通過類案判決提煉出裁判規則,以此為基礎制作裁判文書才是最重要的。張騏教授就曾在某法官講座中指出,法官在作出判決時都可以從類案中看到裁判要旨,但實際作為承辦法官最應該做到的是通過裁判要旨提煉裁判規則。[6]我國作為典型的成文法國家,其性質決定了法官是法律的適用者而非創造者,但司法實踐中中國法院必然會從事賡續法律方面的工作。尤其像一些典型的疑難、復雜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就會以典型案例的方式進行法律賡續,將其中的裁判內容進行凝練得出規則,雖然此種裁判文書的效率不及司法解釋,但也具有一定的約束力和指導力。基于此就有學者提出相應觀點,認為我國最高法應將司法規則供給模式由“權力輸出型”逐漸變為“權威生成型”。[7]目前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還只是一些典型性、指導性案例具有類似裁判規則的效力,在其他類型案件中不足以體現裁判規則等。以此考量,是不是未決案件的承辦法官檢索得到的一定數量的類案并無太大參考意義?
三、淺析人工智能與人民法院融合互補機制
類案檢索機制是裁判經驗和人工智能雙方共同融合進步的結晶,能夠充分保證人民群眾對司法裁判的合理信賴和對公平正義的期待,同時也限制了法官個人的自由裁量權。2020年,最高法就發布《關于統一法律適用加強類案檢索的指導意見(試行)》,進一步要求三級法院加強類案檢索,做到法律適用的統一,旨在通過強制性意見從實體和程序上要求承辦法官規范裁判。[4]最高法推出這一舉措是給類案檢索加以指導以達到統一裁判尺度的根本目的。當然,該指導意見的頒布也是從實體及程序上拓寬承辦法官的思路,為處理相似案件提供有效保障,進一步實現司法公正。[8]
針對中國裁判文書網上眾多類案情況,法官檢索繁瑣,付出的時間精力巨大,從智慧法院建設外部來說,應當對大數據進行一定程度上的再造、更新,以適應法院裁判案件的要求。而以裁判文書網為例,一億篇裁判文書重新細分細化程序繁瑣,需要技術的繼續更迭以及科技和司法的進一步融合。因此解決類案檢索機制的實踐困境,筆者認為還是要以法院內部自身為抓手,以裁判規則為角度,為類案檢索尋找出路。類案檢索最終離不開對裁判規則的適用,如何提煉規則、諸多規則之間沖突如何協調,筆者將以個人拙見簡要討論。
(一)類案裁判規則的抽取
筆者作為法院人,以實踐為基礎,結合對中國裁判文書網的調研,裁判規則其實就是將法律規則通過案例做出了精細化的解釋。現階段我國法官在辦理未決案件時,應著重警惕以下幾點:首先,法律規則是根基不能動搖的,對既有法律的賡續要以此為基,慎之又慎;其次,提煉具體案例中的裁判規則要把握關鍵性事實,切勿主次不分;最后,圍繞爭議焦點提煉裁判規則,分歧之所在才是每一個案件所持有的特點,把握分歧焦點就可以更好適用法律,更好地提煉裁判規則。
(二)類案裁判規則沖突協調
前文已經提到,智慧法院建設的根本目的是保證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而我國現實國情是地大物博、東西部發展不均衡、各省市之間的法治化程度高低不一,這就必然導致實踐中的裁判會因此而產生差異;同樣以時間軸為參考,已決裁判文書同當下或者未來的裁判所展示、所面臨的現實國情、實際情況都會不一致,更有甚者同一名法官過去、現在或未來都可能產生前后矛盾的觀點。最高法為類案同判做出了很多的實踐,現階段最高法以類案強制檢索、類案統一法律適用標準作為司法裁判探索的新方式。然而考慮我國現實國情,南北差異、東西差異巨大,實踐中完全實現類案同判并不現實,最高法發布指導意見也旨在幫助承辦法官針對類案有據可循、有法可依,現實判決過程中還是要依靠承辦法官的法律智慧,通過相似案件的論證,具象化真正有法律意義的裁判規則,以同案中最佳解釋或者最優規則為依據,有效化解同案不同判的法律風險。[4]最高法官網上每一年都會公布指導性案例,旨在指導每一名法官提煉相關裁判規則,為類似案件判決提供幫助,而其他類案檢索得來的裁判內容是否適用,是否與承辦法官未決案件在合理性和正確性上保持一致,這需要法官自由裁量,盡可能地避免出現向上尋找出路的情況,將案件交給承辦法官,就保證案件由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類案檢索通過實踐觀察,其實只是智慧法院建設的一小步,科技融入司法的腳步注定向前,我們應在勇敢地開拓進取同時保持警惕,不要過度美化智慧法院現有成果,現在就大肆宣傳智慧法院是“法治中國的一張靚麗名片”還為時過早,早早剝開智慧法院過于繁榮的外衣利遠大于弊。
(三)確保司法人工智能有序穩步推進
1.區域協同不足問題。在下一階段智慧法院建設中最高院要主動牽頭負責統籌、推進、監督、落實、評估,并與電商服務平臺、技術服務企業對接,整合社會資源,避免重復建設問題,對于現存智慧法院建設模塊原則上不再重復,而是按照各地方特色以及基礎進行優化升級,保證智慧法院的建設在全國一體推進;
2.潛在風險評估問題。第一步從源頭抓起,在司法數據分類、整理、匯集環節實現再治理。最高法推動司法公開,嚴格法律文書上網,現階段已經形成數據紅利,這在基礎的數據積累上已經為智慧法院的建設提供了極大幫助,以此為基礎最高法應建立起裁判文書大數據串聯、共享機制;第二步從根基抓起,科技融入司法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階段,司法領域應用要時刻保持審慎態度,人工智能技術遲早會出現發展的瓶頸期,因此要降低人民群眾對司法人工智能的期待,打破固有的“智慧法院萬能論”,肯定承辦法官在司法活動中的獨特地位。同時要由最高院牽頭成立智能司法審查組織,對數據進行備案、審查,保證智慧法院建設的道路正確。
3.智慧法院建設社會各界實質參與問題。社會力量的參與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由政府牽頭與一些法律科技企業簽訂戰略合作協議,使更多企業投身智慧法院的建設和研發當中去;第二,我國法學院校眾多,在之后的人才培養過程中,應全面強化法學院校在智慧法院建設中的復核作用,法學院校將人才培養模式從單純的培訓專業法律人轉變到培訓熟練掌握法學理論知識和科技研發能力的復合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