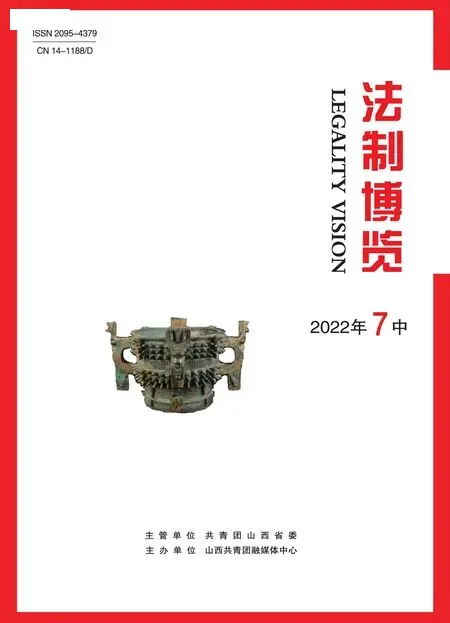《民法典》視域下居住權制度的基本理論探究
李自毓
東北師范大學,吉林 長春 130117
一、溯源居住權制度
(一)居住權的起源
羅馬法開辟了外國居住權的先例,居住權制度最早來自羅馬法系中的人役權制度。羅馬法中的居住權制度是指,由權利人解決住房的需求并對別人的住房加以占有和利用。最初的權利人所獲得的權利范圍非常狹窄,只是部分享有類似于受遺贈人的某些法律利益的事實。羅馬法中的居住權的逐步確立與其當時的社會環境土壤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羅馬共和國初期,家長的地位和權力在一個家族中是至高無上的,不僅全部財產歸屬于家主,就連家屬的命運也掌握在家長手中。可以說,家長在一個家族里擁有的權力之大,不僅是財產上的,就連人身權利也包含在內,甚至可以掌握族人的生死。這使得弱勢方的妻子、子女、奴隸這類特殊群體的利益被完全擠壓,無法得到正當的保護。于是國家從增設義務的角度入手,具體采取以下措施加以制約:家長不得隨意殺傷、出賣家屬;家長有義務扶養家屬等。在婚姻制度中,無夫權婚姻制度成為主流。這意味著妻子沒有因為嫁人而從原生父權中剝離,而是仍在生父的家長權之下,丈夫不享有夫權。因此妻子也無法在丈夫去世后繼承夫家財產,這使得她們最基本的生存權益都沒有保障。與之相對應的是沒有繼承權的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被解放的家主的奴隸等等,一旦家長亡故,他們的生活就成了問題。因此,丈夫或者家主把一部分家產的使用權、收益權、居住權等遺贈給妻子或被解放的奴隸,使他們生有所靠,老有所養。這些權利在查士丁尼時期被確立為一項正式的權利,也被稱為人役權[1]。
綜上所述,羅馬法時期的居住權是為了保障那些不具有繼承權身份的家屬的基本權益,不至于讓他們流離失所。由于羅馬法中的居住權具有助危、恤民的功能,往往是家主去世時通過遺言、遺贈等單方法律行為的方式確立下來。
(二)居住權的含義
居住權雖然起源于古羅馬,但是在我國學術界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就居住權定義而言,不同的學者見解不一,但是均指出:居住權是一種權利。例如,錢明星教授指出,居住權是特定人因居住而使用他人房屋的權利[2]。德雷斯H.C.羅爾夫斯特恩爾(Dres.h.c.Rolf Stürner)認為,居住權是所有權人根據自身喜好而設置的處置物的權利,使部分的所有權可以為他人提供服務。總體來說,這些學者對于居住權的定義大同小異,結合我國目前的發展情況和社會環境,2020年5月8日,我國《民法典》正式出臺,《民法典》中闡明了居住權的概念和定義。根據《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條:“居住權是房屋所有人設立的用益物權之一,是指居住權人有權按照合同約定,對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權,以滿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二、居住權制度的屬性探析
(一)居住權的人役權屬性
正如馬爾西安所言,“役權附著于人身”。因為經濟關系多種多樣,人們對于住所的需求也大不相同。為了回應這種社會需求,具體而言,居住權的人役權屬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居住權具有專屬性,屬于特定人享有的權利。因為其輻射對象特定,大多是所有權人的父母、妻兒或者其他老年人、婦女等,因此該權利的目的不以對房屋收益和不動產財產為中心目的,更在意其對房屋本身為了居住需求的利用和使用。因此,該權利專屬于特定之人,不可繼承和轉讓。第二,居住權的期限如無特殊約定,具有終身性[3]。這是在尊重雙方合意的契約的基礎上,使居住權變得更加靈活和舒適。具體表現為,如果設立居住權之后,沒有合同或契約對期限作出明確規定的,則對該居住權的期限推定為居住權人的終身。該規定也有據可循,居住權在羅馬法的最初規定中,也是涵蓋了居住權人的終身。第三,居住權的取得方式具有無償性。從古羅馬時期開始,居住權制度就是房屋所有權人為了保障家庭成員或者弱勢方而對自己權利的一種讓渡。現代社會設立居住權所保障的目標人群,大致為父母子女關系所引發的、婚姻關系破裂后的無房女性方或者因保姆雇傭關系轉化的一方居住權利等問題。以上類型的關系都有著特殊的情感紐帶維系或者與房屋所有權人存在著某種特殊的關聯,并基于此而設立的居住權。只能由特定人享有的,無需支付使對價,其體現了居住權的恩賜和慈善的特點,所以被稱為“恩惠行為”。其在《民法典》中的第三百六十八條中有詳細規定,居住權無償設立,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二)居住權的物權屬性
居住權是具有人身屬性的人役權,但也屬于用益物權,具有一定的物權屬性。具體而言,居住權的物權屬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四點:第一,居住權對于權利的主體限制較少。一般而言,居住權的主體并不要僅限于所有權人的直系親屬或者服務人員,只要是自然人,在與房屋所有者約定好的情況下,均可以享有居住權。第二,居住權不再強調倫理性[4]。由于居住權的主體限制較少,自然人即可享有該權利,權利主體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到了整個社會,因此居住權不再強調家庭成員之間相互扶助的倫理色彩。第三,居住權的設立更加注重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可以通過合同或者遺囑的形式,在所有的房屋之上設立居住權,并將之授予給特定的自然人,在一定程度上,居住權給予了居住權主體更大的自主權。第四,居住權將房屋的使用價值分配給居住權人,將房屋的交換價值分配給所有權人,實現了權能分離,這一功能就是居住權制度的核心,居住權之所以仍然歷久不衰,這一特點至關重要。
三、居住權制度的演進
(一)域外居住權制度的繼受與發展
1.《法國民法典》
《法國民法典》對羅馬法中關于居住權制度的相關規定,包括用益權、使用權、人役權、地役權、居住權都進行了全面吸收,主要集中編纂在《法國民法典》第二編第三章的第一二節,共20個條文。《法國民法典》雖然對羅馬法的整個居住權體系進行了全面繼承,但是仍在此基礎上進行了調整和發展,主要包括:(1)居住權不局限于遺囑、遺贈等方式,可以通過當事人合意或者法律規定設立,體現了契約自由的精神;(2)將羅馬法中居住權利人不因未行使居住權而使權力就此的消滅時間由終生調整為30年;(3)為保護房屋所有權人的房屋不受居住權人的惡意侵害,增加了擔保制度,即居住權人在行使權利時必須提供擔保,同時還要盡到善良管理人的義務:支付稅費和房屋修繕費用。《法國民法典》中關于居住權的調整中,最為關鍵的一點就是其設立方式不僅局限于單方面的遺囑、遺贈,而是增加了于雙方合意的契約制,使居住權變得更加靈活和舒適。但是整體而言,相關制度規定較為保守:居住權的權利主體特定,限定在房屋所有權人及其家庭成員中,具有很強的人身依附性和人身專屬性;居住權的性質帶有扶弱、施惠等目的,因為不能轉讓、買賣、抵押,具有不可轉讓性和不得強制執行性。
2.《德國民法典》
《德國民法典》在編撰初期延承了羅馬法中居住權制度的相關規定,具有濃厚的限制人役權色彩,具體包括:(1)設立方式上的狹窄有限,雙方只能通過自愿協商簽訂合同,并且以登記為必要條件;(2)居住權人的權利不得除自己之外的人任意使用和轉讓,具有很強人身專屬性的色彩烙印;(3)為了保護房屋所有權人對自己房屋利益的知情權和維護,居住權人在房屋存在殘損、履行不能等各種情況時,或者面臨他人侵吞等無法控制的危險時,應當及時示知所有權人。
然則,德國的經濟發展迅猛,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對上層建筑的需求也不可同日而語。《德國民法典》中有關居住權部分的相關規定和整個社會發展相比,亟須更新。因為經濟關系多種多樣,人們對于住所的需求也大不相同。具體表現在,原有居住權的適用范圍僅僅是存在于家族內部,而不是向外部延伸流通的,而這一規定顯然已經跟不上時代的腳步。根據這一問題,《德國民法典》采用的解決方式與羅馬法的傳統意義上的居住權相比是一項頗具創造性的革新之措:居住權可以移交他人,代為行使。這項規定賦予了居住權制度一項全新的物權屬性,即準用用益權。德國的《用益權和限制的人役權轉讓法》中明確提到,限制人役權在滿足條件時,可以轉讓。不僅如此,德國立法機關還增設了長期居住權這一新型居住權概念:居住權人如果通過登記的方式獲得居住權之后,即可以長期享有房屋的居住權和使用權。這一制度無疑更好地服務社會大眾,貼近人民需要。
綜上所述,德國的居住權起到了一個繼承發展的作用,既在羅馬法居住權的基礎上取其精華,有所保留,又根據其本國需要增添了新的需要,使居住權變得更加靈活開放,符合了社會大眾基本的社會需要。但《德國民法典》因為對于概念解釋詳盡、體系構造復雜、語言邏輯繁瑣,也被后世學家褒貶不一。
3.《意大利民法典》
1865年剛剛成型的《意大利民法典》深受《法國民法典》的陶染,除了一些細致微調外,基本各個制度規則和整體架構都一一對照了《法國民法典》居住權的相關內容。但該法典將居住權的相關規定更加精練,1990年的《德國民法典》也將這部分內化為己用。具體調整包括:(1)對家庭內部成員進行了清晰的劃分,主要包括配偶和子女,其中子女的范圍囊括了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居住權人的養子女,并且該居住權利同樣延伸至居住權人未來增添的新成員;(2)詳細地規定了居住權人對于所涉房屋的稅費分擔規則,居住權人應當按其使用的部分占房屋整體的比例來承擔正常的維護費用,對本應由所有權人承擔而所有權人不履行的修繕義務,居住權人可以自行修繕,修繕的費用有權向所有權人請求償還,所有權人拒絕償還的,居住權人可以在其居住權消滅時留置該房屋;(3)關于消極行使居住權的最長保留有效期從30年縮減至20年,逾期不行使的,居住權滅失;(4)分別在《與家庭編》和《繼承編》中編纂居住權的相關內容,著重強調了居住權作為了一項濟弱性權利對于家庭風險相對高的弱勢群體的保障[5]。
如上所述,正是這些不斷前進發展的法律研究,使居住權在每個國家的制度中都煥發出了新的生機。正如羅爾夫· 施蒂爾納(Dres.h.c.Rolf Stürner)所說,居住權是所有權人根據自身喜好而設置的處置物的權利,使部分的所有權可以為他人提供服務。
(二)我國居住權制度的發展:存廢之爭
20世紀居住權制度逐漸進入我國學者的研究視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為居住權制度的萌芽提供了可行性的土壤;國外與國內的法學理念和研究的不斷碰撞,讓我們開拓視野、取其精華;我國法律體系的逐步形成與完善更是帶動了民法學的蓬勃發展。最開始,居住權制度引入我國的過程并不順利,學界大多采取批判的態度。2005年居住權制度曾短暫地出現在原《物權法》草案中,但是由于反對學者的據理力爭后隨之刪除,但這次未成的嘗試并沒有為居住權制度入典定下最終章,反而掀起了學界更加熱烈的又一波討論,越來越多的學者加入到居住權制度的研究中,有關居住權制度的討論空前高漲。
《民法典》草案一、二的修訂就像是一個催化劑,贊同居住權制度這一主張的學者們,將居住權視為物權的一種形式,應歸屬于物權法體系中,該制度不僅對房屋的使用提供了更多樣化的途徑,使其發揮了更大的價值,并且對于該制度今后應用于市場經濟中也有著巨大的潛力。這場曠日持久的學界探討,從20世紀90年代即拉開帷幕,從2005年《民法典》草案被刪除暫放,歷經12年再次在2018年8月的《民法典》草案修訂中予以編纂且納入物權編中,并最終在2020年5月28日,《民法典》正式通過而塵埃落定。
總體而言,對于《民法典》是否應當規定居住權制度的問題,學者們已經進行了充分的討論,但是,對于居住權制度的構建,學者們意見不一,現行《民法典》中有關居住權制度僅有6個法律相關條文,仍有不少的規范空缺仍亟需更詳細地說明,其含義也多有模糊之處,有待進一步厘清。即在物權編的整體骨架中新增了該制度,但其中血肉部分仍需進行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