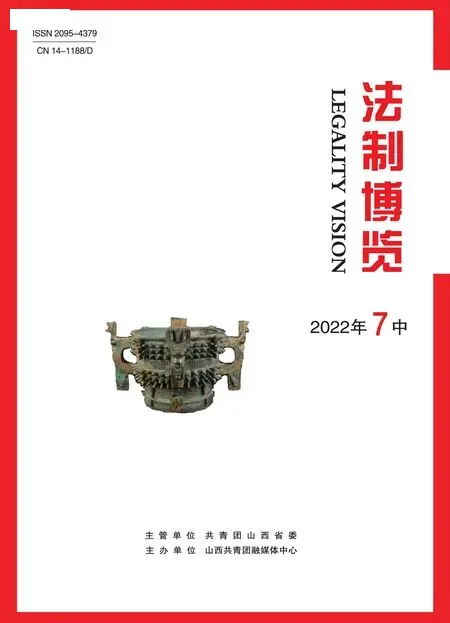代購管制藥品案分析
李佳明
貴州民族大學(xué),貴州 貴陽 550025
2021年9月河南發(fā)生一起案件,一位年輕媽媽因長期代購治療罕見癲癇病的管制藥品,涉嫌走私、運(yùn)輸、販賣毒品罪(下文簡稱“運(yùn)輸毒品罪”)被立案,后因其系初犯和為兒子治病且未獲利等原因,檢察院認(rèn)為犯罪情節(jié)輕微,綜合考量后作不起訴決定。在本案中檢察院適用的是《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即檢察院認(rèn)為行為人的行為構(gòu)成犯罪,只不過犯罪情節(jié)輕微社會危害性不大,因此定罪不起訴。本案中檢察機(jī)關(guān)在公正司法的前提下充分發(fā)揮刑法的謙抑性,彰顯了司法的法律和社會效果相統(tǒng)一,正是我國司法在不斷進(jìn)步的一個體現(xiàn)。筆者試將此案置于階層體系下進(jìn)行分析,以探討出罪的可能性和路徑。
一、法益侵害性
刑法的目的或任務(wù)是什么,或者說犯罪的本質(zhì)是什么,對此刑法理論上有兩種對立的學(xué)說。法益保護(hù)說認(rèn)為犯罪的本質(zhì)是侵害或威脅到法律所保護(hù)的利益,因此刑法的任務(wù)是保護(hù)法益;規(guī)范維護(hù)說則認(rèn)為犯罪實(shí)際上是對刑法背后規(guī)范的違反,因此刑法的目的是維護(hù)法律的規(guī)范。法益保護(hù)說在刑法理論上占據(jù)優(yōu)勢地位,根據(jù)我國《刑法》第二條的規(guī)定也可以看出,我國《刑法》的任務(wù)是保護(hù)國家安全、公民權(quán)利等各種法律所保護(hù)的利益,因此可以認(rèn)為法益保護(hù)說與我國《刑法》的規(guī)定相契合。法益概念具有解釋規(guī)制機(jī)能[1],所以刑法理論研究和司法實(shí)踐在對刑法條文進(jìn)行解釋和適用時,要以刑法規(guī)范的保護(hù)法益為指導(dǎo),才能符合刑法的目的。
運(yùn)輸毒品罪所侵害的法益為何,這在理論上存在一定爭議,總體上有國家管理制度說、公眾健康說和雙重法益說。國家管理制度說認(rèn)為運(yùn)輸毒品罪侵害了國家對于毒品這種管制物品的管理制度;[2]公眾健康說認(rèn)為本罪的保護(hù)法益是公眾健康,但并不是具體個人的身體健康,而是作為超個人法益的公眾健康。[3]雙重法益說認(rèn)為運(yùn)輸毒品罪不僅侵犯了國家對毒品的管理秩序,同時也侵害了公民的健康。[4]國家管理制度說沒有揭示運(yùn)輸毒品罪的本質(zhì),也不能很好地指導(dǎo)運(yùn)輸毒品罪的適用,例如吸食毒品明顯侵害了國家對毒品的管理制度,但我國《刑法》并沒有將此種行為納入規(guī)制范圍。雙重法益說也存在如上問題,國家對毒品進(jìn)行管制歸根到底是為了其使用規(guī)范化、合理化,以免部分民眾濫用而危害公眾健康,從而維護(hù)國家的安定和社會穩(wěn)定。相比之下筆者更贊同公眾健康說,如上所述國家管理毒品就是為了防止其被濫用危害公眾健康,從我國《禁毒法》的規(guī)定中就可見端倪,該法第一條①《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毒法》第一條 為了預(yù)防和懲治毒品違法犯罪行為,保護(hù)公民身心健康,維護(hù)社會秩序,制定本法。就規(guī)定其制定目的是打擊毒品違法犯罪行為,從而保護(hù)公民身心健康。
明確了運(yùn)輸毒品罪的保護(hù)法益是公眾健康后,就可以將本案置于公眾健康法益的審視之下。本案的行為人是為了給其孩子代購藥品才違反了管制藥品的規(guī)定,且其代購的藥品除了自己用以外,只給了代購藥品群的其他需要此類藥品的父母。從客觀上來說代購藥品行為會挽救部分孩子的性命和破碎的家庭,而侵害到公眾健康安全的可能性并不大。
二、構(gòu)成要件故意
責(zé)任主義是大陸法系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其強(qiáng)調(diào)“無罪責(zé)即無刑罰”,只有在兼具責(zé)任能力與故意或過失時,才能就行為人所實(shí)施的行為進(jìn)行非難。[5]這體現(xiàn)的是消極的責(zé)任主義,除了要求行為人具備非難可能性以外,還要求法益遭受侵害的結(jié)果或危險在主觀上能歸責(zé)于行為人,即行為人對實(shí)施的違法行為具有故意或過失。在刑法理論發(fā)展的過程中,故意在犯罪論體系上的地位也發(fā)生了變化。目的行為論之前的犯罪理論將故意與過失視為罪過的兩種形態(tài),而今日的犯罪理論將故意和過失從責(zé)任階層提前到不法階層進(jìn)行考察。因此犯罪故意也被稱為“構(gòu)成要件故意”,其包含認(rèn)識因素和意志因素,行為人不僅要認(rèn)識到客觀的構(gòu)成要件事實(shí),還要基于該認(rèn)識意欲實(shí)現(xiàn)不法事實(shí),簡言之就是對實(shí)現(xiàn)不法事實(shí)的“知”與“欲”。
認(rèn)識因素中包含諸多內(nèi)容,如行為、行為對象、結(jié)果、因果關(guān)系等,在本案中需要討論的是行為對象。本案中行為人涉嫌的是運(yùn)輸毒品罪,行為對象是“氯巴占”這種被國家列為管制的藥品,在刑法上被評價為毒品的藥物。此時涉及對犯罪事實(shí)的認(rèn)識的不同階段,第一階段是對該當(dāng)構(gòu)成要件的事實(shí)的認(rèn)識,如對于將他人所有的財物轉(zhuǎn)移到自己控制之下這一形式上的事實(shí)的認(rèn)識;第二階段是對該當(dāng)構(gòu)成要件事實(shí)的社會性意義的認(rèn)識,例如對實(shí)施“盜竊”這一事實(shí)所包含的社會意義的認(rèn)識;第三階段則是對刑法關(guān)于該行為的規(guī)定的認(rèn)識,例如《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guī)定盜竊數(shù)額較大的公私財物應(yīng)處刑罰。[6]對構(gòu)成要件事實(shí)的認(rèn)識要達(dá)到上述的第二階段,才能認(rèn)定行為人具備故意,如果行為人連事實(shí)所包含的社會意義都沒有認(rèn)識到,則不能進(jìn)行故意的非難。本案中行為人對代購的藥品系“氯巴占”這一事實(shí)的認(rèn)識肯定具有,但在第二階段即對“氯巴占”所包含的社會性意義是否有認(rèn)識則存有疑問,行為人可能對該藥品未在國內(nèi)獲批上市甚至系管制藥品有了解,但將此作為對“氯巴占”包含的社會意義有認(rèn)識的依據(jù)則值得商榷。
三、緊急避險
緊急避險是《刑法》中非常重要的制度,大陸法系國家一般都有規(guī)定,我國《刑法》也在第二十一條①《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一條 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chǎn)和其他權(quán)利免受正在發(fā)生的危險,不得已采取的緊急避險行為,造成損害的,不負(fù)刑事責(zé)任。就緊急避險作出規(guī)定,對于成立緊急避險者不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緊急避險作為一項重要的制度有其適用的條件,只有滿足這些條件才能認(rèn)定行為人屬于緊急避險,阻卻行為的違法性。
(一)現(xiàn)在的危險
緊急避險的首要條件是發(fā)生現(xiàn)實(shí)的危險,即法益正遭受現(xiàn)實(shí)的損害或危險。動物襲擊和疾病等都可以作為緊急避險中危險的來源。并且緊急避險的危險針對的可能是自己的利益,也可能是他人或者國家的利益。本案中的行為人面臨的正是自己的兒子患有罕見的癲癇疾病,到處求醫(yī)卻未能找到救治辦法,其子的生命健康利益一直遭受著疾病的威脅。緊急避險的危險必須具有現(xiàn)在性,即法益處于受到侵害危險的狀態(tài)且尚未解除。時間的判斷需要結(jié)合具體的案情,這種時間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是長期持續(xù)性的危險狀態(tài),只要危險有變?yōu)楝F(xiàn)實(shí)侵害結(jié)果的可能性即可。本案中行為人的兒子自小便遭受疾病的威脅一直未能治愈,病魔隨時有侵害其子身體健康和生命的可能性,而行為人代購藥品的時間處于其兒子生病期間,因此符合緊急避險的時間條件。
(二)不得已
緊急避險要求行為人出于不得已而損害另一較小或同等法益,這是緊急避險的補(bǔ)充性要件,該要件意味著避險行為必須是消除危險的必要手段,如果有其他更好的途徑能消除對法益造成的危險,則行為不成立緊急避險。避險行為的必要性應(yīng)當(dāng)以社會一般人面臨行為人當(dāng)時的處境來考察,結(jié)合危險發(fā)生時的客觀情況進(jìn)行判斷,若彼時存在一些更優(yōu)的解決辦法,則不能認(rèn)定避險行為的必要性。本案中行為人的兒子患有罕見的癲癇病,經(jīng)四處醫(yī)治仍未能治愈,在醫(yī)生建議后方知“氯巴占”能起到一定效果,試想如果國內(nèi)有藥效更好的替代性藥品,誰會冒著風(fēng)險去代購呢?也許有人說國內(nèi)并不是沒有其他藥品,但從媒體報道可知國內(nèi)現(xiàn)有的藥品相比“氯巴占”副作用較大,作為需要長期服用的藥物來說難免會對身體機(jī)能造成傷害,所以相比較而言代購“氯巴占”確實(shí)屬于不得已而為之。
(三)避險意思
行為人必須認(rèn)識到正在發(fā)生的危險,并意圖以避險行為保護(hù)更高的利益。本案中行為人對兒子遭受的疾病痛楚有認(rèn)識,且為了治病而不惜違反法律,因此具有避險意思。但行為人只是認(rèn)識到代購行為可能有違藥品管理法規(guī),并未認(rèn)識到其行為可能違反《刑法》中毒品犯罪的規(guī)定。
(四)限度條件
緊急避險的限度條件是未超過必要限度,造成不應(yīng)有的損害。正當(dāng)防衛(wèi)的對象是危險來源,即所謂“正對不正”;而緊急避險的對象是另一合法利益,實(shí)際上是通過損害另一合法利益來保護(hù)當(dāng)前的法益。所以在限度上緊急避險要比正當(dāng)防衛(wèi)嚴(yán)格,正當(dāng)防衛(wèi)只要沒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就不會防衛(wèi)過當(dāng),而緊急避險則只能在必要限度內(nèi)實(shí)施。緊急避險的必要限度是什么,刑法理論上存在爭議。傳統(tǒng)理論認(rèn)為緊急避險所造成的損害要小于所避免的損害[7],但該說不利于發(fā)揮緊急避險的作用,緊急避險本就是為了鼓勵人們?yōu)榫S護(hù)更重要的利益而放棄價值稍低的利益,如果僅根據(jù)損害結(jié)果來進(jìn)行比較難免導(dǎo)致避險過當(dāng)?shù)恼J(rèn)定過于寬泛。利益衡量說則認(rèn)為避險行為保護(hù)的利益應(yīng)明顯地高于受侵害的利益[8],在個案的適用中要考察以下幾個要素:法益的位階關(guān)系,如人格利益優(yōu)于財產(chǎn)利益;法益受影響的程度,為了保護(hù)較低位階的法益免受更嚴(yán)重的侵害,而不得已導(dǎo)致較高位階的法益受到輕微的損害,也符合緊急避險限度的要求;損害發(fā)生的可能性,被救助法益實(shí)際發(fā)生損害的可能性越大,則緊急避險成立的限度就越高;避險成功的概率及實(shí)害風(fēng)險。[9]具體到本案來說,人的生命健康利益自然是無價的,但在位階上與作為集體法益的公眾健康比較確實(shí)難以得出結(jié)論。避險行為導(dǎo)致管制藥品擴(kuò)散并影響公眾健康的可能性較小,因為行為人只是為群內(nèi)同樣需要此類藥物的家長進(jìn)行代購,但行為人的兒子因疾病有損身體健康的可能性較大,相比較之下避險行為確實(shí)沒有超過必要限度。而且行為人避險成功的概率明顯很大,其兒子的疾病在藥物的控制之下得到明顯好轉(zhuǎn),從實(shí)害風(fēng)險的角度來看,行為人用制造一個抽象危險的緊急避險行為避免了一個具體危險的發(fā)生,因此可以承認(rèn)避險行為的正當(dāng)性。
四、違法性意識
違法性意識(或稱不法意識)是指行為人對其行為被法律所禁止有認(rèn)識,該問題在理論上存在諸多爭議,一般作為禁止錯誤展開討論。關(guān)于違法性意識有多種學(xué)說,違法性意識不要說認(rèn)為不法意識并不是故意的內(nèi)容,所以禁止錯誤并不足以故意導(dǎo)致犯罪不成立。[10]故意說認(rèn)為違法性意識應(yīng)作為故意的組成部分,行為人對其行為的不法存在認(rèn)識時方能認(rèn)定具有故意。[11]區(qū)分說認(rèn)為自然犯的故意無需存在違法性意識,法定犯則要求違法性意識作為故意的內(nèi)容。[12]責(zé)任說認(rèn)為不法意識是與構(gòu)成要件故意相互獨(dú)立的責(zé)任要素,因此行為人對不法意識的缺乏并不影響罪責(zé);但是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對法律的認(rèn)識錯誤不可避免時可以阻卻罪責(zé)。[13]故意說和責(zé)任說的支持者相對較多,兩種學(xué)說持對立之勢已久,直至今日仍有爭論,但責(zé)任說得到多數(shù)學(xué)者的支持。
筆者也贊同責(zé)任說,因為故意解決的主要是對事實(shí)的認(rèn)識和決意問題,違法性意識系規(guī)范評價與故意的關(guān)系不大,且禁止錯誤無法避免時仍可阻卻罪責(zé),不會像違法性意識不要說那樣絕對導(dǎo)致個案有違責(zé)任主義。本案的行為人正是缺乏違法性意識,沒有認(rèn)識到代購該管制藥品“氯巴占”的行為具備刑事違法性,因此屬于典型的法律認(rèn)識錯誤(或稱“禁止錯誤”)。但如上所述故意的成立并不需要具備違法性意識,因此需要進(jìn)一步審查禁止錯誤的回避可能性。禁止錯誤是否可回避要基于行為人的能力而非一般人來判斷,據(jù)不起訴書顯示行為人系碩士研究生,完全有獲取“氯巴占”相關(guān)信息的能力和現(xiàn)實(shí)可能性,因此該禁止錯誤可以避免,不能阻卻行為人的責(zé)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