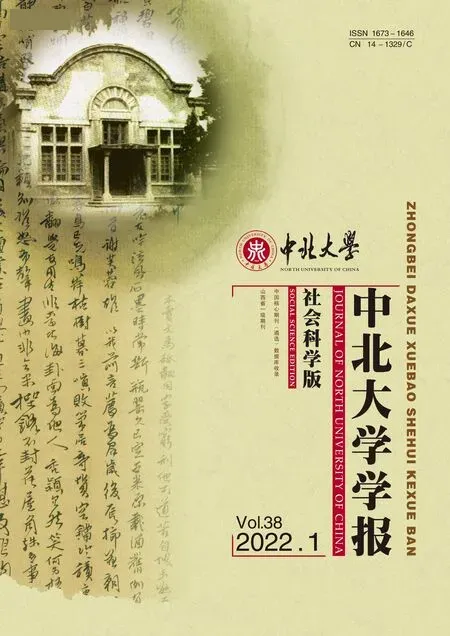存史·載道·化人 《劇談錄》的內容和結構特點及其文史觀
韓 婷
(安徽大學 歷史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康駢, 又作康軿, 字駕言, 池州秋浦(今安徽貴池)人, “篤于自修, 善論議”。[1]252據史書記載, 康駢于咸通中曾應進士試, 至乾符五年(878年)登第, 乾符六年(879年)舉博學宏詞科[2]561, 官至崇文館校書郎[3]1457。 后避廣明戰亂退居鄉里, 晚年曾以幕僚身份入宣州田頵幕府, 薦授中書舍人。[4]5479其札記體著作《劇談錄》成于乾寧二年(895年), 是康駢保留下來的為數不多的著作, 其版本有三卷本、 兩卷本之別, 歷代書目著作歸為子部小說類, 視其文學性多于史學性, 但《劇談錄》內容包含大量的歷史事實、 社會民情、 名宦軼事、 典故紀聞、 災異怪談等, 這些資料不僅可以佐史、 補史之闕, 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而且對文學、 社會學、 宗教學等學科的研究也具有相當的價值。
目前, 學術界對康駢及其《劇談錄》已有關注與成果: 從研究的綜合性來看, 南京大學韓曉嬋、 淮北師范大學王晶和西南大學胡燕三位碩士, 以《劇談錄》為研究對象, 展開了文學視角的研究。 其中韓曉嬋的《〈劇談〉箋證》對《劇談錄》所錄內容中卷上的其中9條和卷下的其中8條合17條有疑義和舛誤的內容作了箋證; 王晶的《〈劇談錄〉研究》則探討了《劇談錄》的文體特征, 認為《劇談錄》是介于筆記體小說與唐傳奇之間的特殊文體, 它亦真亦幻的內容及其對于后世的影響, 說明其在小說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進而將其內容進行了分類并探討其在敘事、 人物刻畫和語言風格上的特點; 胡燕的《〈劇談錄〉研究》突出特色是從心理學角度談了晚唐士人宗唐與不遇、 入世與出世、 命定思想與懷疑批判、 追慕盛世與感傷當下的多重矛盾心態, 從文學角度談了《劇談錄》的藝術成就和價值。 另有, 王琳的《〈劇談錄〉的描寫藝術》一文從《劇談錄》所載的俠義故事入手, 對其在情節結構、 人物描寫和語言藝術方面的描寫藝術進行了分類分析。 《〈劇談錄〉及其作者史實考辨》一文則針對歷史文獻中關于康駢本人的籍貫故里不清、 功名時間不明、 仕途官職參差、 名字用字模糊的現象做了考證, 可作一家之言; 其文對《劇談錄》所載史實內容的考辨相對有限, 集中在對“潘將軍失珠”“袁相雪換金縣令”“說方士”三條史事的簡介和論略。 除此以外, 對《劇談錄》有所涉及的研究, 多將其作為唐代傳奇和筆記小說群體的構成者進行群書性、 整體性研究與分析。 由此來看, 目前, 學界對《劇談錄》的已有關注成果相對集中于文學藝術角度, 對其史學價值和功用的探討尚有可為之處。 從康駢個人的主觀著述目的和緣由看, 康駢的《劇談錄》具有著文存史娛情和文以載道的雙重文史觀念, 康駢在收錄內容條目之后夾雜個人看法和觀點的夾敘夾議式書寫方式更是展現了唐末士人, 尤其是康駢個人的價值取向和處世態度。
1 《劇談錄》的內容特點
《四庫全書總目》言其“記天寶以來瑣事, 亦間以議論附之, 凡四十條”[5]1210。 按《四庫全書總目》認為其記天寶以來之事, 其據當是有二: 其一, 《劇談錄》卷上“劉平見安祿山魑魅”條定之, 然細讀該條乃記咸通中道士亦是五經博士盧斝。 盧斝假稱生于隋代, 并與天寶時劉平執友修道, 劉平口稱自己見過安祿山魑魅, 安祿山乃為邪物所輔。 事涉天寶, 故此《四庫全書總目》定其所記之事年代及于天寶。 其二, “廣謫仙怨詞臺州刺史竇弘馀撰”條, 考證竇弘馀撰《謫仙怨》詞序于本事有誤, 追述本事, 言及明皇馬嵬賜死楊貴妃, 悲傷哀婉之余吹笛成曲, 為有司所錄, 后將此曲進呈玄宗請名, 玄宗名之《謫仙怨》。 康駢此條敘及唐玄宗并非記唐玄宗事, 其主要為校正竇弘馀之序而追述本事。 實際上, 該書內容反映唐宣宗至唐昭宗年間朝野逸聞, 追述淵源之際, 也常涉及文宗朝事。 據作者自序稱, 書成于乾寧二年(895年)。
《劇談錄》的內容量并不大, 但其包含的信息量卻是廣泛的, 涉及唐末多個領域, 最為突出者是名宦軼事、 典故紀聞、 災異怪談之類, 為后世展示了唐末社會的多角度圖景。 今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收錄校點本《劇談錄》, 較為精良, 上卷收錄20條, 下卷收錄22條, 附有逸文4條, 共計46條。 其中有21條內容與高官權貴相關, 此外, 康駢繼承了魏晉以來好言鬼怪靈異、 僧道神仙、 方士數術的風氣, 全書有18條含有民間信仰或制度性宗教的價值面向, 所余則多與任俠之風、 社會風氣奢靡腐敗或文壇典故軼事等時事有關。
1.1 重視記載名宦軼事
在內容上, 康駢首先十分注重對名宦軼事的記載。 “李朱崖知白令公”條記載李德裕與白敏中,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記令狐绹相國, “劉相國宅”記劉瞻相國, “鳳翔府舉兵討賊”記鄭相國, “曲江”記裴休相國, “元相國謁李賀”記元稹相國等。 耳目所見多為名人, 尤其是對宰相事件的記載, 宰相一言一行關乎政治興廢和社會風貌, 這充分體現了康駢著書關注政治動態的價值取向。 而事涉之人非名人時, 則多關神仙鬼怪之事。 如“狄惟謙請雨”條講述狄惟謙為晉陽縣令時, 屬邑大旱, 自禱雨于晉祠數旬無果。 乃邀當地女巫郭天師同入晉祠禱雨, 巫者先后兩次禱雨, 言三日、 七日必雨, 且將境內亢旱災沴歸咎于縣令無德, 狄惟謙只得引罪, 然至期亦未雨。 巫者愈逃離, 狄惟謙見其所言不中又曾侮辱自己無德致旱, 遂謀擊打巫者, 便高喊:“左道女巫, 妖惑日久, 當須斃在茲日, 焉敢言歸!”[3]1472于是當眾審判巫者, 笞背三十, 投于潭水, 令設席焚香, 合縣驚愕, 奔走相告縣令打殺天師, 觀者如堵。 討擊巫者后, 天降甘霖, 亢旱數月遂解。 該記載反映了唐人在面臨干旱時, 常有祈雨的操作, 祈雨的主角包括官吏、 巫覡等, 此事中祈雨后半程審判巫者又繼而成為祈雨儀式的一部分。 雨下之后, “士庶數千, 自山頂擁惟謙而下。 州將以杖殺巫者, 初亦怒之, 既而精誠有感, 深加嘆異, 與監軍發表上聞。 俄有詔書褒獎, 賜錢五十萬, 寵賜章服, 為絳隰二州刺史, 所理咸有政聲。”[3]1472狄惟謙、 合縣士庶、 州將對祈雨、 請巫者祈雨、 以巫者祈雨等一系列變換中的祈雨形式的態度從信巫到殺巫, 從驚愕到簇擁, 從初怒到嘆異, 過程中其態度和心理是矛盾復雜的。 康駢對該事的選取摘錄, 體現康駢對統治階級在天人感應理論支撐下的禱雨活動持認可的態度, 對狄惟謙殺禱雨失敗巫者的行為持贊許之態的同時, 表達了對巫術方士的所謂法術的懷疑, 并在此條最后附上朝廷敕書對狄惟謙祈雨之事的褒獎之詞更說明了康駢在此事上的價值取向。
1.2 摻雜大量災異怪談
《劇談錄》充滿彌漫性民間信仰的神仙鬼怪、 災異怪談。 “劉平見安祿山魑魅”“王鮪活崔相公歌妓”“崔道樞食井魚”“李生見神物遺酒” 4條帶有明顯的鬼神觀, 言及冥間之事, 反映了唐人對鬼神之說多持信而有之的態度。
“龍待詔相笏丁重相于駙馬附”“郭鄩見窮鬼”“裴晉公天津橋遇老人”“道流相夏侯譙公”4條充滿前世命定觀念, 認為人之前途命運可以預知推算, 其中亦塑造了較多道流術士相面之術。
“韋顓梟鳴”條記載韋顓有才學不中第, 窮困潦倒, 寄居韋光之所, 后韋光中第, 韋顓修賀禮, 坐于堂感慨之余, 忽檐際有鳴梟, 韋顓以為妖禽作怪, 不祥之兆, 恐橫罹災難, 持杖逐之, 俄而榜到, 韋顓登第。 康駢認為:“世以鵩至梟鳴, 不祥之兆。 近觀數事, 亦不然乎?昔鄧艾梟鳴牙旗, 乃軍勝之兆, 張率更聞于庭樹, 亦授官之祥。 以此推之, 未必皆為不吉者。”[3]1490他一方面認可符瑞感應之說, 另一方面又對符瑞感應抱有懷疑之態。 “命相日雨雹”條言乾符六年(879年)五月崔沆、 豆盧琢策拜為相之日, 天雨雹大儒雞卵, 以為不祥之兆, 果在明年大寇攻陷京師, 二相皆及于難。 作者在其后言曰: “天意乎?非人事也!”[3]1491“御史灘”條亦多祥瑞感應之言。 可知, 康駢抱著一種天人感應的災祥理念來看待人事與時事, 充滿彌漫性民間信仰的鬼神觀、 命定觀與福禍感應的災祥理論。
1.3 好于關注僧道及相關軼聞
除了命定觀、 鬼神一類的中國傳統民間信仰以外, 康駢《劇談錄》里充斥著大量僧道及相關軼聞, 體現了唐代三教融合, 宗教繁榮的整體社會背景。
“玉蕊院真人降”“老君廟畫”“嚴使君遇終南山隱者”“說方士”4條反映了唐末士人慕道之風, 在現實離亂的社會背景下, 追求宗教解脫的愿望。 在“說方士”中康駢分別言及方士5人, 其中既有“靈驗變通, 諸如此類”的驚異與懷疑, 亦有“深得真道”的贊許。 可見, 康駢對神仙異術得態度尚顯曖昧。 “真身”條康駢更是對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年)自鳳翔迎釋迦牟尼中指節骨真身之事不吝筆墨。
都城士庶奔走云集, 自開遠門達于岐川, 車馬晝夜相屬, 飲饌盈溢路衢, 謂之無礙檀施。 至京日, 上與諸王親御城樓。 坊市以繒彩結為龍鳳象馬之形, 紙竹作僧佛鬼神之狀, 幡花幢蓋之屬, 羅列二十余里。 間之歌舞管弦, 雜以禁軍兵仗。 緇徒梵誦之聲, 沸聒天地。 民庶間有嬉笑踴躍者, 有悲愴涕泣者。 身以寶輿舁之, 居于內殿數月……先是, 眞身到城, 每坊十字街以磚壘浮圖供養, 妖妄之輩互陳感應。 或云夜中震動, 或云其上放光, 以求化資財, 因此獲利者甚眾。[3]1496
對懿宗佞佛迎真身事件的記述細致入微, 對迎真身事件帶來的社會影響更是談及頗多, 為我們保留了豐富的直觀史料。 康駢在文中夾敘“有好事者密詢放光之由, 云以大云母片窺看, 遠而望之, 靡不傾信耳”[3]1496, 更是一語戳穿所謂佛放光的顯靈事件是人為, 反映出康駢對崇佛的懷疑與反對。 康駢在此條之后附自己讀《名僧傳》宋文帝與僧人永那跋摩的對話, 用以表明自己對帝王禮佛的理解和應持有的觀點和態度, 說明帝王禮佛不在于吃齋念佛、 以身殉物, 而應持道在心, “以四海為家, 萬民為子, 出一嘉言, 則士庶咸悅; 布一善政, 則人神以和。 刑清則不夭其命, 役簡則無勞其力。 然后辨鐘律、 定時令。 鐘律辨則風雨調, 號令時則寒暑節。 知百姓之饑, 斯所以就于無饑; 知百姓之寒, 斯所以就于無寒。 如此, 持齋亦大矣, 不殺則眾矣, 安在于闕一時之膳, 全一禽之命, 然后乃宏濟也?”[3]1497“白傅乘舟”條以白尚書為代表, 表現出唐末士人向往隱逸逃遁, 避世修行的趨向。
1.4 多面展示各階層人物形象
《劇談錄》內容多見當時社會的任俠風氣。 “潘將軍失珠”條塑造一位十七八歲的女子, 輕盈可飛, 有俠者風范, 為潘將軍找回丟失的寶珠。 并告誡王超“便可將還, 勿以財帛為意”, 一改唐末世風日下, 追求名利的敘事背景, 告誡人們減少追求富貴名利之心。 “田膨郎偷玉枕”王敬宏小奴有俠者之風, 助其為文宗皇帝找回禁中所失于闐國獻貢之白玉枕, 卻不以財帛為目的, 隱逸蜀中。 “管萬敵遇壯士”條管萬敵逞強使力, 眾皆驚愕, 棋逢對手之后, 神力遂消失。 “張季弘逢惡新婦”亦是勇而有力之人, 遇一老媼求助, 言其新婦悖制, 然孔武有力, 制之不可。 張季弘與新婦論理, “新婦拜季宏曰:‘乞押衙不草草, 容新婦分雪: 新婦不敢不承事阿家, 自是大人憎嫌新婦。’ 其媼在傍謂曰:‘汝勿向客前妄有詞理!’新婦因言曰, 只如某年日月, 如此事, 豈是新婦不是?每言一事, 引手于季宏所坐石上, 以中指畫之, 隨手作痕, 深可數寸。 季宏汗落神駭, 但言道理不錯。”[3]1483在展現張季弘的形象之外, 新婦形象亦躍然紙上, 同時, 將唐代婆媳關系和女性形象展現無疑, 一改將婦女塑造為溫順賢良的柔弱形象, 將其塑造為敢于反抗、 敢于直面強權的俠者風范。
書中還描繪復雜多樣的女性形象。 康駢在《劇談錄》“潘將軍失珠”塑造了輕盈可飛的俠女形象, “張季弘逢惡新婦”塑造了新婦這樣的不畏強暴、 孔武有力的新女性, “老君廟畫”塑造了投入道觀的女冠群體, “狄惟謙請雨”塑造了女巫的形象, “孟才人善歌”塑造了武宗孟才人的忠貞烈女形象。
此外, 該書內容中還多涉及長安城中的古跡, 如唐昌觀、 老君廟、 慈恩寺、 含元殿、 劉相國宅、 李德裕宅、 曲江亭等, 都為后世了解唐代社會風貌提供了重要線索和窗口。
2 《劇談錄》的結構特征
在結構上, 《劇談錄》與大多數唐代筆記小說類似, 每條獨立成篇, 各條之間互補連屬, 相互并無聯系。 每條以簡短內容命以標題, 簡要展示本條核心內容, 當然亦不乏內容繁雜, 條目題名不能概括所載內容, 條目本身不具備故事連貫性, 在核心人物選取上亦于現今不同。 如“潘將軍失珠”條, 事件與名宦有關, 但內容對名宦本人所寫甚少, 核心意旨亦非在名宦身上, 卻以名宦之事命名, 僅由于寶珠為潘將軍所有, 內容記載于潘將軍所述并不多, 更似豪俠故事。 這也為我們了解唐人札記文章的命名觀提供了一個案例。 為筆記小說中的每個條目命以短名列為目錄, 在唐代諸多筆記小說中亦不多見, 大多筆記小說僅分卷而已, 甚至并無分卷, 雜然相揉, 僅分段落以明條目。 可知, 唐代筆記小說在編撰手法上尚不成熟, 而《劇談錄》無論是有心為之還是無心插柳, 在這一點上有較好的處理方式, 至宋以后筆記小說各條目多有題名, 乃至發展為章回小說。
《劇談錄》在結構上的另一個特點在唐代筆記小說中則更是少見。 康駢在條目之后或以第一人稱雜以議論, 或借他人之口做出評價, 或借古書所言進行點評。 唐代筆記小說數量豐富, 內容多分條記述相關人、 事、 物, 《劇談錄》與其他唐代筆記小說相比, 其內容選取上雖有自己的特點卻無創新, 然而在諸多筆記小說中能在每條記述之后, 頗類史書雜以作者議論者僅一二而已。 通過總結康駢的點評議論, 不僅可以知曉康駢的史學觀, 而且可以透過個案了解唐末士人的史學觀和價值取向。 在史料選取上, 康駢側重高官權貴及可資勸諫之事的史料選取觀。 《劇談錄》 46條中有21條與高官權貴相關, 約占半數。 康駢以高官宰輔作為選取人物的主要構成, 意在通過敘述高官故事, 并夾以自己的議論, 闡發自己的政治觀點。 如“李朱崖知白令公”條, 康駢不厭其煩地將白敏中平叛之事詳加記載并多有贊賞之詞, 深刻揭示了如康駢一般的唐末士人在目睹當前朝廷實力衰落、 藩鎮割據、 戰爭頻仍的局面, 對如白公之強有力的將官寄托的希望與認可, 并在其后將同列唱和贊賞之詩悉數羅列展示了當時朝廷之中包括宣宗及諸朝臣對白敏中凱旋的重視與肯定。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條在敘述宣宗與令狐绹關于治國理政的討論之后, 康駢議曰: “凡懷才抱器, 有時而通, 非得茍容, 雖遇不顯。 向使明主有任賢之意, 近臣無專對之能; 徒彰妄進之譏, 方病退慚之說, 殊恩厚渥豈及于身?是以君子勵志飭躬, 以遭逢之運, 良有旨哉。”[3]1461康駢載此事意在說明士子無論何時當以提高自我能力與修養為重任, 必有被賞識重用之日, 不應妄自菲薄、 急功近利。 同卷有“續坤蹶馬”條, 載京師醫者續坤醫久病不愈大將得一馬匹, 因其步驟多蹶賤價賣于王生。 得遇伯樂, 調習步驟, 縈轉如風, 得賣高價。 康駢議曰: “是以物之逢時亦有冥數, 不遇其主, 則駑驥莫分。 乃知耨莘野, 筑傅巖, 未遇良途, 奚異于此。”[3]1467康駢在此條中除持有命定觀外, 更多的是討論馬遇到伯樂, 甚至于任何人和任何職業前途遇到知遇之人的重要性。 兩條內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康駢的矛盾性, 一方面盼望有識人之伯樂, 一方面又相信命數, 勸諫士人安心學識。 在“含元殿”“鳳翔府舉兵討賊”中康駢皆言億兆人心未厭棄唐德, 皇帝有中興之舉, 則億兆人民之心復新于唐德。 可見, 康駢此時對大唐仍抱有希望, 以及以康駢為代表的相當一部分支持唐王朝的士人都有向往盛唐、 恢復盛唐的幻想與期待, 并抱著僅有的希望, 呼喚中興之主和積極入世的士子, 同時, 又不時產生懷疑與失望, 在鬼神僧道和追求隱逸的麻痹下堅定信心, 呼吁與感慨。 這都體現了唐末士人在隱逸與入世之間的矛盾處事心態, 政治紛亂下無能為力的無奈感, 最終以一種記事傳史的態度選錄成書, 聊備一說, 為后世好事者提供談資和勸諭之效。
3 “文以載道”的文史觀念
康駢借助《劇談錄》夾敘夾議的撰寫方式, 傳遞了自己的價值取向和處世態度, 反映了康駢作為晚唐士人的文史觀念, 這種敘述形式本身又構成了《劇談錄》引人關注的特點。 康駢生活于晚唐, 其個人生活顛沛多變, 經歷豐富, 康駢在《劇談錄》的自序中言其曾游歷于秦洛之間, “新見異聞, 常思紀述。 或得史官殘事, 聚于竹素之間, 進趨不遑, 未暇編綴”[3]1459。 后又因時局動亂回到自己的家鄉, 過程中書稿亡逸頗多。 而家鄉也是離亂不定, 深感無可作為, 便深入云林間, 想要“敘他日之游談, 跡先王之軌范, 不可得矣。”[3]1459想來自己于國無功, 又怎能吝惜筆墨?鑒于“時經喪亂, 代隔中興, 人事變更, 邈同千載, 寂寥埋沒, 知者漸稀; 是以耘耨之余, 粗成前志”[3]1459, 康駢作書目的之一是恐怕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人事變更, 先前為人所知的史事難以留存后世, 并著意于記錄史官未及之殘事。 由此, 康駢帶有“存史”意識來編撰《劇談錄》, 大量名宦軼事、 典故紀聞, 既有勸誡后世的“載道化人”之意, 亦有將之保存下來以補史闕的用意。 雖不乏鬼神仙怪、 靈異任俠之說, 但從中亦可見唐末五代社會風尚和民俗特點, 表達自己的價值取向。
該書收錄條目之末或于條目文中多附加康駢發微之詞, 如其塑造的多變的女性形象, 對不畏強權的女性和貞潔烈婦抱著同等的記敘態度, 體現了唐代相對寬容的社會環境, 時代所塑造和標榜的理想社會女性與社會實態中復雜多樣的女性是同時交叉存在的, 女性社會地位是一個多面向的復雜社會動態構成, 并非單一格局。 再如, 康駢對宗教、 天命等信仰理論與體系的曖昧反復的論述, 也反映了時代背景下, 對宗教和怪力亂神之說的模糊定義和變動態度。 對統治者崇佛佞佛的奢靡現象婉轉批判, 對治國之要首在用人, 士子當勵志奉君, 對強干忠君的軍事將領的肯定, 都體現了康駢存史與史論并重的歷史記述觀, 在有唐一代的筆記小說中不甚多見, 是筆記小說發展史中的重要代表, 這種以史為鑒的勸諭良言, 充分展示了作者的政治觀點和價值取向。 康駢在描述史實、 記人記事記物之時, 又不時揭露賣官鬻爵、 奢靡成風、 不思進取、 民不聊生的社會不良現象, 更是體現了史家常有的人文關懷情懷和以史為鑒、 經世致用的史學功用觀念。 面臨 “貞觀之風”“開元盛世”等代表著“大唐盛世”榜樣符號和共同記憶的初唐一去不復返的局面, 在藩鎮割據、 農民起義不斷、 動蕩不安的社會背景下, 文人顯得更無用武之地, 小民之于帝國的渺小和無力感, 在這樣一種復雜多樣的背景和心態下, 康駢作為晚唐時期的文人, 選擇徜徉在文史作品中, 寄托于宗教鬼神的異說中。 當然, 康駢對靈異鬼怪的書寫是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的, 這是唐代筆記小說群體的共性特征, 與漢魏以來傳奇作品、 筆記小說的撰述傳統和唐代濃厚的“三教”氛圍是密不可分的。 但他們仍不忘關注政局, 不放棄任何可能存在的救世機會的情懷, 在消極懷疑與積極宗唐、 入世與隱逸、 思慕盛唐與反思當下、 天命前定與批判反抗的矛盾中尋求歷史真實與虛幻故事的結合, 在虛實之間追求平衡, 以備勸誡與寄托, 聊為后世載道化人, 以史為鑒。 由此, 《劇談錄》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唐末士人, 尤其是康駢個人的文以存史、 文以載道、 文以化人的文史觀, 值得引發關注與省思。 當然, 其不足之處, 如小說中充斥著的迷信色彩, 故事中怪力亂神的成分降低其本身的可信度; 記載史實時缺乏嚴謹的史學考證, 出現史實錯訛, 這些也是不容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