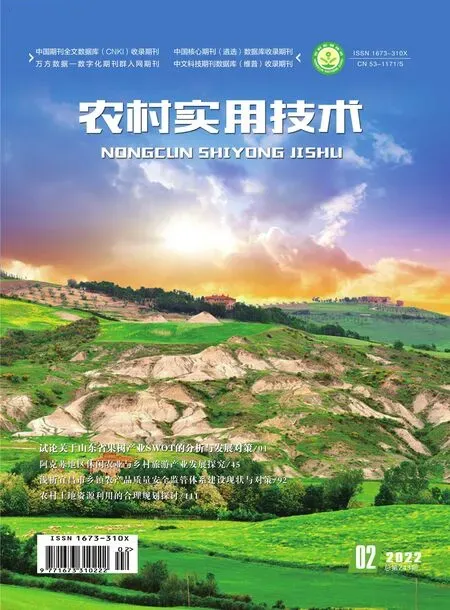共同體視角下鄉村鄰里“互助帶娃”的行為研究
呂 龍 婁康杰
(云南師范大學,云南 昆明 650500)
1 問題的提出
面對農村難以獲得有效的獲利機會,農村青壯年(大多為人父母)只能前往城市地區尋求獲利機會。他們只能將嗷嗷待哺的孩子交給年邁的老人照看。據有關數據顯示:“留守兒童”雙方父母都在城市打工的有將近690萬,他們生活在鄉村的場域,年邁的老人不僅需要照料“留守兒童”還得維持家庭生計,在農村存在一定的“農忙”時間,在平時照顧孩子的爺爺奶奶都需要進行農業生產,這樣產生了在“農忙”時節留守兒童無人照顧的困境,面對這樣困境,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本文基于鄉村鄰里共同體建設視角下,探究行之有效的這一困境的對策。
2 共同體理論概述
鄉村社會的發展經歷了從梁漱溟筆下“倫理本位,職業分立”再到費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的熟人社會”。“差序格局”由一根私人關系構成的網絡,[1]形成了沒有陌生人的社會。而當下的鄉村社會的圖景,學者賀雪峰的用“半熟人社會”甚至“無主體熟人社會”。對于當下鄉村社會的不斷搬遷,黨中央在論述農村社會建設中指出“積極推進農村社區建設,健全新型社區管理和服務體系把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2]滕尼斯看來:共同體是一種持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種原始的或者天然狀態的完善統一體”。共同體的類型主要是建立在自然基礎之上群體(家庭、家族)里面實現的,此外,他也可能在小的、歷史形成的聯合體(村莊、城市)以及思想的聯合體(友誼、師徒關系等)里面實現、共同體是建立在有關人員的本能的中意或者習慣制約的適應或思想有關的共同體記憶之上的”。
3 鄰里間共同體“互助帶娃”的互助行動
3.1 血緣共同體代際之間“互助帶娃”的互助行動
張佩國從農民的細微瑣碎的日常生活的視角分析長江三角洲地區農家生計,進而對鄉村血緣共同體進行分析[5]。基于上述部分學者的分析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鄉村血緣在我國鄉村存在已久,然而由于我國長期以來的城鄉分離開政策,導致農民生計模式不斷變遷,從年輕人的“城鄉兩棲生活”到農民理性家庭分工模式:年級稍微較大“中堅農民”在家種田并且承擔他們年輕子女進城務工而不得不留下的下一代子女的照顧任務,這樣照顧孫輩一代的子女的行為是基于我們鄉村的血緣共同體的紐帶聯系作用。
3.2 地緣共同體鄰里之間“互助帶娃”互助行為
在滕尼斯的“理想的社會類型”社會中對于村落共同體的重構就是從血緣共同體發展為地緣共同體,并最終形成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系和對共同居住地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形成人與人之間親密關系和強烈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對于我們鄉村鄰里間的“互助帶娃”起著必不可少的作用,我們都知道鄉村是一個農業社會,農民的主要生計手段就是種地。學者賀雪峰認為當前中國農村的家庭結構存在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一家兩代人,既務農又務工,獲得務農和務工兩筆收入,仍可以維持相對較高的生活質量。
3.3 親緣共同體間“互助帶娃”的“救急”行為
與血緣共同體以男性為主體不同,親緣共同體:基于血緣、地緣和情感而建立起來的共同體稱為親緣共同體[6]。從以上親緣共同體定義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親緣共同體是我們農村鄰里之間“互助帶娃”的“救急”行動,當農村鄰里之間同時面對“農忙”時,親緣共同體是我們解決無人照看“留守兒童”困境時的最后途徑。在村民簡單的行為邏輯中,他們在需求照顧兒童的時候,他們往往最先是血緣共同體里獲得需求支持。
4 共同體視角下鄰里“互助帶娃”的存在現實困境
4.1 村落共同體“衰敗”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是這樣描述“中國的鄉土社會的基層結構是一種所謂’差序格局’,是一個“一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在一個安居的鄉土社會,每個人都可以土地都可以自食其力的生活時,只是偶然的臨時的非常狀態中才需要在不同的程度的結合,因而鄉土社會人民常常維持“差序格局”的社會[7]。然而隨著社會主義中國的建立,國家先后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隨后進行人民公社體制的建立,摧毀了村落中基于地緣的共同體,更為顯著的是: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推進和市場經濟的建立,進一步加速了鄉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導致了當下鄉村社會日益原子化,從“熟人社會”到“半熟人社會”再到“無主體的熟人社會”。
4.2 鄉村鄰里間共同的“農忙”
對于仍然堅守在鄉村生活的村民,他們基本生計都是以農業的種植來維護基本生活,農業的生產要遵循基本的時令節氣,在同一地域中,地緣和血緣共同體村民都有基本一致行為來進行農業種植,這就導致了村落里面的鄰里在同一時間的都忙于農業生產,在這一期間,村民“互助帶娃”因為共同的農業生產無法得到落實。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基層村委組織,可以將村落地緣、血緣、親緣共同體加以有效組織并且形成聯系廣泛的村莊共同體,村莊的互助行為特別是包括“互助帶娃”基本行為將會得到較好滿足。
4.3 鄰里共同體的“交叉”與“斷裂”
本文是基于村落共同體不同三個視角下(地緣共同體、血緣共同體和親緣共同體)討論農村鄰里間“ 互助帶娃”,從以上視角我們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我們討論的鄰里”互助帶娃“限制一定的空間范圍中的,而且根據筆者基于對于家鄉村民之間“互助帶娃”具體實踐中這樣空間范圍甚至被限制共同地緣相鄰的幾戶之間,導致了鄰里之間的幫助很難形成共同的需要。
5 鄉村振興助力村落共同體建設
5.1 鄉村振興助力鄉村互助社會組織建設
在筆者基于家鄉調研中發現,鄰里自發的“互助帶娃”不能滿足的村民的需要,在國家鄉村振興的戰略背景,加強鄉村互助社會組織建設,有助于村民們更好的完成互幫互助基本生活需求。社會組織,在已有的社會組織的研究中,一般將社會組織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以市場為主體的社會組織。市場經濟運行產生的,以平臺的方式為政府、企業以及個人提供相應的服務[8]。為企業和政府之間提供日益廣、深入,例如公證機構等。鄰里之間的互幫互助的行為,積極鼓勵并引導村民之間行為的組織化。并在此基礎上成立村名自愿基礎上的基于地緣共同體社會組織。地緣共同體鄰里居民可以發動親朋鄰里,提供互助服務或者積極參與。
5.2 互助社會組織建設助力鄉村鄰里“互助帶娃”
在國家鄉村振興不斷支持下,基層政府特別是村民自治組織和村民的共同配合下。鄉村鄰里間互助的社會組織在村民中的“互助帶娃”將會發揮重要作用,在上文中我們談到村落共同體對于鄉村鄰里間“互助帶娃”分析中,不管村民之間基于地緣共同體“互助帶娃”還是血緣共同體抑或是親緣共同體實踐,村民鄰里間的“互助帶娃”都存在各種各樣難以在共同體框架解決的實踐困境,通過對整個村落社會互助的社會組織再造,實現更廣闊意義上的村落共同體的建設。
5.3 鄉村振興實現村落共同體社區記憶復興
隨著鄉村社會原子化的加劇,鄉村社會記憶面臨著“記憶斷裂”的風險。學者賀雪峰認為:“社區記憶的對立面是社區不記憶,也即社區本身有無歷史的問題。構成對村莊性質影響的是村莊活的歷史而非死的歷史,是村莊過去的生活為村莊今天的生活留下的影響力”[9]因此,“對轉型期鄉村社會記憶的變遷進行考察,是探究鄉村社會性質的有效途徑之一”。[10]因此,在鄉村振興中應當重視村落共同體里社會記憶建設,發揮宗族的意識凝聚作用,從社區中生發出基于地緣的共同體。為鄉村鄰里間的“互助帶娃”提供“文化網絡”支持。
6 結語
本文基于滕尼斯共同體視角,論述鄉村振興背景下如何重構村落共同體以幫助農村鄰里之間“互助帶娃”行為,在大的村落共同體的視角下,筆者進一步將共同體劃分為地緣共同體、血緣共同體,親緣共同體三個維度。依據不同空間范圍,對象,互助頻率等不同方面論述大的共同體視角三個不同維度共同體在鄰里之間“互助帶娃”存在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