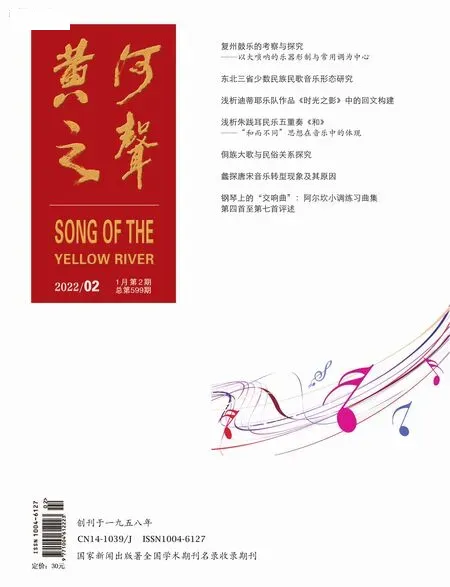蠡探唐宋音樂轉型現象及其原因
柳中岳 / 張思嘉
縱觀中國古時歷代的發展,歷經了漫長的歲月,伴隨著人類社會生產力及科技的進步,音樂也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中,其中唐宋時期可以說是中國音樂歷史發展道路上的重要轉折點,無論是在音樂的形態、性質、功能、還是表演場合都有不同的特點,宋代在繼承唐代文化的基礎上,又發展了具有自己時代特色的文化,這一定離不開兩代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教育制度、禮樂制度還有思想文化的發展。宋代音樂具有承上啟下的劃時代意義,它使中國音樂從宮廷音樂到民間音樂,由貴族化到民間化,由場面性到故事情節性,也為之后明清音樂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使我國音樂文化在中國古代史發展到一個高峰。
一、唐宋社會背景概述
(一)唐朝社會文化概述
唐朝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時期,唐太宗派兵攻打東突厥,俘其首領頡利可汗,不殺反而給予優待,在東突厥設立都督府,任命突厥貴族為都督,管理突厥各部,設安西都護府管理天山以南直至蔥嶺以西、阿姆河流域的西域部分,唐朝上承魏晉南北朝,其文化受胡人習俗、佛教等外來文化影響頗重,唐太宗李世民曾言:“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秋,朕獨愛之如一。”所以當時的唐朝接納融入外來文化和音樂,還有“絲綢之路”的發展,也使得中原與各個國家、地域有了穩定的交流與交融。
經濟的高度繁榮,生活質量的極具提高,漸漸的人民開始不止于滿足“吃飽穿暖”的基本要求,普遍都希望能在精神上得到享受。詩人王維曾寫道:“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杜牧也曾寫道:“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由這些唐朝流傳下來的詩句可以窺見當時高度繁榮的經濟。
唐詩的創作就形成了中國古典詩歌當中一個鼎盛時期,中國是詩的海洋,而唐詩又是這海洋中涌起的最絢爛的浪花。唐代三百余年歷史中涌現出無數詩人墨客,如王維、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隱等人更是名垂青史、光照萬代的大詩人。正是由于無數著名的大詩人和默默無聞的小詩人一道構成了唐詩星光燦爛的景象,甚至足矣讓千百年以后的詩人、詩壇黯然失色。詩歌的繁榮也推動了當時音樂的繁榮,當時的歌姬也以能夠歌唱文人墨客的詩為榮。
(二)宋朝經濟文化概述
宋朝重文輕武,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為鞏固皇權,杯酒釋兵權,皇帝逼迫武將交出兵權。在此之后,北宋朝廷在打壓武官的同時,同時提高文官地位,倒是深諳“馬上得天下,馬下治天下”的道理,但卻較為偏激的實行重文輕武的國策,使宋朝出現了從未有過的文官政治局面,促進了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繁榮,如書院的昌盛、理學的形成、宋詞以及市民音樂的崛起等等。
宋代十分注重社會經濟的發展,宋代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不限制商業、重視南方地區發展的朝代。這是歷史上開發商業力度最大的發展時期,這也正是經濟重心由北方向南方轉移的關鍵時期。宋代歷朝歷代帝王較為重視經濟和技術發展,所以統治階級的支持也是宋代經濟繁榮的主要原因之中的一個。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曾說過:“中華民族的文化,源遠流長,始于趙宋。”正如中國十大傳世名畫——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一般,我們能夠從畫中看出北宋時期的城鄉生活的多姿多彩與熱鬧非凡的景象,以東京為例,據《東京夢華錄》記載,當時東京城內的大街上,酒店彩樓相對,店鋪屋舍雄壯,且門口廣闊,“每一交易,動則千萬”,些許樓店“三層相高,五樓相向”,手工業作坊甚多,幾乎家家門庭若市。所以筆者認為,宋朝繁榮的商品經濟,使得資本力量變得強大,可以為市民音樂的產生和發展提供相應的時間,場地和資金,因而市民音樂就逐漸發展起來了。
二、唐宋音樂文化特征及其轉型原因
由于唐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以及社會形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革,所以音樂轉型的現象出現也是必然的。宋朝音樂不僅承接了輝煌燦爛的隋唐宮廷燕樂,又為后代元明清世俗音樂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不管是從音樂的形態性質還是音樂的功能以及表演場合,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一)唐朝音樂特征及其原因
寺廟、宮廷音樂機構,如教坊、梨園、太常寺等場所是唐朝較為常見的音樂場所。西漢末年,佛教從天竺,即古印度、西域等地逐漸傳入我國中原地區后,經過了大約五百年的傳播與發展,唐朝時已達到了繁盛期。初唐經濟高度發達,休養生息、輕徭薄賦是當時國家采用的政策,除此之外還采取實行了一系列改革制度,如均田制與租庸調制,并且還有嚴密的戶籍制度。貞觀后期,經濟開始全盤恢復和快速發展,國力更加強盛,最終成就了“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中唐時,由于土地兼并的情況俞發嚴重,造成土地還授這一舉措無法實行。因此,初唐時期的租庸調制被取消,由“兩稅法”代替。此法即分為一年四季中的夏季、秋兩季分別征收。這一舉動調動了人民生產與勞動的積極性,推動了當時的農業發展,同時也增加了朝廷的賦稅收入。此外,自太宗以來,朝廷還對商業和手工業進行了扶植,這些政策使得唐朝的手工業和商業發展異常迅速。如此一來,經濟高度發達的唐代社會在當時便能很好使得社會各級階層人士能夠投人一定的錢財來從事佛教音樂等文化藝術類活動。所以佛教音樂的盛行,與當時發達的經濟是息息相關的。
唐時佛教音樂與寺廟的盛行,與各級階層的喜愛與支持是離不開的,尤其唐朝歷代統治者。唐高祖李淵在未臨朝稱制前便是一位虔誠的佛教信徒,他曾親自為了患病的皇子李世民去寺廟祈禱,后來還在此廟建造了一尊佛像供奉。唐太宗李世民從小又受到父親高祖的影響,他與眾多僧人的關系異常交好,在他的隊伍中還有僧人的參加,另外他還對佛教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佛教產生了進一步發展。女皇武則天可謂是最虔誠的佛教信徒,她撰寫了《開經偈》、禮敬高僧、建寺造像、支持譯經等舉措從多個方面對佛教做出了貢獻。其次,還有達官貴人以及王公貴族們對佛教的支持,他們對佛教的信奉與推崇僅次于統治階級。還有一個最主要的群眾階級,在封建社會期間,不同于王公貴族,大部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平民百姓仍然處在貧困線上,他們并不富裕,或逢天災人禍,甚至會連最基礎的溫飽問題都得不到解決。所以現實的環境決定了百姓們的意識形態,那就是相信佛教所提倡的因果輪回、前世報應、極樂世界等思想學說,據說玄奘高僧去世時,出殯者有千百萬人。“安史之亂”被稱為是大唐盛世的一顆“毒瘤”,在此期間戰亂頻繁,國家處于內憂外患的一個階段,但還存在“皆廢人事奉佛”的現象。由此可判,佛教在當時深入人心,當時全國各地都有人信仰與崇拜佛教,所以信佛也慢慢的成為了一種社會習俗,由于民間存在著大量的佛教信徒,也是造成了佛教繁榮興盛的一個重要因素。[1]
“太常寺”為九卿之首,由“太常卿”領導。作為國家重要的禮樂音樂機構,亦是國家禮儀制度不可分割一個重要部分。[2]教坊與梨園屬于唐代國家音樂機構,其中的燕樂在唐代興盛,這與朝廷為培養和管理音樂表演者而設立的教坊有很大關系。教坊始建于唐高祖李淵執政期間,后期宮廷設立“內教坊”;在紫禁城外和東京洛陽設有兩個“外教坊”。教坊的主要任務有培養音樂和舞蹈人才,教授、排練歌曲、舞蹈和散曲并演出。教坊根據藝人音色與技能等級分為幾個層次,如“宮人”、“內人”、“前人”等。唐玄宗年間,教坊的藝術家隊伍大大擴張。僅長安教坊就有一萬多名歌姬。根據崔令欽的《教坊記》所記載,每個教坊累計有325 部民族音樂、舞蹈和戲曲作品。
唐朝是以宮廷音樂為主的燕樂歌舞大曲,宋朝是以市民階級為主的宋雜劇,以及南方民間的一些戲文。唐代燕樂的發展是唐代初年的多部樂,再到中唐時期的坐、立部伎,再到盛唐時期形成燕樂歌舞大曲。多部樂是隋唐初期發展的一種歌舞,一個作品分為若干樂章,每個樂章一種風格,體現了中西音樂的大吸收。如唐代多部樂中最后的“十部樂”反映了唐代宮廷音樂的興盛與繁榮,也為后來唐大曲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由各族人民共同創造,是我國古代善于吸收各民族優秀文化成果的一個絕好證明。到中唐時期,坐、立部伎形成,坐部伎是在堂上表演,舞者3—12 人,樂工與舞者技藝水平較高。有絲竹細樂的閑雅風格。代表作品有《景云樂》等六曲,與其場地不同的立部伎則在堂下表演,舞者數量為坐部伎的幾十倍,最多至180 人,節目有《破陣樂》等八曲。
唐代燕樂大曲是我國舞蹈藝術發展的一個高峰時期,而唐燕樂歌舞大曲中的《霓裳羽衣曲》不僅是當時的一部優秀的樂舞作品,直到現在的舞蹈屆也可稱其為一顆璀璨的明珠。此作品為唐玄宗李隆基所作,由他寵愛的貴妃楊玉環所舞,富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且諸多唐代詩人的詩作中都涉及到了《霓裳羽衣舞》的素材。《霓裳羽衣舞》在服飾方面十分講究,舞者黑發梳為雙鬢,飾以嵌金銀珠翠。舞態優美,搖曳動人。水袖飄飄,似弱柳扶風,羽毛輕擺搖曳,如鳳凰展翅。與一般的普通舞服不同,裙色如虹,裙上絲鍛宛若流霞飛云,另有黃金與瓔珞珠串相配,鏘金鳴玉、悅耳清脆,故《霓裳羽衣舞》所表現出來的場面性也是唐代燕樂大曲的一個主要特征。[3]
(二)宋朝音樂特征及其原因
上文提到,宋朝有一項國策,就是重文抑武,這一風氣從開國皇帝宋太祖“杯酒釋兵權”開始,皇帝逼迫武將交出兵權,選擇享樂的生活,從而導致重文抑武之風開始盛行的同時,享樂奢靡的社會風氣也開始蔓延開來。宋朝的社會環境相對比較安定,盡管宋朝與一些少數民族王朝仍有一些小摩擦,但這并不會影響到國內的發展,經濟隨之發展,奢侈享樂的生活風氣逐漸從上層的王公貴族蔓延到下層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統治者作為領頭羊,帶領眾多大臣們進行奢靡享樂的日常生活,逐漸不滿足于有些高雅但卻更加正式的宮廷音樂,渴望更加具有娛樂性質的音樂。市民音樂就逐漸出現在了皇室的面前,憑借他自身所帶的娛樂性質,很快就贏得了皇帝和各位大臣的喜愛,有了皇親國戚的支持,市民音樂的發展就更有動力了。
其次,由于唐朝適用于宮廷慶祝的音樂并不能直接照搬到市民階層的生活中,且市民階層中大多數人文化水平不高,對于宮廷音樂等燕樂雅樂的鑒賞能力也有一定局限,所以宮廷音樂在民間發展不起來。所以為了代替宮廷音樂,符合市民需求的音樂也就產生了。宋朝市民音樂能夠發展得如此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了宋朝市民階層的發展壯大的力量才得以有如此繁榮的態勢。所以,宋朝世俗音樂之所以能夠發展繁榮起來,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市民階層的發展壯大,群眾逐漸有了話語權,對于文化生活,尤其是音樂的需求也提高了,市民音樂自然而然也就開始蓬勃發展。從另一角度來看,宋朝的市民階層一般是生活在城市當中,不被農業生產所禁錮,同時也不被官僚體制內部的框架而束縛,是一個相對自由的階層。他們從農村來到城市生活,有的在客棧、酒肆謀取差使,有的憑借自己的技術獲得一份較為穩定的生計,有的會選擇在城市里置辦房產,開店生活。從這些工作看來,選擇進入城市發展的農村人口都相對來說發展較好,溫飽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而在生理上的需求也就得到滿足。正所謂飽暖思淫欲,沒有基本的生存問題后,自然就會尋求別的樂趣,音樂就是一方面。
唐代時期的宮廷樂以排場盛大,篇幅大,持續時間長為特點,而支撐這種大型歌舞源自唐代經濟實力強盛,國家富庶,唐代文化講求富貴華美,因此對宮廷的歌舞也就自然而然反映了唐代文化特色。而宋代,在經歷五代十國割據戰爭以后,宋代皇帝認識到需要休養生息,減少賦稅和開支,來恢復經濟,同時儒家文化也要求統治者節儉。因此,排場盛大,衣著華美的唐代宮廷樂規模便逐漸沒落。受到這些影響,原有的宮廷樂便縮小了規模,并且只選擇唐代宮廷樂中的部分進行編排,而這種方式也被稱為“摘編”。南宋時期,宮廷樂經歷更長時間的低谷期,宮廷樂的代表場所“教坊”也被取消,這就代表專門培訓宮廷樂的歌姬失去教習場所,宮廷樂走向沒落也就無可避免。而那些被裁剪的歌舞樂師失去謀生手段,就不得轉向民間演藝場所,這也就在客觀上推動了民間市井歌舞文化的發展,他們帶來的宮廷舞曲提高了民間市井音樂的水平與水準。以上種種原因,最終導致以市民階層為主體的市井音樂文化開始成為主流。
臨安,即當今杭州在作為南宋國都后,城市經濟與人口都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在當時瓦子的數量十分之多,如臨安城內的南瓦、北瓦;城外的新瓦、舊瓦等,諸如此類的瓦子有50 座左右,且個別大型瓦子可容納數千人之多。都城瓦子之的數量所以如此龐大,是由于其高度發展的經濟與興盛的文化。此外還有一客觀原因,當時有大量軍隊在都在此駐扎,吳自牧曾在《夢梁錄》中記載:“是以城內外創立瓦舍,以為軍卒暇日娛戲之地”。此外,瓦子應當類似于現代的大型商業廣場,除各種文藝表演外,還有一大部分的商業活動。可以說,瓦子是集商業交易、休閑娛樂、文化活動于一體的大型場所。所以,瓦子的興盛發展必然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有關。當社會和平穩定、經濟繁榮發展時,瓦子的場地數量就會增加,而如果社會動蕩不安且經濟實力較弱,則數量減少。[4]
隨著宋朝商品經濟的發展,商業的繁榮,坊市合一制度的實施,兩宋京都大街小巷上的酒肆茶坊如同雨后春筍般拔地而起。因為宋人嗜好飲酒品茶,還形成了宋朝獨有的酒文化和茶文化。而在喝酒品茶之余,也少不了聽曲助興。
另外發展較快的還有一些流動性的街頭表演,顧名思義就是在街頭巷尾等非固定場地演出。在這些地方表演的藝人有一個特殊的稱謂,叫“路岐人”,而其演出形式也有一個專門的稱謂,叫做“打野呵”。由此可見,跟瓦子勾欄中的專業藝人相比,路岐人屬于“藝之次者”,上不了大雅之堂,因此只能在街頭巷尾表演。但好處是他們比較自由,支起攤子就能表演。宋朝上到王公貴族下到黎民百姓,對于春節、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傳統節日都非常重視。為了烘托節日氣氛,宋人常常舉行大型的節慶表演。以元宵節慶活動為例,一過冬至,節慶表演就開始了,一直到正月十六才收燈結束。從《東京夢華錄》記載來看,可窺見宋代元宵節的節慶表演盛況:“擊丸蹴鞠,踏索上竿。趙野人倒吃冷淘;張九哥吞鐵劍;李外寧藥法傀儡;大特洛灰藥;木骨木出兒雜劇;鄒遇、田地廣雜扮;蘇十、孟宣筑球;尹常賣五代史;劉百禽蟲蟻;楊文秀鼓笛。”宋代的市井音樂,除了表演場所不一,其表演形式更是百花齊放,精彩紛呈,如諸宮調、鼓子詞、陶真、宋雜劇等說唱戲曲體裁是當時在大眾中較受歡迎的一些音樂形式。而每種表演類型也都有一些名家名角,正如當今的娛樂圈明星一樣,受到當時人的追捧和喜愛。
結 語
到唐朝為止歌舞大樂仍然只是供宮廷享用的奢侈品。從宋代開始,市井文化逐漸發展起來,人們對音樂美的看法也有所改變,由大曲向宋詞元曲轉變。由于城市的發展帶動了市民音樂的發展,被宮廷壟斷的音樂文化開始下移,宋詞當時就是符合市民的審美需要,宋代的戲劇戲曲繁榮,是因為它有著繁榮的都市經濟,有理想的表演場所,川流不息的市民觀眾,這些都為它創造了條件,而在南北方也都有其各自特點的地方戲劇戲曲形式,比方說南戲,它是在南方民間歌舞小戲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的演唱形式也是多種多樣。保留了濃厚的民間戲曲色彩,很多作品都是抨擊社會的丑惡現象,反映民間呼聲的,也反映了宮在雅樂與民間音樂共存,但逐步傾向于民間音樂發展的文化現象。這一時期也可以看出,隨著國家的安定以及政治言論上的自由,音樂的發展空間也在逐漸的擴大,開始趨向于全民化社會化,它不會單單以宮廷音樂為主流音樂了,更多的是要達到整個社會共同的和諧與審美需要。唐宋音樂的轉型是歷史大變革的一個重要體現,但不論是唐代的歌舞大曲、教坊梨園、法曲俗講,還是宋代的瓦子勾欄、說唱戲曲都在整個中國音樂發展過程中具有十分深刻的歷史價值,也是整個人類音樂史上的燦爛瑰寶。隨著我國政治經濟的不斷發展,藝術的不斷進步,中國的音樂藝術必將走向更加輝煌燦爛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