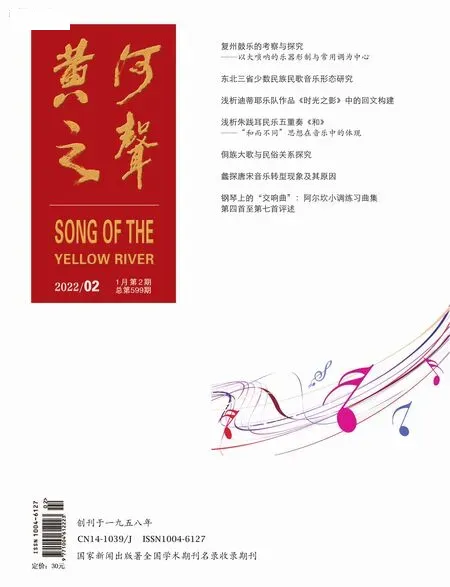從《禮樂論》《老子》來看王安石的音樂思想
呂夢潔
王安石,北宋時期政治家、思想家。他的論樂文字有《禮樂論》、《夔說》、《老子》等,本文主要通過《禮樂論》與《老子》兩篇來剖析王安石音樂思想。
一、王安石對儒家音樂思想的繼承
先秦儒家音樂思想強調音樂的教化功能。在宋代,王安石也辯證的繼承了儒家音樂思想。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禮記·樂記》
“禮樂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世俗之言曰‘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禮樂論》
由以上,我們可以看出,王安石認為先王創建禮樂的目的是使人養神正氣,從而使人正性。他認為性無善惡,但是由性所散發出來的情是可以分為善惡的,所以要通過后天的禮樂對其進行教化,對其進行正確的道德引導,從而達到一個良好的統治環境。王安石強調音樂的教化功能,這是對先秦儒家音樂思想的直接繼承。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禮記·樂記》
“蓋言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神明。”《禮樂論》
孔子以“中和”為音樂創作的標準,認為音樂應盡可能達到中正平和,這樣才能對人起到良好的教化作用。王安石同樣認為音樂應以“中和”為其準則,只有“中和”才是圣人所要傳達的音樂觀念,這是王安石對儒家“中和”音樂標準的直接繼承。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禮記·樂記》
“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禮樂論》
王安石與先秦儒家看法相同。正如孔子所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人的最高品德,最終還是由樂來完成的。王安石同樣肯定“禮、樂、刑、政”四術的重要性,正是因為“禮、樂、刑、政”,才得以使“圣人得以成萬物已”。
“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制道,則惑而不樂。”《荀子·樂論》
“非圣人之情與世人相反,圣人內求,世人外求,內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去情卻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成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禮樂論》
王安石認為圣人與世人對于音樂有著不同的需求。圣人從音樂中得“道”,世人從中得“欲”,但只有從中得“道”者才是君子之為。這與《荀子·樂論》中的觀點相一致。
通過以上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王安石在音樂思想方面與先秦儒家有著共同的看法。王安石同樣強調音樂的教化功能以及調解人心的作用,可以說王安石對儒家音樂思想的核心部分進行了直接繼承。
二、王安石對道家音樂思想的吸收與批判
王安石除對儒家音樂思想進行繼承之外,也了解到儒家音樂思想所不足的地方。為了使儒家體系能夠更加系統與完備,王安石把目光投向道家,對其音樂思想進行辯證性的吸收。
(一)對于道家音樂思想的吸收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圣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為也。故昔圣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為己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圣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也,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于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
王安石將“道”分為本、末兩部分。一種是不靠人力所形成的自然之道,此為本;另一種則是需要人為才能成的社會倫理之道,這是末。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王安石在對于“道”的認識上更為全面,不再將音樂限于人與社會的倫理關系上面,也認識到道家“無為自然”的重要性,吸收了道家“天道無為”的觀念。
自然之道不需圣人之言、之為便可自生;社會倫理之道只有通過人的作為才能得以成。在過去,圣人經常將萬物之成為己任,通過王安石的言論表達,圣人是“成”萬物而并非是“生”萬物,由此肯定了圣人是通過后天人為得以“成萬物”這一觀點。在王安石這里,圣人代表著道德的最高境界,由此可看出,相較于自然之道,王安石更為強調后天人為之道這一觀點。
那么圣人是如何通過自己后天的行為達到“成”萬物的呢?王安石在《老子》篇中做出了回答:“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王安石認為圣人正是因四術的教化與約束才得以成萬物,因此,王安石對四術以及后天人為是持肯定態度的。
在這里,他除了對儒家思想的繼承之外,還創新性的將道家“天道無為”與儒家“人道有為”觀念融合在一起,構成自己獨特的音樂思想體系,是對儒家音樂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禮記·樂記》
“是故大禮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禮樂論》
王安石對于禮樂的要求與《禮記·樂記》相同,認為禮制不應該太過復雜,音樂也不能太過繁瑣。除此之外,王安石在他的言論中也吸取了道家的一些思想,如注重樸素、“大音希聲”的觀點,由此使禮樂達到“簡而無文、易而希聲”的狀態。這是對儒家音樂思想的補充,同時也賦予了道家音樂思想其倫理道德之意。
“而神之所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賢者,盡誠以立性者也;圣人,盡性以致誠者也。”《禮樂論》
“言性者,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圣人所以配之。”《禮樂論》
通過王安石的言論,我們可以看到圣人,是通過對自己的天性進行后天約束使其達到一種至誠的狀態。除“誠”之外,王安石也特別注重“精”。上面我們講過,圣人是王安石認為的最高境界,在《禮樂論》中他說道“圣人,盡性以致誠也”、“精者…圣人所以配之”,可以看出“誠”與“精”都是圣人所需要具備的品質,“精、誠”二字出自于《莊子·漁夫》:“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比喻只要專心去做,什么疑難問題都能解決,這與王安石所表達的意思是相同的。由此可以從側面證實道家對王安石造成的影響。
通過以上的梳理,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在王安石音樂思想中,融入了道家的部分思想,這也正是儒家思想所缺乏的。王安石吸收道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儒家思想體系,使得儒家音樂思想得以找到內在依據的支撐,更具說服力。
(二)對于道家音樂思想的批判
“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修性者,歸于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為禮樂者獨以順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樂之文以順流俗為事,欲成治其國家者,此梁、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禮樂論》
王安石認為儒家的思想已經很少人知道了,現在說到養生修性,都是關于佛、道兩家的學說。但是佛、道兩家的說辭只是順應當時的世俗社會,如果將佛、道兩家的音樂思想用于治國,那么國家就會落得梁、晉滅國的下場。王安石批判佛、道兩家的禮樂思想不正統,在他內心深處,只有儒家才能是正統的音樂思想。
王安石以“道有本末”為準則,批判了老子“重天道、輕人道”的觀點。“老子者獨不然,以為涉乎其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為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王安石批判性的將其認為“是不察于理而務高之過矣”。
道家崇尚“法天貴真”,主張一切任其自然,沒有注意到社會倫理之道的重要性,所以認為不需要四術等方式對人進行后天的教化。王安石認為老子此觀點太具片面性,沒有認識“道”是具有本、末兩方面,同時也否定了后天人為的主觀能動性,這也是王安石所不能認同且批判的觀點。而儒家主要通過“禮、樂、刑、政”這些方法對人之性進行約束與教化,使其達到“正性也”,正如王安石所說“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效諸其行,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
綜上,王安石認識到儒、道兩家音樂思想都具有片面性。道家思想適用于本,儒家思想也僅適用于末,認為只有將兩家音樂思想進行互補,才能建構起一個新的儒學體系。他的這種做法,對于后世的學者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同時也對儒學的發展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三、王安石音樂思想形成的原因
王安石的音樂思想既有對儒家思想的繼承,同時也對道家思想有所吸收,其音樂思想的產生有著多方面的因素。本文主要對社會背景及成長經歷兩方面進行詳細說明。
(一)社會原因
隋唐兩代,雖然儒學重回了政治社會的核心,但整個思想界的狀況并沒有多大變化,佛、道兩家給儒學帶來了非常大的沖擊,北宋時期亦是如此。在這一時期,儒家學者收不住民心,所以唐代出名的儒家很少,大都是屬于道家與佛教,如我們知曉的李白便屬于道家,而王維、白居易則屬于佛教。從唐代“儒門淡薄”這個情況來看,如果想要挽回儒學的正統地位,那么儒學必須做出改變。
王安石深刻認識到這一點,認為必須鞏固與完善儒家的本體論與心性論。儒學主要是針對倫理與社會的思想體系,在本體論和心性論方面,明顯沒有佛、道兩家出色。出于對儒家正統地位的維護,復興儒學就必須以完善其自身的理論缺陷—“修其本以勝之”為始,這就使得儒家學者把目光放在了佛、道兩家。出于對民族文化自信心的維護,儒學并沒有選擇佛教,而是向道家學習,產生了聯合儒、道以御外侮的潮流。并且道家主張清靜無為,有助于封建統治,所以也受到了統治者與儒學的提倡與推崇。王安石亦是受到此種現象的影響,所以將目光轉向對道家的學習之上。
(二)個人經歷
王安石出生于官宦人家,父親王益任地方官時,頗有成績。在王安石十歲時,隨父親赴任,王益關心民生疾苦,于是幫助民眾改良風俗、進行教化等事宜,贏得許多民心。這段經歷對王安石的一生有著重大的影響,他寫了《先大夫述》一文,記述了父親的一生。他以父親為榜樣,立志報效國家,在他心里有著儒家思想的根,隨著他的成長而逐漸蓬勃。
史料記載王安石生平最喜愛《老子》,對于老子的解釋也最為用心,對《老子》和《莊子》有著很高的評價,同時也對其中的部分觀點表示贊同。除此之外,其門下的弟子都作有《老子注》,或多或少的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響。
王安石在學術方面有著很高的造詣,他熱愛讀書,涉獵廣泛。“自百家諸子之書,至于《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他在讀書時不分派別、不分職業,求知若渴。蘇軾也稱贊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糍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王安石雖然具有儒學的立場,但他不排斥佛、道兩教,甚至會將其認為正確的思想吸收進來。
通過以上兩方面的原因,我們對于王安石吸收道家音樂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但王安石正是因為吸收了道家音樂思想,也使其受到了指責和猜疑,認為他背離了正統的儒學。除此之外,也有人認為王安石是對先秦時期儒家音樂思想的超越,如李俊祥先生、魏福明先生。筆者認為,正是王安石對于道家音樂思想的吸收,使儒家音樂思想具有深刻的內在依據,也使得儒家音樂思想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總的來說,王安石所處的北宋時期,是一個思想較為自由的時代。王安石以儒家音樂思想為基礎,批判地吸收了道家“天道自然”、“無為而治”等思想,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音樂思想體系。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儒家音樂思想的正統地位,同時也因在儒、道兩家音樂思想上進行融合,對后世的音樂發展起著重要的啟迪作用。■
——由刖者三逃季羔論儒家的仁與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