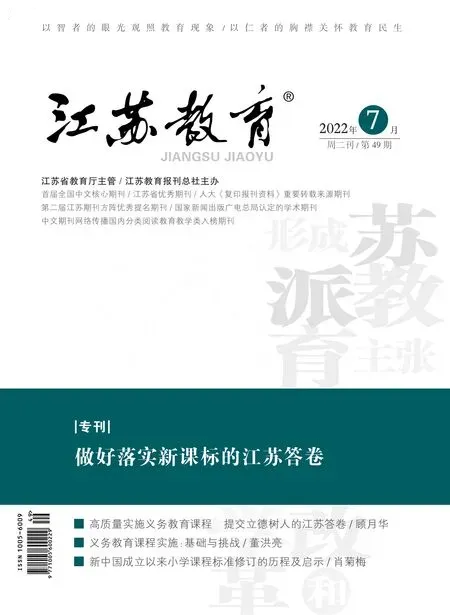新中國成立以來小學課程標準修訂的歷程及啟示*
肖菊梅
課程標準體現的是國家對學生的認知、情感態度、知識、技能等方面發展的基本要求。[1]85-86制訂課程標準是一項系統工程,包括醞釀、制訂、實驗再到正式頒布等過程,與課程標準的歷史、現在與未來密切相關。[2]38課程標準一經頒布,在其推行實施過程中會出現新問題,面臨新挑戰,須不斷修訂完善。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課程標準修訂經歷了教學大綱時期、課程標準時期以及新課程標準時期,推動了課程改革的深入發展。
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小學課程標準修訂的歷程
1.教學大綱時期(1949年—2001年)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使全國小學教育平穩過渡,國家對正規小學課程加以變更,但并沒有全國統一規定的學制。1951 年8 月,政務院頒布了改革小學學制的政令,規定小學實行五年一貫制。1952 年,教育部頒發了《四、二舊制小學暫行教學計劃》。是年12 月,教育部頒發了《小學算術教學大綱(草案)》和《小學珠算教學大綱(草案)》,為全國小學算術實行統一教學提供參考。之后,教育界開始全面學習蘇聯,廢棄原有小學課程體系并以“教學大綱”取代“課程標準”。[3]1701956 年,教育部頒發了小學語文、算術、歷史、地理、自然、唱歌、圖畫、體育8 科教學大綱,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統一的小學各科教學大綱。概言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教學大綱修訂采用蘇聯教學大綱模式,沒有繼承民國時期和建國初期課程標準、教學大綱中的有利因素,這使得這一教學大綱在實施過程中出現種種不適應現象。[3]174此外,受蘇聯正規化、統一性經驗影響,教學大綱注重對教學內容的范圍、要點、順序和教學方法作過于細致的統一規定,不利于教學過程的彈性處理和教師創造性的發揮。
1957—1965 年間,隨著中蘇關系惡化,此前照搬蘇聯經驗進行的小學課程改革所形成的許多問題要予以糾正。1958 年,全國掀起工農業生產的“大躍進”高潮,波及并引發了教育領域中的“教育大革命”,并對小學教育教學產生重要影響,如課程內容任意刪減、隨意自編教材、教學大綱頻繁變動等。《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對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材進行一次大改革,是目前教育工作中的迫切任務。”[3]174為吸取“教育大革命”教訓,1961 年根據“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教育部在全國開展小學教學改革實驗并制訂新的小學教學大綱,經過廣泛調查研究,于1963年3月頒發《全日制小學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小學四十條”),根據此條例重新修訂了小學語文、算術、歷史、地理等各科教學大綱。可以說,1963 年教學大綱重新確立了小學各學科的性質和任務;教學內容有所充實,教學要求也相應提高;加強“雙基”教學,突出多讀、多練。[3]178
“文革”期間,教學大綱失去了應有的價值與作用。自1963年教學大綱被否定之后,真正稱得上教學大綱的書面材料幾乎沒有。[4]34“文革”結束后,教育部組織力量重新編寫小學各科教學大綱。1986 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和《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初級中學教學計劃(試行草案)》的頒布,當時的國家教委開始相繼修訂小學教學大綱。1988 年1 月,九年制義務教育24 個學科的教學大綱(初審稿)頒布,其中小學階段包括思想品德、語文、數學、自然、社會、音樂、美術、教育、勞動等9 科教學大綱。此套教學大綱以宏觀指導為主,適當照顧了地方差異;精簡教學內容,適當降低難度;大綱規定的教學要求更為明確具體。[3]1891992 年,教育部頒布《全日制九年制義務教育課程標準(草案)》,把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合并,并編訂了綜合式格局的課程標準。1998年《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要求構建“現代化基礎教育課程框架和課程標準”。1999 年,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全面啟動。2001 年,《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和義務教育各學科課程標準(實驗稿)頒布,要求在全國38 個國家級實驗區開始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實驗,課程標準正式取代教學大綱。新修訂的課程標準文本在內涵、結構框架以及目標陳述等方面均不同于原有教學大綱文本,這使得課程標準文本負載著課程改革與發展的理念和設想,具備更強的規范和指導功能,使各部分結構形成內在的聯系。
2.課程標準時期(2001年—2011年)
2002年,隨著義務教育各學科課程標準(實驗稿)的頒布,課程標準正式成為我國小學教材編寫、教學、評估和考試命題的依據。隨著小學階段課程改革的深入推進,小學各科課程標準在實施過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如小學各學科容量多,難度大;一些小學學科教學及評價要求不具體;相關學科、學段銜接不合理等。[5]34為應對課程標準推行過程中的問題,鞏固小學課程改革成果,貫徹《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 年)》精神,在堅持德育為先、全面發展、能力為重、以人為本以及與時俱進等課程標準修訂原則的基礎上[5]35-36,教育部于2003 年3 月開始在全國29 個省(區、市)和38 個國家首批試驗區開展大規模的小學各科課程標準問卷調查研究。2004 年2 月,教育部在征集各省反饋意見的基礎上,成立課程標準研制組,修訂義務教育各科課程標準。這次課程標準修訂主要在于處理“雙基”訓練與學生創新實踐能力培養以及學科發展與學生經驗的關系。同時也使小學課程標準更加適應時代和小學生發展需要。2007 年,通過前期課程標準樣本大規模調研發現,相關學科、學段間的縱向銜接、橫向配合有待加強。特別是一些相近學科,有些內容交叉重復,加重了學生負擔。[5]34-39在對實驗區大規模調研的基礎上,2007年4月,教育部開始全面啟動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稿)修訂工作。2011年12月,教育部正式印發義務教育階段19 個學科的課程標準(以下簡稱“2011年版課標”),并于2012年秋季開始執行。2011 年版課標的修訂,各科整體上呈現出一些共同特點與變化:落實德育為先,突出了德育的時代特征;加強學生能力的培養;適應時代發展需要,合理控制課程容量,有效減輕學生學業負擔。[5]36-37
3.新課程標準時期(2011年—2022年)
隨著網絡的普及和人工智能的興起,青少年成長環境發生變化,社會對人才培養提出了新要求。進入21 世紀,我國已經全面普及了義務教育,上好學已成為新時代的教育發展需求。為此,“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成為義務教育課程標準修訂必須回答的問題。2011 年版課標在深化小學階段課程與教學改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如缺乏對小學生學習程度的具體規定,教師難以把握教學的廣度和深度,不能明確課程實施的要求等。另外,根據課程改革自身的規律,2011年版課標已經實施了10年,有必要進行修訂完善。為此,2019年1月,教育部正式啟動義務教育課程標準修訂工作,圍繞教育目標、課程設置等進行專題研討。2021 年4 月,國家教材委及其專家委員會審核通過了義務教育課程方案和語文等16 個課程標準。2022 年4 月,義務教育課程方案和課程標準(2022 年版)頒布,這是自2011 年版課標頒布之后,以十年為一個周期的義務教育課標修訂的重要成果,標志著新一輪課程標準修訂工作完成。此次課程標準修訂根據義務教育培養目標,注重學生核心素養培養,優化了課程結構,確定了學生學業質量標準,增強了指導性,加強了學段銜接。[6]78
二、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小學課程標準修訂的啟示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小學課程標準修訂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給當今小學課程改革以啟示:
其一,立足本國現實需要,合理吸收國外先進經驗。新中國成立初期,完全照搬蘇聯小學教學大綱模式,未能根據當時社會實際情況,在課程實施過程中出現不適應現象。然而,蘇聯教學大綱的教學目的和教學要求相對合理、完整,要求教學大綱實行統一標準,有利于教學管理與實施。吸取這些有益經驗,可為后續課程標準修訂提供參考。進入21 世紀,我們要積極引介他國小學課程標準修訂經驗,為完善我國小學課程和優化課程政策提供參考,開闊我國課程研究者的學術視野。讓研究者們認識到,“課程標準的研制要從封閉的體系走向開放的體系”[7]39-43。
其二,協調好課程標準的繼承與改革、穩定與發展的關系。繼承以往課程標準的有利因素是修訂的基礎,改革課程標準是其發展的動力,保持課程標準的穩定是保障,確保課程標準的發展是目的,四者缺一不可。我國歷次課程標準修訂均是在延續新課程改革的基礎上推行的,修訂后的課程標準雖然呈現新的特點與變化,但本質上遵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基本精神與指導方向。誠如有學者所言,“全盤否定過去的虛無主義變革,往往只是曇花一現”[8]3-9。在修訂課標時,一定要在“明確清晰”上多花工夫;修訂課程標準是課程改革與發展的動力,要使課程標準充滿活力和時代感。若頻繁修訂課標,沒有一定的穩定期,也不利于學校課程發展。每次新修訂的課程標準在一定時期內有其合理性與優勢,但隨著社會和時代的發展,其內容陳舊與體系缺陷的問題就會暴露出來,同時在實施過程中積累的經驗教訓,能為下一次課程標準修訂提供佐證。然而,若一味地追求課程標準的穩定,長期固定不變也不可取。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小學課程改革約3 年多就變動—次,小學教學大綱(課程標準)頻繁變動,影響了小學教學質量的提升。
其三,進行課程標準修訂制度化建設。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教學大綱、課程標準的修訂有其時代發展的烙印。隨著各個時期社會發展需求的變化,對課程教學也提出相應要求,課程標準修訂的內容與方法也隨之改變,這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學科發展的歷史繼承性。此外,課程標準修訂人員隊伍的不穩定,容易造成課程標準研制的斷層,不能保障課程標準的質量和水平。為此,要建立并完善課程標準修訂制度,成立專門的課程修訂委員會,確保一定時期內課程標準修訂委員的穩定性,形成課程標準修訂的長效機制,實現課程標準修訂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此外,每次課程標準修訂前要開展試點工作,確保課程標準修訂的實踐性和科學性,并建立專門的課程標準修訂網絡平臺來接受大眾的建議與監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