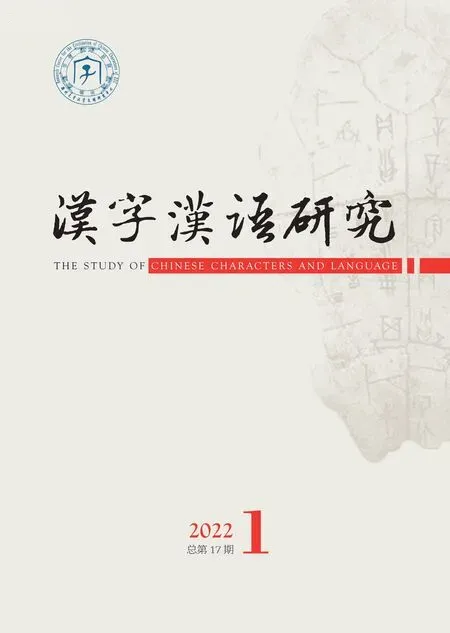對文分析與碑志文獻釋讀舉隅*
董 憲 臣
(西南大學文學院)
提 要 對文是古代文獻中一種被廣泛使用的修辭表達手段,在碑志銘文中尤為常見。對文分析是石刻文獻研究的常規手段之一。妥善利用對文,有助于碑志銘文的正確釋讀,具體表現在指明原石誤刻、補足缺泐字詞、校正錄文訛錯、辨析疑難字形、判別結構屬性五個方面。
“對文”指句讀內部或句讀之間相互對稱的結構形式中,在相對應位置上采用意義近同或相反的詞語。它是古書中一種常見修辭表達手法,又稱“相對為(成)文”“對言”“對舉”“對仗”等。古代學者如東漢鄭玄、北齊顏之推、唐孔穎達等很早就注意到典籍中的對文現象,并開展了利用對文進行訓詁的初步嘗試①這些成果散見于鄭玄《三禮注》、顏之推《顏氏家訓》、孔穎達《五經正義》等著作。。至清代,高郵王氏父子、段玉裁、俞樾等樸學大師利用對文辨析詞義、考訂文字,解決了很多校勘、訓詁方面的難題,成效卓著②這些成果散見于王念孫《讀書雜志》《廣雅疏證》、王引之《經義述聞》《經傳釋詞》、段玉裁《經韻樓集》、俞樾《古書疑義舉例》等著作。。當代學者楊琳(2006)對這種利用對文考求詞義的方法進行了系統闡釋和總結,稱之為“對文求義法”。
我國石刻文獻歷史悠久,源遠流長。作為一種文體,碑志銘文自東漢中期正式形成之初,便呈現駢儷化的傾向,演至南北朝,政權雖然處于對峙的狀態,但兩地作家在追求駢儷的文風方面趨于一致(馬立軍,2015:197)。此后歷經各代,駢散并行、崇尚對仗被逐步確立為碑志文體的一個寫作范式并得到繼承發揚。因此,歷代碑志銘文保存了極其豐富的對文辭例,既是對文產生的一大淵藪,也是對文訓詁實踐的絕佳材料。實際上,至晚在清代,金石學家已有意利用對文提供的信息來明確碑志疑難字的身份。在當今的石刻文獻研究領域,毛遠明(2009)、梁春勝(2012;2018)、周阿根(2015)、章紅梅(2017)、趙家棟(2020)等學者繼踵前賢,妥善利用對文,綜合各種考釋方法,解決了不少疑難字詞問題,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但遺憾的是,目前學界似尚未對這種手段予以專門討論。
與傳世文獻相比,碑志文獻(包括拓本)的特殊性在于更大程度地保存了當時文字的真實樣貌,具有極強的文字學價值;其后往往又經各家迻錄、注釋,形成“次級文本”,兼具語義學及校勘學價值。因此對于碑志文獻來說,對對文的利用并不單純地體現在“求義”上,也體現在匡補字形、釋錄校正等諸多方面。因此,我們不妨將這種利用對文分析語義、校勘文獻的方法稱為“對文分析法”,以更廣泛地涵蓋其多維度的利用價值。
以下試參考歷代碑志拓片、釋錄①本文所引碑志例證均注明出處,斜線前的數字表示冊數,后表頁數。為求行文簡潔,部分文獻采用簡稱:《北圖》指《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校注》指《漢魏六朝碑刻校注》,《集成》指《南北朝墓志集成》,《墨香閣》指《墨香閣藏北朝墓志》,《字典》指《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隋唐匯編》指《隋唐五代墓志匯編》,《唐匯編》指《唐代墓志匯編》,《唐續集》指《唐代墓志匯編續集》。以上著作詳情見參考文獻。及相關研究成果,對碑志文獻釋讀過程中對文分析的利用加以初步總結。
1.利用對文指明原石誤刻
程千帆、徐有富(2020)在總結古人校勘成果的基礎上,將書籍文字的錯誤歸納為訛、脫、衍、倒四種基本類型。由于文字系統自身復雜性及刻工文字水平參差等原因,碑志原石或原拓中亦存在上述諸類型的誤刻之處,尤以訛、脫居多,其中有些可參考對文提供的信息加以指明。
從對仗的角度看,“悴綠于樤間”與“摧紅花于枝上”字數不協,當有衍脫。核對拓片,此段錄文除“樤”外別無它誤。品讀文意可知,原志或在“綠”下脫“葉(葉)”字,“綠葉”可與“紅花”對仗,或在“紅”下衍“花”字,“綠”可與“紅”對仗。
(2)唐顯慶三年《王法墓志》:“故休璉裁書,高子雍之宿德;伯喈倒,異仲宣之逸林。”“孝惟橋梓,林架椅桐。”(《唐匯編》274頁)
前段文字“宿德”“逸材”對言。“休璉”句暗含用典,指曹魏時應璩(字休璉)在寫給曹長思的信中褒揚王肅(字子雍,曹魏著名經學家)素有德行①《文選·應璩〈與侍郎曹長思書〉》:“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后進見拔。”。“伯喈”句化用“蔡邕倒屣”的典故②據《三國志·魏書·王粲傳》,王粲(字仲宣)少有才名,為蔡邕(字伯喈)所賞識。有一次他聽說王粲到訪,因急于迎客,忙亂中把鞋子都穿倒了。志中“倒”下一字拓片局部殘泐,據文意當是“屣”或“屐”的異體。《唐匯編》錄作“”,備參。。“宿德”“逸材”皆偏正結構,“宿德”指積久之德,“逸材”又作“逸才”,指卓越出眾的才華。
后段文字“孝”“材”對言。“橋梓”即“喬梓”,指喬木、梓木兩種高矮不同的樹木。《尚書大傳》卷四《梓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后因以“喬梓”稱父子。“椅桐”指椅樹、梧桐,木材皆可制作器物。兩句志文乃是贊譽墓主事父孝敬、才堪大用。
(3)北齊天保四年《元賢真墓志》:“羲和莫按,望舒罕留。始言避,奄送侵丘。八珍圖設,四馬停辀。”(《墨香閣》102頁)
按:《集成》(648頁)錄文亦同。此段為四言韻語對仗格式的銘辭,然“始言避”僅三字,恐有脫文。核對原拓,錄文無誤,當屬原石漏刻。結合“始言”句的結構及各詞詞性判斷,“始”與“奄”皆副詞,“言”與“送”皆動詞,“侵丘”充當“送”的賓語,故疑缺字當在“避”下,“避□”充當“言”的賓語。
再結合對文所表達的內容來看,“侵丘”即“寢丘”,古地名,在今河南固始、沈丘二縣之間,土地貧瘠。春秋時期,楚國令尹孫叔敖臨終前囑咐自己的兒子將來不可接受楚王封地,如果推辭不掉,就請求把寢丘封給自己③事見《呂氏春秋·異寶》:“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荊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墓志援引此典,一方面喻指志主的死亡,一方面暗譽志主個性儉素。故缺字似當補作“世”,“避世”謂隱居不問世事。“始言”句的大意為“剛打算避世隱居,就忽然與世長辭了”。
2.利用對文補足缺泐字詞
由于自然或人為因素的破壞,很多碑志材料存在不同程度的殘損。如果殘損傷及字形,就會造成殘字,給釋錄帶來困難。另外,時代較晚、質量不高的拓本,以及經過縮印的拓本的圖版,與較早的善拓和清晰的圖版相比較,殘損也往往更為嚴重(梁春勝,2018)。結合對文,或可補足原石或拓片中殘損缺泐的字詞。
(4)唐永徽四年《周藻墓志》:“彭澤□□之篇,緣情染翰;潘岳閑居之作,寓目披文。”(《唐匯編》185頁)
按:核對原拓(《北圖》12/96),兩個缺字已完全泐失,只能依據文意補足。“潘岳閑居之作”指西晉文學家潘岳所作的《閑居賦》,該賦表達了作者厭倦官場、渴望歸隱的心情。“彭澤”與“潘岳”對舉,此處應代指東晉文學家陶潛(曾出任彭澤令,故名);“彭澤□□之篇”中缺文當系陶潛的某篇文學作品名,且中心思想與《閑居賦》相近。綜合這些線索并考察唐代墓志文例,可知缺文當補作“歸去”。“歸去”即《歸去來兮辭》的簡稱,此文作于作者辭官之時,也是一篇脫離仕途、回歸田園的宣言,正與《閑居賦》主旨契合。唐志常引此文贊譽墓主的隱逸情懷。開元八年《楊璉墓志》:“撫鄭君之風俗,政是用和;憶陶令之田園,欻歌歸去。”(《北圖》21/138)天寶三年《范如蓮花墓志》:“慕梁竦之平生,恐勞郡縣;詠陶潛之歸去,遂樂田園。”(《唐匯編》1561頁)
(5)唐麟德二年《張滿墓志》:“嗣子伏奴之悲陽烏易逝,魂暨年代而遷訛;陰菟難留,馬方陵谷而銷貿。”(《唐匯編》432頁)
綜上,《張滿墓志》“塊”上所脫字當為“鳥”“雁”或“燕”。“鳥(雁、燕)塊”亦代指墳塋。
(6)唐貞觀五年《□諒墓志》:“陳榻長懸,□琴罷彈。”(《唐續集》9頁)
“陳榻長懸”典出《后漢書·徐稺傳》,東漢陳蕃為太守,在郡不接賓客,唯徐稺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牙琴罷彈”典出《呂氏春秋·本味》:“伯牙鼓琴,鐘子期聽之。……鐘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兩句皆悲嘆知音已去再難得,旨在表達對墓主的痛悼。此處“陳榻”“牙琴”對舉,分別指陳蕃之榻及伯牙之琴。唐代墓志中,兩則典故常以對文的形式出現。唐永徽四年《趙爽墓志》:“徐樽虛湛,牙琴長絕。”(《北圖》12/86)延和元年《蕭貞亮墓志》:“悲隙光而易謝,陳榻長懸;嗟逝水難留,牙琴永絕。”①原志“逝水”后當脫“而”或“之”字。(《北圖》21/1)
3.利用對文校正錄文訛錯
碑志原文釋錄是石刻文獻整理的一項基礎工作,但由于歷代碑志文獻資料紛繁且異體蓁蕪,各家在迻錄過程中難免存在訛錯之處,主要表現在誤點句讀和字形確認失誤兩大方面。參考對文在字數、詞性、結構、意義等方面的對應關系,有助于校正錄文的疏誤。
(7)東魏武定六年《張遵墓志》:“明珠奪照,錐劍無光。”(《墨香閣》74頁)
(8)北齊天統三年《李淑容墓志》:“玉苽永閟,金珥長淪。”(《新見北朝墓志集釋》157頁)
按:“玉苽”費解。此處“玉苽”“金珥”對舉,“金珥”指鑲金的珠玉耳飾,則“玉苽”似乎也應該是一種飾物。依字書及文獻,“苽”字形兼二用:一指茭筍(《說文·艸部》:“苽,雕苽,一名蔣。”);二是“瓜”的加形字,碑志用例甚多。文獻可見“玉瓜”一詞,指傳說中的仙果名。東晉葛洪《抱樸子·祛惑》:“(昆侖)有珠玉樹,沙棠、瑯玕、碧瑰之樹,玉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李。”但此“玉瓜”顯然并非飾物,與“金珥”意義不協。核對原拓,“苽”實作,當即“花”的俗寫。北魏景明元年《楊縵黑造像碑》“花”作(《校注》3/332)、北齊天統四年《謝思祖夫妻造像記》“花”作(《校注》9/286),字形皆與近似,可資對照。“玉花”,此處蓋指玉制的花朵形首飾,即玉鈿,又稱花鈿。鈿、簪、珥在古代多為高貴婦女的首飾,常用作女性死者隨葬飾品,這在志文中亦有體現。東魏興和三年《祖子碩妻元阿耶墓志》:“簪珥備陳,牲牢具宰。”(《北圖》6/74)唐咸亨三年《嚴朗及妻燕氏墓志》:“金鈿響滅,□□聲終。”(《隋唐匯編》洛陽卷13/12)。
4.利用對文辨析疑難字形
碑志文獻中存在著數量不少的疑難字,它們為銘文的正確釋讀和使用增加了難度。妥善利用對文所提供的線索,有助于確認疑難字的大致身份,縮小推測范圍,進而與其他字形進行認同和別異,提升考釋的準確度。
(11)東魏武定七年《李府君夫人鄭氏墓志》:“斯言無玷,容止何。”(《校注》8/106)
綜上,“諐”是“愆”的異體,文獻有證,若釋作“侃”則于義無取。《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377頁)、《集成》(587頁)錄文皆作“侃”,并誤。《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修訂本)(476頁)錄文正作“愆”,是也。
(12)唐龍朔元年《房寶子墓志》:“湫隘有居貞之慘,沉冥得大隱之情。”(《唐匯編》348頁)
5.利用對文判別結構屬性
互為對文的成分通常具有相同的結構形式和語法功能。對照處在對文位置上已知方的結構和功能,有助于明確判別另一方的內部結構關系及語法屬性,防止將詞組誤析為詞或將詞誤析為短語。
(13)東漢建寧元年《楊統碑》:“武稜攜貳,文懷遐冥。”(《校注》1/269)
(14)北魏永安三年《元彧墓志》:“綱紀邦國,舟楫生民。”(《校注》6/314)
按:《字典》(378頁)“楫”字頭下義項②“救濟”引該志為例證。依此作解,則“舟楫生民”是主動賓結構。實際上,“楫”本身指船槳,無救濟義,“舟楫”泛指船只,此處活用作動詞,猶言“救濟”。參考對文,“綱紀”與“舟楫”對言,“綱紀”本指法律制度,此處亦用作動詞,義即治理,故《字典》宜刪除“楫”的“救濟”義項。
(15)北齊天統元年《天柱山銘》:“民猷鄙薄,風物陵遲。”(《校注》9/191)
按:《字典》(1115頁)“猷”字頭下義項⑥“通‘猶’,欺詐”引該志為例證。依此作解,則“民猷”是主謂結構的詞組。參考對文來看,“民猷”與“風物”對舉,“風物”謂民風、民俗,“民猷”猶言“民德”,指民眾的道德。兩句互文見義,大意是“民德鄙薄,民風衰敗”。故“民猷”當是偏正式復合詞,“猷”表道德義,不表欺詐義。
以上通過舉例的方式探討了對文分析在碑志文獻研究中的利用價值。楊寶忠(2005:870)指出:“詞語所處的上下文對詞語本身具有制約作用,對詞語的意義具有體現作用。記錄某詞的字音義不詳,利用該詞所處的上下文,對其語法關系、語義邏輯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有助于確定字義并對疑難字進行辨識。”對文分析是語境分析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對于碑志銘文這種大量使用駢偶句式的特殊文體來說,對文所提供信息的重要性尤為突出。但對文分析有其局限性,它通常只是提供了發現問題的線索。對文的語言形式只是給我們提供了理解字詞的一種可能,并不具有必然性。因此,對文分析的結論要具有合理性及可驗證性,利用對文所推測出來的碑志誤刻、缺字、錄文訛錯、字詞形義等結果,要契合字形演變、詞義引申、駢體行文等通例,要驗之他處皆可通,如此方能更大程度上避免主觀臆斷,提高結論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