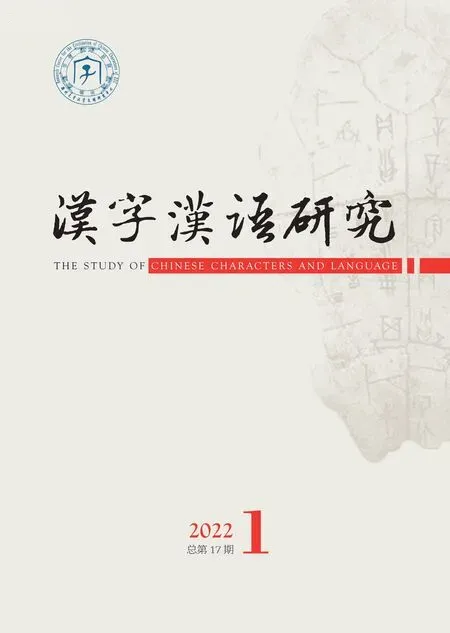“妞”的形義演變與滿漢文化關涉
薛 瑾 周 密
(1.浙江樹人學院人文與外國語學院 2.浙江古籍出版社)
提 要 宋代伊始,“妞”字作為古“”的訛誤而產生。“妞”是形聲字,最初其形旁“女”并非專指女性,據“聲符有義”原則,其聲旁“丑”也無“丑陋”“丑惡”義,而是承接古“”的“好”以及宋時的“高麗姓”二義而來。清中葉后,滿語與漢語融合,“妞”有了“未婚女孩”之義,“妞妞”成為滿語Nio nio([ni?:ni?:])的漢字音記,此乃彼時“滿式漢語”之特色。“妞”字復雜的古今異變,既揭橥了漢字簡繁轉換中“一對多”現象,又體現了漢滿兩大民族語言、文化次第交融的過程。但其體變結果,不能以滿漢兩族語言最終調和無二而片面視之,還關涉到雙方內部的語言形塑、自我修補,以及各自民族體認與情感留存因素,這對追溯今日北京方言的真實演變規律,有一定的價值。
“女丑”為“妞”,此論斷關乎漢字“妞”古今音形義的發展與演變。從唐至清,多有學者探討,尤其是清代考據學家為我們提供了較為嚴密的考證過程,但其觀念受到當時學術思潮和流派的限制,并未涉及滿語與漢語言的接觸融合,更未與現代漢語的形義相貫穿。下文先梳理“妞”音形義的發展演變歷程,再考辨之。
先談“妞”字音形義的發展與演變。《說文解字·女部》中并無“妞”字,卷十二下載:“,人姓也。從女,丑聲。《商書》曰:‘無有作。’”(許慎,1963:258)另《廣韻》也將“”歸入“呼到切”(陳彭年,1912:41),未提及“妞”。以上論著追溯“”之起源,并未談及與“妞”有關聯。
但在宋代編撰的字典或訓詁書籍中,出現了“妞”字,并將此字與古“”合二為一,至此宋人對“妞”字的認知始現分歧。《宋本玉篇》將“妞”與“”視為同一字:“妞,呼道切。姓也。亦作。”(陳彭年,1983:64)《集韻》將“妞”歸“有”韻,“女九”切(丁度,1983:901)。司馬光(1987:458)也將“妞”闡釋為“妞,女九切。姓也,高麗有之”。他們均認為“”“妞”為一字,但是關于“妞”的讀音,卻以為是“女九切”非“呼到(道)切”,值得注意的是,增加了一個“高麗姓氏”義。后北宋末《古今姓氏書辯證》(鄧名世,2006:394)便綜合前說,將“妞”與“”二字的演變進行了梳理:
鄧名世之說是彼時解釋“妞”音形義演變的代表性觀點。據此,因《廣韻》《集韻》不載,古似并無“妞”字,與“”更無淵源。“妞”于北宋始現,以“氏”為“妞氏”,被視為“”的異體字。換言之,“妞”從宋代出現,由古“”的形近訛誤而來,與“”的古音義不盡相同。然自宋伊始,二者遂有合并的趨勢。究其因果,或許與“高麗姓”在北宋的出現密不可分,此點須另撰專題從宋與高麗政治文化的頻繁交流切入。無論如何,后世相關字書,遂將“妞”“”并見,而后“妞”日漸取代了“”的音形義,得到更為普泛的使用。如明代王圻《續文獻通考·皓韻》有“妞”“”(王圻,1986:3138),“二十五有”中亦有“妞”“侴”(王圻,1986:3140),并對該卷“內有字同而音異者”而兩見于類目的“妞”闡釋云“一音紐,一音好”(王圻,1986:3148)。這無疑就是將“”“妞”二音合一。另外較有代表的是《說文解字注》(段玉裁,1996:7):
段玉裁既整合了前人看法,也給出了自己的意見:第一,肯定“”是形聲字,從女,丑聲,呼到切;第二,“丑”的古音讀“狃”,與“好”的古音“朽”相近;第三,因為讀音相近,《尚書》中“”遂假借為“好”,以此援經為據,成為同聲假借通用的肇端。
據此,“妞”字音形義,便出現了漢學與宋學兩派觀點。前者以為“”乃“呼到切”、“好”義、人姓。至于與“妞”的關聯,語焉不詳。而后者以為“妞”即“”,有兩義,兩音。從形聲字構字演變規律來看,似乎宋學推測不無合理。漢字屬于表意體系的語素文字,在發展演變中,出現了一系列的異體字現象。王力先生(1981:171)將異體字分為四類,“變換各成分位置”便是其中之一,裘錫圭先生(1988:200)表達為“偏旁相同但配置方式不同”。因為構字元素置向變換,構意不變或相近而成的異體字是有一定數量的,例如和—咊、峰—峯、壟—垅、群—羣、嵒—嵓等。“妞”“”為一字,最早出現于《宋本玉篇》中,部件換用過程,也當然有各種內外部社會文化原因,宋代“妞”字的出現,是“”在漢字長期書寫演變過程中,在宋與高麗日益密切頻繁的社會文化交流接觸中,在活字印刷泛濫而易致訛誤等各種內外因作用下的結果,此并非本文贅述范圍。宋代出現的“妞”逐漸代替了古“”字,這已是社會約定俗成的事實,那么我們便不能循著段玉裁的思路,對這樣的改變視而不見了。
2.“妞”非“女”“丑”——“妞”字形聲部首濫觴
首先,聲符“丑”在古代漢語中并無“丑陋”義。究其原因,追溯至古今繁簡轉換中呈現的“一簡對多繁”現象。在這一過程中不同的繁體字用同一簡體字代替,同音替代,類推簡化,隨之而來的意義合并雖在大多數上下文中并無齟齬,然以破壞漢字的表意性為代價,在某些語境中極易出現謬以千里之誤。如“才—纔”,在古漢語中,前者是草木之初,后者才是副詞,而今以“才”總之,其“初始”含義在無形中就被淘汰了。再如“發—發—髮”,古“發財”和“頭髮”并非一字,而今以“發”總之,原字表意之別便不得而知了。又如“卜—蔔”,前者才有“占卜、卜卦”之義,而后者是“蘿蔔”專用字,今以“卜”總之,蘿卜的草木屬性,便不能從形聲字的結構中展示出來。
“丑—醜”同理可證,“丑陋”“丑惡”是用“醜”來表示。《說文·鬼部》(許慎,1963:189)訓“醜”:“可惡也。”《廣韻》(陳彭年,1912:45):“《釋名》曰:‘醜,臭也。如物臭穢也。’”張自烈《正字通》(1996:1260)列舉了很多例子,證實“可惡曰醜”“刺人之非曰醜”“謚法威肆行曰醜”“鱉竅曰醜”等屬于“醜”的含義。其一云:“《大玄·玄摛》曰:‘書以好之,夜以醜之。’注:好事在晝,醜事在夜。”《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顯而易見,古漢語“醜”才具有與“好”相對,與“惡”相同的核心義。
那么“妞”的聲旁“丑”核心義到底為何呢?《說文》(許慎,1963:310)訓“丑”為:
丑,紐也。十二月,萬物動,用事。象手之形。時加丑,亦舉手時也。凡丑之屬皆從丑。
許慎認為“丑”本是象形字,本義象手之形,引申為表時辰的“子丑”含義。對于他的觀點,后世學者是基本認同的。張自烈(1996:81)認為“丑”的“手”“手械”乃原核心義,演變為“子丑”是假借,且作為“手”和“子丑”含義的讀音是不同的。而“孥九切”才是“丑”的原音,他闡釋為:
這不失為一家之言。他對“丑”的讀音和假借關系有所修正,但是段玉裁并沒對其觀點亦步亦趨,反而對作為時辰的“子丑”含義如何由本義假借而來作出了詳細辨析:
(丑)紐也。《律歷志》曰:“紐牙于丑。”釋名曰:“丑,紐也。”寒氣自屈紐也。《淮南·天文訓》《廣雅·釋言》皆曰:“丑,紐也。”《糸部》曰:“紐,系也。”一曰:“結而可解。”十二月陰氣之固結已漸解,故曰紐也……人于是舉手有為。又者,手也,從又。而聯綴其三指,象欲為。而凓冽氣寒,未得為也。敕九切。三部……上言月。此言日。每日太陽加丑。亦是人舉手思奮之時。
“丑”是象形文字,象手;引申為時辰,即丑時。丑時就是舉手之時,是“萬物動、用事”之時。段氏認為一年中丑時的特征是“紐結解開”“陰氣消散”“陽氣上通”,此時正乃將春之際,眾皆欲舉手有為,奮發圖事。如果綜合張氏、段氏二人看法,概而言之,丑的引申義是從“取物”—“解結”—“舉手”—“子丑”一步一步漸進而來。而“凡丑之屬皆從丑”,意味著凡是具有“丑”義的字,都用此字素表示。
綜合許慎、段玉裁、張自烈的說法,以“丑”為聲符的大部分形聲字共證,歸納出最大公約數的聲符核心義素與規律,可見“妞”“紐”“扭”“忸”“狃”“鈕”“杻”“炄”“沑”“?”“羞”“?”“衄”“粈”“吜”等,因“凡丑之屬皆從丑”,便都多少沾上了“丑”的含義。這可分為幾組。一是有“丑”的本義“手”的內涵,例如“羞”,手持羊進獻;“扭”,用手揪打;“炄”,用手烤;“?”,手拿肉食;“杻”,手銬狀刑具;等等。二是有“丑”的“解結”之義,如“紐”,結而可解;“鈕”,印鼻,配印以帶穿之,上栓可解之環。三是以“丑”為聲,就是純粹的聲旁表音功能了,如“妞”“忸”“衄”“?”“沑”“?”“狃”“粈”“吜”等。
以上以“丑”為聲符的一組字,有些“聲符有義”,有些僅僅“以丑為聲”。即便如此,綜合古文“丑”所記語音的語義,并無現代漢語簡化字“丑”中“丑惡”“丑陋”之義,可見“妞”從誕生之初,其構字義素并不與現代漢語語義抵牾。
3.“妞”與“女孩”——滿語與漢語的漸次融合
“丑—醜”含義的南轅北轍,雖是繁簡轉化體系下產生的普遍現象,但僅以此闡釋“妞”字意義的古今演變,卻有囫圇吞棗之嫌。從上述分析可見,宋代雖出現了“妞”字,然其本義是“高麗姓氏”或“好”,并沒有“小女孩”之義,那后者是如何漸次出現并取代其原核心義的呢?《現代漢語詞典》(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2016:953)中,“妞”組了三個詞:“妞兒”“妞子”“妞妞”,注釋為“女孩子”或“小女孩兒”,且為方言。《漢語大字典》 (2003:1003)將“妞”分為兩個含義,一是高麗姓氏,二是方言中“對女孩兒的昵稱”。《漢字形義分析字典》(1999:390)專門指出,妞“作女孩兒講是現代義”。那么對應的“高麗姓氏”便是源自宋代的古義了。
“妞”的義符“女”,在古時則亦可用“子”代替。可見最初的“妞”與“女孩”并無絕對意義關聯。“”“”都可用作“好”的同聲通假字,在古文中作“”,在今文中作“”。《宋本玉篇·子部》:“,古文‘好’字。”(陳彭年,1983:529)《集韻·晧韻》:“好,古作‘’。”(丁度,1983:828)《集韻·號韻》:“無有作‘’,或從子。”(丁度,1983:1206)也就是說該字的義符在一定程度上可“女”“子”互換。實則直至清中葉,“妞”尚未完全有性別之分。曹廷杰(1985:21)在介紹庫頁島沿革形勝以及還境諸小島時,有一島名為“妞妞斐顏島”,注釋云:
妞妞斐顏島。滿洲語“妞妞”,呼愛小兒之詞。斐,顏色。
“小兒”無論男女,可見在當時的滿語里,“妞”并不專屬于女姓。《八旗通志》里,有許多“妞”作為姓氏之處,如“以管領妞妞管理,妞妞降革,以管領威和德管理”(鄂爾泰,1983:366);“福勒賀升任,以妞賀管理,妞賀故,以成太管理”(鄂爾泰,1983:429)。諸如此類因官職調遷提及的名字,亦可見其為男性。《八旗通志》 (鄂爾泰,1983:332)卷28中載“妞妞”:
妞妞,滿洲鑲黃旗人。……雍正九年,隨靖邊大將軍公傅爾丹征準噶爾,……力戰陣亡,賞如例。
《八旗通志》卷127有“正藍旗滿洲馬甲妞妞之妻李氏”(鄂爾泰,1983:104),卷256有“正黃旗滿洲馬甲妞格之妻齊氏”(鄂爾泰,1983:316),此類記錄隨處可見。《續通志》將“妞氏”正式編入《氏族略》(嵇璜,1983:390),可知“妞”在清代也有姓氏之義,而“妞妞”也非確指女性。而后乾隆道光年間,“妞”釋義性別化,傾向于獨指女性,但此時尚未劃分年齡層而確指“小女孩”。滿漢語境中所用“妞”而遵循的約定俗成年齡范疇也并不一致。滿族語“妞妞”雖字面來源于漢,然內涵卻有延續滿族名稱“格格”的意思,即云英未婚的“姑娘”“小女孩”,而漢語人群駁雜流動,地域廣袤,“妞妞”一詞使用則更廣泛。例如主要記錄嘉、道間北京民俗風情、藝林掌故的李光庭(1982:54)《鄉言解頤》卷三“優伶”條云:
嘟嚕胡、餡兒餅,人以聲傳;禿大漢、胖三妞,技因形肖。
以駢文的語言形式記錄了戲劇班的劇演與亂彈,說唱不僅兼合了各種聲腔,也化用了當時的滿、漢各類語調與方言。這“胖三妞”很明顯就與“禿大漢”的性別是對應的關系,乃為女性,但并非專指小女孩。“妞妞”尚未分界年齡,僅專指性別的情況延續至清末,王彥威、王亮父子(2015:165)前后輯成的《清季外交史料》,有眾多牽涉女性案件的實例,其中書寫“妞”處甚多,如:
堂中婦女胡宋氏、譚蘭英、李再姑、戴貞姑、劉三妞,被黃之紳、楊琴錫愚弄入堂,其失身也,由于威脅,并非出自本心,應一并免其置議;與孀婦劉吳氏幼女侯佑妞、白香妞、鄭幺妞、李六毛,均發還建平縣,飭令具領干證。
上引檔案中的“姑”“妞”雜用,身份有婦女,有遺孀,還有幼女,有的是已婚成年人身份,有的卻是幼小女孩。可見當時漢文中“妞妞”含義唯在于性別間,不拘泥于年齡處。而嘉、道間的滿語雖被漢語不可逆轉地強勢演化,然自己的底蘊特征也仍是有跡可循的。例如本是皇族女兒的專有稱謂“格格”,在身份地位下降演化為官宦家庭的女兒以后,與“姑娘”含義便接壤起來。滿族文學家文康的古典小說《兒女英雄傳》是第一部兼用漢、滿語寫成的小說,客觀實錄了嘉、道之際滿漢兩族語言的拉伸搏擊、北京方言引用滿語詞匯的過程,書中兩種語言兼用而形成的生疏、流動狀態,使得書中旗人的性格更為栩栩如生,在第七回(文康,2018:92)中有:
格格兒,你可別拿著合我的那一銃子性兒合人家鬧。
顯然,這里的“格格”是“姑娘”含義。以“格格”為“姑娘”本是建構于滿語內部自身的演變系統之下,然由于漢語言的強勢風靡,漢語中的“妞妞”與“姑娘”逐漸掛鉤起來。“妞妞”在滿語中本體之義是“眼珠兒”,經過漢語專指“女子”意義的感染后,滿族對愛女、女孩子等稱呼“妞妞”,中和了滿漢兩族的語言內核。《清稗類鈔·皇室皇族之女稱謂》(徐珂,1984:2182)中載:
若宗室,若覺羅,若閑散八旗,若內府三旗,凡對于未嫁之幼女,皆稱妞妞。
《清稗類鈔·八旗方言》(徐珂,1984:2225)亦云:
妞兒,姑娘也。
《清稗類鈔·小姐姑娘》(徐珂,1984:2185)還對此解釋:
姐,姐兒也;輕之之辭也……北方有稱姑娘者,旗人尤多,揣其意義,實較小
姐為尊也。既嫁,則稱姑太太,或姑奶奶。
實則是將漢語原來“妞妞”的女性性別特殊化為滿語“格格”中尊貴身份的未婚閨女,兩相糅合而稱為“妞妞”,并徹底劃清了已嫁女性的稱呼,將“姑”綴改為“太太”或“奶奶”。以此來對應眾多滿族作家的文學創作,可以看到,他們是遵循了這一滿漢語言的中和結果,默認使用“妞妞”的“女孩”“姑娘”含義范疇的。如剛剛提到的《兒女英雄傳》(文康,2018:562)中,出現了眾多筆涉“妞妞”處,茲舉一例:
何小姐最是心熱不過的人,聽了婆婆這話,一面歸著那東西合張姑娘道:“實在虧婆婆想的這等周到。”安老太太笑道:“妞妞,也不是我想的周到……”
何小姐在文中是“證明守宮砂”之人,文中將何小姐稱“妞妞”,是遵循了“妞妞”的年齡劃分循例的。又如《清文指要》(張美蘭,2013:233):
你的那個妞妞若是不撂,也十幾歲了①嘉慶十四年三槐堂重刻本此句為:“你那個兒子若是不丟,也有九歲十歲了。”文中引文是嘉慶十四年大酉堂重刻本。。
英國欽差威妥瑪(2002)編寫的《語言自邇集》中《談論篇》抄錄自《清文指要》,此條為:
你們妞兒若不扔,如今也有十幾歲了?(《談論篇百章之87》273頁)
該句下有注,但威氏對于此例注釋未探本求源,說成“這個字(詞)據說來自朝鮮語”。其顯然將“妞”在宋代之前的字形、含義演變腰斬,只看到了宋代后的“高麗姓氏”含義。近代日本漢語課本以威氏此書為主,讓學生習得抄寫,日本靜嘉堂文庫8冊16卷抄本的頁面欄外針對此條有“明治十五年(1882)”的學生眉批(2010:53):
眉批:妞→姐,滿洲曰“妞兒”,漢人曰“姑娘”,或曰“姐兒”亦可。
批注筆記比《語言自邇集》本書更能反映當時北京地區的流行語特點②日本漢語教育從明治九年(1876)開始從南京官話轉為北京官話(參看何盛三,1928:71-72)。。此處對“妞”作注疏,也是因為“妞”字有自身的滿族語言內涵與情感色彩,與古漢語“妞”存在不一樣的敘述范疇,而滿語中的“妞”更符合漢語“姑娘”“姐兒”內核含義,須得加以注釋說明。此外,嘉慶年間的滿洲鑲黃旗大臣托津為上奏白蓮教興起后的剿滅始末,呈《平定教匪紀略》(托津,2002:298),其中數條案宗如:
妻楊氏,生子三人,長男幅昌,次男重慶,三男鶴齡,女妞兒。(《史部》卷16)
又(托津,2002:60):
稱田米鳳有二子,長名元妞兒,十九歲,次名拉妞兒,十二歲,現在不知下落。(《史部》卷39)
上述諸多舉例可見,“妞妞”在滿族文獻中,不約而同嚴格恪守了由“格格”演化而來的“姑娘”含義,有意識將“妞妞”一詞應用于未婚弱齡段,而舍棄了原漢語中的已婚成年女性的年齡雜指范疇。
此外,曹雪芹《紅樓夢》成書于乾隆朝,其中使用“妞妞”“妞兒”處甚多,如“我瞧大妞妞這個小模樣兒,又有這個聰明兒,只怕將來比鳳姐姐還強呢”,“王夫人也哭道:‘妞兒不用著急。’”(曹雪芹,2015:538)可見遠紹于清中葉,“妞妞”滿語使用的年齡弱化、“姑娘”含義固化,已經有成熟的使用文獻可證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妞妞”是滿漢兩族語言在清中后葉始次第交融的產物,然兩種語言的熔鑄,自然也有一個從分割到合流的歷程。這不僅體現于“妞”使用的南北地域有語言實踐習慣的不同,還體現于該詞的感情色彩轉移演化。前者因為地域局限而致語言傳用隨民族人口分布而各異,后者實際上體現了滿語自身體系的重構、完善與接納漢語的雙重演化過程。
首先,“妞”的使用有地域之別,尤其在生活口語使用層面,生活于乾隆朝的郝懿行(2002:467)《證俗文》卷4有載:
青、徐州呼女曰娪娪,忤也。女始生,人意不喜,忤忤然也。《釋名》案:“娪”音“誤”。《廣韻》又音“吾”。《埤倉》美女也。今京師謂女曰“妞”,亦作“”,音“紐”,呼為“妞妞”。若大曰“大妞”,次曰“二妞”,又次曰“三妞”。
郝懿行所謂的京師謂女曰“妞妞”,青、徐呼“娪娪”,顯然是地域方言分化且發展不平衡的投射。梁章鉅(1996:91)《稱謂錄》亦有文獻條錄,可與《證俗文》兩相呼應:
娪 《方言》吳人謂女曰“娪”。《釋名》云:青、徐州呼女曰娪,娪,忤也。女始生,人意不喜,忤忤然也。
珠娘 《閩小記》:福州呼女亦曰“珠娘”。
阿嬌 《輟耕錄》:關中以兒女為“阿嬌”。
奧姑 《遼史·公主表》:契丹故俗,凡婚燕之禮,推女子之可尊敬者坐之奧,謂之“奧姑”。
若以“妞”字的“姑娘”“女孩”“女性”之義求之,南北方與京師的稱謂習慣顯然是不同的,附帶的地域痕跡,跟南方遠離京城,人口流動駁雜,方言眾多,而滿族旗人卻大多集中于京師附近有關。俞正燮《癸巳存稿》(1937:473)亦載:
孃者,少女之稱,亦作娘,轉作妞。北人稱妞妞,南人稱娘娘是也。南人音亦轉孃,蘇湖言某老孃是也,倪、嫛、嬰,方言不同,亦轉為妞,其義亦同。詩《季女斯饑》箋云:“弱者之稱。”則呼小兒曰妞,曰娘,曰妹,亦詩季女義也。
“妞”的音變,與方言調律尤其是南方的音腔雜蕪、輔音變化、古音保留等語言特色互為匹配,因此出現了“妞”與“娘”“孃”之間的轉音現象,然其“弱女”之義已緩然趨同。北方地區,尤其是滿漢接觸頗多、語言融合程度較強的“京師”,稱少女為“妞妞”已相當普遍。正如前引《清稗類鈔》中“八旗方言”條,也是“妞”在八旗聚居的京師而成為滿族雅言常用語的例證。
滿漢“妞”的語調雖有音轉,但語義已漸趨同,然細究其間,仍然有感情色彩的偏差。此偏差并非顯性的敘述,除去與南北風俗觀念潛移默化之關聯(如前引《稱謂錄》吳人、青徐州生女不喜,以“忤忤然”音代之“娪”,而京師卻以“”代之),事實上還與滿語經過漢語的沖撞而自身內部體系的演變、重組、建構有關。滿語中本也有“妞妞”,那我們為何認為滿語中的“妞妞”是由漢語“妞妞”內蘊引入而來呢?因為“妞妞”在滿語中最初并非貴族旗人的雅言,反而是極其口語化的俗語,跟它后來的“格格—姑娘”含義演變實則未曾接壤,是割裂的。奕賡《佳夢軒叢著之八·管見所及》(1994:87)中提道:
我朝在東土時,上古純風,樸而不雕,故滿洲、蒙古命名,多不取吉祥字面,有七十三、八十四、五十、六十之名,又有騷達子、白達子、二妞、黑小子、白小子、妞妞等名,正藍旗輕車都尉名六十兒,廂藍旗云騎尉名老米,皆乾隆間人也……
可知“妞妞”與“二妞”在“我朝東土”時,即未入關接受漢族文化以前,被歸為“不取吉祥字面”的名字,此處“吉祥”實則并非今日之“吉利”,乃指代日常俗語、口語化,與雅言是相對的,此條追溯了滿語“妞妞”最初的下里巴人的本體內蘊。以此亦能窺見“妞妞”在未漢化的滿語中,與后來的比“小姐”稱呼更為尊貴的“姑娘”含義毫無關涉,甚至性別也可為男性(前已論之)。而滿語在自身體系重構下,將“格格—姑娘—妞妞”含義關聯起來,顯然是接受了古漢語“妞”字中的“好”含義;而將“妞妞”特指為女性,則是接受了漢語中“妞”的性別專名演變結果。
在旗人小說、滿族文獻或旅居于京師附近的文人創作的文學作品中,“妞妞”的使用與純粹南方作家隱藏于字里行間中的內涵認知與情感從屬也有細微區別。例如滿族民歌《寄生草》與江南本土小說《孽海花》中“妞妞”的情感從屬,便是有異有同的:
有一個妞妞兒在門前立,抬頭看見個挑擔的……欲要買,作女孩兒的怎出去?(《寄生草》)
宮里喚金妃做大妞兒,寶妃做二妞兒,都生得清麗文秀。(《孽海花》)
那天是內務府紅郎中官慶家的壽事,堂會戲唱得非常熱鬧,只為官慶原是個紈挎班頭,最喜歡聽戲。他的姑娘叫做五妞兒,雖然容貌平常,卻是風流放誕,常常假扮了男裝上館子、逛戲園,京師里出名的女戲迷。(《孽海花》)
表面上但看兩書“妞”的運用,似乎僅是年齡的不同,這本可歸為漢滿語言尚未完全融化、尚留存本民族觀念的闡釋,但其中的確也潛藏了些許情感差異。首先,滿族民歌是“妞妞”合用,寫出了嬌弱憐愛、楚楚動人的未嫁女孩子的靦腆羞澀,而《孽海花》的作者金松岑、曾樸都是江蘇人,記敘語言自然地夾雜了蘇州地方語,其中的民間諺語、俗語也多隸屬吳語體系,且這部本來是諷刺譴責小說,上舉兩例,一說的是宮里的皇帝嬪妃,二說的是滿族豪奢大臣家的紈绔女兒,對“妞”的描繪對象都有貶義的反諷語調,因而單用一“妞”,而并未“妞妞”連用,筆下亦藏微言。無獨有偶,同為譴責小說的《老殘游記》,也是如此單用“妞”字。劉鶚(2001:10)在小說中寫到了兩個山東曲藝界梨花大鼓的代表藝人16歲的“白妞黑妞姊妹兩個”。兩人吸收皮簧、梆子、昆曲及臨清小曲和眾多新腔,使得梨花大鼓,也即后來的山東大鼓呈現出新的韻味,《明湖居聽書》一段就是描寫白妞精湛高亢的演唱技藝的。雖是贊譽之辭,但細究其所指代人的身份,是賣唱的歌舞藝人,社會地位低下。換言之,此“妞”的隱述式身份,離滿語中“格格—姑娘—妞妞”的“可愛小女孩”情感色彩,是有一定差距的。此隱形式的差異,存在于滿漢作家的潛在性共知中,下筆行文時時有所涌現。延續至現代滿族文學家老舍《駱駝祥子》中塑造的一個著名女性形象——祥子的妻子、性格強勢的“虎妞”,老舍先生將虎妞這個名字,與潑辣爽利、強悍自主甚至市儈的形象關聯起來,這與文中名為“小福子”的另一人物——代表著傳統柔弱溫順、逆來順受的女性形象對比,判然有別。
4.結論
現代漢語是在以北京話為代表的北方方言基礎上生成的。17世紀以后,滿語與漢語雜糅而成的“京腔兒”自然遺留了下來。“妞妞”便是滿語Nio nio([ni?:ni?:])的漢字音記,也保留著滿族“未婚女孩”的內涵。因此,把未婚小女孩稱“妞”體現了自清代中后葉伊始的“滿式漢語”的語言特點。隨著現代漢語的規范與普及,“妞”作為“小女孩”這個并不悠久的歷史含義趨于成熟,然而古漢語中“妞”的“好”“高麗姓”義乃至更為遙遠的包含聲旁“丑”含義的相關義素,卻逐漸廢弛。我們以“妞”一斑窺豹,看到滿漢兩大語言體系從分據割裂而至義理通釋,在融合創變中卻仍封存各自的民族傳統觀念、情感的復雜過程,也能看到今日的“北京話”(即京腔)不能片面以滿漢兩族語言撞擊融合而一貫視之,還有兩方內部的語言形塑和修補過程,以及各自的“殘留碎片”存于其中,這些因素如“妞”一樣,有的能從今日北京方言遺留的表象中追溯到曾經分歧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