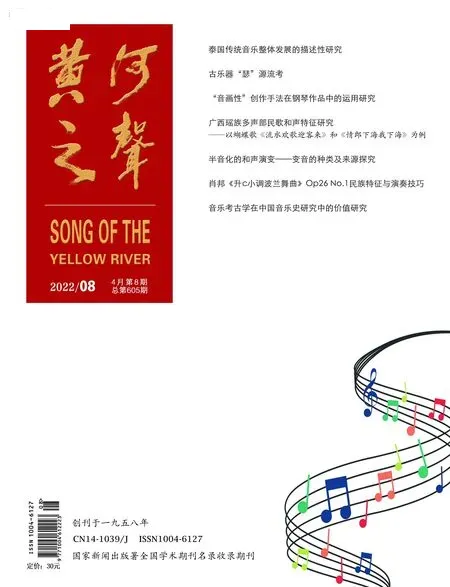歷史民族音樂學(xué)當(dāng)下發(fā)展探析
葉智超
在民族音樂學(xué)的發(fā)展長(zhǎng)河中,不管是比較音樂學(xué)時(shí)期還是現(xiàn)代民族音樂學(xué)時(shí)期,其更多的是從共時(shí)研究的定位出發(fā)去研究音樂事象。但在上世紀(jì)七八十年代以來(lái),隨著西方民族音樂學(xué)的不斷發(fā)展,學(xué)界學(xué)者們認(rèn)識(shí)到歷時(shí)研究的視角對(duì)于學(xué)科發(fā)展的重要性。國(guó)內(nèi)外音樂學(xué)界均紛紛開始注重從歷史的角度去重新看待民族音樂學(xué)的發(fā)展,一時(shí)間,歷史民族音樂學(xué)到底是作為一門學(xué)科還是領(lǐng)域或視角來(lái)發(fā)展這一頗具爭(zhēng)議性的話題被推到了風(fēng)口浪尖上。而回顧民族音樂學(xué)這一肇始于西方、首創(chuàng)于西方的學(xué)科之整個(gè)發(fā)展歷程,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早在比較音樂學(xué)時(shí)期,學(xué)者們對(duì)于歷史的研究就有很大的興趣。本文對(duì)歷史民族音樂學(xué)當(dāng)下發(fā)展闡述筆者自己的一些拙見,希望能對(duì)中國(guó)歷史民族音樂學(xué)當(dāng)下的發(fā)展起到些許推波助瀾的作用。
一、歷史民族音樂學(xué)的研究范疇
民族音樂學(xué)(或稱音樂人類學(xué))自誕生至今,更多的是從共時(shí)研究的定位出發(fā),正如內(nèi)特爾曾談到的:歷史音樂學(xué)用歷時(shí)觀,民族音樂學(xué)用共時(shí)觀,而這早已是過(guò)去的范式了。眾所周知,西方民族音樂學(xué)理論多關(guān)注“活態(tài)音樂”的研究,對(duì)于音樂的歷史進(jìn)程卻很少予以研究和關(guān)注,導(dǎo)致了共時(shí)性研究的色彩偏重。針對(duì)研究對(duì)象,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這種局面在20世紀(jì)下半葉有所改觀。民族音樂學(xué)的歷史研究是隨著20世紀(jì)下半葉出現(xiàn)歷史學(xué)人類學(xué)化與人類學(xué)的歷史化進(jìn)程不斷加速而受到音樂學(xué)界關(guān)注的。事實(shí)上,新史學(xué)或歷史人類學(xué)并不是新興的“學(xué)科”,甚至也不是特殊的研究領(lǐng)域,它是一種學(xué)術(shù)思維或方法,目的是“始終將作為考察對(duì)象的演進(jìn)和對(duì)這種演進(jìn)的反應(yīng)聯(lián)系起來(lái),和由這種演進(jìn)產(chǎn)生或改變的人類行為聯(lián)系起來(lái)。”①
在學(xué)界注重歷史研究的思考的大背景下,亦有學(xué)者在文論中指出,歷史民族音樂學(xué)應(yīng)把音樂史還原到上下文語(yǔ)境中思考,也就是從文化語(yǔ)境入手,注重整體研究。“過(guò)程”研究理念早在上個(gè)世紀(jì)民族音樂學(xué)者就已經(jīng)提出來(lái),而筆者認(rèn)為“過(guò)程”研究應(yīng)結(jié)合文化語(yǔ)境去思考。相信我們都還記得梅里亞姆曾說(shuō)過(guò)“把音樂作為文化來(lái)研究和文化語(yǔ)境中的音樂研究。”②而民族音樂學(xué)研究就是要在知道“是什么”的這一層面轉(zhuǎn)向文化內(nèi)涵和語(yǔ)境層面,從而去說(shuō)明“為什么”的問(wèn)題。若能說(shuō)清楚這一問(wèn)題,豈不是加強(qiáng)了學(xué)科的歷時(shí)性定位,從而完善學(xué)科多注重共時(shí)性研究、較少觸及歷史的缺憾。而力圖要說(shuō)明“為什么”這一問(wèn)題,必然會(huì)涉及歷史文獻(xiàn)資料的收集和整理,下文就將主要圍繞這一問(wèn)題展開。
二、研究理論與方法
眾所周知,民族音樂學(xué)最核心的方法論就是田野調(diào)查。在《民族音樂學(xué)導(dǎo)論》里的《歷史民族音樂學(xué)》一文。筆者認(rèn)為該文僅對(duì)歷史民族音樂學(xué)做了概論式的敘述,并未論及當(dāng)時(shí)歷史民族音樂學(xué)的前沿觀點(diǎn),但該文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民族音樂學(xué)面對(duì)歷史研究的困境,即民族音樂學(xué)無(wú)法真正回到過(guò)去開展田野考察。在空間維度上我們已無(wú)能為力,但記憶是承載在人的頭腦里的,樂事必然與樂人緊密相關(guān)。口述史的發(fā)展帶給我很大啟發(fā),傳統(tǒng)是歷史的連續(xù)統(tǒng),既存在于過(guò)去也存在于現(xiàn)在,是連接過(guò)去與現(xiàn)在的紐帶,而口頭傳統(tǒng)與音樂表演則是連接過(guò)去與現(xiàn)在的核心元素,因此民族音樂學(xué)者們可以依靠田野考察以口述史方法收集口傳與表演資料來(lái)親觸歷史。
行文至此,腦海里突然想起一位對(duì)我學(xué)術(shù)研究影響很大的學(xué)者—英籍學(xué)者鐘思第。鐘先生在南高洛考察音樂會(huì),連續(xù)十年,最終成為一名南高洛音樂家,這種研究精神確實(shí)令人敬佩。我們常常在思索如何做田野調(diào)查,如何更好地關(guān)懷我們的研究對(duì)象,從鐘先生的身上可以看到那種“參與式觀察、浸入式體驗(yàn)”的學(xué)術(shù)品格。
對(duì)于歷史研究,文獻(xiàn)分析可能是大多數(shù)學(xué)者更傾向于采用的方法,而文獻(xiàn)資料大多是前人田野考察累積下來(lái)的經(jīng)驗(yàn),我們?cè)谝脮r(shí)必然會(huì)發(fā)現(xiàn)有和自己觀點(diǎn)不相契合的地方,這種不相契合并不是一種矛盾或沖突,而是在提醒我們要去挖掘隱藏在文字背后的一些現(xiàn)象,即追問(wèn)歷史文本到底想表達(dá)什么問(wèn)題。1998年人類學(xué)家卡洛琳布列特爾提出“文獻(xiàn)中的田野調(diào)查”這一個(gè)概念,她將其分為兩方面,一方面可以理解為文獻(xiàn)研究與口述歷史相結(jié)合、相印證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可以理解為在文獻(xiàn)中進(jìn)行田野考察,這引出一個(gè)問(wèn)題,即如何在文獻(xiàn)中做田野考察?筆者認(rèn)為,歷史文獻(xiàn)的價(jià)值不僅在于歷史文獻(xiàn)向我們傳達(dá)了什么信息,而更重要的是去理解文字、文獻(xiàn)所內(nèi)含的意義。在文獻(xiàn)分析的過(guò)程中,再加上對(duì)歷史、史料的學(xué)習(xí),困擾我的問(wèn)題也越來(lái)越多,自己也做了很多思考,但終究因自身學(xué)術(shù)能力淺薄,還是一直“云里霧里”,下面談?wù)勎宜伎嫉囊恍﹩?wèn)題。
三、文本的歷史書寫
歷史是由誰(shuí)構(gòu)建的?歷史又是由誰(shuí)來(lái)書寫的?歷史似乎很遙遠(yuǎn),但又離我們很近。正如意大利史學(xué)家、哲學(xué)家克羅齊所說(shuō):“一切歷史都是當(dāng)代史”。③在讀完郝苗苗老師的《西方民族音樂學(xué)視野下的“音樂政治學(xué)”研究》一文后,我深感若想要追求歷史的絕對(duì)客觀性似乎不太可能。歷史是由人來(lái)書寫的,難免帶有一定的主觀性和選擇性,而歷史事實(shí)本身是怎樣的?恐怕只有回到當(dāng)時(shí)那個(gè)歷史語(yǔ)境中才能探知一二。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大多是對(duì)社會(huì)精英階層的描寫,而對(duì)下層、底層人士以及草根階級(jí),筆墨所及之處實(shí)屬罕見。還有相當(dāng)一部分文獻(xiàn)史料是采用口述的方式記載下來(lái)的(音樂口述史的發(fā)展),通過(guò)訪談,可以將樂人對(duì)歷史的記憶用文字呈現(xiàn)出來(lái),但隨著時(shí)間的流逝,記憶也在慢慢“溜走”,樂人們對(duì)過(guò)往的歷史也在漸漸淡忘,口述史料也并不與歷史事實(shí)完全相符。其次,有學(xué)者在文論中指出,怎樣看待傳統(tǒng)歷史文獻(xiàn)與在場(chǎng)音樂表演文本之間的差異性問(wèn)題。④我們都知道,每一次的音樂表演都是“去語(yǔ)境化”與“再語(yǔ)境化”的過(guò)程,傳統(tǒng)歷史文獻(xiàn)再現(xiàn)的只能是聲音語(yǔ)境,而音樂表演語(yǔ)境已成為無(wú)數(shù)個(gè)“過(guò)去式”。
如何看待“歷史文本”與“歷史事實(shí)”之間的差異性問(wèn)題。⑤從不同角度出發(fā)會(huì)有不一樣的答案,史學(xué)研究關(guān)注“歷史民族”,而民族音樂學(xué)學(xué)科早期主要關(guān)注和研究“無(wú)文字族群”,通過(guò)口述的方式獲取資料,也稱“口述文本”,歷史學(xué)主要關(guān)注傳統(tǒng)歷史文獻(xiàn)的研究,也就是“書面文本”。學(xué)科在后來(lái)的發(fā)展過(guò)程中,受到傳統(tǒng)歷史學(xué)的影響,逐漸轉(zhuǎn)向“歷史民族”的研究,歷史民族音樂學(xué)這一學(xué)科概念的提出,即是對(duì)這一學(xué)科研究層面轉(zhuǎn)向的呼應(yīng)。不管從哪個(gè)視角去分析這一問(wèn)題,其實(shí)都殊途同歸。何謂“真實(shí)”?何謂“不真實(shí)”?萬(wàn)事萬(wàn)物本就沒有絕對(duì)的客觀性。歷史放在過(guò)去的那個(gè)語(yǔ)境下是真實(shí)的,放在當(dāng)下來(lái)看,由于種種客觀因素,歷史在被不斷重構(gòu)。正如湯亞汀在其《民族音樂學(xué)與現(xiàn)代音樂史》⑥明確指出,從這本著作的15篇文章可以看出:民族音樂學(xué)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已經(jīng)從對(duì)音樂結(jié)構(gòu)的分類、描述、解釋,轉(zhuǎn)向了力圖理解作為文化的音樂。
這給我們民族音樂學(xué)者帶來(lái)些什么啟示呢?類似的問(wèn)題在音樂口述史中也很常見,口述文本的真實(shí)性和準(zhǔn)確性也很值得商榷,“歷史表述”并非“歷史真實(shí)”。那既然“史料”如此的“失真”,如此不值得信賴,那為何我們還要不斷在歷史文獻(xiàn)中去做田野?我們不是應(yīng)該拋棄史料,只關(guān)注當(dāng)下的“活態(tài)”音樂,不就夠了嗎?顯然不是這樣。無(wú)數(shù)個(gè)當(dāng)下最終都會(huì)成為歷史,構(gòu)成歷史。若是如此,那豈不是又回到了比較音樂學(xué)時(shí)期,學(xué)科的歷時(shí)性定位還有何意義?歷史民族音樂學(xué)這一學(xué)科概念的提出又有何意義?在這樣的一個(gè)“漩渦”里,我們要學(xué)會(huì)“求真”。何謂“求真”?如何“求真”?存在主義哲學(xué)家馬丁海德格爾把“真理”解釋為“去蔽狀態(tài)”。實(shí)踐是檢驗(yàn)真理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我們只有通過(guò)不斷地回顧歷史,在田野考察中去檢驗(yàn)歷史,收集第一手的田調(diào)資料和口述材料,從而去反觀歷史。當(dāng)下的事物都有以前歷史的影子,任何事物的發(fā)展都需要借助歷史的力量,二者相輔相成,通過(guò)當(dāng)下來(lái)反觀歷史,通過(guò)歷史來(lái)映照當(dāng)下。
四、“領(lǐng)域”亦或“作為一門學(xué)科”
Ethnomusicology這一外來(lái)術(shù)語(yǔ)在剛進(jìn)入中國(guó)的時(shí)候,對(duì)于其譯名及其學(xué)科性質(zhì)問(wèn)題在中國(guó)音樂學(xué)界引起了廣泛關(guān)注。學(xué)者們紛紛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觀點(diǎn),主要圍繞“民族音樂學(xué)”和“音樂人類學(xué)”這兩種譯名展開論述。Ethnomuscicology的中文譯名“民族音樂學(xué)”為我國(guó)學(xué)者羅傳開20世紀(jì)70年代末從日文譯名引入。關(guān)于此方面的文論有:魏廷格1985年發(fā)表的《對(duì)民族音樂學(xué)概念的思考與建議》、喬建中、金經(jīng)言發(fā)表的《關(guān)于Ethnomusicology的中文譯名建議》、薛藝兵的《從學(xué)科名稱說(shuō)起》、杜亞雄的《關(guān)于民族音樂學(xué)的幾個(gè)問(wèn)題》、蕭梅、韓鍾恩的《音樂文化人類學(xué)》、楊沐的《漫談音樂人類學(xué)的定義與范疇》、孟凡玉的《音樂人類學(xué)的范疇、理論和方法》、連赟的《芻議民族音樂學(xué)的歷史演變、概念泛化及學(xué)科分野——兼論“民族音樂學(xué)”與“音樂人類學(xué)”和“音樂文化學(xué)”的關(guān)系》、洛秦的《音樂人類學(xué)的歷史與發(fā)展綱要》等。關(guān)于其學(xué)科性質(zhì)問(wèn)題,有學(xué)者認(rèn)為民族音樂學(xué)(或稱音樂人類學(xué))可以作為一門獨(dú)立的學(xué)科,但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其只是一個(gè)領(lǐng)域、一個(gè)視角。洛秦老師曾明確指出:他認(rèn)為音樂人類學(xué)是一種思想,而非學(xué)科,并闡明了自己的理由和看法。洛秦老師認(rèn)為,構(gòu)成一門獨(dú)立學(xué)科必須具有三個(gè)基本要素:1)獨(dú)特的研究對(duì)象;2)特有的理論體系;3)學(xué)科自身所需的方法論。⑦雖然,田野考察和民族志寫作是音樂人類學(xué)區(qū)別于音樂學(xué)其他領(lǐng)域的主要特征,而二者恰恰又是人類學(xué)的核心所在。
那么,歷史民族音樂學(xué)應(yīng)被看作是一門獨(dú)立學(xué)科還是一個(gè)領(lǐng)域或視角呢?赫伯特和邁凱倫在《歷史民族音樂學(xué)理論和方法》一書中指出,應(yīng)將歷史民族音樂學(xué)定位為民族音樂學(xué)的一個(gè)新興子領(lǐng)域。筆者認(rèn)為,如果將歷史民族音樂學(xué)視為某一學(xué)科,容易畫地為牢,束縛其可能涉及的學(xué)術(shù)空間,若將其看作是一個(gè)多元開放的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則能將多學(xué)科研究方法共同納入這一研究領(lǐng)域之中,這也是能夠?qū)v史民族音樂學(xué)視作一種學(xué)術(shù)視角,一類學(xué)術(shù)方法,一個(gè)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的原因。并且,如果將其看作一個(gè)研究視角或領(lǐng)域的話,就是在強(qiáng)調(diào)我們做民族音樂學(xué)研究時(shí)需要關(guān)注歷史維度,這就有益于我們?cè)谧约旱难芯恐写蜷_自己的視野。作為一名資歷尚淺的民族音樂學(xué)方向的碩士研究生,拙文必定有很多不足之處,分析問(wèn)題還很不全面,有待進(jìn)一步探索。■
注釋:
① 雅克·勒高夫.新史學(xué)[M].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238.
② 趙書峰.歷史民族音樂學(xué):把音樂史還原到上下文語(yǔ)境中進(jìn)行研究——兼論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音樂史書寫的難題與對(duì)策[J].武漢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7,(01):120-121.
③ 貝奈戴托·克羅齊著.傅任敢譯.歷史學(xué)的理論和實(shí)際[M].商務(wù)印書館,2010:13.
④ 趙書峰.關(guān)于中國(guó)歷史民族音樂學(xué)研究中幾個(gè)關(guān)鍵問(wèn)題的思考[J].中國(guó)音樂,2019,(01):58.
⑤ 趙書峰.關(guān)于中國(guó)歷史民族音樂學(xué)研究中幾個(gè)關(guān)鍵問(wèn)題的思考[J].中國(guó)音樂,2019,(01):57.
⑥ 湯亞汀.民族志新寫作與歷史重構(gòu)的故事——《民族音樂學(xué)與現(xiàn)代音樂史》譯后[J].音樂藝術(shù),2008,(03).
⑦ 洛秦.音樂人類學(xué)的理論與方法導(dǎo)論[M].上海音樂學(xué)院出版社,201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