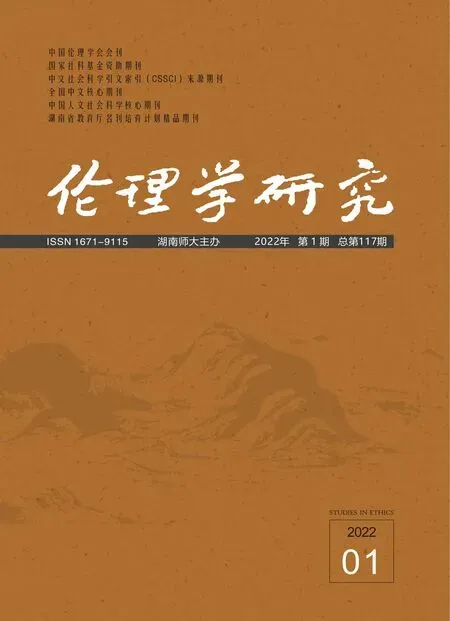董仲舒經權觀對道義論立場的回歸
趙清文
儒家關于“權”的學說始于孔子。在孔子和孟子等先秦儒家的論述中,與“權”并提的往往是“道”“禮”等概念。在中國思想史上,將“經”與“權”對舉是從成書于漢景帝時期的《春秋公羊傳》開始的。公羊家提出的“反經為權”的觀點,一直到宋代之前,都是經權觀上的主流思想。從倫理思想的角度來說,不同的經權觀不但反映著學者們對具有原則性和普遍性的道德準則與具體情境中主體道德選擇的靈活性和能動性之間的關系等具體問題上的看法,而且也體現了他們倫理思想上的基本傾向。
一、背反于“經”還是返歸于“經”:字義訓詁背后的倫理思想傾向
《春秋公羊傳·桓公十一年》在評價鄭國的祭仲“出忽而立突”一事時說:“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后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這是中國思想史上關于經權關系的最早的直接闡述,也是《公羊傳》中唯一一處直接對經權問題的論述。這段論述中,涉及了“經”“權”“善”“道”等幾個中國傳統(tǒng)經權觀中核心的概念,并且通過這幾個概念,對“經”與“權”的關系、“權”的合理性限度以及行權的條件和一般原則等問題進行了闡述。
關于“經”和“權”之間的關系,《公羊傳》認為,“權者反于經”。對于這句話中的“反”字,學者們有著不同的解讀。歷史上,大部分學者都是將其理解為“背反”或“違背”之義。但是,清代之后,有人認為,這一“反”字應是“返”的通假字,意思是“返歸”“回歸”。最早明確提出這種見解的是俞正燮,他說:《公羊傳》中的“‘反經’之‘反’,為‘十年乃字,反常也’‘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之‘反’,為反歸之反,非背反之反”。他還認為:“以背反于經為權,漢以前經傳箋注實無此說也。”[1](63)現代的一些學者也沿襲此說。比如,蔡仁厚曾經說:“《公羊傳》云:‘權者,反于經然后有善者也。’無經則權無所用,故必須反(返)于經而后乃能成其善。由此可知,一個不能守經的人,根本不足以言‘行權’。”[2](345)在引用《公羊傳》的論述之后,他特意對“反”字加了一個“返”的注解,來說明他所理解的行權和守經的一致性。李新霖不僅認同俞正燮的觀點,而且進行了補充論證。他以“《公羊傳》中言及‘反’而有‘返’意者,所在多有”為論據,通過對《公羊傳》中其他部分出現的“反”字的分析,總結認為:“無論‘反’接虛詞再接實詞,或‘反’接實詞而虛詞而實詞,皆有‘返’意。故用是而觀,《公羊傳》云:‘權者反于經,然后有善者也。’意指道有經有權,若經立大常,權則用以應變。但經權雖不同,卻不相反,甚至通變之權原本于經。”[3](195-198)
當然,也有許多學者并不贊同這種觀點,認為將“權者反于經”的“反”字解釋為“返”的論據本身是有問題的。盡管在傳統(tǒng)典籍中,“反”常用作“返”義,甚至有可以將“反經”解釋為“返經”的先例,如《孟子·告子下》中的“君子反經而已矣”中的“反經”。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公羊傳》中“權者反于經”的“反”字也必然訓為“返”。針對李新霖等人的觀點,林義正反駁說:“《公羊傳》文中,‘反’字并非皆作‘返’意,如‘反袂拭面’之‘反’即作‘背反’解。”[4](139)由此可見,《公羊傳》及其之前的經典文本中沒有釋為“背反”的“反”,本身就是不符合事實的。退一步講,即使?jié)h代之前的經典及箋注中真的沒有這種先例,僅僅因此就認為公羊家們“反經為權”的“反”字也不應釋為“背反”,這種觀點未免過于狹隘,所得結論也過于草率。
“權者反于經”中的“反”字究竟作何解釋,最重要的還是應當從這一觀點本身來進行分析。有學者論證說,依據《公羊傳》中的傳文,“權若‘歸返’于經,又何必再次強調必須‘有善’?且若以‘歸返’釋權,則權亦只是經,又何必再拈出‘權’字,徒增理解之困擾?……傳文所謂之‘有善’,實乃《公羊傳》對于‘權’之行使所設之限制。之所以另設條件限制,蓋不欲世人誤以權既可違反經之原則,遂乃‘濫權’妄為,此固圣人之所不樂見者。準此,‘權者反于經’之‘反’實當作‘違反’解,如此方符傳文之旨意”[5](173)。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漢人的著作在論及經權問題時,都是在與“經”相對的意義上來使用的。比如,《韓詩外傳》中說:“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6](34)“經”和“權”是在“常”和“變”兩種情境下實踐“道”的不同方式。這里的“經”,既是指一般情境下普遍適用的道德準則本身,也表明一般情境下普遍適用的道德準則在具體情境中的應用限度,即,這些準則僅僅被視為是在一般情境下適用的,在此之外,則需用“權”。作為公羊家的董仲舒繼承了《春秋公羊傳》中“反經為權”的觀點,并進一步解釋說:“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7](79)這里特別突出強調“權”“亦必在可以然之域”,如果董仲舒也將“權”理解為“返于經”,這種強調則全無必要;之所以做這種強調,是因為“權”是要違背一般情境下普遍適用的準則的,如果沒有一定的限制,就有可能溢出“可以然之域”。因此,姑且不論漢儒觀點之是非,單從漢代學者的論述可見,他們所主張的“權”,就是與“經”相反的。
之所以會將漢儒的“權”的含義理解為返歸于“經”,直接的原因,是誤解了漢人所說的“經”字。漢儒經權觀中的“經”,指一般情境下普遍適用的道德準則,它是“道”落實于具體的實踐生活的體現,而不是“道”本身。在道德準則體系中,“道”是最高的原則,它的普遍約束力是具有絕對性的,而“經”則源于對現實中合乎“道”的行為的概括和總結,它是有限的,不可能涵蓋“道”與現實情境相結合的所有可能。因此,當遇到以前未曾經驗過的情境,或者與一般性的情境不一致的特殊情況時,“經”對行為的普遍約束力就會暫時失效,因而必須回到“道”本身,去尋找合宜的行為方式。這種處理方式,就是漢儒所說的“權”。因此,“權”的合理性依據之所在,并非是“返于經”,而是“合于道”。將“反于經”理解為“返于經”,關鍵原因就是混淆了漢儒經權觀中的“經”與“道”,將“經”看作與“道”等同的概念。蔡仁厚有一種觀點,他說:“常理常道雖然永恒而不可變,但表現理、表現道的方式,則必須隨宜調整,因時制宜。一般人把‘理道’和‘表現理道的方式’混為一談,所以引出許多無謂的夾纏。”[8](154-155)如果按照這種區(qū)分,漢儒所說的“經”,應為“表現理道的方式”,而非“理”或“道”本身。正是將二者混為一談,所以才導致在對漢儒經權關系的理解上出現了偏差。
對于“權者反于經”中的“反”的解釋,從表面看只是一個文字訓詁的問題,但其實質卻體現了詮釋者倫理思想上的基本傾向。如果承認“權”可以背反于“經”,并且仍然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那也就意味著承認暫時拋開道德準則而僅僅根據行為后果進行道德選擇的合理性。總體來說,在道義論和結果論之間,儒家是傾向于道義論的立場的。宋代之后,程頤等理學家之所以激烈抨擊漢儒“反經為權”的觀點,并提出了經權統(tǒng)一的理論,正是在于他們認為如果沒有堅定的道義原則,承認“反經”的“權”的正當性就極有可能會造成權術、變詐的流弊。近代之后的學者以返歸釋“反”,正是繼承了這種觀念,認為“一般人既無所守,而又侈言通權達變,不過是‘飾非自便’的說辭而已”[2](345)。認為“反于經”就是“返歸于經”,無疑最大限度地維護了道德準則的普遍約束力。但是,以此作為《公羊傳》中提出的經權觀的基本立場,卻未必合適。況且,在宋代之后堅定地堅持道義論立場的理學家們的眼中,公羊家的經權觀主張的也是“權”背反于“經”。從程頤提出“權即是經”的經權統(tǒng)一理論開始,漢儒的經權觀都是他們抨擊的對象,恰恰說明,他們認為,漢儒的“權”就是違背“經”的。否則,如果認為漢儒的經權觀強調的就是“權”返歸于“經”,則程頤就不必再感慨“自漢以下,更無人識權字”[9](295)。因此,將“反于經”之“反”字解釋為“返”,從基本觀點上說,是繼承了宋代理學家經權統(tǒng)一的觀點和傾向于道義論的立場,但是,如果要因此而否定《公羊傳》所說的“權”字就是背反于“經”之義,并以詮釋者自己在倫理思想上的立場取代公羊家的傾向,則全無必要。
二、董仲舒的經權觀對道義原則的堅持
《公羊傳》中“反于經,然后有善”的“權”表現出明顯的重后果的傾向,董仲舒繼承了《公羊傳》中“經”“權”相對的思想,但他又極力試圖將對經權問題的理解拉回到儒家重道義的立場上來。《公羊傳》談到祭仲行權的效果時,說:“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生死存亡之間,行為給君和國所帶來的“以生易死”“以存易亡”的結果,彰顯了行權的正當性和可取性。但是,在董仲舒看來,能否稱為“知權”,不是單純以“生其君”或“存其君”來判斷的,如果以不合“義”的方式使其君得以生存,也是不可取的。
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對比了祭仲和逄丑父的行為。在齊國和晉國的鞌之戰(zhàn)中,齊頃公被圍。作為車右的逄丑父為了幫助國君脫困,與其互換位置,假扮齊頃公迷惑晉軍,結果被晉軍俘獲,齊頃公則趁機逃脫。董仲舒認為,雖然祭仲和逄丑父都是“枉正以存其君”,逄丑父為了“存其君”而被殺,所作所為難于祭仲,但祭仲卻因“知權”而值得稱贊,逄丑父的行為不但不能稱為“知權”,反而應當受到譴責。這是因為,祭仲讓鄭昭公“去位而避兄弟”,是“君子之所甚貴”的行為;逄丑父幫助齊頃公“獲虜逃遁”,則是“君子之所甚賤”的行為。祭仲用將他的國君置于“人所甚貴”的位置來使其免于災禍,所以在《公羊傳》中得到贊揚;逄丑父用將他的國君置于“人所甚賤”的位置來幫助其逃脫,所以在《公羊傳》中被認為“不知權”而受到貶低。所以,董仲舒說:“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后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后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逄丑父是也。”[7](60-61)在這里,董仲舒依然認為“知權”與“不知權”的判斷是看行為的結果,但是,他所指的結果并非是生死存亡這樣的功利性的后果,而是結果是否合乎“義”的要求。如果一個行為初始時違反共識性的規(guī)則,但結果卻是合乎“義”的,這就叫作“中權”;這樣的行為即使沒有獲得成功,在《春秋》中也是被稱道的。相反,如果一種行為初始時看似合乎正道,但最后的結果卻不符合道義原則,這就叫作“邪道”;這樣的行為即使成功了,在《春秋》中也不會得到褒獎。
由此可見,在董仲舒看來,在行為是否合乎“權”的判斷中,結果是重要的,但對結果最終的判斷依據卻是它能否使行為整體符合“義”的要求。在儒家的思想中,“義”是一個比“經”與“權”具有更高的價值優(yōu)先性的標準。孔子說:“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里仁》)孟子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一直到宋代之后,程朱理學在論及經權關系時,依然堅持“義統(tǒng)經權”的主張。經權觀中對“義”的強調,是儒家重視道義的一貫原則的體現。從《公羊傳》中的“反于經然后有善”,到董仲舒的“前枉而后義”,“把‘權’和榮辱、義不義、正邪的關系聯(lián)系起來,使經權關系不僅關系到生死存亡的問題,而且跟孔子的‘殺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義’統(tǒng)一起來”[10](286)。《公羊傳》中的“權”是權變之義;既然權變,就必然是出于結果的考慮。董仲舒將結果好壞的判斷依據設定為“義”,可以看出他在經權問題上回歸重道義立場的努力。
董仲舒不但將“義”與“權”直接聯(lián)系起來,而且還將“道”或“天道”作為“權”的合理性判斷的最高標準。《公羊傳》中將“有善”作為行“權”的正當性依據,是將這一判定標準置于現實的實踐之中。董仲舒則試圖為“經”“權”的正當性判定尋求一個形而上的終極標準。在他的“天人合一”的理論體系之中,這一標準就是天道。在董仲舒看來,“經”和“權”的依據,都在“天”那里。“天之道有倫、有經、有權。”[7](340)也就是說,“經”和“權”,本身都是內在于“天之道”的。根據這種理解,在實踐之中,無論是“守經”,還是“行權”,都可以是遵循天道的體現。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這里所說的“道”,與孔子和孟子思想中多用“道”來指稱人們實踐中所追求的最高價值標準不同,也不同于《公羊傳》中“行權有道”的“道”和《韓詩外傳》中“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的“道”,而是將“道”的根源寄托在“天”那里,強調了道德原則和標準的客觀性。秦漢之后,列國紛爭局面結束,大一統(tǒng)的國家的建立對穩(wěn)固的社會秩序的需求突顯出來,在倫理思想上必然要求道德標準日益規(guī)范化、客觀化,并且被賦予越來越多的神圣性和權威性。董仲舒思想中具有主宰者和監(jiān)督者的意義的“天”,便承擔起賦予道德行為判斷的標準以客觀化和權威化的任務。
因此,在董仲舒那里,對行為的合道德性判斷的最終依據,不是人性,也不是人心,而是具有客觀性的“道”。“《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于性,雖不安,于心,雖不平,于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7](74)“經禮”和“變禮”的區(qū)別在于,前者因與禮的一般性要求相一致,所以行為者依此行事,會感到心安理得;而后者因為是與禮的一般性要求相違背的,所以行為者依此行事,會產生不安的感覺。但是,二者本質上又是一致的,他們都是在各自不同的情境之下遵循“道”的要求的行為,因而都是正當的,合乎道德的。因此,董仲舒說:“明乎經變之事,然后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7](75)所謂“明乎經變之事”,最為關鍵的,就是能夠在具體的情境之下做出如何行動才是符合“道”的要求的理智判斷。合乎“道”的要求,既是“經”和“權”的共性,又是行“權”的界限。“權”雖然表面上看似違背了共識性的道德準則,但從根本上說,它與作為最高原則的“道”仍然是一致的。“權譎也,尚歸之以奉巨經耳。”[7](80)這里所說的“巨經”,指的其實就是作為“第一原理”或者最高原則的“道”。
董仲舒的這一思想,就是后人概括漢儒經權觀時常用的“反經合道為權”。董仲舒發(fā)展了《公羊傳》中“權者反于經,然后有善”的觀點,將“經”與“權”的合理性依據建立在“天道”這一客觀且至上的基礎上,從而為“經”“權”相反相成的經權觀的道義論立場找到了一個相對堅實的理論基礎。
三、董仲舒的經權觀回歸道義論立場的理論路徑
在西方倫理學中,道義論與結果論在觀點上往往是兩相對立的。“道義論從基于規(guī)則之上的視角出發(fā),對倫理進行探討。在這種探討中,道德原則具有絕對的、無條件的規(guī)定性地位。”[11](42)道義論認為行為的道德價值取決于它所遵循的道德準則,而與行為的結果無關。結果論則以結果的好壞作為行為道德價值的判斷標準,它認為:“判斷道德意義上的正當、不正當或盡義務等的基本或最終標準,是非道德價值,這種非道德價值是作為行為的結果而存在的。”[12](28)然而,在中國傳統(tǒng)倫理思想中,雖然也一直有“義”與“利”、道義與功利等問題的爭論,卻很少有將道義與結果完全割裂對立的學說。思想家們雖然所主張的側重點不同,卻都試圖在二者之間尋求一種統(tǒng)一或平衡。
從總體上說,儒家在道德問題上是強調道義準則的指導和約束作用的。結合《春秋公羊傳》中引出“權者反于經,然后有善”這一觀點的史實,即祭仲“出忽而立突”一事,可見《公羊傳》中作為行“權”的正當性判斷依據的“有善”,是直接從結果的意義上來說的。但是,從《公羊傳》中對經權問題的完整論述可見,它的作者盡管試圖以權變的方式來化解道德生活的復雜性與道德準則缺乏應變的靈活性之間的矛盾,卻不想放棄儒家重道義的基本立場。可是,僅僅通過“權者反于經,然后有善”這一定義,是無法明確地體現出重道義的立場的。為了避免直接以結果為正當性依據的行為背離具有共識性的道義原則,《公羊傳》中的處理方式,只能是根據儒家的道德觀念,為行權的實踐加上種種限制。首先,《公羊傳》為行權設置了嚴格的情境約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它將合理的“權”限制在生死存亡的緊急情況之下,明確了“權”所適用的前提條件,大大限制了“權”的使用范圍,目的就是強調,一般情況下,不能輕易用“權”,守“經”才是合理的行為。其次,《公羊傳》還為行權規(guī)定了明確的原則,為其設置了道義上的界限。“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行權雖然意味著為了取得好的后果而違背一般性的準則,但是,這種后果的考慮不是為了迎合行為者自身的某種利益要求,而是為了滿足他人或者整體的利益。與此同時,對于行為主體來說,行“權”往往會造成自身利益的損失。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通過損害他人利益,甚至傷害他人生命來保全自己,是不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的。
董仲舒對于“反經為權”觀點的最重要發(fā)展,是將道義原則貫徹于“權”的含義和經權關系之中,從而彌補了《公羊傳》中的經權觀只能在經權關系之外設置實踐限制的方式來避免行權可能違背道義原則的弊端。
在對于“權”的基本含義的理解上,董仲舒明確了“道”和“義”對于“權”的正當性判斷的根本性意義,強化了“權”以“合道”為特征的觀念。他認為,人與其他動物的根本區(qū)別在于,人不是僅僅為了生存或利益而活著;單純?yōu)榱松婊蛘呃娑`背道義,蒙受恥辱,并不是真正的權變行為。在對逄丑父幫助齊頃公逃遁一事的分析中,董仲舒說:“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眾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于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茍為生,茍為利而已。”[7](61)正是由于此,董仲舒認為逄丑父“枉正以存其君”的行為雖然難于祭仲,但卻不可稱其為“知權”。
“茍為生,茍為利”的變通行為不值得稱道,值得稱道的變通是以仁義為質、扶危救難的行為。春秋時期,楚莊王圍攻宋國都城,派司馬子反探查宋國都城內的情形。子反從宋國大夫華元口中得知宋國已難以支撐,“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于是動了惻隱之心,不僅告知了華元楚軍已僅余七日之糧的事實,而且力勸楚莊王撤圍退兵(事見《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關于此事,有人提出疑問:“司馬子反為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董仲舒的回答是:“為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他認為,子反這樣做完全是惻隱仁愛之心的自然流露,推己及人,不忍心讓宋國整個都城的人落到人吃人的悲慘境地,從而不再考慮宋國人和楚國人之間的利益區(qū)分,因此是非常崇高的行為,《春秋》才予以贊揚。他又進一步解釋說:“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于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于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禮”,本質上應該是仁愛之心的表達,是外在形式和實質內容的統(tǒng)一。如果看到人相食的慘狀而不知道同情,這就是失去了仁德;仁德這一本質喪失了,禮節(jié)也就沒有了意義。所以,子反的所作所為,是為了挽救實質的喪失,在這樣的特殊而緊急的情境之下,當然也就無法再顧及那些作為形式的東西。總之,在董仲舒看來:“《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于變,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諭矣。”[7](51-55)用于“變”的“權”之所以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正是由于它是以仁義為質的。
不僅如此,為了強化重道義的立場,在“經”與“權”的關系上,董仲舒運用陰陽五行學說,論證了“經”和“權”之間存在著尊卑關系。他說:“陽行于順,陰行于逆。逆行而順,順行而逆者,陰也。是故天以陰為權,以陽為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于盛,權用于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后刑也。”[7](327)董仲舒認為,“陽”的順著常道的方向而行,“陰”的是逆著常道的方向而行。這樣,“經”與“權”的屬性和“天道”的“陽”與“陰”就是一致的。根據陰陽五行學說,屬于“陰”的范疇的“權”是末節(jié),而屬于“陽”的范疇的“經”則是根本。同時,天之道“貴陽而賤陰”“近陽而遠陰”,陽尊而陰卑,所以上天是顯揚“經”而隱匿“權”的,以“經”為常道,以“權”為變通,“先經而后權”[7](327)。也就是說,在現實中的大部分情境之下,人們的行為都是遵循“經”這一體現著“常道”的要求的一般行為準則的,只有在偶然的、非常的情境之下,才可以使用“權”。同時,不同于“經”具有的普遍性價值,“權”是“一用而不可再”的,任何一次權變的行為都因與特殊的情境相聯(lián)系,其正當性價值只存在于這一孤立的事件之中。
總之,在中國傳統(tǒng)的思想之中,合乎道德的行為,必然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而要“順乎天”,就不得不重視體現著“天道”“天理”的道義準則,而要“應乎人”,就不能背離人的特殊生活方式、生活情境、生活需要和幸福追求。經權問題的討論,正是為了彌合遵守具有抽象性、確定性的道義準則與具體生活情境中行為結果的具體性、變動性之間可能會出現的縫隙。經權理論承認基于結果的考慮而暫時違背一般情境下應普遍遵循的道德準則的權變行為的合理性,同時又警惕著道德相對主義甚至道德虛無主義的風險。基本的途徑,就是在堅持重道義的基礎上,把道義與結果有機地結合起來,努力地將道義準則寓于行為結果的判斷之中,從而避免二者產生根本的對立以至于出現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的局面。大一統(tǒng)的封建國家建立之后,從《公羊傳》到董仲舒,經權觀中道義論立場的明確和回歸,反映的正是經權關系理論提出初期儒家學者對道義和結果之間的關系在理論上的調適與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