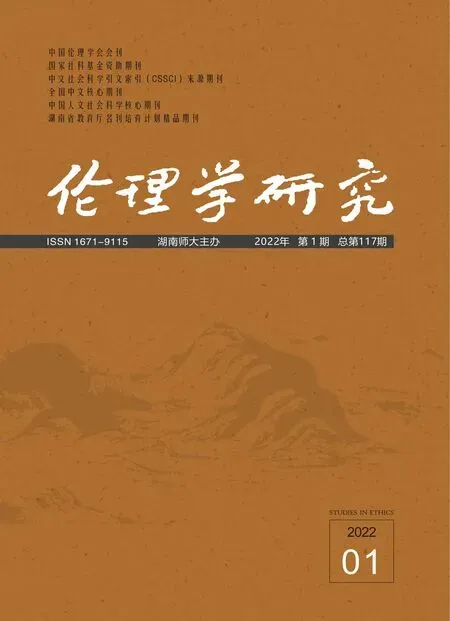亞當·斯密的同情概念解析
何 鑫
同情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倫理學的核心概念。目前對同情的研究較多且不乏共識,但在其定義上尚有爭議,即斯密用同情概念究竟指什么。回答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同情是情感,也是對情感的理解能力[1](79-85)[2](43-46)。當同情表示情感時,是指旁觀者想象在當事人處境時產生的與當事人相似(resemble)[1](85)的情感,通過處境轉換的同情,旁觀者得以理解當事人的情感。因此,同情既是旁觀者的情感,又是情感的理解能力。第二類,同情不是情感,而是人們普遍具有的情感理解能力[3](32-34)[4](19-25)。理由是:同情是對任何一種情感的理解,因此它本身不是情感,而是情感的理解能力。第三類,同情是情感,不是情感的理解能力[5](85-105)[6](109-115)。理由是:對情感的理解需要以他人的實際情感為目標,但同情者不關心他人的實際處境和情感如何,因而不是情感理解能力。可以看出,對同情概念的解讀存在的爭議集中表現為兩個問題:其一,同情是否是情感①雖然英文研究者在討論同情是否是情感時,使用的詞匯(如emotion、passion、sentiment 等)各不相同,但在表示廣義的情感時,它們是同義詞。并且結合各自的語境看,研究者都是在廣義上使用以上詞匯。本文同樣意指廣義的情感,即人們感受性的心靈狀態(mental states)。參見PEARSALL J 等:《新牛津英漢雙解大詞典(第2 版)》,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第712、792、1606、2001 頁;AUDI R,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2nd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59.;其二,同情是否是情感理解能力。
通過分析《道德情操論》的文本和比較斯密與同時代其他思想家對同情的用法,本文的結論是:(1)同情是旁觀者的情感;(2)同情不是情感理解能力②需要說明的是,同情是情感并不反對同情是某種能力或心理機制,只是同情作為能力或心理機制時,它不是情感理解能力。。
結論雖與前述第三種觀點相同,但并非重復,而是通過改變論據做出的理論推進。第三種觀點的論據分別是同情忽視他人的實際處境和情感,這暗示斯密陷入了封閉的自我論。蒙塔格和希爾(Warren Montag & Mike Hill)甚至斷言,斯密的同情“根本不需要他人的存在”[6](114),也“不可能為道德或正義提供基礎”[6](117),但這一推論明顯有悖于斯密的理論初衷。本文認為,同情雖然不是情感理解能力,但它是對他人處境和情感另一種形式的關注,斯密以此為基礎說明情感和利益不同的個體如何形成和諧的社會生活。重新界定同情概念,不僅有助于理解斯密的理論,也可以為涉及它的其他研究(如鏡像神經元等)提供概念清晰的理論資源。
一、同情是否是情感
本節將提出,在斯密的一些文本中,同情概念只能表示情感。作為情感,同情有兩層含義:(1)現象層面:同情是旁觀者類似于當事人情感的情感。(2)原因層面:同情是想象的處境轉換產生的情感。
(一)
依據沃哈恩(Patricia H.Werhane)和夏紀森的觀點,同情不是情感,而是“對情感的贊同、理解和同意”[3](36-37)以及“感知他人情感的能力”[4](25)等。這一觀點將導致一些文本的解讀出現困難。在此選取《道德情操論》中同段的兩句話:
A.在當事人的原始情感(original passions)同旁觀者的同情的情感(sympathetic emotions)完全一致時,在旁觀者看來,這些情感必定顯得正當和合宜,并且適合它們的對象。相反,如果他在設想自身處于當事人的處境時,發現當事人那些原始情感和他所感覺到的不一致,那對他來說,它們便顯得不正當與不合宜[7](16)。
B.一個人的同情(sympathy)與我的悲傷合拍,就說明他承認我悲傷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7](16)。
可以看出,A 句中“同情的情感”是旁觀者設想在當事人的處境時感受到的情感,并且斯密在此提出一個評價原則:旁觀者根據自身同情的情感與當事人的原始情感是否一致,來判斷當事人的原始情感是否恰當。由于A 句是段落首句并提出評價原則,B 句是對這一原則的舉例闡述,因此B 句中的“合拍”與A 句中的“一致”對應,“合理性”與“正當”、“合宜”等正面評價對應。暫且不論同情在B 句中的含義,僅梳理邏輯關系:因為他的同情與我的情感(悲傷)一致,所以他認為我的情感合宜。
下面將“對情感的贊同、理解和同意”與“理解情感的能力”分別代入B 句,看句意是否合理。將“同情”置換為(1)“對情感的贊同、理解和同意”:因為他對情感的贊同、理解和同意與我的情感一致,所以他認為我的情感合宜。(2)“感知他人情感的能力”:因為他的感知情感能力與我的情感一致,所以他認為我的情感合宜。以上兩種含義導致的句意均不符合斯密的評價原則:旁觀者根據自身同情的情感與當事人的情感是否一致來判斷當事人的情感。
因此,在一些文本中,同情只能表示情感。并且,在A、B 句中,同情與同情的情感同義。此處的情感是廣義上的情感(feeling or emotion),即感受性的心靈狀態,而非特指含義,例如特別強調包含認知因素的情感(sentiment)等。
(二)
除了表示廣義上的情感外,同情是否有更詳細的規定?斯密認為,“同情……被用來指與任何情感的共鳴或同感”(sympathy…be made use of to denote our fellow-feeling with any passion whatever)[7](10)。可以看出,同情等同fellow-feeling。但fellow-feeling 在中文中被翻譯為共鳴、同感和同情感,因此等同關系無法說明問題,需要進一步看fellow-feeling 的含義。
在同小節中,結合另外兩句話:
A.“這就是我們對他人的不幸所以有同情感(fellow-feeling)的根源”[8](3),這里的“根源”指的“想象的他人處境”[8](2-3)。
B.無論當事人在任何處境中產生什么樣的情感,只要一想到他的處境,旁觀者就會產生類似的情感(an analogous emotion)[7](10)。
A 句說明想象的他人處境是旁觀者產生fellow-feeling 的根源,B 句說明想象的他人處境讓旁觀者產生類似的情感,可以推出fellow-feeling 表示類似的情感。由于同情概念等同fellow-feeling,因此,它的含義也是“類似的情感”。
同情是旁觀者產生的類似情感,這是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最先使用的含義。他認為同情“究竟如何,取決于主要當事人原始感情的性質,因為旁觀者同情的感覺必定總是多少會保有主要當事人原始感覺的特征”[8](53)。因此,同情是類似的情感是指與原始情感的性質相同,諸如快樂、悲傷、恐懼等具體屬性。
斯密繼而指出,由于我們不能直接體驗他人的感覺,同情來源于想象的他人處境。可見,斯密主張情感的個體性,反對直接的情感傳遞,注重產生情感的原因和處境。因此,雖然同情表現為與他人情感的性質類似,但實質上是原因相同。他詳細描述了同情的過程:“借由想象,我們把自己擺在他的位置……在某一程度上與他合二為一,從而對他的感覺有所體會,甚至我們自身某種程度上比較微弱,但也并非與他的感覺完全不相像的感覺。”[8](3)這一過程在發生上是順序,在認識上是倒序。也就是說,斯密最先看到的是我們與他人情感一致的現象,于是在“類似的情感”含義上使用同情概念,然后發現類似的原因是我們想象了他人的處境。經過對來源的分析,斯密從“類似的情感”含義中引申出同情概念的第二個含義:“處境轉換產生的情感”。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來源于同樣處境的類似情感都可稱為同情。雙方如果真實地面對同一處境產生的類似情感,則不是同情。斯密將情感對象(即處境)分為兩類:一是沒有特殊影響的對象,比如“一座山峰的雄偉、一棟建筑的裝飾、一幅畫的意境”[8](16)等;二是于一方有特殊影響(切身利害關系)的對象,比如個人遭受的不幸等。面對前者時,人們在同樣的處境中,則“沒有同情發生的機會(no occasion for sympathy),或者無須借助產生同情的處境轉換的想象”[7](19)。而后者則需要旁觀者想象身處當事人的處境,才能有類似的情感。因此,可以認為,同情的前提是雙方沒有身處同一處境。于旁觀者而言,處境是想象的處境,同情是來源于想象力的情感。
這里回應一個可能的反駁。斯密提出在認知和審美的對象中不存在同情,這一觀點也可以解讀為:認知和審美的對象于我們而言沒有切身利害關系,即便產生分歧也不大會有“互不相容”(intolera?ble)[7](21)的危險。因此,同情存在的前提似乎是對象是否切身,而非共同。并且,如果處境相同便沒有同情,那如何解釋同病相憐這一經驗事實?這一反駁可以用同情喪子者的事例來回應。斯密認為,當我為了與失去獨子的男人同感悲傷,我不是想象我失去了獨子,而是想象我是他在他失去獨子的處境中會有什么樣的感受,這才是同情[8](405-406)。我是我與我是他有什么區別?打個比方,如果我是他的妻子,或者我和他都在地震中失去了各自的獨子,那么,他和我的處境可以說是共同的,我也因此可以更好地感受到他的悲傷,這是同病相憐的現象。但是,他妻子或我因為自己失去獨子的悲傷不是同情,只有在我把自己想象成失去獨子的他時感受到的悲傷才是同情。討論同情現象時,斯密始終涉及的是旁觀者(spectator)和當事人(the person principally concerned),而旁觀者的含義是“不是利益相關的一方”[9](34),他與當事人的區別在于處境會影響當事人而非旁觀者的利益,否則就是當事人和當事人了。因此,同情發生的前提是處境不是共同的,或者說處境與同情者的利益無關,這一點將在第三節中繼續說明。
正因為此,斯密不止一次地提到“同情來源于想象的處境轉換”[7](21),這也顯示了同情的“他人性”特點。由于情感是“一種心靈狀態,具有被動的承受性”[10](259-260),比如尷尬是因為令人尷尬的處境作用于心靈產生的情感狀態,快樂也是由對象和心靈的共同作用產生,因此,決定情感的因素分別是處境和心靈。如果說自我情感是自我心靈面對自我處境產生的情感,他人的情感是他人的心靈面對他人處境產生的情感,同情則是自我心靈面對他人處境產生的情感。從形式上可以粗糙地說,同情是自我心靈中的“他人”情感;從內容上可以看到同情不再局限于自我感受,而是涉及他人。這一涉及不是從自我角度對他人的涉及①例如,因自我利益對他人的憤怒或喜歡,雖然涉及他人,但仍是以自我為中心。,而是拋開自我利益,以他人為中心。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始終反對以霍布斯和曼德維爾為代表的“自我中心主義”[11](263)。
綜上,同情是情感。但它不是某種具體情感,而是總稱,表示通過想象他人處境產生的情感,包括喜怒哀怨等;同時,同情又與以自我為中心的情感不同,它是涉及“他人”的情感,是非利己主義形成的可能性條件。
二、兩層含義的關系
上節表明同情有“類似的情感”和“處境轉換產生的情感”兩層含義,后者由前者引申出來。但完成這一過程后,斯密似乎又取消了“類似的情感”含義。
為了說明同情源于處境而非當事人的情感,斯密舉了四個例子[8](6-8),分別是:有羞恥感的人對無恥之人的同情、心智正常的人對瘋子的同情、母親對嬰兒的同情和生者對死人的同情。這是“旁觀者根據當事人的處境產生的情感,而當事人本人沒有”[8](6)的情況,斯密以此證明同情來源于處境而非當事人的情感。然而,這些事例也顯示了旁觀者的同情可以與當事人的情感完全不同。那么,這是否表示斯密在完成引申過程后就取消了“類似的情感”一義?例如,在同情死人時,斯密說到“我們的同情(sympathy)無法提供他們什么慰藉”[8](7),同情在此不是“類似的情感”,而是“處境轉換產生的情感”。
但在隨后的一節中,斯密說到“我們雖然贊許,但心里似乎沒有任何同情或彼此一致的情感(sym?pathy or correspondence of sentiments)”[7](17),結合上下語境,同情與一致的情感同義,并且這一短語出現多次。可見,斯密沒有取消“類似的情感”一義,且多處使用這層含義。
因此,同情兼有“類似的情感”和“處境轉換產生的情感”兩義,且在不同的文本中,同情只能被理解為其中之一,即兩義不等同,無法替換。那么,它們之間是什么關系?
斯密在描述同情與當事人原始情感的相似度時,分別說過三段話:(1)在想象的處境轉換時,旁觀者“會產生雖然在程度上微弱點,但并非與他(當事人)的感覺完全不同的感覺”[7](9);(2)由于同情產生的處境轉換是想象的,這“足以使他(旁觀者)的那種情感無法像本人那樣強烈”[7](22);(3)由于同情產生于當事人的處境,“我們有時會從想象的處境中感受到他在現實的處境中沒有的情感”[7](12)。可以看出,斯密反復強調同情來源于想象的處境轉換,但這一因素,會分別導致與原始情感“不可能完全不同”“不可能完全一樣”“可能完全不一樣”的同情。因此,作為“類似的情感”的同情必定來源于想象的處境轉換,但想象的處境轉換不一定會產生類似的同情性情感。同情始終是“處境轉換產生的情感”,卻不一定是“類似的情感”。后者可以表述為“處境轉換產生的類似情感”,它是前者的一個偶然結果。
提出同情與當事人情感的不一致性,正是斯密對英國傳統用法的改變。同情在18 世紀(尤其在英國)表示廣義的情感分享[12](18)和個人之間的協調一致性[13](9-18)。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認為同情(sympathy)來源于我們的本性——公共感(public sense)[14](13),它為他人而非自己的處境產生相應的感覺[14](5),因此,同情表現為“看到他人的幸福會不由得讓我們開心,看到他人的不幸會不由得讓我們痛苦”①這句與斯密的開篇首句異曲同工,可見斯密和哈奇森討論的是同一個心理現象。,在這一過程中,旁觀者絲毫沒考慮自己的利益[14](13)。因此,同情既是利他情感,又顯示了自我與他人的情感一致;而休謨(David Hume)則認為同情是分享他人情感的心理機制,它“使我們經過傳達而接受他們的心理傾向和情緒”[15](316)。這種復制型傳達的原理是觀念聯想理論,由于當事人的情感會通過顯露在外的表情、言談中傳達給旁觀者相應的觀念[15](317),在看不到外在表現時,通過處境的觀念也可以聯想到由此產生的情感觀念[15](370-371)。而觀念來自印象,也可以逆轉為印象,印象就是生動的情感體驗[15](317)。因此,旁觀者根據情感觀念可以產生與當事人相似的情感體驗。值得強調的是,休謨同樣使用了同情無恥之人的例子,但他稱之為“片面的”(partial)[15](371)同情。片面的同情是由于只觀察到“對象的一面,而沒有考慮它的另一面,這個另一面卻有相反的效果”[15](371),此處的“另一面”是指無恥之人缺乏羞恥心,即當事人的心理狀態。格頓-瓦赫特(Lily Gurton-Wachter)認為,按照休謨的觀點,如果我們對他人的同情是完全的同情(考慮到缺乏羞恥心),我們就如同當事人一樣不會羞恥和臉紅[13](9-18)。因此,休謨的同情注重對當事人實際情感的還原。
上述可見,哈奇森和休謨強調旁觀者的同情與當事人情感的一致性。雖然他們對同情的歸因不同,但都討論了處境,并認為對當事人處境的了解有助于形成彼此情感的一致。而斯密首先將處境置于中心地位,他認為情感一致的原因是旁觀者想象了當事人的處境。但他很快意識到旁觀者的同情來源于想象的處境,而想象的處境和真實的處境有區別,因此同情和當事人的原始情感之間有各種差異。于是,情感的一致性在斯密這里消失了。可以說,哈奇森和休謨共同面對的問題被斯密更新了,斯密從情感一致性的原因前進到處境,但從處境的差異中又推出情感的差異。18 世紀的同情概念表示旁觀者與當事人一致的情感,斯密的同情則表示旁觀者與當事人處境一致但可能有差異的情感,將重心從情感一致性轉移到處境一致性是斯密對同情概念用法的改變。
三、同情是否是情感理解能力
由于同情來源于想象的處境轉換,因此被研究者認為是情感理解能力[1](79)[2](45-46)[3](33-34)[4](25)。本節將提出:同情雖然重視他人的處境,但由于處境轉換時不包括當事人的心理因素,因此不是對他人實際情感的理解,反而是評價他人情感的參照。但這不表示同情忽視他人的實際情感,相反,同情為個體交流創造了一個共同語境。
同情不是情感理解能力的根本原因正是它被誤解的地方。理解X 意味著從原因層面去了解X[16](2378),而情感的原因除了感受對象還有感受者的心理狀態,同一個對象會引起不同的情感反應是由于不同的心理狀態。因此,要理解他人的情感,需要充分了解這兩個因素。斯密的同情正是由于強調產生情感的處境,才被認為是理解能力,但同情轉換的處境似乎僅是客觀對象,不包括心理狀態。
在同情瘋子時,斯密說道,旁觀者“是用他目前的理智和判斷去看待那種狀況時自己將會有的感覺”[8](6),同情死人也是“我們將自己擺在他們的處境中”[8](8),即“把我們自己還活著的靈魂塞進他們已經失去活力的軀殼里,然后設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自己將會有什么樣的情緒”[8](8)。并且這一現象并非例外,雖然瘋子和死人不同尋常,但對無恥和溫馴之人的同情同樣顯示了旁觀者沒有轉換為當事人的心理狀態:我們同情無恥之人而臉紅,是因為從自己的羞恥心出發,而當事人缺乏與我們相同的羞恥心;我們同情溫馴的人而感到憤慨,也是以自己的心態想象被他人侮辱時會奮起反擊,而當事人缺乏該有的憤慨,只會乖乖順從[8](37)。以上事例表明,旁觀者和當事人的心理狀態不同,并且同情似乎不要求旁觀者轉換為當事人的心理狀態。
但在處境的轉換問題上,研究者認為斯密沒有給出明確標準[4](23)[17](48)。尤其斯密允許男人同情分娩中的女人,和她同感痛苦,“雖然他不可能想象他自己會在他本來的身份和角色(person and character)上蒙受她的那種痛苦”[8](406),并認為虛擬的處境轉換“不應被認為是發生在我還是我自己的那個身份與角色上,而應被認為發生在我換成我所同情的那個人的身份與角色上”[8](405),但卻不允許我們和無恥者同感麻木。看似矛盾的表述,關鍵在于如何理解“身份和角色”。
“身份和角色”在《道德情操論》中出現三次,集中在同一段,斯密以此說明“同情不是自私的本性(selfish principle)”[18](419),并反對霍布斯的同情觀。那么,“身份和角色”與自私、霍布斯有何關系?霍布斯對同情①雖然霍布斯在此未使用sympathy 概念,但無論是compassion 還是fellow-feeling 與斯密使用的sympathy 都是同義詞,且霍布斯和斯密討論的是同一種情感現象。因此,在此將霍布斯的compassion 和fellow-feeling 翻譯為同情,與斯密的同情概念相同。參見SMITH A,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RAPHAEL D D & MACFIE A L(e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10-11.的定義是“為他人的苦難而悲傷謂之憐憫(pity),這是想象類似的苦難可能降臨在自己身上而引起的,因之便也稱為共感(compassion),用現代的話來說便是同情(fellow-feeling)。這樣說來,對于巨惡元兇所遭受的災禍,最賢良的人對它最少憐憫。同樣,那些認為自己最少可能遭受這種災難的人,對之也最少憐憫”[19](32)。可以看出,霍布斯也認為同情來源于想象的他人處境,但這一想象是發生在“自己身上”,因此,只要當事人的處境不是旁觀者可能遭遇的處境,就不會發生同情。這樣的同情正是出于對自我利益的考慮,是斯密所說的“自私的本性”。
而斯密正是以分娩者的例子反駁霍布斯:男人永遠不可能經歷分娩的處境,但他依然同情分娩中的女人。所以,在處境轉換時,旁觀者絕不是以自己的“身份和角色”,而是清醒地意識到與自我利益無關,由此產生的情感也是出于對他人利益的考慮。用斯密的話說,同情發生在我是當事人的“身份和角色”上。因此,“身份和角色”不是性格、心理等人格角色,而是承擔利益得失的個人角色。
綜上,旁觀者在同情時轉換的是客觀處境和利益立場,不包括當事人的心理狀態,因此同情不是對他人情感的理解能力②但不排除通過同情有理解他人的可能性,例如格里斯沃德認為,我們通過同情行為人的自私情感,即意識到在相似處境中會產生同樣的情感,雖然不贊同,但是可以理解這一自私情感。參見GRISWOLD C L,JR,Adam Smith and the Virtue of Enlighten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85.。并且,與當事人情感有差異的同情,正是評價當事人情感的參照和標準。在斯密看來,道德評價必須要看到行為人的客觀處境和利益立場,沒有這樣的共同視野,從各人特殊利益出發的評價絕非道德判斷,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做出的反應而已。哈孔森(Knud Haakonssen)進一步認為,人們的道德生活正是對共同立場的不斷追求[20](205-221)。
但是,否定同情是情感理解能力,并非暗示同情忽略他人的實際處境和情感。誠然,理解和分享他人的實際情感的確是對他人的關注。在理解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他人,甚至他人的情感和利益在同情中被我們真實地感受到了。哈奇森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將同情看作利他情感,而休謨也通過同情形成了“共通的利益感”[21](109-120)。但理解式同情的實質是消解了自我,正如休謨所言,同情使“我們經過傳達而接受他們的心理傾向和情緒,不論這些心理傾向和情緒同我們的是怎樣不同,或者甚至相反”[15](316)。也就是說,在同情中,我完全拋開自己的不同感受去復制他人的情感,我與他人情感一致的前提是我成了他人。而霍布斯的同情則相反,它將他人消解于自我之中,是真正的忽視他人。斯密與他們不同,他始終強調個體差異性,即便我代入到他人的處境中,也不會和他人的情感完全一樣。但情感差異不是忽視他人的結果,斯密的同情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對他人的關注。我們之所以會代入到他人的處境中,以同情去評價他人的情感是否合適,是因為我們把他人看作同類,需要在同樣的處境和立場中看待他人的行為和情感。我們不會為了評價地震,把自己代入到地殼運動中去判斷地震是否與它的處境適合,只會看它對我們的影響如何。
并且,有差異的同情是為了強調自我與他人應該共同努力來實現情感的一致,而不是依賴一方的努力。由于自我和他人在斯密的同情中沒有被同一化,直接導致情感的一致性消失了。但一致的情感是情感主義的根本要求,斯密必須從不同于前人的方式繼續實現一致性。在他看來,一致性不是通過放棄自我成為他人,而是自我和他人通過相互處境轉換的同情,雙方共同調整各自的情感強度來達到情感的一致。同情與原始情感的差異,正是雙方努力的空間,最終達到的一致性表現為情感的合宜度,是建構道德秩序的基礎。因此,斯密的同情不但沒有忽視他人的實際處境和情感,反而將自我和他人看作平等對話的主體,在交流中達成共識。相較于評價標準,同情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對處境的共同視野和不同情感的對話平臺。
總結
18 世紀的道德情感主義開端于反對以霍布斯和曼德維爾為代表的自愛論[22](112-117),哈奇森提出人除了利己情感外還具有天然的利他情感,利他不能還原為利己。在對這一觀點的證明中,始終穿插著同情的身影。因為同情并非情感主義的專場,霍布斯早在16 世紀就解釋了這一情感現象:雖然看上去是為他人的不幸而悲傷,但本質上是從自我利益出發,想象自己在他人的不幸處境中為自己悲傷,同情最終還是利己主義的產物。而情感主義為了反駁自愛論,反復證明同情是想象自己是他人的立場并在他人的處境中,其中不涉及任何自我利益。可見,對同情的解釋是情感主義與自愛論交鋒的重要戰場。
斯密的同情概念既立足于反對自愛論的立場,又改變了傳統情感主義的用法,他提出旁觀者的同情和當事人的情感之間始終存在差異。本文呈現的差異①同情與當事人情感有差異的原因,斯密析分為個別特殊的心理狀態和普遍具有自私本能(包括當事人和旁觀者)。本文因主題限制,未作深入討論。并非出于特殊的個人利益,而是特殊的心理狀態。因此,為了追求彼此情感的和諧,旁觀者和當事人需要努力調整自己的情感以達到一個平衡點,這正是道德規則形成的過程。從這點來看,斯密是對以上兩種同情觀的推進。他看到了霍布斯式的同情是消解他人,而利他主義式的同情是消解自我。然而在道德生活中,自我和他人并非對立的關系,自我利益和他人或公共利益也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斯密反對霍布斯的利己主義,但并非從利他主義的角度。在他看來,作為社會秩序的道德規則是社會運行的基本保障,利他主義雖然崇高也值得鼓勵,但不是一個社會得以存在的必要條件[21](109-120)。因此,斯密將利己和利他行為都放在處境中去考慮是否合適,而是否合適即行為和情感的合宜性需要我們用自己“與之對應”[8](16)的情感(來源于同樣處境的情感)來評價,道德判斷正是以此為基礎。同情概念體現了斯密的道德觀:旁觀者努力轉換為當事人的處境和立場是為了擁有道德評價的共同視野,在這一過程中沒有消解自我和他人,因此會有不同于當事人的情感反應,這一情感是評價他人情感和行為的參照物,斯密稱之為同情。
因此,無論是從文本解釋還是理論需求看,同情都有情感的含義——旁觀者由想象的他人處境產生的情感。這一含義并不否定同情是相應的心理機制,只是斯密改變了同情的傳統用法,因此不再是傳遞他人情感的機制或情感理解能力,而是旁觀者對當事人處境的想象機制。由此產生的同情性情感不僅為評價他人的情感提供了參照,還促使人們調整自己的原始情感和行為,起到了道德規范作用。因此,同情的作用在于分享他人的處境和立場,為個體的情感或觀點提供對話平臺,從而形成共同的道德規則。通過對同情概念的不同詮釋,斯密開出了一條不同于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的道德建構之路。